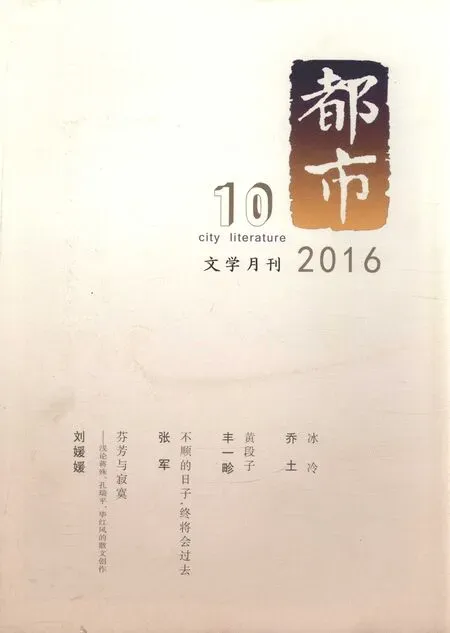苇地
郭忠辉
苇地
郭忠辉
今年的端午来自一缕苇叶的清香。
那天我一回家,就看见母亲买回来一大堆东西,有江米、红枣,还有一扎苇叶。尤其是那一小把青翠欲滴的嫩叶儿,散发出淡淡的清爽怡人的香气,像在刻意提醒我节日的临近。
母亲还不无遗憾地说,今年的苇叶小了些,比不上我们以前在村里自己掰的。
母亲说的倒是实话,只是老家村前那片苇地早在多年前就已消失了。前一段时间我回村还路过那片河滩地呢,河里早就没水了,开垦后的苇地一部分成了庄稼地,一部分成了经济林。
母亲虽是说说而已,却使我总想起村子里的情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正是那片苇地养育了我们整个村子。而关于苇地的话题,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也是一年四季都扯不完。
那时候芦席还是一种常见的日用品,几乎家家户户炕上都少不了一张席。芦席不但能铺炕,还能搭雨篷,围篱笆,作粮囤,所以人们家里总备着那么几块大小不一的席子。平时不用了就把它卷起来搁在墙角。夏天纳凉时有人把席子铺在地上,躺坐都随意。不过席子性凉,还免不了有小刺,有条件的人家往往会在炕席上加一层油布。
席子和油布虽然都在炕上,但油布却是奢侈品。一块好的油布代表着一个家庭的面子。我记得小时候最有名的是汾阳油布,绿地红花,鲜艳夺目。不过席子虽铺在底下,却也必不可少,隔热,防潮,透气,还能起到蓬松的作用。
我们那里管织席叫“打席”,织席的人就叫“打席子的”。我有个四叔就是个打席子的,他从小家寒,四处谋生,学了不少手艺,养蜂,做醋,烧窑,还会织席。记得当年他不过二十来岁,老院的厢房里就满垛着他打的一卷卷黄灿灿的席子。
每年入冬前,当寒霜把地上的热气一点点吸尽,苇地也显得疏朗而辽阔。柔软肥实的苇叶也枯黄了,凌厉的寒风几乎毫不费力就可将它们折断。一丈多高的苇子瘦得像一根骨头,衣不蔽体地裹着干涩的外皮。割苇的时候到了。人们把苇子齐根砍倒,打成捆拖回家里去。于是院子里、墙上,堆着靠着,一捆捆的苇子塞满了农家小院,也充实了村里人的期盼。
打席有好几道工序,一开始是破苇。用一柄特制的小刀,形状像匕首,厚实而锋利。人坐在地上,一手拈起苇子,一手使刀,从粗的一端把苇子劈开。刀锋哧啦一声就从苇子身体里穿过,酣畅淋漓。当刀子走到尾部时,苇子也到了人的另一侧,一根苇子已被分成了两半。劈开的苇子还留有水分,有的地方还看得见青皮,苇节中间有柔软的隔膜,轻轻一触就破了。
下道工序是压条。破好的苇子均匀地铺在地上,人们推着碌碡在上面来来回回碾,压开压扁了,就成了一根根柔韧的苇眉子,把上面的皮轻轻捋掉就可以编席了。
织席是真正的技术活儿。如何起头,打什么纹路,需要多大尺寸,怎样收边等各环节都得成竹在胸,运用自如。席子有多种用途,织法不同,材料也有所区别。打席不但工序烦琐,而且非常辛苦,好的打席人席子织得又密实又漂亮。
编好的席子卷起来,扎紧,码放成堆,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那时候我们村的苇地可是村里的聚宝盆。村里搞副业全靠苇地,哪一年没有几百张席子从村里运出去。卖席得来的钱使得村里人的生活格外滋润。在周边村子里,我们村既是少数有苇地的村,也是少数副业搞得最好的村。苇子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不需栽种却年年收割。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是苇地养育着我们的村子,犹如一位善良无私的母亲,源源不断地奉献着她的乳汁。
除了冬天割苇编席,苇地在其它季节里也是我们的乐园。
每年一到春末,在村外的小河边,苇地的苇子就长得密密匝匝,无边无际,像一座巨大的方阵,也像一个深不可测的迷宫。在野外苇地算得上是独特的标志,它依山临水,与沙滩为邻草地为伴,四野生机勃勃,景色迷人。
孩子们常常在天气晴好时钻进苇地去,那里面藏着太多的未知,在孩子们心里充满着新奇与刺激。野外可不同于村道,野外是更大的世界,也更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我们打小就在山野里摘野果、玩耍,在小河里戏水、捉鱼,在苇地里割草、挖野菜。还记得给村里割草的事,我那时大概有十二三岁,村里刚刚分了队,牲口还是集体的,假期里我就跟着大一些的孩子挑上笼担去野地里割草,回来村里有人负责过磅、记分,一个暑假我还能挣好几块钱呢。
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山韭菜、灰丢丢、打碗花,以及黑枣、茹茹、山李子等,还了解了山野里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记得那时苇地里有一种小红果,外面包着一层皮,就像四片叶子拼在一起的。用手把外皮轻轻扯开,里头就露出一枚指头肚大的鲜红果子,那果子汁挺多,吃起来甜丝丝的,我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红灯笼”。
想起少年时代的苇地,便都是珍藏在记忆深处最美好的情感,点点滴滴,丝丝缕缕,难以割舍啊。
一到端午前,苇子就长得特别茂盛,好像正是为了这个节日才如此繁茂的。人们在明媚的春光里迎来了一年里最热闹的时节。当微风轻轻掠过,苇地里沙沙的响声此起彼伏,相互糅合、交融,如浪潮在四周涌动,也似一杆杆苇子在窃窃私语。在节前的十天半月里,苇地要迎来一拨又一拨的人群,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包,三三两两地涌进苇地里打苇叶。一片片厚实饱满的苇叶从杆上掰下来,扎成把塞进包里,不长时间每个人都会有丰厚的收获。打苇叶是端午节的前奏,苇叶的清香提早就充溢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了。
粽子可是最难得的美食,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
包粽前先得把苇叶在开水里煮一煮,为的是杀菌、祛除苦味,以及增加叶子的柔韧性。煮过的苇叶被一片片分拣出来,丢掉纰裂的、有虫眼的或过于窄小的,留下的叶子片片肥实饱满,又宽又长,翠绿鲜亮。煮好的苇叶泡在水盆里备用,然后把淘好的糯米——我们那地方叫江米——也备好,还有红枣,这样就可以包了。
孩子们也蹲在水盆边学着包,可是总不成,不是包不住漏了米,就是包成圆的失了形状。在他们看来这真是个高技术活计,至少我也是这样的,直到如今我也没学会包粽子。
粽子包好了,我们的兴趣又随着到了大铁锅里,粽子入锅要煮两三个钟头才能熟,只有把皮煮透了,馅儿煮熟煮粘了才好吃。这一段时间孩子们是耐不住性子的,见香气从铁锅里咕嘟嘟往外冒,隔一会儿他们就得往灶前跑。大人见了就笑骂一句:“馋嘴猫,等不及了吧?还早着呢!”
煮熟的粽子从锅里捞出来,搁在凉水盆里,等着闲暇的时候慢慢吃。在炎热的晌午从外面回来,去水盆里捞个大粽子,坐在院里边吃边说闲话,那时候浓浓的粽香味儿,还有那份清爽可口,真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享受。小时候粽子的香味儿在记忆里一直都那么浓烈,有时甚至会穿越时空出现在我梦中。
现在,我们当然也能吃上粽子,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卖的。如果想做,市场上买了苇叶自己包也成。但始终感觉现在的粽子不如以前那样香甜,也许是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吧,但也许,那个时候的粽子和现在就是不一样!
在我看来,苇子可称得上是一种非凡的植物,它至少有两点值得我敬佩,一是它有着博大的奉献精神,二是它有着极强的生存耐力。
不过苇地也给村里带来过麻烦,而且后来还因此招致了被开荒的命运。起初的苇地是由集体经管的,单干后就承包给了个人,记得有几年苇地有人看守,是禁止孩子们去那里的。但再后来就被开荒了,主要原因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席子渐渐失去了销路,没人用席子苇地当然也就闲置了。苇子没人收割,地里经常乱糟糟的,而且每年因四处来的人打苇叶还免不了招惹些长短是非。村里于是决定把苇地开荒,分成许多小块地给不同的人种了。
由于苇子是“熟根子”,在之后的好几年里,人们充分发扬“不消灭决不罢休”的大无畏精神,刀砍、火烧、拔根等各种手段一齐上,终于将其清理完毕。苇地在我记忆里就以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消失了,但也最后显示了它的坚韧和顽强。
当然,在若干年之后村里人再说起苇地来也难免会空落落的不自在。我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一个陪伴已久的亲人,留在心底的是无尽的伤感!
唉!苇地要在,我们老家的小河就不会显得那么孤寂;苇地要在,我们的端午节也会过得更有滋味;苇地要在,我们的思念里便会拥有一方温暖的湿地!
(责任编辑贾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