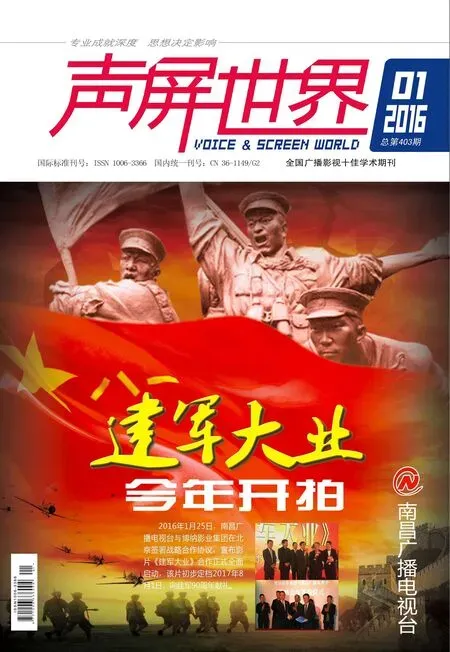中国动画传统叙事融合好莱坞技术经验分析
□陈 静
中国动画传统叙事融合好莱坞技术经验分析
□陈静
伴随着 2015年暑期档的结束,《捉妖记》凭借24亿元票房的好成绩刷新中国自 1994年以来 200项电影记录,它的传统叙事策略为当下华语电影追崇奇观式影像开辟了新的视角,这一现象在电影工业急速发展的当下值得深入思考。不论是以配角出现的萌宠“胡巴”,还是井柏然饰演的宋天荫等角色,虽以觉悟、追寻和成长为主要叙事基点,但其中对各个环节的创意编排成为了影片最大的“笑点”。导演许诚毅20多年梦工厂的动画经验,使得《捉妖记》或多或少有迪士尼的影子,但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一个融合与共生的东方故事的经验值得肯定。本文以《捉妖记》为例,具体阐释好莱坞技术融合东方叙事经验的得与失。
配角奇观:萌宠“胡巴”
从《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哆啦A梦:伴我同行》里的机器猫、《小黄人大眼萌》中的小黄人等角色,使观众看到了一个并非真实的人物形象却俘获大众的一种奇观。但与前三部电影所不同的是,胡巴并非整部电影的主角,它的影像缺席了电影时长的三分之一,在影片中没有一句台词。这种重量级的角色在整部电影中长时间的缺席是一种冒险,但同时也是一种传统叙事的成功尝试。
许诚毅透露《捉妖记》当中的小妖王胡巴的灵感来自《山海经》,但并没有完全照搬里面所描述的妖。《山海经》讲到有些妖的叫声很像宝宝,有些妖没有眼、耳、口、鼻,所以在《捉妖记》里,小胡巴可以把它的眼耳口鼻“收”起来。他表示并没有特意把它们做成像吃的菜,只不过是想让它们跟大自然有联系。《山海经》描述说有些妖可以拿来吃,有药用效果。有的吃了对身体好,还有的医治失眠。而在电影里,也有一场十分重要的戏码——“人吃妖”。
重量级角色小妖王胡巴的真实影像在影片进行到50分钟时才显现,在前50分钟的叙事中,它是一个缺席的重要角色,这在快餐文化腐蚀的今天重新找回中国叙事当中的娓娓道来,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美感才属于中国电影的传统叙事策略。
成长奇观:开辟传统叙事新视角
中国传统的佛教生死观看到了生命脆弱的一面,肯定了生老病死的规律。自从人类有史以来,面对生死就有一连串疑问:吾人的生命是一世?还是三世?是否真有轮回?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伴随一个角色的消失。西方电影在阐释“死亡”时,总会有某些缺憾在内,如唐·霍尔在《超能陆战队》中设计大白这个角色时,将大白的身高和性格都偏向了小宏哥哥泰迪,主要是为了让大白最终替代泰迪,最后完全取代泰迪照顾他。《超能陆战队》中的泰迪牺牲,是为了营救他尊敬的教授,而这个“教授”并非他理想当中值得尊敬的人。再如《冰雪奇缘》当中,姐姐艾尔莎和妹妹安娜的成长也是在父母离开人世之后,而影片也同样将姐妹俩父母的离世(一次意外的航行)写的很简单。
《捉妖记》中,为“小妖王”而牺牲的妖后历经了种种磨难,在临死前将腹中的胎儿“托付”给宋天荫,虽然宋天荫一开始无法接受他成为一个 “孕夫”的角色,但由于其原本善良还是愿意将大丈夫的角色抛到脑后,决定先“生”出小妖王。小妖王的出生和经历隐秘了一个关于影片不同人的成长主题,这个主题原本沉重,但在编剧袁锦麟的手下变得轻松幽默。
二钱天师霍小岚这个角色在片中也经历了一次成长,同时她对影片气氛的调节,成为本片喜剧性的一个标志。霍小岚捉妖一开始就是为了换银子,不论是保护还未生出小妖王的宋天荫,还是跟四钱天师罗刚一直对着干,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拿钱。其实,这不难被解释成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一种隐喻,不少人在忙碌的日子里,变得唯利是图,忘了身边的真和美。在整个影片当中,小妖王的萌动淘气没有变,宋天荫的善良傻气没有变,变的是霍小岚的心境。她从一开始只为了钱财,到后来被宋天荫和小妖王之间纯粹的情感所感动,不顾一切要救出小妖王;再到霍小岚在混乱中被宋天荫吻了一口,这一吻犹如打开了霍小岚心中的潘多拉魔盒,原本掩盖的善良和女性的温柔就此释放了出来,霍小岚从此之后女性特征更加明显。这个觉悟和成长的主题同时也指出了人在善意的环境下可以被感染和改变。
追寻这个主题可以从宋天荫和奶奶的角色当中解读出来。奶奶对于爸爸的追寻主题从一开始就告知了观众,观众处于“全知全能”的状态,但对疯疯癫癫的奶奶从未有过过多的关注。奶奶总是半醉半醒的状态,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自己的儿子是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宋戴天,随身携带宋家的斩妖驱魔宝剑,奶奶不明就里地追寻着爸爸。宋天荫迷惑地生活在永宁村,他本性善良,不知原由地练着奶奶说的宋家十段锦。到了影片最后一场戏才给出了所有的答案,原来宋戴天作为最高级别的天师,并没有杀害所有的妖,而是让他们披上人皮伪装成人,教他们吃素,留他们在永宁村,永宁村的名字也很好的诠释了父亲的愿望,希望村子永远安宁,希望儿子和母亲永远安宁,而自己作为天师却不能和妖共存,所以才有了他跟小时候宋天荫的决裂分离的一场戏。在宋天荫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永远处于“缺席”状态,所以他认为抛弃孩子的家长都不是好家长,他不愿意卖了小妖王,也是因为他把自己化为小妖王的“父亲”角色,而在最后当他揭穿了葛千户这个邪恶派的大阴谋后,用自己的鲜血打开宝剑,同时配以宋家十段锦战胜妖魔,明白人妖不可共存才下决心定和小妖王分离,这时闪现了当年他与父亲诀别的同一场景,然而从小妖王在妖界生活时选择吃果子等细节可以看出小妖王的另一层释义。小妖王善良的体现是它的成长,被导演巧妙地借以阐释宋天荫的过去,而父亲正是接受铜币的宋天荫作为天师的未来,他的未来依旧是善。至此,宋天荫身上的追寻、成长和人生三世、性本善等主题全部阐释清楚。
华语电影在阐释为新生命而经受的“磨难”“牺牲”时总会显得沉重,这不仅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源于整个民族的灾难史。综观上个世纪华语电影,不论是《高山下的花环》对真、善、美的追求,还是《暴风骤雨》中对正义战争的讴歌、对革命的美好期待,亦或是《人生》对改革开放下小人物命运的讲述,正面形象的苦难和死亡都赋予了强大的震撼力。华语电影在经过“伤痕电影”时期,对“苦难和死亡”的宏大叙事的经验和类型给当今的电影、文学都奠定一个厚实的基础,整个民族阐释死亡时都显得小心和谨慎,这也构成了华语电影的一个经典的叙事特色。
喜剧奇观:混合好莱坞经典元素
在电影工业急速发展的当下,包括《捉妖记》在内的很多商业片对“苦难和死亡”的阐释慢慢消解掉了最传统的叙事方式,以“觉悟”“追寻”“成长”的主题来替换确实是一种好的选择。然而这些看似严肃的主题以戏谑的态度来讲述,也挑战了观众的心理防线,引起了观众的不满。如果说《捉妖记》从配角奇观中胡巴的设置,从成长奇观中开拓传统叙事的新视角还坚守着中国文化的话,那么,许诚毅在喜剧方面的设置是对电影工业和市场的一次妥协,其中混搭的好莱坞经典元素也是从导演在创作中作出讨好观众的让步。
妖界忠臣竹高和胖莹是一对欢喜冤家,许诚毅对他俩的塑造就使用了好莱坞经验。曾志伟和吴君如本就是出色的谐星,在这里面演出也真实地还原了二位的喜剧特色。竹高和胖莹刚开始为了护送妖后,但不料因为想贪吃“小鲜肉”宋天荫而被天师霍小岚盯上,在茶楼展开了一场极具香港武侠电影风格的打斗。打斗之前,竹高和胖莹在毫无女性特征的霍小岚面前上演了一场酸溜溜的对吻,胖莹立马从一个泼妇形象转变成一个温柔可人的女子。这个可笑的场面为接下来霍小岚的转变和觉悟提供了一个铺垫,霍小岚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因为一个吻变得温柔贤惠。
四钱天师罗刚道行比霍小岚高,在霍小岚眼里是个贼,这个武艺高强无所不能的天师,在许诚毅手中也被嘲弄了一番。竹高和胖莹被罗刚抓走后,上演了一出歌舞剧,这个歌舞剧恰好是梦工厂推动剧情、揭示主题的经典元素。歌词“甜酸苦辣,委屈挣扎,生活就是彼此不断的吵骂。皮相复杂,心灵狡猾,所谓生活不过就是一场厮杀。谁要丰衣足食算了吧,混得可以就不差,今天千军万马一人之下,明天就给找茬。没有希望出路忘了吧,肚子空着才可怕,渴望天赐锅巴”。罗刚的回应“干巴巴,我舌头干巴巴,给生活踏踏踏,不断践踏。不成话,我年纪都一把,却像混球煤渣,江河日下”,以及最后的高潮“做人做妖一样的烦恼,无情喝水撑不饱,为了生活像个跑龙套,却啥样也做不了,渴望啃到一个小笼包,情愿脸皮也不要,生存绝不逍遥”都表达了导演对待生活的积极乐观,豁达面对出世入世的人生境界。这也为影片最后罗刚的反转做了一个铺垫,在一场捉妖王、救妖王的抉择中,罗刚选择了跟竹高和胖莹一起拯救小妖王,竹高和胖莹最后对罗刚的吻也升华了罗刚作为天师的职责意义。
除了竹高、胖莹和罗刚,影片还用了很多喜剧片段来增加笑料,例如霍小岚帮宋天荫接生、爱打麻将的大押店老板娘,为求开枝散叶的郑式夫妇、厨子天师等等角色都让影片的氛围变得轻松。然而就是这些轻松的片段也被质疑为内涵空洞,主题不明确,观众对待生与死的严肃态度被挑战了底线,所以对这些“笑点”并不买账。
结语
《捉妖记》是许诚毅的特效加上袁锦麟的传统叙事,票房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中国特效的希望,然而在这一奇观影像下,依然要关注中国的传统叙事,这是影片的内核。好莱坞利用“中国元素”特效装点西方经典叙事,为中国观众炮制“中国提供版”的策略应该引起华语电影人的重视。《捉妖记》作为商业片虽避免不了向市场妥协,但已然可以让中国电影人看到中国传统叙事的力量。鉴于此,华语电影应该谨慎对待特效的使用,不可盲目创造奇观式的影像而忽视最本真的东方故事内涵和叙事传统。只有重视传统叙事,考虑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底线,才能让特效制造出来的奇观式影像发挥最大的优势。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栏目责编:曾鸣
1.[法]克里斯蒂安·麦茨著,王志敏译:《想象的能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2.[法]让·拉特利尔著,吕乃基译:《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熊芳芳,赵平喜:《好莱坞电影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新闻爱好者》,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