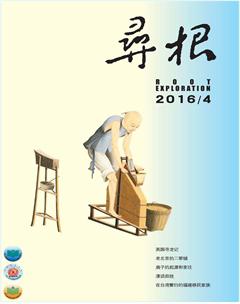且流连,那些文学史上的风景
陈四益
何宝民先生新著问世,责我作序。序,我何敢!但他结集之前,散见于几种期刊的“民国文学旧刊寻踪”系列文章,确曾读过一些。随着他的笔触,行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那多姿多彩的“山阴道上”,一丘一壑,一草一木,大有应接不暇之感。
我读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史”包括了“五四”以后中国的全部文学。后来强调“十三年”(1949-1962),于是,把“现代”断在1949年之前,之后一段就叫“当代文学”了。这样,所谓“现代”便大体同“民国时期”重合。
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皇皇巨著出了不少。我因不做专门研究,细心读过的并不多,倒是宝民先生这些“旧刊寻踪”,一人、一刊、一文、一事,不去分阵营、归流派、别正闰、排座次,娓娓道来,颇合我“闲读”的口味。许多旧人、旧刊、旧文、1日事,若不是他细心梳扒,或许无须多久都将归于湮灭。
譬如,郑振铎、巴金、靳以于1934年创办的《文学季刊》,是广为人知的。《文学季刊》还有一个同年创办的姊妹刊《水星》,今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主编者都鼎鼎大名,除郑、巴、靳外,还有卞之琳、李健吾、沈从文等人,由卞之琳负责。作者群,更是群星灿烂——茅盾。周作人、张天翼、冰心、何其芳、李广田、蹇先艾、臧克家、吴伯箫、废名、丽尼、艾芜,荒煤、梁宗岱等,都是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
《水星》的作者群中还有一位名叫张天,南阳人,孤陋如我,便闻所未闻。他的作品多写南阳农村的生活,除《水星》外,在《新小说》和《人间世》也有作品发表。《新小说》称他为“特别值得推荐的”“新出的作家”,认为他的笔致、语言直可追踪老舍的短篇。卞之琳回忆《水星》,说他和靳以都对张天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可惜《水星》只出了九期便因时局等各种原因终刊,而张天也就此消失于文坛,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失踪”了的作家。宝民先生曾想通过南阳地方史志查出些他这位乡贤的踪迹,可惜也如南阳刘子骥之觅桃花源,无果而返。其实,就是《水星》这本相当重要的文学刊物,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几近于“失踪”了。
有些作家和文学刊物,虽然并未失踪,但也因种种原因消失于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宝民先生有专文介绍《谈风》:1936年在上海创刊,主编为周黎庵。大概因为刊物和编者在文学趣味上同周作人、林语堂等走得较近,被归于幽默一派,连带着刊物上不少揭示现实的作家与作品,也都长期被冷落或被消失了。原名王焕斗的作家老向,在《谈风》上连续发表的《宛西见闻记》,也如张天的小说,是对现实的揭露,那真实与残酷,是许多标语口号式的左翼作家所远远不及的。老向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大革命时期离校南下参加北伐,后又重返北大求学。抗战时期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创作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通俗文化作品,深受民众喜爱。香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刘以鬯称:“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显明,不大有洋葱味。”可惜这样一位有独特贡献的作家,长期被漠视,自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更是入了另册。他在“文革”中死去。即便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记得他并给予恰当评价的人,也已寥寥,他是一位“被失踪”的作家。
旧刊寻踪,还会有许多有意思的发现。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作家间或作家群间的壁垒,其实并非像后来某类叙事那样红白分明,似乎真个“汉贼不两立”似的。
章衣萍,因着鲁迅《教授杂咏》一诗的讥嘲和他那些小说,被列入色情文学作家,并非无因。但他先前与鲁迅一起筹办《语丝》,“三一八”惨案后,愤而作“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的联语,也曾相当激进,便很少有人还记得,或虽然记得却不敢或不肯提及了。
鲁迅到上海后,在暨南大学的讲演,有两次都是章衣萍所邀。其中一次,就是直到今天还为人不断提到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讲稿最先发表于暨南大学学生文艺社团秋野社的社刊《秋野》。秋野社就是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章衣萍发起建立的。这一次讲演,有章铁民与曹聚仁两个记录稿,后来鲁迅在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收入了《集外集》。
鲁迅在暨南大学还有一次讲演,讲题是《离骚和反离骚》,记录稿刊于《暨南学刊》。这次讲演的记录稿记得粗疏,还有一些错误,也未经鲁迅认可或重新整理,所以后来不曾收入鲁迅的各种文集。但记录稿中,仍保留了不少鲁迅式的深刻与幽默。譬如他说“离骚”就是牢骚。“反离骚”就是反对发牢骚,以为人应听天由命,发什么牢骚?人一发牢骚,社会就会扰乱了。而发牢骚的则说,因为社会扰乱了,所以我要发牢骚。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现在的出版物《新月》,说是只限于文艺的研究,不许人发牢骚,这便是“反离骚”遗下来的精神。不过,鲁迅以为,这两派——牢骚与反牢骚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牢骚也绝不至扰乱社会。发牢骚的也都为一己利禄而已,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
直到现在,“离骚”与“反离骚”的争论依旧在继续,而大致是与权势者同一步调的,都是“反离骚”派,而相反立场者则是“离骚”派。鲁迅说这两派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牢骚绝不至扰乱社会,至今也依然是不刊之论。
李长之在1957年之后,渐被世人淡忘,只是这几年才又稍稍被人提及,他的《鲁迅批判》也得以再版。他关于“批评是反奴性的”见解,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这期望,我们今天做到了吗?
读宝民先生新著,语皆平实,如聆听“讲古”,如对坐闲谈,不求“体大思深”,但那一花一树、一枝一叶,许多现代文学史上自行消逝或被消失的人物与作品,社团与期刊,已足令人流连。鲁迅曾说他的杂文集“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宝民先生的书中,我想读者也一定会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在喧嚣的时代,这种吃力的、细致的工作,未必讨好,但若想细致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细节”怕也真是不该忽视的元素。
(《旧时文事——民国文学旧刊寻踪》,何宝民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