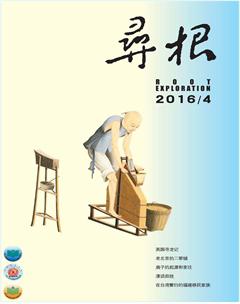南朝时期丧服学的历史考察
黄炯炯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曾经被作为调节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纷争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法律。然而在魏晋时期,礼法却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儒家的社会伦理逐渐被社会所抛弃,社会大多数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心理上蒙受了巨大的阴影,他们开始倾向于追求道家那种无拘无束的恬淡生活,以期在动荡和纷争的社会中明哲保身,这就使得儒家的礼法观念在社会中不断地淡化。
礼法大幅度遭破坏,是在曹魏政权建立之后。曹魏政权的奠基者和创造者曹操本出身于非儒的寒族,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少年时便“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样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决定了曹魏政权不可能单一地站在儒家的立场之上,加之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其政治措施更加功利化。这种功利化从其《求贤令》便可看出,为了笼络人才,曹操取法古代圣君贤相下《求贤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选人上,他主张“唯才是举”而不是“唯德是举”,使得大批的寒族进入官僚阶层,大胆使用被“清议”派诬为名声不好的革新人物如郭嘉、戏志才,任用出身士卒的于禁,乐进,连原来是敌对阵营中的战将张辽、徐晃等也予以重用。另外,这种不顾礼法还出现在曹氏政权内部,曹操死后,其子曹丕“悉取武帝宫人自侍”,以至于其母卞太后发出了“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而”的无奈。
魏晋易代之际,尽管统治集团一再强调礼法的重要性,可是在这天下多故的政治高压之下,这种强调不仅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响应,反而使得礼法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阮籍、嵇康等七人“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而“竹林七贤”亦多放达之士。阮籍的嫂子“尝归宁”,阮籍与其相见而别,当别人讥笑他时,阮籍说:“礼岂为我设邪!”至于刘伶则经常饮酒,“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而讥之,刘伶答日:“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裨衣,诸君何为入我裨中!”在这个“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的时代,无怪乎“国家多难,宗室迭兴”。
西晋时期礼法崩溃曾弓I起学者的注意,西晋裴颁“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于是著《崇有论》以重塑礼法权威。
礼法重塑到东晋及其以后才大规模地出现。晋室南渡之后,士人们开始积极地思考和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他们的结论也无非是魏晋清谈以及清谈所导致的礼法崩溃,于是大多的知识分子便投入到礼法重塑的事业中。礼法重塑最重要的表现便是“三礼”学研究的兴盛,这一时期“三礼”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礼学研究著作共计“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加上亡书共“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如果没有几次书籍的浩劫,其书将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朱熹曾有“六朝人多精礼”的评价。
在南朝所有的礼学研究之中,丧礼研究是重中之重,“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丧服》本为《仪礼》中的一篇,有经有传,相传为子夏所著,而《礼记》中《丧服大记》《丧服传》等亦为《丧服》的解说。但直到东汉马融之时似乎并未有明显为《丧服》单独作解说的著作,将《丧服》从《仪礼》中析出而为其单独作解说大致是从马融开始,继而是郑玄。到了东晋和南朝宋时期,大规模的名家《丧服》解说才纷至沓来,“融其后则有王肃《丧服经传注》《丧服要记》,射慈《丧服变除图》,杜预《丧服要集》……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就连方外之士慧远亦讲《丧服》于庐山。
南朝时期研究《丧服》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者亦大多是仕宦之家。《丧服要集》的作者杜预出身于曹魏政权的高级官僚家庭,其祖父杜畿是三国曹魏的名臣,曾担任河东太守十六年,备受曹操的信任,其父亲杜恕在魏明帝曹毅时担任散骑常侍等职务。如果说把杜预放入儒家的范畴,那么在道教界和佛教界亦出现过研究《丧服》的高潮,道教以葛洪最为著名。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出身江南士族。而佛教方面则以慧远和雷次宗为显,《世说新语注》引《张野远法师铭》称其世为冠族,游学许洛,后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遂以为师。后南渡东止庐山东林寺三十余年,由于他的学问兼及儒释道,四方问学之士纷至沓来,其中宗炳、雷次宗事慧远讲《丧服经》,后雷次宗创《丧服》雷氏学,《隋书·经籍志》载有:“略注丧服经传一卷,雷次宗注。”
至于对《丧服》的重视程度,史书中亦多有记载,刘宋元嘉时期,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陈“后主在东宫,引(沈文阿)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不一而足。
《丧服》不单单是关于丧礼的专篇论著,其实质内容仍是依据亲属称谓划分亲疏等级关系,在维护家庭和社会伦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代的陆德明就曾说:“《丧服》一篇,凶礼之要。”它之所以能从《仪礼》中析出,并被社会广泛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有社会对“丧服”制度的需要,可以说丧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多种力量综合的结果。
丧服学的兴起是经籍缺损和经籍解释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在经历一系列的浩劫之后,有些已经面目全非。就《仪礼》而言,在传播中已经出现了缺损,尤其是在经历秦代的焚书坑儒后失去了本来面目。董卓之乱后,“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以至晋代挚虞发出了“《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的感慨,这种文化典籍的缺损使得典籍的整理成为大势所趋。另外,《丧服》的研究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丧服》本来就产生于一个礼制极其混乱的先秦社会,本身就带有很多疑点。而在后世儒者的解说过程中也是莫衷一是,“《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颧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颁异说,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又说“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经生们对于《丧服》的解说众说纷纭,使得一般的士人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行为标准,而丧礼在古代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活动,因而使得整个社会自上而下产生了整理和重新解释《丧服》的要求。
汉末以来的长期分裂和社会动荡使士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家庭伦理困境之中,如亲属失散或两地隔绝,生死不明,或亲属丧于异国他乡而自己却无从奔赴,同时出现了大量如“前妻”“前母”之类的亲属关系,其伦理地位《礼经》中从未记载。面临此类问题,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做到既遵循礼法原则而又合乎亲情。并且不妨碍自己及家族成员的婚宦仕进。为解决当下的家庭伦理困境,南朝的知识分子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而他们的救命稻草便集中在礼学的研究上。为此,他们编纂了大量礼学著作以调整伦常关系,指导土族生活。在他们的研究中,《仪礼·丧服》篇的地位不断上升,研究《丧服》成为一时风尚。丧服学在此时的兴起还有着学术风气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学术的兴奋点,而玄学的一大特色便是崇尚道家的简易,而《丧服》篇从《仪礼》中析出恰恰迎合了这一时期的学术风尚。
丧服学的兴起也是士族自身发展的要求。士族在南朝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几乎充斥着整个社会。像王氏家族就曾掌握东晋的大权,随着士族家族的扩大,家族的管理也变得艰巨起来,《颜氏家训》的《风操》篇曾对家族的状况有一个很明晰的概括:“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可见江南土族同族仍采用五服制度,另外在称呼上也同样遵循这样的原则,“凡与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称之。……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而在越辈之间的亲属也同样严格,他们称呼自己:“父母之世叔父,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父母之世叔母,皆当加其姓以别之;父母之群从世叔父母及从祖父母,皆当加爵位若姓以别之。”由此可见,丧服制度对于维护南朝士族家族的稳定是何等的重要。
结语
丧服学是南朝礼学的精髓,但是丧服学的产生却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南朝知识阶层努力重建秩序的结果。东汉末年社会动乱使得礼法制度遭到巨大破坏,上自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受此风气影响。但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却从学理的建构上致力于恢复传统的礼仪秩序,在这种大环境下,《丧服》逐渐从《仪礼》中析出而单独成篇,受到学者的重视,形成了所谓的丧服学。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