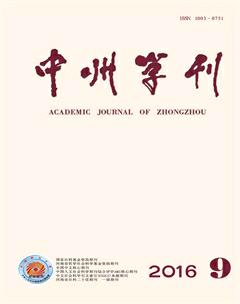《星流发愿文》与归义军初期时势研究
赵玉平 李沁
摘 要:敦煌文献P.2854《星流发愿文》为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写本,用于观测到“星流变异”天象后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时僧人祈愿宣诵。“星流变异”在中国传统星占中多预示凶兆,且在史籍中大都附会于国家政治军事时势。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受到来自唐王朝、周边吐蕃势力及西州回鹘等多方面的外部军事压力,张氏统治阶层内部也因权力斗争而暗流涌动。借助禳灾斋会这一形式,不仅可强化归义军辖下民众对张氏家族统治的认同感,亦可平抑政权内部斗争而潜藏的危机。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星流;禳灾;斋会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9-0142-07
我国是东方天文学的发源地,①在距今6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已存在较为成熟的天文观测及天体信仰。②在我国传统术数文化③体系中,星占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即通过对星象(星流变异)的占察(包括日占、月占、五星占、列宿占、流星占、客星占、彗星占及云气占等)④预言人间之事。《史记》及其后所有正史文献中都专门辟有“天文志”一类的专志用以引征军国大事。有唐一代,星占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了的重要创新,⑤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星占之风也十分盛行,以致唐代田园诗人王绩曾用“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之句作为对当时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⑥
在星占观念系统中,部分“星流变异”虽为祥瑞之兆,但绝大部分“星流变异”预示着君主忧、大臣死、边兵起、谋叛、旱灾、饥荒、盗贼等方面的危机。⑦所以,祈禳之法便一直与星占相伴而生。在唐代,举行佛教禳灾斋会是较常见的祈禳方式。如代宗时,“时以星变,羌虏入寇,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讲”⑧;文宗时,“三月甲戌,以彗星见,命京师诸佛寺开《仁王经》道场”⑨等。将各方星宿与各地州郡一一对应投影的“分野”之法一直是星占理论的重要基础,但唐代传世典籍对地方藩镇应对危机星象时的禳灾活动却颇吝笔墨,使人难窥其详。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1件记载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为应对星象“危机”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情形的文献——《星流发愿文》(即P.2854号敦煌文献所载20篇(正面17篇、背面3篇)斋会祈愿文中正面第10篇)。⑩《星流发愿文》虽幅制简短,却完整展现了禳灾斋会的各项重要信息。通过研究这些信息,不仅可以一窥唐代地方藩镇星占信仰及佛教禳灾斋会的面貌,还能从更广阔视角下审视“星流变异”现象通过禳灾活动与国家(或藩镇)政治军事时势间微妙的互动机制。
一、录文及断代
P.2854《星流发愿文》释录如下:
星流发愿文
夫诸佛兴悲,无缘普被,有情见异,感迹缘差。故使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从心起。
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憎者欤。厥今白帝届序之晨(辰),金风落叶之日,集四众于宝地,开五印之真文。日尽三朝,启嘉愿者有谁施之。则有我释门都统和尚爰及刺使(史)等倾为星流变异,虑恐不祥,竖福禳灾之所为也。今既福事廓被,胜善咸亨,先用上资梵释四王、龙天八部。惟愿威光炽盛、神力无疆,扫彗勃(孛)于天门,殄灾殃于地户。然后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摩诃般若,以用资熏,大众虔诚,一切普诵。B11
《星流发愿文》所展现的禳灾斋会信息十分完整。(1)举办斋会的原因:“星流变异,虑恐不祥”;(2)举办斋会的时间:秋季(“白帝届序之辰,金风落叶之日”)、连续三天(“日尽三朝……今既福事廓被”);(3)斋会参加者及规模:“集四众于宝地”;(4)斋会组织者:“我释门都统和尚爰及刺史等”;(5)斋会祈愿对象:“诸佛”及“梵释四王、龙天八部”;(6)祈愿方式:诵经(“开五印之真文”)、行香(“以用资熏”);(7)祈愿所望:“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此外,还以佛教义理对“星流变异”出现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轻毁三宝、造作恶业(“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从心起。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憎者欤”)。
根据书体字迹特征判断,P.2854号敦煌文献正面17篇愿文当为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写。对这些愿文中包含的时间信息进行考证,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星流发愿文》源本写作的时间。17篇愿文中出现的时间信息依次为:第1篇《国忌行香文》中“……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第3篇《先圣皇帝远忌文》中“……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第8篇《竖幢伞文》中“……当今大中皇帝……”、第9篇《转经画像祈愿文》中“……奉为尚书……”、第11篇《行城文》中“……当今大唐大中皇帝……河西节度吏部尚书……”、第12篇《礼佛发愿文》中“……大中皇帝……河西节度吏部尚书……”。
上述信息中三次提及的“大中”年号为唐宣宗李忱在位时所用(懿宗859年继位后延用1年),即847年至860年。两次提及的“张议潮”,大中五年(851)十一月被唐朝任命为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检校吏部尚书;大中七年(853)其兄张议潭入长安(议潭子张淮深继任沙州刺史);咸通二年(861)率军攻占凉州,因功转授检校司空;咸通八年(867)应召入长安授右神武统军兼司徒(河西军政委侄男张淮深。时张淮深遣使求节未获,遂自称河西节度),咸通十三年(872)病卒于长安。B12
P.2854号敦煌文献正面17篇愿文中并未提及张议潮“司空”一职。由此看来,推论《星流发愿文》源本写于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大中五年)至转授检校司空(咸通二年)间当不会有太大出入。而《星流发愿文》中所称颂的功德主“刺史”,当为张议潮之兄张议潭或其侄张淮深。
二、“星流变异”对唐代国家政治军事时势的附会
敦煌文献中已知含有星占资料的文献共17件,即P.2512、敦博藏076V、P.3288、P.2536V、S.2669V、S.2729V、P.2610、P.2632、P.2941、S.5614、Дx01366V、P.3794、S.3326、P.2811、P.3589、P.3571V、S.5777。B13唐代李淳风(太宗、高宗朝时任太史令)所著《乙巳占》部分段落在敦煌文献中亦有抄本,且与今本差别不大,B14当为敦煌地区星占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在唐代官修史籍中,以“星流变异”附会国家政治军事时势的现象十分普遍。以《新唐书》为例,其“天文志”中所载“星流变异”事件几乎都可应验国家政治军事时势。兹撷两例:
第一,陈硕真起义事。《新唐书·天文志》“星变”条载:“永徽三年十月,有流星贯北极。四年十月,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有星陨于贼营。”B15《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犯北极十五”条云:“黄帝曰:‘使星色白,入北极,天下兵聚。一曰国有大变,若有称兵。……焦延寿曰:‘流星入北辰,兵大起。”B16《乙巳占》“流星占第四十”条云:“坠星之所,其下流血,破军杀将,为咎最深。”B17由此看来,流星与陈硕真谋反事间的“应验”关系为:永徽三年(652)观测到流星入北斗(“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兆),翌年发生陈硕真起义(预兆应验),剿乱过程中有陨石坠落敌营(“破军杀将”之兆)。但当我们观察高宗永徽年间史料时不难发现,睦州女子陈硕真以神仙身份用道教方式聚众,B18自永徽四年十月起事至十一月“陈硕真伏诛”,B19历时仅1月旋被剿灭,更像是星占中常出现的“盗贼起”或“聚众之事”,实难堪“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兆。“破军杀将”之兆的详情又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永徽四年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楯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馀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B20可见“破军杀将”之说应为崔义玄针对兵士畏惧陈硕真仙术所采取的励兵之法。B21
第二,光启年间藩镇攻掠事。《新唐书·天文志》“星变”条载:“光启二年九月,有大星陨于扬州府署延和阁前,声如雷,光炎烛地。十月壬戌,有星出于西方,色白,长一丈五尺,屈曲而陨。占曰:‘长庚也,下则流血。三年五月,秦宗权拥兵于汴州北郊,昼有大星陨于其营,声如雷,是谓营头。其下破军杀将。”B22此段文字为发生在僖宗光启年间的三次陨石记录:其一,光启二年(886)九月流星陨落扬州;其二,光启二年十月“长庚”自西方而陨;其三,光启三年五月“营头”陨于秦宗权营。三次流星陨落皆为凶兆,但根据陨落表现之不同,“应验”亦有差别。落地后声光并现的扬州陨石,星占中称“天狗”,《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名状一”条云:“巫咸曰:流星有光见面坠地,若不至地,望之有足,名曰天狗,所往之乡有战流血,其君失地,期不出三年灾应。又曰:大流星堕破如金散,而有音声,野雉尽呴,名曰天狗,其所之地必有战流血。”B23“天狗”所应为光启三年(887)扬州兵变事。是时,淮南节度使高骈割据东南七州,“(光启三年四月)甲子,淮南兵马使毕师铎陷扬州,执其节度使高骈。……五月甲戌,宣歙观察使秦彦入于扬州。……(九月)秦彦杀高骈。……(十月)秦宗权将孙儒寇扬州。十一月壬申,庐州刺史杨行密陷扬州,秦彦、毕师铎奔于孙儒。”B24经此反复,号“富甲天下”的运河名都扬州不仅“破军杀将”、“其君失地”,其地百姓亦有血城白地之灾。“长庚”即金星,又称太白、启明。关于“长庚”西出而陨之兆,司马迁所著《史记·天官书第五》云:“(太白)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B25“长庚西陨”观测中未明示陨落之地,权按图索骥,不妨推其为杨行密在谋士袁袭建议下弃扬州、撤庐州、夺宣州之事。《新五代史·杨行密传》云:“(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蔡州军阀秦宗权来攻)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行密欲走海陵,袭曰:‘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行密乃走庐州。……进围宣州,(赵)锽弃城走,追及杀之,行密遂入宣州。龙纪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观察使。”B26若如是,“长庚西陨”虽为凶兆,但却有补救之法,即“举事右之背之,吉”。杨行密放弃左撤海陵的计划,右撤庐州以避秦宗权之攻,后成为十国时期吴国的实际开创者。所谓“营头”者,《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昼行三”条云:“甘氏曰:星昼行名曰营首,营首所在,有流血滂沱,则天下不通。一日大旱,赤地千里。所谓昼行者,日未入也。”B27“营头”所应为光启三年蔡州割据势力秦宗权进攻汴州朱全忠兵败事。《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载光启三年事:“(五月)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大破之,斩首二万馀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B28此役中秦宗权战败,役后又发生了郑州、河阳屠城事件,实应“流血滂沱”之兆。是役,秦宗权已自称大齐皇帝,且兵力十倍于朱全忠,“营头”陨营之事,或与流星陨陈硕真营事相类,亦为朱全忠励兵之法。
前文已述,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即便是对于流星这种每天都在发生的天象,也只有极少数被后朝录入史籍。由此看来,“应验”是否为“星流变异”观测记录选录史籍的前提呢?历代天文官员中不乏上究“星流变异”下度宫廷气象者——谏者依天而奏,闻者顺天而行,天、人间的“感应”通过中国封建伦理关系实现了美学上的平衡。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志”正是史家们对历史的注解。《星流发愿文》也具有这种意义。
孤悬西北的敦煌虽未卷入唐末之乱,但当某位敦煌僧人应禳灾斋会所需写作《星流发愿文》时(大中五年至咸通二年间),归义军政权正处于内忧外患积聚的局面。通过禳灾斋会正确解释“星流变异”所预示的征兆,对稳定敦煌民心、树立张氏“天命”威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都统和尚与刺史竖福禳灾所祈愿的“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便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是时归义军政权所面临的时势。
三、归义军政权初期时势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朗达玛因施行灭佛政策被僧人射杀,吐蕃政权遂因二子(云丹B29、约松)争位陷于内战,约松派贵族洛门讨击使论恐热攻杀吐蕃东道节度使尚思罗,实际控制了河陇地区。会昌三年(843)至宣宗大中二年(848)间,论恐热在与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及唐军的战争中实力不断削弱,河陇地区秦、原、安乐三州回归唐朝。大中二年,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击败吐蕃守军,至大中五年(851),相继攻占沙、瓜、肃、甘、伊五州之地,并与周边尚婢婢(占据廓、兰、鄯、岷四州)、尚延心(占据河、渭两州)等吐蕃势力结盟,B30大中五年十一月“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张议潮)为节度使”B31,建立起形式上归复唐朝的汉人割据藩镇。张氏归义军藩镇政权建立之初,至少面临以下5方面的时势危机:
第一,唐朝朝廷的猜忌。荣新江在研究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时曾指出,张议潮、张淮深任节度使期间,敦煌文献中多使用“河西节度”一名,而非唐朝中央政府命名的“归义军节度”B32。冯培红认为,这一现象预示了唐朝朝廷与归义军政权间的微妙关系。B33实际上,这种“微妙关系”在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攻占凉州后变得愈趋表面化。是时,归义军政权已实际控制了沙、瓜、肃、甘、伊、凉等六州之地,基本恢复了睿宗景云二年(711)所设河西道(治凉州)的规模,“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河山,宛然而旧”B34。张议潮占领凉州后,即奏请朝廷允许归义军经营凉州。归义军政权与唐朝廷间的信任危机围绕凉州问题发酵起来——朝廷并未准许归义军于凉州建制,仅是转授张议潮检校司空以彰其功。与此同时,唐朝廷开始修筑凉州城防,“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B35,并于咸通四年(863)设凉州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试图接管凉州并抑制归义军势力发展。
第二,与吐蕃势力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敦煌自德宗贞元二年(786)以和平方式降于吐蕃,为吐蕃统治长达60余年。其间敦煌汉人社会从社区政治组织结构到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或主动融入了吐蕃因素。B36领导各方势力驱逐沙州吐蕃守军的张氏家族本身即为吐蕃政权中世袭的沙州“汉人刺史”B37。张议潮本人不仅谙习吐蕃文化,还曾赴逻些朝觐赞普。B38这一身份不仅是张议潮与周边尚婢婢、尚延心等吐蕃势力保持联盟关系的基础,更是其能获得河陇地区吐蕃军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唐代诗人薛逢在《凉州词》中曾这样描述凉州战役:“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B39张议潮也奏称:“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B40当时凉州亦为吐蕃军占领,《凉州词》中所称“蕃兵”之“国仇”,当指论恐热支持约松继任赞普事。凉州战役为归义军建制后最重要一战,而吐蕃军在战役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周边及治内吐蕃势力的利用与笼络当为关系归义军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与西州回鹘争夺伊州的战争。大中五年(851)至咸通二年(861)间,除河西吐蕃诸据点外,归义军的另一个主要战争对象为西州回鹘。文宗开成五年(840),踞于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在内乱及天灾中被黠戛斯人攻破,其后西迁的回鹘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B41。西州回鹘即西迁的庞特勤部。归义军初期与西州回鹘的战争集中在对伊州的争夺上。大中四年(850)张议潮驱逐吐蕃势力夺占伊州,B42此后西州回鹘势力向东扩张,占领了伊州城西的纳职县,并“频来抄劫伊州”。大中十年(856),张议潮率军进攻占据纳职县的西州回鹘。B43至僖宗乾符三年(876),伊州终为西州回鹘所占。
第四,经济调整期的军事掠夺及外贸交易。吐蕃趁安史之乱河陇守军内调平叛之机于广德二年(764)至贞元二年(786)间,相继攻占或招降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并在河西地区“焚烧庐舍,驱掠人畜……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B44,致使河西诸州人口逃逸,土地荒芜。吐蕃统治相对稳定后,政权组织上以吐蕃地区的部落制取代唐朝的乡里制,政治上以吐蕃人为主官、汉人为辅吏,文化上以吐蕃文化同化占领区各民族,经济上则是以计口受田的“突田制”取代唐朝的均田制,这些措施使河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在进行人口调查及土地调整的基础上,实行了类似中原地区两税法的据地出税及请田负役制度。B45这些改革措施并未触动旧有的大量私田主利益,因而推行得较为顺利。但归义军初期征战频繁,即便是进行了相应的土地及税赋改革,应仍难供给军用。以周边民族势力(如河西论恐热系吐蕃诸据点)为对象的军事掠夺及对外贸易似为供给军用的重要来源。前文已述,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尚婢婢、尚延心等吐蕃势力保持着联盟关系,除政治因素外,战利分配应是维系这一关系的经济因素。关于归义军政权的外贸情况,齐陈骏、冯培红曾指出,尽管战争频繁,丝路上的商业交往却不曾间断,这归因于河西地区良好的商贸传统与商业环境。B46据齐、冯考察,归义军时期主要的贸易对象为西方的中亚诸国及东方的唐王朝,外贸输出品主要为丝织品,输入品为棉织品、金属器、毡褥及毛皮(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述商品同时亦为转口贸易品)。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掠夺与外贸交易两种经济来源在对和平环境的选择上,本身便为一对矛盾体。
第五,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据已有材料看,归义军初期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主要体现在张氏家族中张议潮支系与其兄张议潭支系间的矛盾。P.2762+S.3329+S.1616+S.6973+S.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称张议潭:“入陪龙鼎,出将虎牙,武定文经,语昭清史。推夷齐之让,恋荆树之荣。手足相扶,同营开辟。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由此看来,张议潭、张议潮兄弟当同为大中二年(848)率众击败沙州吐蕃守军事件的领导者,其后议潭效伯夷、叔齐故事,推让其弟议潮为节度使,自己则奉表入朝为质,以换取唐朝廷对归义军政权的承认与支持。杨秀清曾据相关材料推测,议潭退出归义军政权入朝为质是出于兄弟间达成了由张淮深(议潭之子)继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协议;指出咸通八年(867)议潭卒于长安后议潮接继入朝为质是出于张淮深势力的逼迫。B47《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载:“(咸通八年)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张议潮)入朝,以为右神武统军,命其族子淮深守归义。”B48张议潮入朝后,沙州刺史张淮深即自称节度使。至光启四年(888),朝廷正式授张淮深为节度使。但在大顺元年(890),张淮深与妻、子八人同时被杀,B49张议潮之子张淮鼎重掌归义军。
四、归义军政权初期举办禳灾斋会的社会学意义
在吐蕃统治的60余年中,相较河西道时代(景云二年(711)至广德二年(764),河西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处于低谷期,“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永远成为定格的历史。B50这一时期,佛教是少数获得巨大发展的领域。以敦煌为例,据藤枝晃研究,吐蕃占领时期佛教寺院从六七所增加到二十所,僧尼由数百人增加到近千人(约占敦煌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B51敦煌张氏、索氏、李氏、翟氏、令狐氏、阴氏、宋氏等大族中不乏出家修行者,在家者亦多皈依三宝、行居士道。B52张议潮即自称“清信佛弟子张义潮”。B53从佛教发展史角度看,吐蕃占领时期河西地区佛教的兴盛一方面是由于唐朝开元时期佛教盛世与藏地前弘期赤松德赞赞普弘法两大佛教发展高峰波峰叠加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在河西战乱中各族人民渴望心灵慰藉的客观需要。
方立天在论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曾指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涉的重要根源,也是佛教渗透、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B54吐蕃统治时期,这种渗透与转化在河西地区汉人族群中表现得愈发明显——佛教越来越多地浸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体现出独特的民俗化倾向。B55敦煌的佛教“星流变异”禳灾斋会便是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术数文化相融合的表现。这使得因“星流变异”而举行的佛教禳灾斋会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学意义。沙州刺史张淮深(或张议潭)借助佛教斋会仪式,通过对“星流变异”的祈禳,以“启嘉愿者”这一主祭功德主身份,代表张氏家族,亦代表归义军辖下民众向“诸佛”及“梵释四王、龙天八部”祈愿“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在这一“日尽三朝”的庄严禳灾仪式中,不仅强化了归义军辖下民众对张氏家族统治的认同感,张氏家族内部因权力斗争而潜藏的危机也获得了暂时的平抑。
注释
①东方天文学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西方天文学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东西两派天文学各有渊源,各自独立发展”。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页。
②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第一阶段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划分黄道天区四象的贝壳图案,这是长期积累天文观测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天文历法知识的体现,以四象图案陪葬墓主人的现象表明,天文知识已融入信仰世界。参见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057—1066页及图版壹、贰。
③传统文化所称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者”。参见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④参见李淳风:《乙巳占》,商务印书馆,1955年,目录页。
⑤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⑥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七《王绩》,中华书局,1960年,第480页。
⑦参见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页。
⑧《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页。
⑨《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50页。
⑩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385页《星流发愿文》“题解”称:“伯二八五四,存文十七篇,此其第九篇。”笔者参阅文献照片逐一考订,发现《敦煌愿文集》中共校录P.2854号敦煌文献所载愿文19篇(正面卷首残篇录于第720页《国忌行香文》“题解”中),所录末篇《正月十二日先圣恭僖皇后忌晨(辰)行香》(第724、725页)后,记有一段文字,“顺宗忌日正月七日,龙法海;穆宗……;德宗……;宪宗……;僖宗……;肃宗……;顺圣皇后……;睿宗……;懿宗……;宣宗……;敬宗……”,为11位帝后忌日及行香执事,且书体特征与《正月十二日先圣恭僖皇后忌晨(辰)行香》一致,可补录其后。“帝后忌日”之后,仍有“忌辰行香文”一篇(计13行),其中言及“太上皇帝”、“光敷帝业”、“五十岁……退习无为……推让宝位”等,所述当为睿宗事,故该篇脱录忌文可拟名为《先圣睿宗忌辰行香》。如此,P.2854号敦煌文献当存文20篇。
B11《敦煌愿文集》第385页已对《星流发愿文》进行录文。笔者进行了三处校正:一、原文第4行3字,《敦煌愿文集》(以下简称《集》)录为“者”,校为“憎”,录脱;二、第6行2字,《集》录为“作”,校为“之”;三、第8行3字,《集》录为“享”,校为“亨”。
B12B13所含天文星占资料分别为:P.2512:含星占残卷、《廿八宿次位经》、《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玄象诗》、云气占1则;敦博藏076V:含《紫微宫星图》、《占云气书》;P.3288:含《西秦五州占》部分内容;P.2536V:含《乙巳占》部分内容;S.2669V:含《乙巳占》部分内容;S.2729V:含《西秦五州占》部分内容;P.2610:含日占、云气占数则;P.2632:含《西秦五州占》、《乙巳占》部分内容;P.2941:含《西秦五州占》部分内容;S.5614:含《西秦五州占》部分内容;Дx01366V:含《西秦五州占》部分内容;P.3794:含云气占1则;S.3326:含《二十八宿分野图》、《乙巳占》部分内容;P.2811:含《流星占》,五星占、云气占数则;P.3589:含《玄象诗》;P.3571V:含日占、月占、云气占数则;S.5777:含《浑天赋》部分内容。参见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凤凰出版社,1996年,第16、51、52、71、95页;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6、25—37页;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41—56页;赵贞:《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文献》2004年第1期。
B14今本《乙巳占》载“星流变异”占法共十卷百类。P.2536V、S.2669V、S.3326、P.2632号敦煌文献中皆抄写有《乙巳占》部分内容。据考,敦煌文献中所抄写的《乙巳占》内容与传世版本“几乎一样”,故可以《乙巳占》相关内容佐考敦煌地区星流变异占示情况。参见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47、56页。
B15《新唐书》卷三二《天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842页。
B16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七四,岳麓书社,1994年,第795页。
B17《乙巳占》,第115页。
B18关于陈硕真聚众的方式,学界一般认为是道教。林梅村曾提出“祆教说”,王永平即撰文与之商榷。笔者查对相关史料及研究动态后,仍取“道教说”。参见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永平:《论唐代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B1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B20《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2、6283页。
B21笔者在研究陈硕真起义相关史料时发现一宗趣事:永徽四年确有可令“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事,即房遗爱、高阳公主预谋以荆王李元景代高宗之未遂政变。其时恰为李淳风做太史令,记录转瞬即逝的流星天象似有所指。李淳风在其《乙巳占》中虽无“流星贯北极”为逆兆之语,但瞿昙氏《开元占经》此象所示皆为引用古人言语,非淳风所未闻。《乙巳占》中更有“流星……冬犯斗魁,大臣逆”、“流星……冲天皇大帝,人主有忧”之说。斗魁者,或为流星贯出所指;天皇大帝与北极紫微紧邻且暗,或亦为流星所贯。设若李淳风假托“流星贯北极”之兆密奏高宗(太史令密奏天象为历朝惯制)以坚定其除逆之心,房遗爱谋反案发似又多了一种解释。此论因暂无更明确证据,仅作一猜测。特留此注,以飨专攻高宗朝史同学研究。
B22《新唐书》卷三二《天文志》,第847页。
B23《开元占经》卷七一,第758页。
B24《新唐书》卷九《僖宗纪》。
B2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中华书局,1963年,第1327页。
B26《新五代史》卷六一《杨行密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48、749页。
B27《开元占经》卷七四,第764页。
B28《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僖宗光启三年五月条。
B29一说云丹为朗达玛之侄。参见扎西当知:《吐蕃末代赞普欧松赞身世辨》,《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B30《新唐书》卷八《宣宗纪》载“(大中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五年十月条亦载“张义潮(张议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张议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陆离、陆庆夫在考证张议潮史迹时认为,张氏并未控制河、渭、廓、鄯等州,“张议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为张氏与相关吐蕃势力同盟关系的体现。笔者从陆说。参见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B31《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B32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79页。
B33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83—215页。
B34参见P.2762+S.3329+S.1616+S.6973+S.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B35《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14页。
B36参见冉永忠:《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部落制度与封建关系研究》,西藏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6—54页。
B37P.3551《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载:“……则有清河张,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亦载有:“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参见《册府元龟》卷九八〇,第11354页。
B38P.3554《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序》云:“昔尚书曾赴逻娑(逻些),引道神人,祭水河边,龙兴紫盖,池现圣鸟,气运冲星,阵上回风,击添雷电。”
B39《全唐诗》卷二七“杂曲歌辞”,第381页。
B40《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四年三月条。
B41《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B42S.367《沙州伊州地志》载:“伊州……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
B43P.2962《张议潮变文》载:“敦煌城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即望沙州而返。”
B44《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B45参见刘进宝:《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郝二旭:《唐五代敦煌农业专题研究——以敦煌写本文献为中心》,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5—110页。
B46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B47参见杨秀清:《张议潮出走与张淮深之死——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新探》,《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B48《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僖宗咸通八年二月条。
B49根据对相关敦煌文献的考证,学界对张淮深之死是否系张淮鼎势力所为仍存异议,但基本认可张淮深之死系张氏家族内部权力斗争所致。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78—88页;邓文宽:《也谈张淮深之死》,《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也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昞麟:《张淮深之死疑案的研究》,《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B5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八月条中称天宝年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B51藤枝晃著,刘豫川译:《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上、中、下),《长江文明》,2011年第1期;2012年第2期;2013年第1期。
B52参见孔令梅:《敦煌大族与佛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31—163页;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B53参见S.5835张议潮所抄《大乘稻杆经》尾题。
B54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B55关于敦煌佛教信仰的民俗化及其表现,参见马德:《从敦煌看佛教的社会化》,《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李正宇:《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