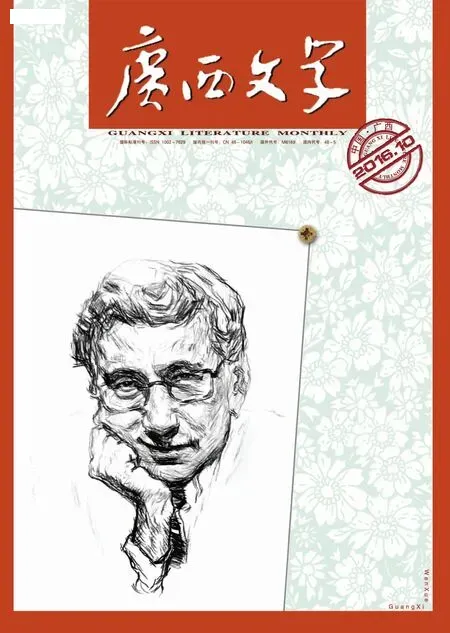江南有苦槠
许含章/著
起得很早。
我入住的小客栈,是一幢新建成不久的农家小楼,深夜十二点多,还有散客入住就很吵。住在隔壁的一对上海小夫妻,似乎第一次到婺源来,特别兴奋,一直到天亮,都在不停地说啊说。天空亦晴亦雨,是江南独有的气象,我一个人前往婺北,进入清华镇时,暮色已经涌上来了。清华位于星江上游,鄣公山南麓,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始建婺源县,县治就设在清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清华得名于“清溪萦绕,华照生辉”,想来初阳升起的一刻,无限美好。
和所有的徽州古镇一样,清华也有一条老街,窄且悠长,两边是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种强烈而鲜明的视觉符号。因持续发酵的旅游热,老街的居民,正在争相翻新自己的老屋或建造新屋,然后挂上客栈的牌子——客栈的名字,都很古雅。我此行到婺北的清华来,特为拜谒朱熹手植的一株老树,要知道在整个婺源县境,有关朱熹的遗迹已经不多了。晚饭前的时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相比较江村、篁岭、晓起、汪口等大热的旅游景点,清华显然有些冷清了。“来找一棵树?”人们很惊诧:“找它干什么!”他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我。然而从镇东到镇西,从老街到新街,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一棵树。我很困惑,在婺源县城,明明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镇有一株与朱熹有关的老树,怎么就没人知道了呢?
街灯渐次明亮,小镇的灯火,似乎更像灯火。城市的夜晚,因为灯火通明,失缺了夜的意味,有些地方,比如CBD、万达广场等,甚至和白昼差不多。所以星空也不如乡村璀璨,更没有所谓的“辽阔”。小镇的清晨会是什么样呢?在隔壁的沪上私语中,我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清华的清晨,没有我所期待的星江日出,江边的柳冠上,有晨雾缭绕。然杨柳依依,流水潺潺,有妇人在河埠头洗涤,岁月静好。
婺源旅游,最热的是婺北旅游,思溪、延村、长滩、严田古村、彩虹老桥、虹关、吴楚古道、大鄣山峡谷等,都在城北一线,所以春季的婺北,和春潮一起不期而至的,是汹涌的人潮。没想到婺北的清华,居然如此安静,徜徉江边,感觉好极了。后来,太阳就跃出了地平线,镇子一下子明亮起来,远山如染,近山如黛,河滩上草色青青,河面上有粼粼波光闪耀。镇子那头的老街,开始有喧腾的声响传来,旅游团的大队人马,到了。
据说历史上的清华老街,绵延五里,这在岳飞的《花桥》诗中有所描述:“上下街连五里遥,青帘酒肆接花桥;十年争战风光别, 满地芊芊草木娇。”但也有人说,岳诗所写“花桥”,并非清华老街,而是婺源县赋春镇甲路乡甲路村,昔日甲路有石桥一座,东西两边各有一条长街,街上饭庄酒肆接连,甚是热闹。赋春镇位于婺源县西南乡,东毗中云镇,南临许村镇,我刚刚去过。甲路村的凉亭,至今保存着岳诗的真迹,所以《花桥》到底是写哪里,我糊涂了。而且他为什么要把石桥写成“花桥”呢?是因为石桥的护栏上雕满了花朵?
据说这是岳飞在南宋绍兴元年,征战途中路过甲路时写下的一首诗。岳飞于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先后平定了游寇李成、张用、曹成和吉州、虔州的叛乱,绍兴四年(1134年)又收复了陷于伪齐政权的襄阳六郡,正是声名煊赫之时,当他从武昌渡江北上,重返抗金战场时,曾对幕僚放言道:“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就是这期间他途经的婺源,所以读他的《花桥》诗,字里行间很是意气飞扬。尽管岳诗所写,不是清华的老街花桥,但清华老街依然人涌如潮。有资料显示,清华老街是婺源一条最长的老街,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代——比岳飞的年代要早多了。过去,清华老街号称“五里长街”,就是现存的青石街巷,也仍有三里多长,两边俱为清代建筑。据说当年的老街下街,有很多家瓷器店,三五步一个窑货铺;而上街多为百货店、南货庄、茶叶店或客栈,处处青帘酒肆,从这一点上看,又与岳诗有很多地方相契合。而且当地人称“彩虹桥”为“上街桥”,另一座桥为“下街桥”,不是更加印证了岳飞“上下街连五里遥,青帘酒肆接花桥”的诗句吗?
因为一直找不到那棵与朱熹有关的树,我有些焦躁。是樟树?杉树?银杏树?问我我也说不知道。“那就没法找了!”镇上的人说。又进了很多铺子,问了很多人,仍然没有人说得清楚,小吃铺老板不高兴道:“你一大早跑了来,就为了找一棵树?这不是耽误我做生意吗!”
我发现,在朱熹的家乡婺源,除了少数乡村文化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而且若不是为了吸引游客,岳飞诗也未必有人知道。生活一天天变化,普通人的日子,充满了琐屑和辛劳。没有人知道朱熹,这也很正常,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柴米油盐比几百年前的朱夫子,更加重要。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然而却不死心,继续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希望能找到点什么。这是清华呢,一千多年前的县治所在地呢,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拦住一位老人,让他想一想,在清华,是不是有一棵什么树,和什么人有关呢?或者和历史……
“噢,知道了!”老人不待我说完,突然大声道:“你说的,莫不是那棵苦槠树吗?嗨!你也不早说!”
重新回到了镇东,回到了此前两次路过的一扇大门前,辗转找到了守门人,总算把大门打开了。一眼就看见了那棵树,郁郁葱葱,兀自沧桑,几乎覆盖了大半个院落。树身的标牌上,写有这样的文字:树高约十九米,胸径二点四七米,冠幅十五平方米,壳斗目、山毛榉科。但我来不及接纳这些植物学意义上的文字,因为我瞬间感受到了它苍劲的覆盖——似乎整个院落,都充满了它的呼吸,和泼墨一般浓重的苍青色。
是苦槠,这是一个陌生的树种,之前它从未在我的视野中出现过。
不过它和朱熹无关,它比朱熹要早得多。
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婺源历史上这个反复出现的年份,又再次出现了。据婺源相关的史志记载,这一年婺源建县,治所设于清华镇,县衙为胡氏宗祠所改建。那时祠堂的大门前,就站立着这株苦槠树。不管它那时多高多大,至少在大约一千三百年前,它就已经存在了。作为婺源建县的标志,这株“唐代苦槠”,见证了婺源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一刻,它真的是一株非凡的树。
苦槠的花期在每年五月,十月果实成熟,坚果呈深褐色。苦槠是不能直接食用的,通常要在太阳下暴晒,待果壳崩裂后,露出坚硬的白色果肉。之后要用清水浸泡,再磨成“苦槠浆”,倒入旺火铁锅,边加水边搅拌,直到凝结成胶状——这就是传说中的“苦槠豆腐”,之前我曾多次听说过。“苦槠豆腐”原是贫瘠山区对粮食短缺的一种补充,近年来因其“纯天然”,在旅游餐桌上持续发烧。
然则为什么叫“苦槠”呢?是因为它的籽实略带苦涩吗?在植物学上,它的名字就叫“槠”,并未加上“苦”的形容词。北方农村也有一种树,叫作“苦楝树”,植物学名就叫“楝”,但老百姓就叫它“苦楝”,是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苦了?这让我想起了《呼啸山庄》里的一句话:生活就是含辛茹苦。与苦槠相对的是甜槠,同属“壳斗科”,似乎是生长在岭南的常绿大乔木。甜槠的果实叫甜槠子,霜后坠地,在福建邵武、泰宁一带,“以其子为果品,磨之作冻”,想来也如“苦槠豆腐”。但甜槠是可以生吃的,其味甘甜;加盐炒熟后如北方的瓜子,是客家人冬闲时的零嘴,而磨粉蒸糕,是极有特色的地方小吃。
据说苦槠是江南的特有树种,号称标志南北的“分界树”,而到了江北,就无法存活。它的寿命特别长久,叶子特别绿,也就特别能抗“氧化”,在江南的低山丘陵间,千年以上的苦槠触目皆是,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一株。院落里空无一人,槠冠上缭绕着晨雾。当年,当它的生命,第一次昂扬在胡氏宗祠的大门前时,它并不知道自己能够站立多久——而今天,一千三百年过去了,胡氏宗祠早已荡然无存,它却仍然枝繁叶茂。
徽州的胡氏异常复杂,外人根本搞不清楚。蔡元培先生曾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说:“适之先生出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声明他与绩溪18世纪以来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著名学者胡培翚并不同宗。资料显示,仅绩溪胡氏就有四支,分四次迁入徽州,因此又有“金紫胡、明经胡、遵义胡、尚书胡”之分。“汉学”又称“三胡礼学”,是清乾嘉年间绩溪金紫胡氏一支经学流派,以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为代表,因精于“三礼”,世人尊为“三胡礼学”。清华胡氏属于他们中的哪一支呢?抑或哪一支也不是,而是属于另外的胡氏宗族?
院子里仍然空无一人,墙上挂着“婺源县财政局清华财政所”的牌子,因为是星期天,办公室的门都上了锁。唯有那株苦槠孑然独立,太阳下显出苍黑的颜色。婺源有很多古木老树,无不经历了数百年风雨,以它们的坚强与柔弱,洞穿人间岁月。
进镇的旅游大巴越来越多,人声越来越喧闹。都是奔着镇子那头的彩虹桥去的,而历史上,彩虹桥名叫“上街桥”。没有人知道这株老树,没有人知道唐代官署,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来过多少人,发生过多少事,没有人知道在2016年4月间的一个早晨,我对这株树的寻找。
江南有苦槠,千载也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