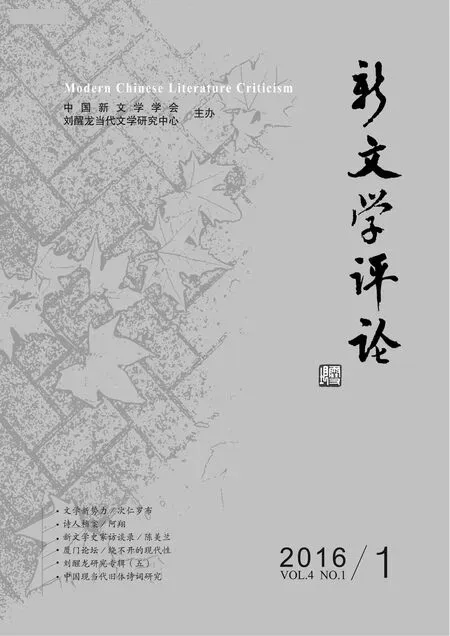奇境:浅谈阿翔的“拟诗记”
◆赵卡
奇境:浅谈阿翔的“拟诗记”
◆赵卡
作为一项神话修辞文本的练习功课,阿翔为他的诗歌建立了一种奇境,作为克制的非连续性的幻觉的集成,呈现了即兴的特点。“拟诗记”就是我们的爱丽丝,它将引导我们进入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拟诗记”,我觉得既是一种奇怪的命名,也是一种奇怪的命名方式,“拟”,在阿翔的写作谱系里可作“模仿”解,“拟诗”,用诗歌的形式模仿诗歌,抑或用诗歌的形式反对诗歌,其真实企图难免让人生疑,但真正隐藏在字面后面的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怀疑精神,好像还有一点自我清算的意味。也就是说,阿翔先对自己的精神动机起了疑心,他对自己既往的文本可能暗含偏见,又对当下的写作持不信任态度,故“拟”之以迷惑阅读者,这显得太狡猾了。重要的,还有紧跟着起注释作用的小标题,这些小标题看起来更像是对主标题的偏离,不妨可视作阿翔在诗中为建立奇境世界准备的建筑材料。
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将在本文中谈到的阿翔可能是一个犹疑的有点自我否定意味的阿翔,在幻象中建立精神秩序的阿翔,缅怀时间的阿翔,即景的和自我约束的阿翔,偏离词义对世界的表象发表意见的阿翔,最后深入深邃现实黑洞里的阿翔。总的来说,我目前读到的仅仅22首“拟诗记”是一个彼此没有关联(除了纳入在主标题的统辖之中)的神话的能指,如同臧棣的“丛书”诗,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诗人才会收手,这是一种将单首诗歌无限裂变为复数化的努力,暗藏了宏伟浩瀚的史诗性写作的抱负。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神话的能指以含混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既是意义又是形式,就意义而言,它是充实的,就形式而言,它是空洞的。”对照检索阿翔的22首“拟诗记”,你会发现,用一个声音说话( speak with one voice)确是阿翔一段时间以来诗写的显著特征。类似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从容不迫的调用词语,没有一个句子不拥有一种相似的形体,懒散的语气,随手即可拈出几例:“从侧面看起来,排在我们之前的人,神色已经平静。”(《拟诗记,松开》)“早些的时候,我努力给拼音生活增加粗粝感,我是说。”(《拟诗记,反隐忍》)“这是在夏日,九月是中年的酷热,躲藏白发,躲藏流动的人群。”(《拟诗记,应和》)等等。甚至包括了句子的长度、节奏感、速度,仿佛连字数都是经过仔细计算过的。如果把每一首诗通读一遍,你会惊讶地发觉,文本空洞一如西川,这也是新古典主义诗写的流弊之一,但它却保留了诗意的骨架。
如果我在此谈到了“空洞”,希望不会引起读者的狭隘的误解,我谈到的“空洞”其实是出于对诗人性格中某种神秘主义嗜好的猜测。怎么说呢,其实这是阿翔对叶芝(所谓的通灵术爱好者)诗艺的秘密传承,因为叶芝认为诗人性格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会为他的诗歌带来隐喻。如果你在阅读阿翔的“拟诗记”中不能发现这些辉煌的隐喻,我想你一定站在了阿翔的对面,也就是站在了形式的反面。阿翔的形式即阿翔的神话修辞术,这是他的真诚,犹如艾略特在谈到布莱克的真诚时说的:“然而即使没有什么东西能妨碍他的真诚,另一方面也存在袒露的人会遭到危险的可能。他的哲学,正像他的幻象、他的透视、他的技巧一样,是属于他自己的。”来看这句子,多么辉煌,如同神启一般:
对日常生活的日复一日浑然不觉
炎热的夏天看起来还没有结束。
异常于月亮昏暗,我隐藏暗褐色的疤痕
长时间的低调
草丛淹没腐朽,孤单更加锋利
城中的喧嚣徒然消失,唯有漫天星斗与之比肩
这一天宜于远离,即使如此,也要经过呕吐和堕落
在梦中才能返回,就像我坐着火车去天堂。
——《拟诗记,远离论》
阿翔和所有的诗人区隔在于,他以优雅和恭顺博得了读者的好感,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示弱的品质,尽管我知道示弱是我们竭力避免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到阿翔固执地局限于一种沉郁的调子,我们不得不考虑阿翔这是不是出于风度的体现。作为一个压抑自我膨胀的,热衷于未完成状态的诗人,阿翔更愿意回到内在的和独有的自我,他保持着一种谦卑的谨慎,不让词句任意放肆。但你不能无视他的深不可测的想像力:
不是无路可走,的确不是。是沮丧的手势
让你低调,即使在林子的隐蔽处
纵有瞒天过海的本事,暗影仍然寸步不离,这也不是什么错。
当孤独遇到了镜子,你被缺席,不在现场
镜子咣当一声破碎,这些都不存在,映不出你辽阔的内心。
岂止黑暗,哪个都不是,就可以看见漩涡
一群吃盐的铜马,慢吞吞的,它们算得上见多识广;而且
厌倦了旁观者的青春
——《拟诗记,“不是……”》
这是他和世界的对话,世界是一面“镜子”,“当孤独遇到了镜子”,“镜子咣当一声破碎”,阿翔所建立的奇境,打碎的岂止是博尔赫斯的一再重复的虚构。这22首“拟诗记”几乎指向了同一种想像,神话在这里是如何成为神话的?那么我们绝不能回避阿翔诗写的意义和形式,这不是一个靠对细节的持续瞩目而获得意义的诗人,也不是通过联系词与物的上下文关系与世界建立秘密沟通的诗人,罗兰·巴特认定神话的特性即“将意义转换成形式”,那么我们不妨认为阿翔的“拟诗记”就是将意义转换成形式的诗篇。当我们看到,在他的22首“拟诗记”里,阿翔断然抛弃了依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去描述生活,而是将生活添油加醋篡改得面目全非,那是一种只有经历过才能追忆描述出来的生活,我们反倒情愿把它视作现实一种。我有时想,“拟诗记”是不是阿翔的一种自传式书写呢?他建立了某种神话修辞文体,奇境式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系列怪癖,超越了既往的偏执,夹杂着似是而非的评论。
阿翔的“拟诗记”不是那种昂扬着的调子,也不是俯首倾诉式的低语,他总是自语,这种自语不是说给读者倾听的,而是返回了他的诗篇内部,像极了年轻时的普鲁斯特。阿翔诗写的秘密之一是对标题的珍视,因为标题可以说是一首诗的灵魂,如“松开”、“反隐忍”、“应和”、“未完成……”、“诗歌史”、“……迟疑”等等,这些标题都隐蔽了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如果回到这些词语的内部,就会发现至少有一种修辞是用来荒废的。22首“拟诗记”如果分开来阅读,那么,每一首都拥有一个声音,最后汇入一个更丰富的一个声音里,但它们又是如此迥然有别:《拟诗记,松开》缅怀了孤独,《拟诗记,反隐忍》对抗了梦境,《拟诗记,……迟疑》善意地对友人张尔给予了小小的讥讽和赞美,《拟诗记,致——,或伪史诗》是对某一首诗的致敬,《拟诗记,几易其稿,小插曲》则像个衰老经……诸如旅行记、唱和、挽歌体、讨论术、隐晦的色情等不一一列举。布鲁姆问:“是什么让一首诗优于另一首诗?”这个处于读诗的艺术核心位置的问题在阿翔的“拟诗记”里是无效的,毕竟“拟诗记”的22首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speak with one voice)。
有时候多读两遍阿翔,忽然发现阿翔的诗篇里偶有自怜,但更多的是自恋,又有点笨拙,这有点和布莱克类似,也应了艾略特之言,“因此他就比一个艺术家所应该的那样更加着重他的哲学。这就是使他偏激、使他倾向于不拘形式的缘故”。你看:
我忘记了钥匙在锁中被卡死,木头椅子在技术上长出蘑菇
青虫身子过于柔软
与一下午的草绳格格不入。
——《拟诗记,10月2日,肥美语》
如果我把他指认为唯美主义的奥斯卡·王尔德,用词自信且精巧过度,大概阿翔也不会反对。他的高蹈的姿态使得他写下的诗句熠熠生辉,特别是有些句子更像是预言、箴言或谶语。我敢肯定这是一个接受古典传统并试图无限扩展传统的诗人,又是一个以暴力手段劫持了现代诗人诗写精华的诗人,他们一起搅和在了阿翔的诗篇里:莎士比亚、歌德、叶芝、特朗斯特朗姆、博尔赫斯、西川、余怒,甚至广子。严格地说,无论阿翔以往的诗篇还是我现在观察的“拟诗记”,均不是一种看上去有难度的写作,但却是极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幻象性和精确性的统一的写作,语调舒缓,富于节奏感,其魅力如本雅明评价普鲁斯特,“仿佛是其使命让他不得不如此”。“随后,这种神秘化和仪式化简直变成他人格的一部分。”阿翔那种抵御反常病态的持久的理想主义孤独感,恰是我们目前的好奇心所热衷的。
[作者单位:包头市敕勒歌民族食品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