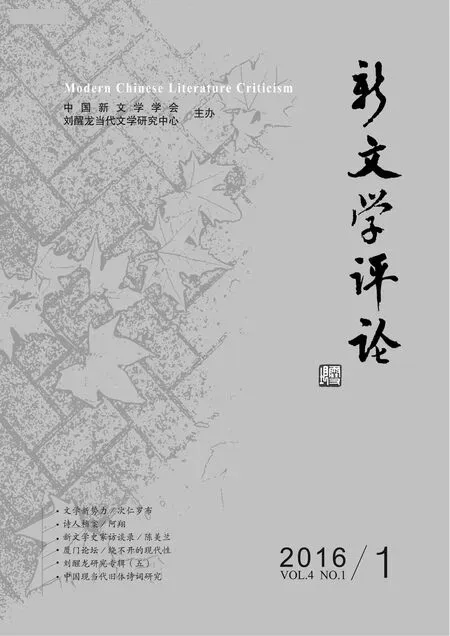当代藏族生活的原生态书写者
——次仁罗布论
◆王大鹏 张丽军
当代藏族生活的原生态书写者——次仁罗布论
◆王大鹏张丽军
西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历来都是一个充满未知的神秘的地方。次仁罗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以藏族人的心境和藏族人的视角,运用新颖的叙事方式,结合西藏的神奇的传说,通过描绘西藏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来展现西藏文化背后的意蕴以及自己对于人性、命运、人生价值的思考。次仁罗布这种对西藏的充满原生态的刻画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他的笔下,神秘的西藏虽然依旧充满神奇,但是已经变得非常的“接地气”。
次仁罗布用充满灵魂的语言来描绘神秘的西藏,在这里他颂扬藏族人民的敢于追爱、信仰坚定、勇于担当、对爱执着坚守的优秀的品质;他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自己对于藏族文化营造的多彩世界的热爱,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次仁罗布在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对于藏族文化发展的担忧与深刻的思考。次仁罗布通过简单的小故事来描绘人生所必须经历的爱、苦难、生死等,不断思考人性、命运和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叙事形式的新探索
藏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相似的。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以降边嘉措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者的叙事方式多为一种带有革命性的叙述,讲述西藏人民以前遭受的苦难和解放翻身之后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与期许。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者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结合藏族的独特的民族传说,叙事方式渐渐地开始变得多元化。次仁罗布也在不断探索关于西藏文学的创作与叙事方式。
次仁罗布的叙事手法是非常新颖独特的,是多个视角、多个角度的讲述。他的小说中经常穿插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以笔录加访谈加回忆的形式,插叙、倒叙灵活运用。在《阿米日嘎》中,次仁罗布以警察的询问做笔录的形式来介绍故事,讲述了“我”作为一个警察去调查一件种牛被害的案件。整篇文章主要是由原告、被告、证人的询问笔录组成的,层层推进,悬念迭生,就像解密一样,带给人一种神秘感,吸引读者去探寻结局。文章最后说“我”断完案子之后出于善心也买了贡布家牛的牛头,在车上似乎和牛的灵魂进行了交流,带有魔幻的色彩,“少数民族对动物的温存、宽厚与怜爱源于对所有生命样态的理解和尊重,源于生存生活上与他们的密不可分,也源于动物本身所具有的通透灵气”,体现出作者对于动物的悲悯之情以及对藏族人民之间那种宽容心态的敬意。在《言说之惑》中,“我”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记录中的英雄加布,从不同的人的嘴里得到关于英雄加布的不同的说法,原来的英雄形象变得让人疑惑。次仁罗布打破了英雄的叙述模式,还原了一个英雄形象在普通人眼里的面目。作者在这里展现了关于英雄的看法和对于英雄真实的疑惑。英雄并不总是像人们说的那么高大,人们对英雄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在《兽医罗布》中,他更是直接用魔幻的手法将“我”与兽医罗布的灵魂交织在一起,“我”经常梦到罗布,甚至有时候和罗布的妻子同时梦到罗布。通过罗布的城镇和牧区的两个妻子来讲述罗布的一生,两个妻子都给予罗布很高的评价来表现罗布的善良。“我”与罗布最后的相遇是在幽暗的巷子里,更是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化腐朽为神奇,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除了打破时空界限的结构主义叙事策略和象征隐喻的艺术技巧外,还存在许多。而将梦境与现实混同,以预示及征兆相互铺垫、相互映照、相互阐释,便是其中重要而常用的一种。”他的这种多视角、多角度的叙事,与魔幻的手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更加全面地展现出来,可以给人更加全面的认知。
次仁罗布的小说标题也充满着象征意味。《尘网》中的跛子郑堆一直活在一种由“被爱”和“求爱”所交织的“尘网”之中,从被求爱的岳母达噶灌醉以致失身到遇到漂泊异乡的泽拉,再到最后娶酒馆的女人为妻子,跛子郑堆一生没有走出这个用“爱”编织的网。虽然郑堆最后突然死去,但是他什么都不惧怕了,也并不后悔来到这世界上走一遭。作者在这里用“尘网”做标题可谓是匠心独运,尘网象征着尘世间的羁绊。只有有了这种羁绊,人来世上走一遭的存在的意义才会更加的独特。就像是钱锺书以“围城”做标题一样,次仁罗布在这里用“尘网”来形容人与人的爱的纠葛。这种纠葛没有人能够逃脱它,那就正视它,拥抱它。《放生羊》中的“羊”已经不再是生物意义上的羊,而是“我”的妻子桑姆的化身。死后一直不得转世的妻子托梦给“我”,让“我”多祈祷,好让她及早转世。放生羊也就是让妻子的灵魂得以转世,文中写“我”为放生羊所有的付出也表现出对妻子的爱。作者也非常善于用比喻的修辞,“雪山融化后从山上流泻下来的溪水,犹如一颗颗碎裂的玻璃珠子,明亮又晶莹”,将溪水比喻成碎裂的玻璃珠子,将洁白的牙齿比喻成海螺,将道路两边的绿比喻成奔腾的江河,狂泻而去,用曲郭山上的雪来隐喻日益变化的自然环境……表现出次仁罗布丰富的想象力。“意象作为兼备表象与意义的审美符合体并不是某种意义和某种意象的简单叠加,它在生成过程中经历了作家的选择和过滤,不但体现出作家本人的才学和意趣,更多程度上还与作家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属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他用这些新颖的形式和生动的意象来介绍西藏的风土人情,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来展现西藏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二、对藏文化的描绘与思索
次仁罗布在结合藏族普通人民的普通生活所构建的艺术世界里,充满宗教色彩,极具民族性。藏族是一个全民都信仰宗教的民族,所以宗教文化、宗教意识也就渗透到了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藏族文化是一种以苯教为基础,佛教为指导,并吸收了汉文化和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藏族文化的灵魂是佛教哲学,因而种族哲学的基本命题与佛学的基本命题是一致的。”次仁罗布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藏族文化的热爱,他的小说中也包含着佛教的哲学以及他对这种哲学的思考。
在次仁罗布笔下,绵延的雪域高原、朝圣的寺庙、平凡却不寻常的八廓街头……都在上演着一段段精彩的故事。次仁罗布把自己对藏族多彩世界的热爱与担忧融入这些景物描写中,营造出一种特定的氛围,而且往往结合藏族独有的传说。在《神授》中拉宗部落的亚尔杰经历了“在草原—离开草原去拉萨—重回草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景物描写也从“晨曦微露,远山正脱掉黑色的幕布,把碧绿一点点地透露”到“林立的高楼压迫着心头,笔直的马路,把大地切割成一块块,让我胸闷气胀,”再到“摩托车的声音响彻在草原上,这种尖锐的声音令人可怕。它把一个个牧民点甩在了后面,像格萨尔王的箭一样射向色尖草原”。在这个过程中经“神授”而开始说唱《格萨尔王》的亚尔杰在草原上是欢乐的,他有着真神的陪伴;进入拉萨后感觉到沉闷,因为真神大将好像离他越来越远,因此甚至想到过逃离;重回草原后一切变得亲切,一切又变得陌生。草原上已经很少有人像以前一样喜欢听他说唱《格萨尔王》。作者通过写一个说唱艺人的说唱过程表达了自己对于藏族文化的热爱,同时也为藏族说唱艺术的逐渐衰微感到惋惜。在《曲郭山上的雪》中,作者借贡觉大爷讲述曲郭山上的雪正在逐渐地消融,而经书上说“曲郭山上的积雪融尽,也就是人类的末日”。曲郭山上的“雪”隐喻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引起人们恐慌的不是那张美国讲述2012末日的DVD,而是近在眼前的曲郭山上的雪。寄予了作者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担忧。
次仁罗布的小说中有许多的藏族传说。一方面作者借传说来展现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揭示人性的良知与愚昧。《传说》中的“金刚杵”是霞帝寺活佛送给强久老头的,可以“刀枪不入”。金刚杵的获得是因为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强久老头归还霞帝寺镇寺之宝金刚橛,金刚橛在传说中的萨迦班智达和外道者争辩中显现过它的威力,在“人寿十岁”与康巴人的决斗中显现过威力,但是佩戴“金刚杵”的小伙子却因为见义勇为被人用木棍打死了,强久老头也只好无奈地说:“原来是遇到了不洁净的东西了。只可惜了我那个金刚杵。”金刚杵在传说中本是一个吉祥的物件,是正义和无畏的代表,但不是有了金刚杵就能够刀枪不入。虔诚地去坚信正义和无畏是正确的,但是金刚杵不能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保护。在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与藏族信仰的完美的结合展现出了藏族文化的风采,表达了作者对于藏族文化的热爱。在次仁罗布的小说中人们虔诚地祈祷,在《放生羊》中“我”为了妻子的转生祈祷,带着供灯、哈达、白酒等去转林廓,“一路上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信徒拨动念珠,口诵经文,步履轻捷地从我身边走过。白日的喧嚣此刻消停了,除了偶尔有几辆车飞速奔驶外,只有喃喃的祈祷声在飘荡。唉,这时候人与神是最接近的,人心也会变得纯净澄澈,一切祷词涌自内心底”。藏族人民转圣山、转圣水、转寺庙,边磕长头边诵经,他们相信通过转山、转水和诵经,便可以得到神灵的祝愿,可以消灾祛病。作者在这里既描写了藏族人民对信仰的虔诚,也表达了作者对于虔诚信仰者的深深敬意。
三、对藏民人心人性的思考
在新颖的叙事形式背后是次仁罗布对于人心和人性的思考。“文学是人学,它更多地注意于人的灵魂和思想感情的挖掘,它的伟大功用就在于塑造了对人民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人物性格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次仁罗布通过描写藏区人民的普通生活来表现自己对于“爱”、“幸福”、“仇恨”、“苦难”、“生死”等的深刻思考。
次仁罗布对于幸福和对爱的追寻有着自己鲜明的见解。《念珠》中的阿酷啦听说有好心的邻居给他介绍过女的,希望他再娶个老婆。他耐着性子听人讲完,最后用这句话来回绝他们:“扎桑一直在我心里,你就不用劳神了。”爱是需要执着去追寻的,爱一个人一时是简单的,最难的是当激情褪去回归平淡后一生的坚守。阿酷啦做到了对扎桑爱的坚守,也表现出作者对于爱的永恒、爱的执着的敬意。《尘网》中跛子郑堆临死前变得一点都不惧怕,因为他坚信“有了爱什么都不惧怕了”。郑堆的一生的爱分为三个阶段:强迫下的爱、机缘巧合的爱、主动地去爱,也在表达着作者对爱的追寻的态度。《秋夜》中嘎巴对梅朵说:“我这生没有过大把的钱,所以不知道。可我觉得我们很幸福,我们相互相爱。”有钱并不一定能够买来幸福,次塔虽然挣到了钱,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作者在这里表达了自己的金钱观、幸福观。幸福是有心爱的人陪伴着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就像嘎巴和梅朵一样。虽然嘎巴家没有像次塔一样有钱,但是嘎巴与梅朵相亲相爱,而次塔有钱后经常不着家在外奔波,次塔的妻子尼玛独守空房。嘎巴一家远比有钱的次塔要幸福得多,就像嘎巴说的“有钱难买幸福”。
对于苦难,不断地与命运做着斗争,想以此来摆脱命运的安排,但到最后还是被命运所无情吞噬。这虽然有种宿命的感觉,但也就是与命运的不断抗争才彰显出了生命力的坚韧。在《雨季》里的旺拉经历着亲人相继死去的苦难,与余华的《活着》里的福贵不同的是,福贵是一个一直在被动接受命运的人,是一个顺应着时代发展的落魄少爷,而旺拉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农民。旺拉始终在与命运做着斗争,当泥石流爆发时,他从短暂的恐惧中惊醒,拼命地逃生。在大儿子出生后,他感到“我觉得这个孩子会使我们家结束隐晦的日子,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将来”,并开始为这个目标努力。他最后还是没能救回自己的爹,但他一直是一个有着积极生活态度的人。他把强拉老爹的遗体背回家后,更大的泥石流向这个小村庄袭来。当苦难来临,已无处躲藏时,旺拉并没有感到绝望,而是坦然地面对。“旺拉真切地看到菩萨眼里涌满的泪水,那泪水滴答滴答掉落到他的心头,他把所有的苦难都给忘记了。”福贵最终一个人活着去讲述生命的悲苦,而旺拉最终死于夺取家人生命的泥石流更诠释着生命的坚韧。通过描写西藏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作者展现了他们生活的悲苦以及面对苦难时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命存活意识。
在《杀手》中,终其一生寻找自己的复仇对象的康巴人,在看到自己的仇人已经达到了垂暮之年时,放弃了复仇行为,也放下了复仇的心念,重新踏上了人生的征途。他虽然是哭着离开的,但是他内心的复仇的火焰已经熄灭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放下了复仇执念的杀手得到了最终的解脱。故事的最后由一个听了杀手故事的司机在梦中帮助康巴人复仇结束。“醒来外面阳光灿烂,白花花的太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作者在这里传达出了藏族人民的宽容的心胸。
在《曲郭山上的雪》中,作者通过贡觉大爷之口阐明了自己对于生死恐惧的观点,那就是:“没有末日哪有重生!别对死亡心存恐惧,要感谢死亡阴影的笼罩,它使我们的心远离了迷乱,看清了内心真实的需求。”就像人们在扔出硬币的那一瞬间就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样。在嘈杂的人世间,人们往往被种种诱惑环绕,无法看清自己内心的真实的需求,但是当人们面临死亡的笼罩时便会真正认清什么是诱惑,什么是自己真实的需求。当2012的世界末日谣言流传开来时,村民们不再去春播,贡觉大爷将自家的牛羊送给了泰雀寺,扎罗将自己的羊全部放生,朗追甚至把自己用来建造新房子的木料和石材捐了出来为村子修一座转经塔,给村民们提供一个积善的场地。村民们自发地去修建转经塔,没有任何报酬却仍然干得很卖力气。一方面写出了村民们在面对谣言时的愚昧,一方面传达出生死恐惧的价值意义。这与藏族全民信佛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佛家有云:“今生种下恶因,来世取得恶果;今世种下善因,来世收得善果。”而村民们这些看似临时抱佛脚式的种善因是不合理的,趁末日来临之前赶紧饮酒作乐去享受更是荒谬的。贡觉大爷要“人们坦荡荡地迎接死亡,对死亡的修行就是寻找解脱之路”,“站在一定的领域之上批判破坏自然平衡的行径,对待死亡,全然没有惶恐与拒斥,只有安然与知足,这是由于宗教信仰带给他们的抚慰与承诺,在民族文化的整体氛围下,形成了对死亡的特殊理解”。面对死亡,我们才能真正明确地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才能够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四、个性且有生命力的表达
小说的魅力来自用精妙的语言结合有生命力的表达方式,来展现平凡普通的生活背后的深刻寓意。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快餐式的文学给人以短暂刺激的千篇一律的语言描写味同嚼蜡,中国人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个性意识逐渐泯灭,主体意识逐渐消失。但是在思想逐渐多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我们的个性意识。次仁罗布在藏族文学的创作上不断地开拓创新,创作出了独具个性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时而幽默,时而深沉,时而随性洒脱。
次仁罗布的语言非常有个性而且富有生命力。他用幽默而朴实的语言营造出西藏独有的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氛围。次仁罗布让自己文章中的语言拥有了灵魂,就像在《阿米日嘎》开头,“开阔的前方是整片的沙棘林,她们等待我穿越过去,灰色的枝干远远地向我招展。要是春季我倒乐意从这里过,沙棘枝叶上细碎的黄花,在阳光下像金子一样熠熠发辉;可是初冬一片萧瑟,让人无端地提不起高兴劲来”。这些描写荆棘丛的语言就像拥有生命力一样,让人仿佛真正看到了荆棘丛。写雨:“雨点密密麻麻地从空际砸落下来,炸裂在强巴老爹褶皱的脸上,碎裂成无数个细小晶亮的水珠,它们经过交融,又汇聚在一块,顺着强巴老爹的面庞淅淅沥沥地滚落下去。”雨是从天际“砸落”下来的,然后“碎裂”成小水珠后淅淅沥沥地“滚落”下去。“砸落”、“碎裂”、“滚落”三个词将雨下落的过程分解成三部分,表现了作者语言的细致。在形容秋天的叶子的时候说叶子“不时发出脆脆的呻吟”。叶子怎么会发出呻吟?但是仔细听,秋天将要坠落的叶子在干枯的时候是会发出响声的。次仁罗布在这里将这种声音加以拟人化的处理,富有感情,很有感染力。而且次仁罗布十分擅长运用叠音词。“眼泪簌簌掉落,干瘪的嘴唇紧紧抿着。疼痛稍稍减轻后,夏辜老太婆这才想起,那隆隆的喉骨节是她的丈夫传给顿珠的。”“片片雪花从空中轻轻飏飏地落下,冷风飕飕地扑打在行人的脸上,让人牙齿咯咯作响。”这种叠音词的巧妙运用不仅将动作形象化,而且更加具有节奏感。
次仁罗布强烈的主体意识则体现在他对于细节的精准把握和精彩描写,像是把镜头放慢一样,甚至具体到每个动作的每个反应。在《德剁》中描写嘉央德剁被枪杀的一瞬间的刻画:“弹头‘噗’地穿破袈裟,抖落了上面的灰尘,钻进了嘉央的体内。一阵巨大的推力,在嘉央的体内绽放。”这种将动作放慢,将动作具体化、细节化的处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就是巧妙地利用对环境的细致的刻画来烘托人物,营造出特定场景的气氛。在《界》中查斯为了能够永远将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不惜将毒药导入酸奶中。但是当真正要下毒的时候,“额头上沁出汗珠。她的胳膊伸过去,焦黑的手掌撕裂了阳光,弯曲的黑指头蠕动着,解开了褡裢的结。小木桶盛满酸奶,像个乖顺的婴儿,安静地躺在褡裢里,恐惧地凝视她。突然,查斯的手抖动,急忙捂紧褡裢的口,胸口压在上面”。作者在这里通过动作描写来表达查斯内心激烈的斗争。作为母亲,查斯想要从小就被领走出家的儿子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面对已经笃定皈依佛门的儿子时,她是那么的无助与无奈。作者在这里写出了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和这个社会带给母亲的深深的痛。
次仁罗布的作品将新颖的形式与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仅给人带来一种神秘又新鲜的感觉,而且更能够让人体会到文章背后深刻的意义,渗透着对于人性和人心的思考。
注释:
①吕豪爽:《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②吕豪爽:《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③吕豪爽:《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④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⑤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⑥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⑦吕豪爽:《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0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