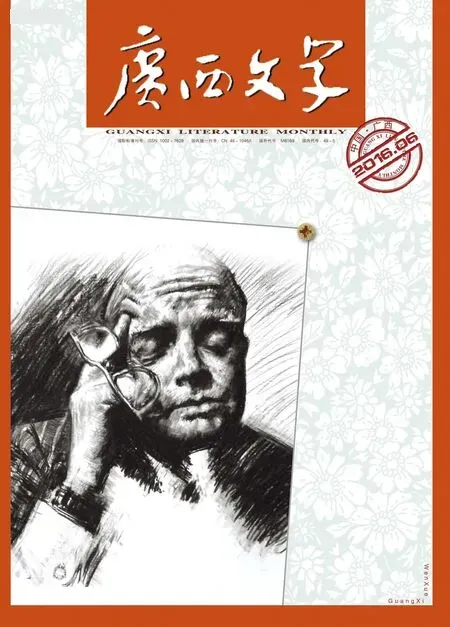身体病
李存刚/著
1
早知道我就不让他去太阳山了。表姐的这句话像一句谶语。
表姐坐在靠墙放着的小方凳上,身体佝偻着,像有千斤重荷压着她的脊背,压得她无法直起腰身。我的姑父姑母和亲友们围拢在表姐身边,眼巴巴地望着表姐。我想他们是要劝慰,或者是要听表姐会做出些什么安排,他们好即刻动手去做。
但是,表姐说完这句话就紧闭了双唇,我的姑父姑母和亲友们就都纷纷沉默着,嘴角嚅动,却没有谁吐出哪怕一个字来。表姐拉着脸,仿佛是在表达对自己和表姐夫的不满,还有一点悔不当初的恨意,仿佛随时可能大哭一场。
谁都能看出,表姐其实是在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的姑父姑母和亲友们都不愿意看到表姐哭,此时此刻,他们也生怕自己说错或者做错什么,从而导火索一样引爆表姐眼中的泪堤,而他们也将因此无法自持,那样的情形无疑是不堪设想也不敢想象的。事实上,我的表姐是大错特错了。或者也可以说,那完全是表姐自欺欺人的假想。表姐夫身上的病,从一个多月前住进医院的时候起,表姐就已经再清楚不过,但在表姐的假想里,表姐夫如果不去太阳山,就不会像伐倒的树木一样轰然倒下。表姐显然忽略了一点,即便表姐夫真是一棵树,他也已经在世上存活了四十二个年头,四十二年,如果不是因为自身已经严重腐朽,已经弱不禁风,要伐倒他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的姑父姑母和亲友们也大错特错了。悲痛欲绝的表姐说完那句话,也紧闭了双眼,深深地吸过一口气之后,再睁开来时,眼睛里便重新涨满了往日的风采,平静而清澈,像断电的灯泡陡然间绽放出了光亮。然后,表姐低下头去,手扶双膝,慢腾腾地支起沉重的腰身,迈开步子,快步步入了表姐夫所在的病房。
那一刻,表姐迈进病房的步伐可能是缓慢的,有一些踉跄,甚至算得上步履蹒跚,但是我、我的姑父姑母和亲友们都没想到表姐会突然站起身,病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又吱呀一声关上之后,我们都还沉浸在方才的想象里。
后来我明白了,表姐如此决绝的举动其实是一种昭示,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此前表姐还有些心有不甘,还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表姐夫将就此倒下,那么,自打在姑父姑母和亲友们的注视下站起身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得不面对和接受这个已然呈现在眼前的残酷现实。
2
表姐夫姓黄,在家中排行老二,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凑巧的是,表姐在家中也排行老二,且是家里唯一的女孩。自小,我们便管表姐叫二老表,表姐嫁给表姐夫后,我们便在“二老表”前面加上表姐夫的姓,管他叫“黄二老表”。一方面是口头表达的方便,一方面是这样叫来让我们觉得比表姐夫三个字更亲近,更独树一帜。
溪头沟是一个土地名,在行政区域上叫作新政村,隶属于四川省天全县思经乡。一说起溪头沟,外面的人们便大都知道具体所指,并且顺藤摸瓜地和实实在在的人或者事联系到了一起,但若向人说到新政村,好些人就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黄二老表家在行政村一小队,表姐家在二小队。说起来是紧挨着的两个小队,实际上隔着不下五六公里的路程。路面崎岖蜿蜒,道路泥泞,实在无法下脚的地方铺了过路石,路面长满了乱七八糟的杂草,路两边的茅草和野树长得更是肆无忌惮,什么时候经过,都须得小心翼翼地前行才行。后来,山道扩展成了机耕道,近些年又在机耕道上铺上了水泥沙石,进出溪头沟的路途于是变得平坦和畅通。一小队毫无疑问地更靠近乡场——那是乡村中学的所在地,而村里的小学校设在二小队,就在表姐家对面,隔着一条小溪。自打读书的时候起,黄二老表就每天背着书包从一小队到二小队,去到表姐家对面的学校里念书,等到表姐也在家对面的小学毕了业,到乡场上念初中的时候,情况便颠倒了过来——这下轮到表姐每天都打黄二老表家门前经过了。这些事情,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细枝末节,但在它们发生多年以后,当黄二老表约请的媒人敲开表姐家的大门,大人们恍然大悟似的说起来时,便有了特别的举足轻重的意味。大人们相信,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大人们这样的解释已然暴露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但在大人们,尤其是我的姑父姑母,他们觉得这事绝对不能有丝毫草率。他们心里十分清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内心一时有些不能接受,却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接受。他们索性把球踢给了表姐。他们所做的,就是叫来表姐,郑重其事地征询表姐的意见。内心正野鹿乱撞的表姐哪里看不出父母的心思,但面对有生以来从未如此庄重严肃的父亲和母亲,表姐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你们,看着办嘛。”表姐红着脸,怯生生地说。我的姑父姑母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脸上绷着,心事重重的样子,暗地里却是把表姐的心思把握了个八九不离十。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姑父姑母说起两句话,姑父姑母说:“都是同沟饮水的人家嘛”,意思是双方对彼此都是了解的,让表姐嫁过去,他们心里是有个大概的谱系的;姑父姑母又说:“人活一世,谁都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黄二老表家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家,让表姐嫁过去,他们心里是踏实的。
就这样,在黄二老表约请媒人上到表姐家大门的第二年春天,表姐便从溪头沟二小队嫁到了一小队。
我们的生活里,从此有了个表姐夫。我们的话语间,从此有了“黄二老表”这个称谓。
来年春天,表姐顺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黄勇。十多年之后,高中毕业的黄勇,如愿考取了重庆的一所大学。表姐和黄二老表、我的姑父姑母、黄勇的爷爷,一家人都很高兴。尤其高兴的是黄勇的爷爷。黄勇的奶奶在黄二老表背着书包从一小队来二小队读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黄勇爷爷一个人把黄二老表他们姐弟几个拉扯大,本希望黄二老表读书能够有出息,但黄二老表勉强读到初中毕业便怎么也不愿再继续读下去。不是不能读,而是黄二老表觉得再读下去,自己的父亲会累垮掉。现在,黄勇代替了他的父亲满足了爷爷的心愿,成了黄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
黄勇爷爷有多年的肺病,一直反复不停地咳嗽。黄勇考取大学的那一年,黄勇爷爷的咳嗽突然变得越发厉害,以前是随便去药店买些止咳药吃了便好了。也不是真正的好,只是咳得没那么厉害,可以承受,黄勇爷爷也便当它好了。这一年却很诡异,黄勇爷爷吃了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的药,吃的时间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长,就是一点也不管用,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咳,坐着咳得厉害,躺下了咳得更厉害,却什么东西也咳不出来。有一天早上,倒是终于顺利地咳出一大口咸腥的黏稠液体来了,黄勇爷爷以为是该死的口痰,因为他感觉到液体滑过喉咙时和往常咳出口痰一样舒畅。黄勇爷爷将手里捏着的纸巾一点点展开,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鬼东西在作怪,让他一天到晚咳个不停。手里的纸巾未及完全展开,纸巾里包裹的血已经浸透了出来,黄勇爷爷见状,脸色铁青,双眼上翻,如爆裂的皮球般忽忽悠悠地瘫软在地。
黄二老表赶紧将父亲送进医院。人是很快缓过来了,但医生强烈建议进一步检查一下黄勇爷爷的肺。为黄勇爷爷看病的那个医生此前也是黄二老表的医生。黄二老表当然地听从了医生的话。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肺癌,晚期。医生要求住院治疗,手术是决然不可能了,但起码可以缓解痛苦。黄勇爷爷若无其事笑了笑,坚持着要黄二老表将他送回溪头沟。
黄二老表木然地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
表姐站在一旁,也摇了摇头,眼眶里的泪水扯着线往外涌。
3
如果要追问黄二老表的病史,起码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早在黄勇爷爷确诊肺癌之前,黄二老表就已经是个病人。
但黄二老表从不觉得自己有病,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
最开始是双眼发黄,亮汪汪的,像是镀上了一层金粉,然后是脸,再后来是全身的皮肤,都隐现出一种日渐加深的黄。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吃不下饭,明明是感觉饿了,看见肉食甚至是油水稍微重些的饭菜,便开始发呕,继之便是狂吐。
眼睛和皮肤刚开始发黄的时候,黄二老表就猜测到自己的肝脏出了问题。他先后几次去到乡卫生院,吃了西药,打了吊针,眼睛和皮肤里的黄不但不见任何好转,反而是更加地深了,黄二老表于是改道去了乡场上的私人诊所,捡了几大包中药,买了药罐回去熬。“西药不行中药改”,这句老话一直被溪头沟里的老辈人真理一样信奉,黄二老表觉得自己就属于这种范畴。但在黄二老表的身上,老话得到的是反面的证实。黄二老表身上的黄一天天加重,继之因为发烧而身体愈发疲软,就连被用来治疗的苦涩中药也是进嘴就吐,面对表姐专门为他精心烹制的菜肴,别说吃下去了,就是听表姐说到吃字,便开始了无休止的狂吐。后来胃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吐了,只剩下一阵阵干呕。
黄二老表感觉到自己是没法再扛下去了。于是辗转来到县城,找到了我。
黄二老表以前好些次来医院找到我。有时候是为我送来家里刚刚宰杀的年猪肉或者菜地里的新鲜菜蔬,有时候是来找我看手上或者脚上的伤病。黄二老表知道我是名医生,也知道我干的是骨科,对于其他系统的疾病,比如他肝脏的问题无能为力。他之所以来找到我,就是希望我替他找个好医生,尽快解除他身体里的痛苦,以免再耽搁下去。黄二老表知道自己的病再耽搁不起了,黄二老表更知道,如果自己不尽快好起来,家里的活计就只能留给表姐一个人了,而我的表姐毕竟是一个女人,很多活计没有他是不行的。
为黄二老表看病的就是后来诊断出黄勇爷爷肺癌晚期的那位医生,早我几年参加工作的一位朋友。他不认识黄二老表,但在初步看过黄二老表的病情之后,便忍不住火冒三丈:“你们这,你们这完全是在找死!”医生朋友冲我嚷道。朋友的眼睛鼓得浑圆,语声有些哆嗦,如果不是有黄二老表在场并且及时澄清,说不定就冲过来揪住我的衣服,扇我两记耳光了。
“不关他的事!是我……”黄二老表躺在检查床上,双目圆睁,死死地盯着我的医生朋友,又扭头看看我,挣扎似的扭动了几下腰身,双手随即紧握成了拳头,似乎要对我的医生朋友的话做出回击。这是我从没见过的,自打成为我的表姐夫的时候起,黄二老表给人的印象就是沉默寡言,是那种只管闷头干事情的人,但在医院里面对为他诊治的医生,他竟然握紧了拳头,露出一副要和人拼命的凶相。好在他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真对我的医生朋友动起手来。
黄二老表说罢,像一个孩子似的扯着表姐的衣服,努力了几下终于从检查床上站起身,身体尚未站稳,便拉起表姐往外走。
黄二老表知道自己病得不轻,但他觉得还不至于真到了要命的地步。在表姐的劝慰和坚持下,黄二老表勉强留了下来,并按照我的医生朋友的要求办理了入院手续。黄二老表得的乙型病毒性重型肝炎,医生朋友说,必须住院和隔离。尽管黄二老表内心有千百个不情愿,但他那时候也只有接受的份儿,就像不久后的夏天面对自己的父亲因为肺癌去世。
那时候,黄二老表没有了发泄的力气,同时也已经没有了拒绝的力气。
病来如山倒。说的就是它汹涌的、无可匹敌的气势。这是溪头沟老辈人常挂在嘴边的又一句老话。
4
表姐说的太阳山我自然是知道的。
溪头沟满眼皆是山,太阳山是其中最高的一座,山上树木葱郁。黄二老表去太阳山便是砍伐那些绿树。
那些绿树生长在荒野,很多年里,溪头沟里谁家需要修房造屋了,就提着斧头去山上,需要多少砍多少,从来没人以为那是偷,但是后来,有个什么公司看中了那些越长越粗的绿树,从有关部门手中买下了溪头沟所有长满树木的山场,还修筑了直通山顶、可供大货车勉强通行的盘山公路。那些树木从此便有了主人,人们再私自去砍伐便成了偷伐。那个什么公司甚至请了几个人整天巡山,以防有人偷伐,还安排了专人在村口设立检查站,放了横杆,专门检查出村的车厢里是否藏有木材。因为那些树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那个什么公司安排守卡的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者,地地道道的溪头沟人,真正遇上偷伐了木材要通过检查站拉出溪头沟去换钱的,老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放过去了。几个巡视山场的也同样是溪头沟人,山是实实在在的巡视,但遇上砍伐者,或者听见砍伐声,打老远就绕道走开。黄二老表很早就知道砍伐下来的树木可以即刻换成钱,而所需要耗费的不过是磨好一把斧头并把它扛到山林,以及一些无所事事的用来打牌、喝酒来消磨的时间。但在很长的时间里,黄二老表总是不屑于去做。黄二老表觉得那样的行为是令人不齿的,其性质和直接从别人的衣兜里取出现金装进自己的衣兜毫无异样。黄二老表觉得自己不应该和那些人同流合污。
但是,黄二老表后来还是加入了盗伐的队伍,成了其中的一员。
黄二老表去偷砍山上的树木,因为那些木材可以快速地变成现金,以解决家里的燃眉之急。他一直和表姐一起,与贫困战斗,与时间战斗。
与此同时,黄二老表还在进行着另一场战斗,他不停地忙这忙那,身体里的癌细胞也在不停地繁殖,每次他一感觉到身体疲倦了,癌细胞的机会就来了。终于,癌细胞成了胜利者——就在黄二老表又一次砍倒几棵树,又将树干砍断变成需要的长度,然后拖着往回赶的途中,因为腹部无法忍受的疼痛,黄二老表像他刚刚砍倒的那些树一样,轰然倒在了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事情,是之前从未发生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他曾经背了二百多斤的毛猪,从表姐家所在的二小队徒步送到乡场去卖,他也曾经在我们家修房造屋时,一个人肩扛起二三百斤的条石。
但是现在,面对几根长柱形的木材,黄二老表败下了阵来。
因为他是个病人。事实上从被诊断为乙型病毒性重型肝炎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个病人。
但那一刻没人想到也没人相信让黄二老表倒下的是癌细胞。黄二老表不相信,表姐也不相信。
是的,黄二老表几年前来县城住院治疗是因为乙型病毒性重型肝炎。这是我的医生朋友后来给出的确切诊断。那时候,住院治疗了不到半月,黄二老表就明显地感觉到身体不再疲乏,能够大碗大碗地吃饭不再呕吐了,眼睛和皮肤上的黄也明显地褪去。黄二老表便以为自己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说什么也要出院回家。我的医生朋友不同意,却没办法强留,于是打来电话要我过去劝慰。“只要吃得(下饭),开些药回去调养也是一样的。”黄二老表对我和我的医生朋友说道。
出院回到溪头沟不久,黄二老表便再次感觉到了恶心,想吐,左上腹还隐隐地痛,但是眼睛里、皮肤上没再发黄,据此,黄二老表想当然地以为这次是自己的胃出了问题。于是和往常一样先后去了乡场上的卫生院和私人诊所,买了吗丁啉、胃复安、多酶片、陈香露白露片来吃。最初吃过几次之后,还真感觉到了些许效果。但没出多少时日,左上腹的隐痛便又开始了,乡场上的医生于是将药物改换成了斯达舒、三九胃泰什么的,但黄二老表左上腹的隐痛和恶心感依然时断时续,时轻时重。
既然吃药尚且有用,就说明他自己估计的诊断、乡场上医生的诊治和用药都是对路的,他就真是胃出了问题。这是他的逻辑,也是他的看法。他在这样想并且这样说的时候,就已经把我的医生朋友在他出院时反复告诫的话——必须定时到医院复查——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我想他应该不是忘记了,相反的,他甚至可能觉得我的医生朋友完全是在扯淡。
这也便是让黄二老表在几根圆柱形木材面前败下阵来的原因,也是他亲手为自己埋下的祸根。
而表姐不相信则更多的是因为侥幸。两年前的夏天,黄勇的爷爷她的公公刚刚因为肺癌去世,表姐不相信可怕的癌症会再次降临到她的家里,祸害到她的家人。尽管黄二老表不时喊胃不舒服,不时大把大把地吃药,人一天天消瘦,但该干的活计他照样在干,且照样干得和往天一样干净、一样利索,她便也和黄二老表一样相信了,他真的只是胃肠出了问题。
5
晚上十点刚过,黄二老表开始喊痛,痛得受不了。
这是黄二老表叫得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喊出声来。入院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从来没听黄二老表叫喊过。此前,痛得厉害的时候,他就不停地改变体位。跪、坐、蹲、趴、侧躺、仰卧,但凡身体能够摆出来的造型,黄二老表都尝试过,但依然没能让腹腔里的积液有丝毫减少,也丝毫未能削弱癌细胞对他身体的疯狂吞噬。
表姐一直没把真实的病情告诉黄二老表。他一直是蒙在鼓里的。但黄二老表似乎早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看着身边的表姐和他的姐姐、妹妹,黄二老表开始冲她们发泄自己的不满。他说,你们光是看着我痛,咋不想想办法呢?表姐束手无策,无法回答。这时候,表姐便强忍着即将翻涌而出的泪水,捧着脸飞奔到病房外,躲在走廊尽头的角落里放声痛哭。哭过之后,表姐擦干脸上的泪痕,若无其事地回到病房里。
表姐握着黄二老表的手,却说不出话来。表姐从来就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表姐是怕一开口,所有想说的话便变成了哭泣。表姐不想当着黄二老表的面哭,只一个劲地握着他的手,静静地看着他,祈祷着能有奇迹在某一刻悄然降临。
这一次,黄二老表没再说什么,也没再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体位,来缓解一下身体里肆虐的疼痛——喊过之后,黄二老表便躺了下去。黄二老表是真的累了,他想让自己彻底地休息一下。在表姐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将自己平放在病床上,黄二老表长吁了一口气,轻轻地合上了双眼。表姐坐在床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任周围的人怎么劝阻,表姐就是不放手。表姐心里清楚,如果此刻放开自己的手,她就可能再也握不到黄二老表的手,再也看不到黄二老表的脸了。
“我们,回家吧。”许久之后,黄二老表说。
表姐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仿佛要把黄二老表整个地装进眼眶里去。静静地看着黄二老表,更紧地握着黄二老表的手,表姐的眼眶里很快蓄满了泪水,泪珠印着黄二老表的脸,亮晶晶的,忽地一下,泪水自表姐的脸颊滑落下来,印在泪水中的影子随之猝然消失了。
这是黄二老表说出的最后一句话。黄二老表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后时刻,他想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里。既然没有了退路,家里的床榻,溪头沟的某片荒野就该是他最后的归属。
表姐迟疑着,慢悠悠地将黄二老表的手掌抽离自己的掌心,顺势摆放在黄二老表身体一侧的白色床单上,起身准备出门的时候,忽又恍然大悟似的转过身,掀起被子的一角,将黄二老表的手放进去,又看了看双眼微闭的黄二老表,掖好了被子,这才放心地跨出病房的门。
“他说,他要回去了。”
表姐颤抖着对姑父姑母和亲友们说罢,双膝开始发软,浑身随之开始了不规则的摆动,要不是被两个亲友即刻搀扶住,表姐就真跪倒在病房门口冰冷的地面上了。
6
黄二老表病倒之后,不得不由人抬着,第三次找到了我的医生朋友。
我的医生朋友摸着黄二老表的肚皮,看着黄二老表面黄肌瘦的脸,面露难色。
“医生,我胃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黄二老表注意到了医生脸上凝重的表情,直截了当地抛出了自己心头的疑问。
我的医生朋友从医已有二十余年,完全称得上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很轻易地就从黄二老表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也因此大致弄明白了上次出院之后,黄二老表为什么一直未来医院复诊。他对黄二老表的病情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但尚且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也不能贸然肯定。这时候作为一名医生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既顺着黄二老表的思路往下走,同时为自己的判断寻找明确而有力的证据。
黄二老表说到了胃的问题,这倒是为我的医生朋友寻找证据的过程减少了不必要的波折——按照我的医生朋友的诊断思路,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建议黄二老表转市里的医院,那里有胃镜检查以排除黄二老表私自的猜测和疑虑,那里同时还有更加直接而准确地诊断肝脏疾病的方法——从见到黄二老表,摸着他青蛙样的肚皮开始,我的医生朋友就想到了两个字:肝癌。
苏珊·桑塔格说:“癌症是一种身体病。”这个身体,包括心、肝、脾、肺、肾,也包括四肢、躯干,甚至毛发和皮肉,总之只要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就都可能成为癌症的标靶。黄二老表的身体最先被袭击的是肝。乙型病毒性肝炎。有权威的统计资料说,肝炎患者患上肝癌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二百倍,而病毒性肝炎一旦走向肝癌,大多已经无法挽回。医学界有个专门的概念,叫五年生存率,用来考核癌症临床治疗的效果,据此统计,大多数确诊肝癌的患者治疗后根本活不过五年。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确定诊断时已是中晚期,早已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黄二老表不知道这些,黄二老表更不大可能知道苏珊·桑塔格,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胃出了问题,因为他越来越吃不下饭,人因此越来越瘦,越来越没有精神。
黄二老表也没法知道接下来进行的肝脏检查结果。
知情者首先是市医院的医生,然后是我的表姐。为了不至于对黄二老表欲盖弥彰,市医院的医生没有专门跑去病房找表姐谈话,而是利用一次为黄二老表开药的机会,将表姐叫到了办公室,开具处方之前,详细告诉了她关于黄二老表肝脏检查的结果,和医生们分析讨论后得出的结论。尽管医生事先反复告诫表姐要有心理准备,但当那两个字陡然传入耳膜的时候,表姐还是轰然瘫倒在了医生办公室的座椅上。医生办公室里的灯光是一如既往的明亮,但那一刻,表姐的世界一片黑暗。
对黄二老表而言,这是个至高无上的秘密。以前,表姐与黄二老表之间从来就没有秘密;现在,她必须按照医生的吩咐,独自将这个秘密压在心底,而她唯一需要隐瞒的对象,就是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爱人。
表姐若无其事地回到病房,轻描淡写地告诉黄二老表:他果真就是胃的问题,没什么特别的,回去县里治疗一段时间就好了。这也是市医院的医生给出的建议。那时候,表姐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她所能想到和做到的,便是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建议。这可能也是那时候既能对黄二老表掩盖真相,又能让他信服的唯一办法。
就是胃出了问题;回县里。在黄二老表看来,这两句话和这样的结果,无异于上帝传下来的旨意,他所希望听到的最大的福音。
下半夜,大伯得知黄二老表回了家,特地去看望。大伯刚一进门,黄二老表便看到了。黄二老表大约是想坐起来,如果可能他还会站起身,迎接自己白发苍苍的大伯。黄二老表使劲地挣扎了一下。却不过是眨了两下眼,转动了几下眼珠而已。他看了大伯一眼,就无力地闭上了,眼角有两串泪水无声地流溢而下,滚落到两旁的枕巾上。事实无可辩驳地呈现出冷酷的面目,这时候,无能为力的黄二老表知道自己只有认命的份儿了……
黄勇从远在重庆的学校里赶回来时,黄二老表已经入殓,并且按照阴阳先生定下的时间送进了墓地,准备下葬,但黄二老表的双眼依然不肯闭上,嘴依然张着,像是随时准备起身和人说话。
黄勇跪在父亲身旁,抱着他,和他作最后的告别。黄二老表一定是听到黄勇说出的话了——黄勇说的,该是普天下的父子之间最想说的最后的秘语吧?黄二老表一直等待的,就是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向自己的儿子说说话吧?现在,他等到了——枕在黄勇怀里,黄二老表渐渐就合上了一直张开的嘴角,一直大睁着的双眼也跟着就闭上了。
坟地里,又一次爆发出惊天的恸哭。哭声里,除了失却亲人的悲痛,也有逝者的灵魂终于得以安息的释然……
这些细节,我是后来听在场的人们一遍遍口述之后拼接整理出来的。
黄二老表在表姐和亲友们的陪同下离开医院回家时,我没有去送他。我是本应去送他。我是一名医生,我见过若干次生离死别,应该算得上不是个胆小的人,但在即将与黄二老表诀别的时候,我退却了。
我站在三楼上的玻璃窗后面。那是内科所在的楼层。一个多月前,黄二老表从市里转回来以后,便再次住了进去。现在,黄二老表将永远离开这里,他将再不需要任何检查和治疗,也再不用忍受痛苦和煎熬。
我站在那里,看着车子在楼下空旷的水泥地上发动,而后载着黄二老表,穿过县城里灯火明亮的街道,一溜烟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车子在视野尽头消失了许久,我还站在那里。我伸手抹了一下冰凉的脸颊,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淌满了冰凉的泪水。
从此之后,我将再也见不到黄二老表。我能见到的,只有溪头沟的山野间一座崭新的坟茔,黄二老表长眠在那里,在世界的另一端。我将再也见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