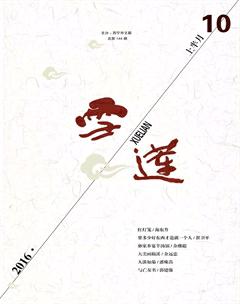爱与哀歌:在连绵的疼痛与负罪中呢喃
詹斌
《昆仑书》是朋友郭建强的第三本诗集,在出版前我就读过大部分诗篇(最初诗集名为《散步的秃鹫》)。作为《西海都市报》的副总编辑事务有多繁忙可想而知,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热情,并不停写作且硕果累累,用他的话说是在坚持,真心为他这种“坚持”高兴。在我眼里,诗歌是文学中最高级的创作文体,很长一段时间,对我而言,读诗都有较大障碍,而建强的诗尤其难解。或许是出于对人类最真挚、最热烈、最传奇、最美好、最悲伤、影响最大的一种情感的感叹与敬畏,或者是出于一种讨巧与方便、连贯与深入,我没有选择从整体上或者综合性地来谈论建强的诗歌,更不想着重涉及建强诗歌中现代的意象与探寻、高原的粗粝与沉郁、语言的柔软与锋利以及情感的深度与感觉的细腻等等。在读到本诗集中的《与亡友书(王康平:1972—1990)》后,感觉这或许才是我理解建强诗歌的一个重要起点。
一、事故摔碎了时间
事故摔碎了时间。
血液把公路烫出了一个大坑。泪珠在车前欢快地奔跑,你看红线断开,一百零八颗佛珠崩溅,倒也散发孩童般的欢快和自由。
然而,这样的崩溅持续了二十年。没有谁能够忍受二十年的断裂、脱落和崩溅。
在雨雪交加的夜晚,你听到大风的呼喊,由嘹亮转而混浊,由混浊突然明亮。
偶然,改变了命运。或许,还有性格。
死亡,每天在打量你;有时,露出亡友明灿的微笑——太亮了。
本诗开篇就直奔主题:“事故摔碎了时间”。时间对自然界而言,是一种匀衡流逝、无形状、无气味不可逆行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理概念,对人类而言,时间就是具有质感的生命印记。是的,时间遭遇到事故,摔碎了。“血液把公路烫出了一个大坑”,这带有叙事性的节奏清晰地表明,失去的生命多么青春、多么激情,多有力量,火热得竟将公路“烫”出一个大坑。接下来,粗读时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建强要用“欢快”来形容“泪珠”,而往下看到“红线断开”,“ 欢快和自由”时我才明白,作者内心是多么的痛啊。诗人用了两组对立的事物来表达此时的“痛不欲生”。“ 一百零八颗佛珠”就是“一百零八种烦恼”,当断除这”一百零八种烦恼”,就进入到一种寂静的状态。“红线断开”与“佛珠崩溅”意味着你与尘世的姻缘完结,不必再面对世间的种种痛苦、烦恼,因而诗人看到摔碎时间迸溅出“孩童般的欢快和自由”。血液进入寂静,远离尘嚣,天性得以解放?
问题是,谁的时间?一般而言,时间具有广普性,属于万事万物。但是对于同处一个“场域”的在者,时间必然具有特殊性,即你的时间,我的时间,他的时间。时间破碎,从此将一个人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年、那一刻。一段时间死去,曾在同一空间的另一个生命却开始了一段新的时间旅程,在破碎的时空隧道中继续穿行。
这“崩溅”必将成为一个刻骨铭心的纪念日。
“然而,这样的崩溅持续了二十年。没有谁能够忍受二十年的断裂、脱落和崩溅。”可见,作者在这二十年始终将这“摔碎时间”作为一个心灵的祭坛,供奉在潮起潮落、风雪交加的夜晚。说谁能忍受“二十年的断裂、脱落和崩溅”,其实是说“我就是这样忍受的”。二十年啊!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时而混沌,时而明亮,强烈与平淡交织而行,但一句话,你从未走出我的心,走出那个悲伤的纪念日。
“偶然,改变了命运。或许,还有性格。”偶然常常改变命运,而建强的这个“偶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表述。 写了这么多,主人亡友应该出场了。王康平,女,时年17岁,与建强是不同班的同学,当时19岁的建强应该成为大通铝厂的工人了。每年建强的生日,作为好友,王康平都要买礼物或生日蛋糕。那天她坐在同学的自行车后面,到大通桥头去为建强买生日蛋糕,但却发生意外,遭遇车祸,她的青春与笑容就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天灾人祸当然是偶然,但如果王康平不是骑车、或者没坐后座,或者再早一秒、或者再晚一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在于,当时王康平或许太过专注与急迫了,她记错了建强的生日,等同于无意拨快了时间,关键在于不是快了一小时、一天,而是整整将时间提前了一个月。难道所有的阴差阳错都是为了去追赶那个灾难性的“碰撞”吗?不是太巧了,而是上帝太阴险了,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偶然而又自然。
时间,生与死都是因为这无常的时间,那真是一杯有毒的水吗?
时间不可或缺,然而它一旦破碎,就将改变了一切。不仅使生命个体的命运转向,而且在瞬间就会腐蚀、击穿和改变当事者的性格或者说内在精神。
在摔碎的时间中,“死亡,每天在打量你;有时,露出亡友明灿的微笑——太亮了。”这个死亡至少有两种隐喻,一是指死亡的诱惑。我是否已是行尸走肉,我有活着的必要吗?这是对死亡的叩问。当然,死亡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无所指的概念,因而,二是指在世界另一头的“王康平”,所以死亡就如一朵花、一束阳光,让你犹豫不决,让你不寒而栗,让你难以割舍、难以面对。你稍有不慎,它都可能灼伤你的眼睛并迅即传导到灵魂。
二、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以你的离去,作为最强烈的爱的宣言;但是——
这宣言更是一种刻骨的复仇。
你把自己刻在我的骨头上。
每时每刻,我都感受你的存在,你的变化,你的小心眼。——还有你的冷酷:绝不和我面对面。
尤其是,当雨珠在玻璃窗上唱着寒凉的歌曲,在光滑的镜面即死即生,即隐即没——
你知道,这时我只想偏执地把脸从屋内伸入玻璃薄窄的空间,然后终于贴向夜晚,贴向你,贴向雨滴的温度——
当然是无情的!
谁也不能穿过玻璃,从这一面到另一面,类似从生到死:你在嘲笑,你在微笑。
你的笑容和雨滴一样凄冷。
其实,作者绝望而延绵不断的痛,来自于“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过去我能感觉到的或许只是友情,但我现在才猛然醒悟。与其说原来你是爱我的,不如说原来我爱的是你。在即死之后,一切都太晚了!这种场景让人不得让人起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生离死别。因为:
“以你的离去,作为最强烈的爱的宣言;但是——
这宣言更是一种刻骨的复仇。
如果我要是早就知道你是爱我的,那么,我也就会珍惜过去的时光。当作者明白这个真相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刻骨的复仇”表明作者自身对王康平情感失察、不懂珍惜的惩罚和深深的忏悔。“你把自己刻在我的骨头上”,多好的诗句啊,我当然不会单一的理解,仅仅是王康平通过一系列的关心与爱把自己注入到建强的生命、铭刻在建强内心深处,而在“时间摔碎”、悟痛之后,建强自觉将你刻入骨髓、刻在了内心黑暗的未来。
是的,“每时每刻,我都感受你的存在,你的变化,你的小心眼。——还有你的冷酷:绝不和我面对面。”可见,你并没有离去,你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因为我每天都能感受你的存在与种种变化,从未离开过你。就这样进入回忆,不断抚摸过去的你,就是抚摸逝去的爱,抚摸你对我绝不晤面的“冷酷”。特别是当作者独自面对“雨珠”,面对空无一人的房间,面对夜晚沉默的“玻璃窗”,面对镜中的人影孤魂,“寒凉的歌曲”必然从内心升起。“屋内伸入玻璃薄窄的空间,然后终于贴向夜晚,贴向你,贴向雨滴的温度”,多想与你真正在一起,“玻璃薄窄的空间”或许就是双层窗户那个空间,当然也可想象为死者的“灵柩”。如何才能贴向夜晚、贴向你,就是选择死亡,这种亲密性的趋向,这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亡友”那种浓浓的思念与爱意。
“当然是无情的!”谁无情?是这世界,还是你或者是我?“谁也不能穿过玻璃”旨在表达,这薄薄的“玻璃”就是界限,生与死亡的界限,当然不能穿越。所以“你在嘲笑,你在微笑”。一定是在笑我,笑我没有勇气;笑这个世界,笑这个世界的无情。微笑是有些轻松与满意吗?你确认你真脱离了人间苦海?“你的笑容和雨滴一样凄冷”究竟那是怎样的一种笑容呢?或许有坦然的绝望、湿润的孤独的意思,但我以为只可意会、感受,不可言传,其实,作者是在回忆与嘲笑自身,是因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爱我的,而我已经永远失去了表达和真正与你前行的机会。
三、我对你的远行,毫无准备
我对你的远行,毫无准备;如同,我对你信任,毫无准备。
而你也仅仅在我的梦中造访过一次。
在梦里,我已经在你未至之时,感觉到你推动微风轻尘的气息;当你面对我,隔着一段不可能两手相握的距离,我已尽知你的心意,你的来意,你的凄惶,和你眼中剧烈的怜悯——是涌向生者的怜悯。
后来,你恰恰属于百天的那张脸,你最后的那张脸,在我的大脑中变成了一只挥别的手,缓慢而坚定,就像一只就要隐藏起来的钟摆。
你的脸,像一只钟摆在黑与白的交叉地带向我挥别;有时又像是永生的呼唤。
诗人并未将与“亡友”分开看作是永别,而是将此称之为“远行”。因为太过意外,所以不可能内心有所准备。在这里显然不能将“远行”仅仅看作是一种诗歌语言的文学性描述,它与作为心理事实认同相关。“毫无准备”,应是指来得太突然,没在事实降临前心理上有所考量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故”,谁会有准备呢?犹如“我对你的信任”,也是没有任何“准备”的,就那么自然而然。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写到了梦。“而你也仅仅在我梦中造访过一次”,作者强调了“一次”的稀缺性和珍贵性,是剪不断、理还乱啊。在梦中,我分明能嗅到先于你身体随风而动的气息,“当你面对我,隔着一段不可能两手相握的距离”这句诗写得非常好,触不到的恋人很凄美,对作者内心而言却是万箭穿心的折磨,这句诗写出了诗人内心的渴望,具有中国古典的美学意境。但不知是建强有意为之,还是笔误,第二节写“还有你的冷酷:绝不和我面对面”,而在第三节中又写“当你面对我”。如果是有意为之,或者反映真实的梦,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框架,那就是在写第二节时的确如此。第三节写得晚,当时在梦镜中面对了。当然,文学与诗歌创作并不能完全等同生活逻辑,或许这只是诗人情感长久陷入深渊而产生的眩晕,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这种可能的误解的话,这一节写得相当的精彩。诗人写道:“我已尽知你的心意,你的来意,你的凄惶,和你眼中剧烈的怜悯——是涌向生者的怜悯。”虽然生死两茫茫,你无论以什么方式出现,我都理解你,你的意识、念想、不安以及对生者的宗教式的爱与怜悯,深深表明你已经成为我的血液,成为我的呼吸,成为我今生挥之不去的温暖与疼痛。
“你恰恰属于百天的那张脸,你最后的那张脸,在我的大脑中变成了一只挥别的手,缓慢而坚定,就像一只就要隐藏起来的钟摆。”当我看到这句诗,内心猛然一疼,明显穿透了泪腺,但眼睛湿润并没有损伤理性,写得太传神了,使我们见识了亡友的“脸”如何变成“挥别的手”,而手又如何变成 “钟摆”的。说“隐藏起来”,是因为原本亡友的脸就或隐或显,似要消失。“你的脸,像一只钟摆在黑与白的交叉地带向我挥别;有时又像是永生的呼唤。”写出了真实梦镜的感觉,“黑与白”不就是灵魂最有可能抵达、驻留的阴阳交叉处吗?之所以写得如此之好,是因为的确这源于一个真实的梦,更在于诗人具有策兰那种“幽灵般的感受力”。“你恰恰属于百天的那张脸”中的“百天”,我原以为是笔误,是 “白天”似乎更易理解,但建强在电话中告诉我,就是“百天”,太神奇了!在王康平去逝100天的当晚,他们在梦中相遇了,对她的远行毫无准备的建强是多么挣扎啊,多么不舍、多么绝望啊!那张脸确实“像永生的呼唤”,建强那晚在雪白的墙上留下了道道带血的“指印”,我们似乎听到建强近在咫尺的呼唤:请你等等我,等等我,请你千万不要离去!
四、熟悉的物件
永远17岁的女孩,我没想到在烈日下,接触你的衣饰、书本和玩物的方式——竟然是焚烧。
让火焰给你带去这些熟悉的物件,也许它们到达你手中时,还保留着人间气息。
火焰轻快地舔舐着白色的裙子,火焰怒气冲冲地翻烤厚重的冬衣。
我是说,在另一个界面烈日正翻烤着我,箭雨般的日光怒气冲冲冲刺我的头顶和脊背。
诗人显然没有、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从如此重大的变故中走出来,死亡的阴霾如同幸福时光需要反复咀嚼。这一节,作者对亡友的情感层次进一步向下延伸,主题是祭奠和审判。是的,17岁,一个豆蔻年华青春刚刚绽放的女孩,一个尚未充分体验美好生命的女孩,一个悄然永生依附在我泪腺的女孩,就这样离去了。作为对死者的追悼、敬意、怀念和追思,亲人、爱人、友人在适当的时候必会祭奠。我们知道,作为仪式性很强的祭奠,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华习俗,“衣饰、书本和玩物”无疑都是祭品,但作者十分感慨:接触你的方式“竟然是焚烧”。 睹物思情,诗人当然知晓“焚烧”的含义,那一缕缕青烟不正是自己无尽诚挚的问候吗,这本身就是与亡友一种晤面的方式。“竟然”一词,表达对如此单一接触方式的一声叹息。作者只能接受,或许这方式有其特殊价值:“让火焰给你带去这些熟悉的物件,也许它们到达你手中时,还保留着人间气息。”“人间的气息”用得意味深长,我理解,除带去人间的花香、鸟语、喧嚣、静默、幸福、痛苦等等,重要在于一定还有我的“气息”。
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要在“烈日下”祭奠?中国虽然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与情怀的国度,但诗人用火焰“舔舐”“翻烤”“熟悉的物件”:“白色的裙子”和 “厚重的冬衣”,实则是写出了内心的忏悔。“烈日”构筑的空间恰似法庭,“火焰”犹如法官,我像一个不愿走出“牢笼”的囚徒,接受着最为严厉的自我审判。 “我是说,在另一个界面烈日正翻烤着我,箭雨般的日光怒气冲冲冲刺我的头顶和脊背”,“箭雨般的日光”表明了审判的密度多大、武器是多么的锐利啊。就是这样,作为精神层面的负重,诗人今生将永远背负死亡、情感和有罪编织的十字架,在充满荆棘与泥泞的路上前行,
五、我就是一个汗粒
我看见自己的汗粒饱满地渗出皮肤,像胆怯的孩子坐在窗台,犹豫着跳还是不跳。
当然是要跳的。
再细小,再纯粹,再柔美,也还要跳的。不跳,也会被推下去。你看,春风撕落了多少花苞?何况,接踵而至的还有急骤的夏雨,刀锋闪动的秋霜。
汗粒从额头、眉间、鼻梁、下巴、脖子、腹背、胯间,双腿,还有脚指缝中艰难地冒出来,失重般、入魔一样滴下去。
我就是一个汗粒。
在时光的碾轧和世事的切割中,尽管独生无依,充满了血一样黏稠的痛苦,盐一样浓重的记忆;却也是爱意饱满,有种自我开花的温软感觉。
跳,还是不跳,这是一个问题。
跳,还是不跳,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汗粒”。或许我们都是“汗粒”。不过每个“汗粒”都是不同的。确实,如果足够细心,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的汗粒饱满地渗出皮肤”,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看似不足为奇。然而,它“像胆怯的孩子坐在窗台,犹豫着跳还是不跳。”这就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看到的了,也就是说,诗人因生活变故,在死亡的微笑中,一眼就看到了“命运”,看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再细小,再纯粹,再柔美,也还要跳的。不跳,也会被推下去。”正如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是啊!生命从一出生那天起,其实就面对死亡,多活一天就是少活一天 ,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
当然,在向死而生的生活中,或许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可能都是相似的,但精神生活却是千差万别。对于作者而言,“尽管独生无依,充满了血一样黏稠的痛苦,盐一样浓重的记忆”,尽管全身被“汗粒”亲吻、包围,孤独也好、疼痛也罢,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你(亡友),“却也是爱意饱满,有种自我开花的温软感觉”,诗人在丰富的痛苦中,反复思考着人生的终极问题。
看看,无论多么细小、纯粹还是柔美,都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必然经历“春风”、“夏雨”、“秋霜”周而复始的考验,死亡都会在最后露出狰狞的面容。因此:“跳,还是不跳,这是一个问题。”可见,莎士比亚式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强行进入诗人的思维,摆在十字路口,但建强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跳,还是不跳,这不是一个问题。”既然结果归一,都会跳,都会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纠结的呢?
六、我爱上了罪孽,爱上了阳光
我爱上了罪孽,爱上了阳光。
血,让我嗅到了自身的狂野。
没有谁不在呼吸,不在饮水,不在啃噬;蠕动的咬肌,开合的牙齿……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贪婪的世界,不是在吃,就是在被吃。
巴列霍说:我不在这里喝咖啡,会有另外一个人……我占据着谁的生存位置,满口满腹嚼咽的是谁的血肉?
我爱上了阳光,就是爱上了罪孽。
我爱上了罪孽,因此分外珍惜阳光。
看上去,诗人似乎释怀了,因为“我爱上了罪孽,爱上了阳光。”实则不然,爱上“罪孽”,表明自己甘愿因愧对亡友的“罪行”应当受到报应。爱上阳光,如前所述,有光亮的生活当然是世人毕生追求的,然而,诗人的“阳光”,则有些不同,为了能自觉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始终认为自己需要永生忏悔,接受日复一日阳光的照耀、烘烤、鞭挞,只有来自这种自责似的苦行生活,他才觉得能做到真正的救赎。只有沉醉苦海,才会有内心安宁。
“血,让我嗅到了自身的狂野”泄露了诗人的内心的秘密,这血不就是那把公路“烫”出一个大坑的血吗?关键在于,当这血注入我的体内,使我感受到了自身的“狂野”。能不狂野吗?既能爱上罪孽,也迷恋上了阳光。而且,我还看到这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贪婪世界,“不是在吃,就是在被吃”。
你是在问王康平之死与现在这个贪婪世界有什么关系吗?建强说,Yes。他借巴列霍之口追问:“我不在这里喝咖啡,会有另外一个人……我占据着谁的生存位置,满口满腹嚼咽的是谁的血肉?”这意味着诗人明白,其实自己生命的此在,一定是占据了一个别人(某人)生的位置,这个位置很可能就是“亡友”二十年前回头一笑挪开的那个位置。当然也可能是其他人的位置。够残忍的!因为你似乎若隐若现地知道“满口满腹嚼咽”的血肉来自于谁。
这就理解了,“我爱上了阳光,就是爱上了罪孽。/ 我爱上了罪孽,因此分外珍惜阳光。”选择这种矛盾的救赎方式,无疑是选择了一种真正的生活之路。唯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能在独自享有“亡友”未来的世俗生活真正得救的人。
七、如果,……那将如何?
如果,我没有主动认识你,那将如何?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天然地相像,那将如何?
如果,死亡不曾打断,你现在如何?
如果,死亡不曾打断,我现在如何?
如果,我不曾产生这持续终生的负罪感,那将如何?
如果,我像失控的浮士德抛却所有,一头扎进幽深密林,在恐怖和无耻中肆意妄为,那将如何?
可是,我在轻饮你,一小口,一小口,让爬上腹腔的茶垢退去,让喉嗓发出清正的声息。
让我们再次回到思想自我审判的“现场”。
这一节,作者用了七个“如果,……那将如何?”,以假设的方式对与“亡友”的可能关系进行追问。第一句:“如果,我没有主动认识你,那将如何?”事实上,建强仍然在自责,没有主动认识,当然就不会有后面的生日蛋糕的事情,换句话也就没有在王康平17岁“摔碎时间”,两人如今仍在两个毫不想干的平行世界“活着”。第二句,“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天然地相像,那将如何?”如果不是心相契,就不会产生爱意,她就不会如“鸡蛋”的另一半或者心脏的另一半一样,不停地围绕你、跟随你、并奋不顾身地扑向你,今天我们仍然会可能会是熟悉的陌生人。第三句,“如果,死亡不曾打断,你现在如何?”如果生命没有被死亡无情的抢走,你也许现在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幸福的妻子,一个勤恳的职工,正在无忧有虑地生活着,一切皆有可能。第四句,“如果,死亡不曾打断,我现在如何?”显然,诗人也不会那么刻骨铭心的记忆,没有那么丰富的痛苦,那么永不消失的负罪感,但也许现在就无法掀开记忆的殿堂,写出接近灵魂深处、人性本质的诗歌。第五句,“如果,我不曾产生这持续终生的负罪感,那将如何?”不会怎样,仍然会是一个诗人,一个父亲,一个劳动者,但可能人性中会缺失一种善良、一种爱,多些麻木、自私与平庸。第六句,“如果,我像失控的浮士德抛却所有,一头扎进幽深密林,在恐怖和无耻中肆意妄为,那将如何?”忘记过去,忘记相遇时光,如梅菲斯特那样与魔鬼交换灵魂,或许带着面具时常出没于灯红酒绿抑或物欲横流的人群,但“亡友”却依然会以17岁的纯洁与善良,时时刻刻在天堂注视着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社会不会嫌弃一个行尸走肉、麻木不仁的“幸福者”。
“可是,我在轻饮你,一小口,一小口,让爬上腹腔的茶垢退去,让喉嗓发出清正的声息。”所有的如果,仅仅是结果之后的假设而已。事实是,时间早已做出了选择,人心已然嵌在了一起,血液穿越了玻璃融二为一,负罪的钉子已经打入骨头,诗人唯一可做的就是“轻饮你”,让腹腔的茶垢渐渐退去,露出温暖的、刺目的光芒,照耀携手前行的路。可见,七个排比句,不是显示力量,而是宣誓决心,它进一步强化了诗人对负罪的认同,使其在假设的想象中与亡友深入交谈,只是不知可否慰平诗人渗血而又充满折皱的灵魂?
八、你以奇怪的方式,和我同在
你以奇怪的方式,和我同在。
你随时翻阅我的灵魂,就像微风或者狂风检视着叶簇。
你哗哗乱响,你汩汩而歌;你有时像窃听者,窥视者;我在你面前没有秘密。
我已经把自己视为一卷书册,有些纸叶落上了字粒画符;还有一些仍然等待你的手指。
书卷哗哗乱响,书卷汩汩而歌;就像叶簇,就像清泉:就像你和我的从前。
人往往以天使和魔鬼相伴而生,具有两面性。人性是介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混合体,是克服动物性向神性接近的一种复杂状态。从宗教与诗的眼光看,人们似乎总是以神性来证明人性。奥特在《不可言说中的言说》中指出,“谁真正相信上帝的真实性,谁也就相信,他自己人性的存在”。 建强不一定相信上帝,但我们通过他对亡友的态度和行为分明感受到他真实的人性,相反,他是以人性来召唤神性的。“你以奇怪的方式,和我同在”。当然,鉴于与“亡友”的界限,作者感到“你”与我同在的方式总是与世俗不同,甚至有些奇怪。因为“你随时翻阅我的灵魂,就像微风或者狂风检视着叶簇。”不在同一时空,你为何能随意进入我的灵魂?这就是神性。由爱由生的神性。在灵与肉、爱与孤独中,在“你哗哗乱响,你汩汩而歌”的诵唱中,诗人深深地感受并体验到你的存在,你对诗人的关心及对生命的价值。
问题是,我们在谈论存在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虽然以世俗眼光看,诗人与亡友早已天各一方、阴阳两界。但一旦进入此时,我们坚信诗人与逝者进入到第三种空间,也可称神性世界。“你有时像窃听者,窥视者” “就像叶簇,就像清泉”, 不管你如何神出鬼没,变成“叶簇”或“清泉”,我依然能清楚的感知你的一切,“我已经把自己视为一卷书册”,意味着我灵魂永远向你敞开,等待你的手指,不仅仅是咀嚼痛苦,而是在“痛”中享受幸福,用“痛”来不断抚平内心缓慢渗血的沟壑。“就像你和我的从前”,不仅表明诗人对曾经时光的怀念,而也暗示今后仍然会将此作为一粒温暖的种子。“你哗哗乱响,你汩汩而歌”“书卷哗哗乱响,书卷汩汩而歌”,显然你就是源头,你就是书卷,需要我终生轻饮、终生阅读,没有你,我的生命将寸步难行。看得出来,“亡友”已经深深融入作者的灵魂,作为另一半,潜伏下来,并成为作者此生前行的动力。
作者用如梦如歌的语言抒写了“亡友”以“奇怪的方式”与我的同在。何为同在?同在就是同时在一起,不分离。同在对于现世来说,可能就是长久的友情和婚姻;对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人来说,就是太极,是阴阳,就是白天与黑夜,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就是阳光下的阴影,阴影中的阳光,就是不同的两只脚踏进了同一条河,就是此在背负彼在而达成的一种柏拉图式精神的存在人生。
九、旅行。流浪。放逐。
旅行。流浪。放逐。
醉生梦死。湖边独坐。用青海话在夜晚的空寂的西宁大声朗读,惊醒了街巷的灯火。
算不算自我表演,自我催眠,自我麻痹?
管他呢!我的人生已经抛却舞台剧。
我活着,我行走;我忽梦忽醒——我相信会在某一刻遇到你;当然也会再次失去——就像日月的交替,就像血液的喧嚣之后骨头的寂静。
大概这也算是灵魂的一种滋养,也算是带有酸苦味道的独自的信仰……
“旅行。流浪。放逐。”如果说前八节诗人主要是写自己对“亡友”种种爱恋与牵缠的回忆与追问的话,那么这一节重点就放在了作者在亡友经历“碰撞”后的外在行为踪迹。这三个词,正是诗人对自身一个文学性的诗意总结。
显然,最真实的情感,不需要修饰,虽然这种方式让人感动,但诗人并不想美化自己。“醉生梦死。湖边独坐。用青海话在夜晚的空寂的西宁大声朗读,惊醒了街巷的灯火。”这看上去似乎有些落入俗套,但诗歌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反映人类最基本又最特别的存在状态与精神状况,这就是爱情,这种“条件反射”是诗人天然的敏感而自然形成的路径。其实在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成灾的今天,这样爱情已经十分稀缺了。因为生者对待亡友至少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保全自身不受伤害而“遗忘”,或者以生活还得继续为名而处处“回避”。过去对有些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既没有利益可言,也不能带来慰藉,反而可能使人陷入无休止的感伤与疼痛。
然而,过去或亡友对建强就如一个深埋黑暗的宝藏,那里有相遇、温暖、爱情、幸福、孤独、痛苦、快乐、感觉、等待、理解、信任、决心、人性、深度、永恒等等,放逐只是一段人生小径分叉的歧路,在经历内心流浪与自我放逐中,作者其实对这种行为也疑惑,“算不算自我表演,自我催眠,自我麻痹?”或许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的确具有表演、催眠和麻痹的性质,但这对世界或他人有影响和伤害吗?这不过是作者的自我意识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充分表明,此时的诗人已从神性返回到人性,最真实的人性。因为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你其实无法改变,无法遗忘,你与亡友曾经的一切已经构成了你的命运。“管他呢!我的人生已经抛却舞台剧。”我喜欢这种态度,感受是自己的、经历是自己的,哪有那么多心机?“我活着,我行走”。既然与舞台剧无关,那么就要为自己的人生好好活着,要不停的行走,因为作者坚信与亡友仍然会在某一时刻再次相遇,然后再次失去。“就像日月的交替,就像血液的喧嚣之后骨头的寂静”。综上可见,“亡友”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的生活,一种灵魂的滋养。因此,作者曾经也许流浪与放逐过,但怎能真正任性?如果自我都放逐了,王康平的“亡灵”如何安放?我如何躲避她那无处不在注视着着我,犹如我的第三只眼睛?就算真正的爱情开始于“摔碎的时间”之后,最终诗人还是要回归正道,因为“你”成为了我的归宿、我的家园、我的生命,同时也成为我“带有酸苦味道的独自的信仰……”。
十、微光:在天堂、海洋和大地黑暗之处
那场“事故”虽然是发生在诗歌之外的重大事件,但对建强一生特别是诗歌创作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摔碎的时间”无疑使建强产生了深深的疼痛感和负罪感,并导致他对世界、对生命、对人性的看法有了重大的改变。当然,他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或者陷入消沉。愤怒出诗人讲的是情绪饱满才能写出好诗,其实忧伤和疼痛才会使诗人更具敏锐性和洞察力。看似本诗写的是爱情,实则写的是死亡,犹如一曲“死亡赋歌”,一典灵魂哀歌,它不仅直刺人心,也照亮了诗人在暗黑之处的灵魂之路。虽然建强后来创作过不少有关爱情或忧伤的诗歌,比如《水晶爱情》(组诗)《爱人,晚安》等,但他并没有过多的抒写,爱情或哀歌已成为一个引子,使他的感觉更细腻、视野更广阔。
本诗集《昆仑书》共七辑,从高原形体《戈壁颂》到《血墨》的《微光》,从游走《河源渡》到仰望《昆仑书》,从诵颂《山中》《野花》到《突然》《沙之忆》,从《蝴蝶的注视》到《残片:赫拉克利特》,大致就可了解建强诗歌创作的气象。或许这些诗歌都是在“亡友”注视下在烈日中写就,“你哗哗乱响,你汩汩而歌”,“亡友”的手指随时翻阅,她一定反复细读了建强充满爱意、凝结血脉的灵魂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讲,《昆仑书》是建强与“亡友”的合著,因为建强的血液中早已流淌着“亡友”的挥之不去的气息。今天,“亡友”或许应该破例一次,再次回到未来、回到梦镜,与建强“面对面”共同分享从远方传来的喜悦:在2015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暨中国诗歌启蒙精神论坛上郭建强荣获中国新锐诗人奖。
我们相信,当爱成为永生,穿过死亡的召唤,“在天堂、海洋和大地黑暗之处”,一定会闪耀着银色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