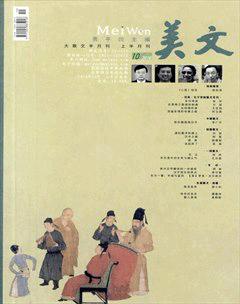曳尾于涂中而化蝶入梦
申成倩
浊世自有翩翩者,化蝶入梦。
庄周的文笔汪洋恣肆,怪诞奇异,使得他本人也似迷蝶翩翩,老龟曳尾,飘乎而安逸。庄子代表着理想人格的极高境界。我们有心羡慕他自由遨游之情,无意仿他曳尾于涂中的拒世作为。
战国中期,群雄争霸,干戈厮杀间,人命如同草芥,庄子不是什么掌握权力之人,存于这种乱世之中,朝不保夕,如何能得逍遥之感?庄子在濮水畔作出决定,从此远离乱世对自我的束缚,他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兵荒马乱不会因他这一句话而停止战争,但心上的枷锁却已然落地。浊世缚了我身,却固不了我心。
鲲鹏展翅非一日可为之。庄子风趣幽默地道来“鹏程万里”的小寓言,并非讲述《齐谐》志怪——乱世之中自满而孤独,胡言乱语方且留存。庄子将这个故事讲得荒诞奇异,却又借此告诉我们厚积才能如鹏一展雄翅,一日千里,与蜩与学鸠之类相比,则可知大小境界。庄子想说,我们要打开心怀,不要被物质形象拘锁,开放心灵,从而精神自由。精神自由,若能忠信于自我而不以身为形役,便同庄子般可以曳尾于涂中了。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诗仙飘遥不羁于山川星河之间,醉卧仰头观望天中一弯勾月,四野烁烁繁星,似有遁世而去之意。而庄子则鼓盆而歌,笑谈生死。许多人畏惧死亡,宁愿苟且偷生,不愿热血倾洒,这是个人意志,庄子大概不会去批判这种做法。每个人的行动都若有若无地体现了自身的价值观,或许也不是境界的小大之分,不过是道有不同罢了。庄子讲述了一个奇异浪漫,充满诗意般优美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在精神的世界里畅快翩飞,当他终于与蝴蝶相融时,蝴蝶与他的界限便不再明晰了。万物相互依存,庄周在这里提到了物化,他与蝴蝶难分你我的这种依存,便是物化。从这个幻化的方面看去,死亡也不过是这种变化的一种回归罢了。庄子将对立的死生连接在一起,融合而和谐,所以面对妻子的死亡,他鼓盆而歌,面对自己的死亡,他愿以天地为棺。
《赤壁赋》中“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子与客泛舟赤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庄子的《逍遥游》恍然一副飘飘然若乘风归去的样子,庄子落地了,还是停留在他那崇高人格的玉阙之上了呢?
“庖丁解牛”中,庄子讲到庖丁为文惠君表演解牛,技艺超群卓然。庖丁掌握了“因其固然”的道理,牛骨盘结繁复,但庖丁能聚精会神,谨小慎微,终究将牛割解。做事处世也是相同的道理。庄子有他消极避世的一面,因为在浊世中追求理想人格本就是痴人说梦,但他从未真正抛下浊世翩然离去,因为理想是基于对现实残酷的不满。
读庄子,心思或可豁然开朗,打破自我局限,扫除闭塞晦然。他汪洋恣肆的文风令人为之惊叹。
读庄子,细细体味那些“胡言乱语”下或有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