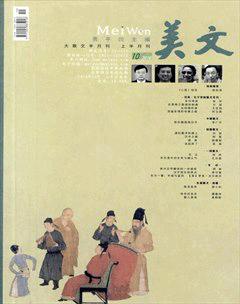苍坡古韵
潘婧
雨是细的,一滴一滴撒入水中,泛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水是绿的,一片一片的绿叶落在水面上,却好像比不过那水的绿。
抬头望了一眼匾额上“苍坡溪门”四个大字,跨过了高高的门槛,恍若穿越了时光,来到千百年前。长长的路,很直,向前铺去,好似没有尽头。石青色的砖似乎沉淀了些什么。
撑着伞走在蒙蒙烟雨中,沿着这条长长的石板街向前走,脚下的石块应是因为今日的雨,多了几分晶莹,几分沉重。一个路口,向前、向左、向右三条路。我微微愣了一下,向着左边那条人极少的小道而去,狭窄幽长的小路,左右是高高的石墙,墙上覆着青青的苔藓,石砖是初时的青色,但它们锋利的棱角早已被磨得圆润。
已是午饭时分,路上几乎看不到人。恰巧走到一间屋子前,里面有两位老人正在低头下象棋。
木制的棋盘上面,黑色的分界线已有一些断开,那木色仿佛是百年老屋的木柱子,一种深厚的褐色。老人手中的象棋,黑色的漆有些掉了,字的凹槽里露出本来的颜色,想必是用了好多年的吧!我这般想着,一时在门前住了脚,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了。屋里的人似乎察觉到了我,老人抬头望了我一眼,我也就此看清了他的面容。年老的皮肤早已被岁月的峥嵘划出一道道痕迹,只是那双眼睛却特别明亮,带着能够看透人的眼神。他开口道:“娒,要看的话进来看罢。”温温的乡音,暖人心。
一进屋,一位老人便准备移一张凳子来给我坐,我连忙摆手道:“不用了,不用了。”站在屋里,才发现这间屋子真的很小,低矮的平房,大概有十平方米左右,一张小小的木床,木制的柜子,摆着棋盘的小凳和二人坐着的竹椅,在采光并不好的屋子中更显得几分狭窄。
二人早已继续投入到棋局之中,移马行车,排兵布阵,一回回的交锋中,步步紧逼对方将军所在。棋子似乎是因为上了些年头,在二人手中显出温润的光泽。“啪”的一声,其中一位老人落下棋子,道:“将军!”另一位老人看了一眼棋盘上的局势,道:“我又输给你了。”二人相视,满是皱纹的脸上漾起笑意,然后理棋,再次开始。他们的动作娴熟而又随意,仿佛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都是这般。沧海桑田,时光匆匆,变的却只不过是岁月,而非人事。
虽然两位老人没有对我站在这里表示不满,但我却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格格不入,仿佛是闯入了一幅古香古色的画卷,破坏了那份韵味。我鞠了一个躬,道:“打扰了。”然后转身离开,背后二人仍在静静地下棋,没有言语交流,最大的声音也不过是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响。
绕出幽深的小巷,回到那条长长的、笔直的石板街上,向右一看,方才围在那里的人群已不见,没有阻挡,我看到这条路的尽头是一棵高高的树,枝叶并不繁茂,枝干却极为挺拔,在路两旁的深青瓦檐中,远与近相合,仿佛是被嵌在一个画框里,只寥寥几笔,却意境深远的水墨画。
恍惚间,仿佛回到了百年前,还是这般景象。雨在淅淅沥沥地下,树上的叶不多,枝干极为挺拔。长长的青色石板街如水一般温润。在那蒙蒙烟雨中,撑着一把油纸伞的女子,袅袅娜娜地走来,颇有几分水乡的柔情。
刹那间,千百年的时光流转,如马儿迍行,车儿快随,一念雕栏画栋,一念繁华都市。只是苍坡却好似从未改变村落的古韵,变的,只不过是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