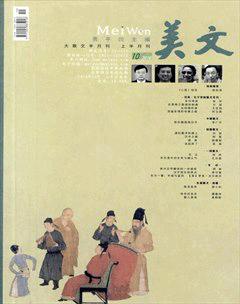瓯苑
袁冰婕
或许是受了老一辈人的影响,打小我便热衷于听戏。每当村里祭祀祖先或是迎财神时,最让我期待的就是所请的戏班子了。
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古老的风俗受到物欲横流世界的冲击,村里不再常请戏班子唱戏了,可我迫切听戏的欲望却愈演愈烈,在我心中久久不散。
许是偶然,那日原想去文成百丈漈游玩,却意外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戏班。
在巴士上睡了足足两个小时,走下车的一刹那,朦胧的睡意被一阵清新的空气驱散得不剩丝毫。或许是因为清晨的缘故,迎面扑来的清风中混杂着些许翠叶晨露的味道,耳畔有隐隐的锣鼓声。
循着声音的源头找去,踏着这覆满青苔的石板,穿梭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夹杂着几分空灵之感盘旋在天际,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山路上陆陆续续地走下几个带草帽的老伯,我上前打听,一位老伯操着浓厚的地方口音,热情地说了许多,不过也才理解了个大概。这条路的尽头拐角处有一个大戏台,而这里上演的大戏,就是传说中的温州名萃——瓯剧。
枝头的露珠依稀与微红的日光融为一体,我们也终于来到这个隐蔽的戏台。
其实,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复式四合院,门口挂着一块似乎已有些年代的牌匾:瓯苑。虽然简洁,却显得苍劲有力,而里屋便是那声音的源头了。可这声音却不像之前那般清脆悦耳,竟显得有几分急促、粗犷。伴着乐曲的渐速加快,我们一行人似乎也融入其中,心也随之慢慢紧绷,随着最后的一声“昆调”,一切又复归平静,雷鸣般的掌声渐渐响起。
台上的演员依旧定在那里,保持着之前的动作,似乎是沉浸在刚刚演完的戏里,久久不能走出。站在一旁的几位老伯见到我们一行人进来,急忙热情地将我们安置在外侧的木质长凳上,摆出一个动作,示意我们继续听。
一个红衣女子走出来,老伯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们说,接下来要唱的这出就是他们这里最有名的《高机与吴三春》。只听见一阵婉转的黄梅弦逐渐传出,之后便是一百八十度的急弯转到了高腔,台侧光着膀子的大汉们,用粗犷的声音在一旁随声喝唱,如此交杂中顿时又混了几种与众不同的声腔。老伯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乐呵呵地说:“这就是瓯剧与其它戏剧最大的不同之处了,这叫作正乱弹的反乱弹,总归为乱弹腔,它们是由温州官话和方言组成的,尤其是在转调的宫调交换上更是与众不同。”
喷薄的日光静静地照在演员们的脸上,粉彩也更添了几分神韵。
老伯依旧在耳边断断续续唠叨着,而此时唯有台上的文武交替才让人入迷。一曲唱罢,身旁竟也坐了些许似我们这般看戏的游客,而二楼的廊道上也坐满了喝茶听曲的人。又是一番痴醉,那乱弹腔的宫调转换依旧回荡在脑海,想必这便是瓯剧的魅力吧。
此时,正午的太阳已升得老高,我们也已饥肠辘辘。老伯说二楼可以尝试一下文成的农家特色。我们便径直去二楼的半露天茶座解决了午餐。或许是因为坐落于山里的缘故,这儿的野味十分鲜美,就连一盘干花菜也独具一格,价格也低于普通餐馆,一行五人才吃了百余元钱。午饭后,我们又欣赏了几首小曲,由于时间原因,不得不下山返家。
回首再望望那苍劲的“瓯苑”,带着不舍,看着它渐渐消失在了薄日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