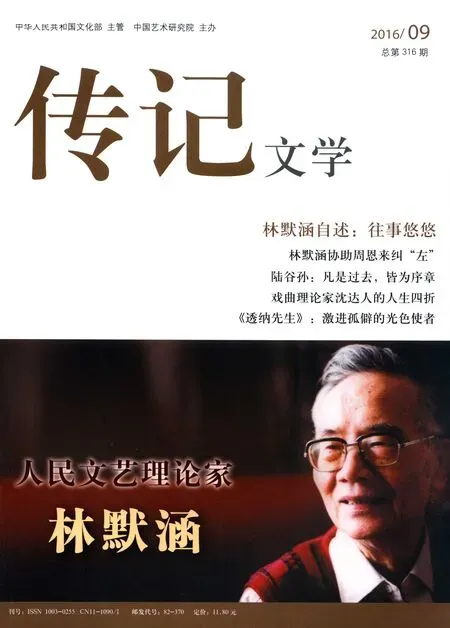张恨水传选章三
文|解玺璋
张恨水传选章三
文|解玺璋

生计
民国六年(1917)深秋,张恨水回到故乡。在上海既找不到出路,总依靠郝耕仁接济,也不是办法,何况郝耕仁也要离开上海了,芜湖那边的报馆要他回去做编辑。
这一年,张恨水已经22岁。虽还年轻,但他是长子,父亲不在了,他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对这个家负有责任。这时,母亲已年过四旬,三个弟弟,大弟张啸空19岁,二弟张朴野、三弟张牧野(孪生兄弟)12岁;两个妹妹,大妹张其范14岁,小妹张其伟只有8岁。这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不说,弟妹都要受教育,而经济来源是没有的,从祖父那里分得几亩田,实在承担不起教养子女的重负;父亲留下的遗产,能卖的卖了,能当的当了,日子越过越艰难。对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来说,即使她心里想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应该能帮帮自己,恐怕也是难以启齿的,何况她深知自己儿子一向是心高气傲,绝不肯屈就的,更不想因此给儿子的未来留下什么遗憾。而张恨水似乎也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在经济上给母亲一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
此时的张恨水,除了继续做自己的才子梦,在生计方面可谓一筹莫展。或者他以为,眼下自己只是怀才不遇而已,如果给他机会,他是不会无所作为的。乡里人看他这个样子,都嘲笑他是个无用的人,叫他“书呆子”,有人甚至说,如果读书读得像张恨水这样,宁肯让孩子放一辈子牛,也不让他去读书。但张恨水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也无心与乡民们深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还像往常一样,把自己关在“黄土书屋”中,磨砺学问,对古文尤为用力。家里藏有不少林译小说,这时也被他拿出来反复把玩,悉心揣摩。林译小说用古文,时称“雅言”,其中古朴顽艳的笔墨,很对他的胃口。对他来说,读林译小说,既是赏心乐事,也因此得到不少关于西方文学的知识和写作手法。
就在他躲进“黄土书屋”享受读书之乐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却并不安生。这一年的三月,北方的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的统治被推翻了,建立了临时政府;到了冬天,十一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又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六月有张勋复辟,清废帝溥仪上台,只坐了十天皇帝,就被段祺瑞赶下了台;七月,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名,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南北再次陷入战争状态;八月,段祺瑞政府宣布“对德宣战”,中国加入协约国,抓着“一战”的尾巴,争取到一张进入巴黎和会的“门票”。
如果说这些都离他较远,那么, 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却不能说与他无关。一月,他的同乡,大他四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章从八个方面论述文学改良所应注重的八件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件事,以第一件事为纲领,提纲挈领,拎出下面七件事来,核心便是一个“物”字,他特别指出:“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他把无此二物之文学,称作“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他认为,对于文学的发展变化,当“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主张“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他谴责刻意摹仿古人,做无病呻吟状的文学,是“亡国之哀音”,老年人尚不可为,少年人尤不应为。
胡适还算是客气的,他以一种书生气的温文尔雅,建议对这个有研究之价值的文学上的根本问题,进行“直言不讳之讨论”。而他的另一位同乡,同为安庆人的陈独秀(又称怀宁人,历史上怀宁又名安庆,与潜山相邻,怀宁县治所在地就在安庆),绝不认为有讨论的必要。《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章宣称:“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所谓吾友,就是胡适。他明确提出“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同期还发表了他与陈丹崖、钱玄同、常乃、程演生讨论新文学、古文与孔教、国学与国文等问题,以及与叶挺讨论道德与科学问题的通信。
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被后来者认为是唤起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胡适也为他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起的作用而感到骄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便把自己的主张称作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文章发表后,他很有些自豪地看到:“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最初,实事求是地讲,他所谓响应,无论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其实只限于大学教授和一些进步学生,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这个小圈子。那时,蔡元培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主张兼容并收和学术自由的,许多观点分歧的教授都被他网罗任教于北京大学,陈独秀就在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胡适也在回国后不久,即九月十日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这些知识精英的风云聚会,固然使得“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却也引起校园内和社会上一些保守的教授和学生的不安和愤慨。不过,他们的反抗相当消极,大约他们以为,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自清末以来,就不断有人在提倡,并不新鲜。所以,当钱玄同附和胡适之说,并点名批评林纾后,林纾也只是站出来说“古文之不当废”而已,以至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叹息,认为不足以“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而不免“大失所望”。因此,《新青年》的编者甚至不惜假造一封读者“王敬轩”的来信,以充当批判的靶子,挑起论争,似乎不如此,他们的许多见解就不能尽情发挥。鲁迅便从这热闹里看到了他们的寂寞,当时,他正寓于绍兴会馆钞古碑,《呐喊·自序》讲到钱玄同(即金心异)来向他约稿时的情形,他且言道:“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暂居于老家潜山闭塞乡村的“文学青年”张恨水是否注意到了这场讨论。不错,他一直很喜欢古典诗文,在诗词、骈体文的写作上下过一番硬功夫,可他绝不排斥白话文。他读过许多小说,无论新旧,也还是以白话居多。他写小说,作诗文,更是白话、文言兼顾,并不特意标榜哪一种。不能说社会上流行的新思潮、新风尚对他没有影响,但他绝不会跟风骂什么“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生活经验告诉他,这个社会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军阀横行,豺狼当道,底层百姓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他为此而感到愤慨,并对穷苦百姓报以深深的同情,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认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他所钟爱的古文,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可见,胡适、陈独秀们的问题并不能成为张恨水的问题。对张恨水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选择文言还是选择白话,而是如何摆脱目前这种无所事事的窘况,找到一份可以维持生计,能够自食其力的事做。回到家乡两个月(一说半年)后,张恨水收到郝耕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在上海分手时,张恨水的小说《未婚妻》放在他的网篮里,被他带回了芜湖。他把小说拿给朋友们传看,大家都说写得好。无锡《锡报》的编辑不仅拿走了小说稿,甚至提出想请张恨水去报社帮忙。信中还说,芜湖的《皖江报》(即《皖江日报》)原想请他回去当总编辑的,他因为开春要到广东去(一说去湖南),很想把这个机会让给张恨水。
小说有人赞赏,张恨水自是一喜,凭空得到一个职位,更让他喜不自禁。他太需要这个职位了,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职位,不仅个人生计问题有望解决,搞好了也许还有余力帮衬家里,岂不两全其美?而且,报纸编辑并不辱没于他,对他来说,倒像是一条新的出路。从这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他相信,那必是一种新的生活。高兴之余,他仿照《未婚妻》的笔法,又写了一部《未婚夫》。
过了残年,凑了3元川资(一说向母亲要了4元钱路费),张恨水便动身到芜湖去了。因为有郝耕仁的推荐,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张恨水说:“《皖江报》的编辑张九皋领我会见了谭经理,他们信得过郝耕仁,也就信得过我。分派给我的工作是每天写两个短评,还要编一点杂俎,新闻稿子缺少,就剪大城市报纸,工作并不难。”这是张恨水报业生涯的开端,他的小说连载于报纸副刊,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谭经理大名谭明卿,《皖江报》是他与张九皋共同创办的,他任社长,张九皋任总编辑。当年的内地报纸,除了几条本地新闻,几乎全靠剪刀和糨糊,副刊也不例外。但年轻气盛而又酷爱写作的张恨水不想这样做,他接手《皖江报》副刊之后,希望能改变这种状况,开创出新的局面。他先把早年的一篇习作文言言情小说《紫玉成烟》拿来,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连载,此外,他每日还撰写一篇小说闲评,又另外找了两个朋友的笔记,也刊发在副刊里。没想到,“这个举动,在芜湖新闻界,竟是打破记录的”, 不仅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还吸引了许多人给报社投稿。多年后他主政《新民报》北平版期间,还忆及当初在《皖江报》时的情景:
三十年前,与大颠(郝耕仁)同编《皖江报》,予看大样,时有错字。大颠立在编辑桌上,填半阙《丑奴儿》调予曰:“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酸,眼也睁圆,谁写糊涂帐一篇?”予亦于纸角立答半阙曰:“一刀一笔一浆糊,写也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大颠笑而佳之曰:“实也。”此等游戏,难求于今日之编辑部矣。
更让他备受鼓舞的,是小说“很得一些人的谬奖”。房东对他的小说闲评大加赞赏,房东太太却喜欢看他写的小说。于是,他乘兴又创作了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逐日在报上连载。如果说《紫玉成烟》只是他小试牛刀,那么,这部《南国相思谱》就是他作为未来小说家在文坛的首次亮相。据说,后者曾受到《花月痕》很深的影响,看来也是个“描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才子佳人故事。区别仅仅在于,一个讲的是老才子佳人,一个说的是新才子佳人。《花月痕》流行于清末光绪年间,是一部所谓“狭邪小说”(鲁迅命名)。在中国小说史上,这是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角的长篇叙事作品。作者魏秀仁,要借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两对人物的穷达升沉,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即所谓“一泻其肮脏不平之气”。蒋瑞藻《小说考证》采用《雷颠随笔》的说法,称赞《花月痕》“笔墨哀艳凄婉,为近代说部之上乘禅”,并为后半部的“蛇足”而深深感到惋惜。至于张恨水的《南国相思谱》以及《紫玉成烟》,目前还在历史深处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我们的发现,作者在小说中写了什么,写得怎样,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也难以同《花月痕》作更多的比较。但读者反响十分热烈,他也在当地得到了善写小说的声誉。多年后,张恨水谈到《南国相思谱》,觉得书名过于艳丽了,便有些言之赧然,很难为情。他说:“记得这时,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中,论起来,十分落伍的了。”这部小说采用章回体,文字有点偏重于辞藻,回目的制作也刻意追求工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花月痕》对他的影响。
这样一来,张恨水就在芜湖住下了。报社包下了他的食宿,每月还有8元薪水,他既衣食无忧,也就不再作非分之想。报社的伙食相当好,大家对他也很客气,他还有自己的房间,用功而不受干扰。他从家里带来一部《词学全书》,一部《唐诗十种集》,放在床头做闲读之用。每天晚上,作罢两篇短评,便和几位同事到街上去玩,有时吃碗面,或再来几个铜板的熟牛肉,就是宵夜了。多余的工夫,他就用来写小说。回忆起往事,他写道:“我先写了一个短篇,叫《真假宝玉》,是讽刺当年演《红楼梦》老戏的,试寄到上海《民国日报》去。去后数日,编者很快来信,表示欢迎。因之,我又写了一个中篇章回,叫《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也投寄给《民国日报》,他们连载了将近一月,竟引起上海文坛很大注意。这两篇都是白话体,前者约三千字,后者约一万字。后来这两篇小说,被姚民哀收到《小说之霸王》的集子里去了。”
这两篇小说分别于1919年3月10日至16日、4月13日至5月27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解放与改造》(一说《民国小说》)上连载。前者借宝玉之口讽刺那些在舞台上扮演贾宝玉、林黛玉的演员,气质、禀赋都与作者心目中的宝玉、黛玉相差甚远。比如欧阳予倩饰演林妹妹,他写道:“黛玉是个国色,一双眼睛本来是像秋波,这个却是近视眼,那面孔更不必说了,还不如小丫头四儿。”对梅兰芳他还比较客气,说是“像这家伙充妹妹还勉强对付过去”,但他对妹妹葬花时“树上花上亭子上统统扎了五彩电灯”深感不解,倒是这位饰黛玉的向他解释:“你不知道呢,现在凡是我出来的地方总有彩灯的,这有什么稀罕呢?”再看几位宝玉的扮演者,更加惨不忍睹,查天影“神情却一脸滑气,加上个钩鼻子,一点儿不像自己”;陈嘉(一说喜)祥呢,“把他放在屠案子上去秤秤足足的有二百四十斤,一双肿眼泡,一张阔嘴,却装着声音嫩声嫩气的说话”;还有那位麒麟童(周信芳),倒像“喝醉了酒的焦大一般”,听到林妹妹叫他,“破锣也似的答应了一声”。显而易见,张恨水在这里用了滑稽、幽默的笔调,对伤害自己心中偶像的艺人给予了相当尖刻的调侃和讽刺。
后者《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也是一篇讽刺小说,如果说前者只是讽刺了几个京剧艺人的话,那么,后者讽刺的对象却涉及到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人物。小说仍采用章回体,只有九个回目,主人公小说迷显然是作者自况,他借小说迷梦游地府,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文坛、作家和出版界种种的丑陋乱象,最后还借地府小说家痛打斯文败类阮大针,武人马士英出面干涉,把他也当作乱党抓去,执行军法,痛斥了北洋军阀的卑劣和残暴。有人用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比附现实,认为书中的“主战军”当指主张参加欧战的段祺瑞政府,而阮大针则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化身。从小说发表的时间来看,是在五四运动之间,然而,他的写作、投稿却在此之前,很难设想他知道五月四日那天发生的故事,并把它写到自己的小说里。小说家痛打阮大针,马士英率兵相救,与学生痛殴章宗祥,警察赶赴现场镇压,只能说是偶然的巧合。但是,他借地府召开“古今小说评论大会”,要选举会长、副会长,让金圣叹说出“我们纯粹是学术上讨论,犯不上朱陆异同,新旧思潮的闹党见”这一番话,也算是对这几年《新青年》闹文学革命,要置旧文学于死地的一种回应。在这里,他表现出来的对党争、党见的极度反感,成为此后几十年里他的基本态度,一直延续到晚年。
接连两篇小说在《民国日报》连载,引起了上海文人,特别是旧派文人对张恨水的注意。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姚民哀在编《小说之霸王》的时候,便将这两篇小说一并收入其中。虽然他一再表示,最初写小说不是为了挣钱,“当年写点东西,完全是少年人好虚荣。虽然很穷,我已知道靠稿费活不了命,所以起初的稿子,根本不是由‘利’字上着想得来。自己写的东西印在书上,别人看到,自己也看到,我这就很满足了”。而实际情况是,他那时并不富裕,说不是为了钱,何尝不是文人的虚荣在作怪呢?如果有稿费,他自然也很受用。可惜当时办报,经费是没有保障的,即使刊载了作者的文章,常常也是不给稿费的,特别像他这种刚刚在文坛上试探手脚的新人,得到稿费的机会就更少了。
不给就不给,他在朋友圈里的名气却与日俱增。同事李洪勋就很欣赏他的文才,曾劝他说:“你老兄笔墨很好,要是到大地方去,是很有前途的,何必在这里拿8元一个月呢。”据说,老板谭明卿听到这种议论,便想了许多办法笼络他,不仅答应给他的月薪增加到12元,还许愿说,将来一定为他在皖南镇守使马联甲那里谋个差使。此时已是民国八年(1919)的春夏之交,这期间,他有过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受到很大的刺激。回到芜湖,他发现人们的革命热情一点也不比上海逊色。他所在的《皖江报》已从5月16日起停刊日商的广告、船期和商情。17日,芜湖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一致抵制日货。18日,栈业公会也做出决定,不再代售日本船票,不上日轮接客,拒绝日本旅客;划船帮也决定不再接送日轮旅客。19日上午,在芜湖开药房的日本商人到街上散发传单和仁丹,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下午,愤怒的群众向日商丸山药房投掷砖瓦,砸毁了药房的玻璃,在芜湖的日本商号因此暂停营业。22日,日本驻南京领事清野长太郎到芜湖,向当地政府提出赔偿,并要求惩办有关肇事者。6月3日,日军舰嵯峨号驻防芜湖,并派遣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到芜湖城里游行示威,并在丸山药房前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这种挑衅行为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张恨水也不甘落后,在他的鼓动下,报社同事二十余人,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针锋相对地走上街头,还特意在丸山药房门前往返数次,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以示抗议。多年后,有人写文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丸山药房(日本人的买卖)斜对面就是皖江日报社,这时小说家张恨水(该报副刊编辑)吃了两杯雄黄酒,爱国热情不禁沸腾起来,提议吃饭后也到马路中间去三呼‘万岁’。全社职工二十多人一致同意。由张恨水掮着旗子,大家突然从社内跳跃到街心,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后,立时退入报社。”
张恨水终于完成了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唯一的一次“壮举”。他的认识固然很幼稚,行为也许还有点滑稽,但他毕竟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他也有一腔爱国的热血。当然,他和激进的革命青年是不同的,当他们走向街头广场,用暴力和血腥向旧世界宣战的时候,在古典文学的熏陶中成长起来,本就装了一肚皮诗词文章,性情和做派总有一点书生气,或曰才子气的张恨水,还是更向往书斋。这时,他的梦想是到北京大学去读书,继续他的学业。他听说,有几个朋友“都进了北大。他们进北大,并非是考取的。那是先作旁听生,作过一年旁听生,经过相当的考验,就编为正式生了”。这样一条捷径摆在那里,他当然想试试:“我想,我还不失求学的机会,我在芜湖这码头上住下去,什么意思呢?于是我一再的向社方请辞,要到北京去。”
民国八年(1919)秋天,张恨水辞去《皖江报》编辑的职务,来到北京。他没有先去北京大学,而是先找了一份营生,把自己安顿下来。张恨水最初是在一个叫王夫三的朋友鼓动下来北京的,到北京后,人生地不熟的他,只能先去找王夫三。王夫三,又名王尊庸、王慰三,安徽歙县人氏,曾任《皖江报》《工商日报》驻北京特派员。民国二十二年(1933)任《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时被人暗杀。当时,张恨水写了《哀老友王慰三君》一文,透露了王氏鼓励他到北京求学、发展的一些细节:
民八在芜湖,与恨水会于某报社(《皖江报》)。时恨水方二十许,好谈革命。王笑曰:“君傻子也,然君文笔尚可,加以造就,未可限量。何株守于此?”既而君北上,供职参战军督练公所,招恨水北上。恨水质衣被入京,拟入北京大学。然一身之外无长物,何以言读书?君原住歙县馆,以其居居我。恨水无衣,君曰:“我入军需学校,有制服,敞裘一袭,可赠君。”恨水无被褥,君曰:“军需学校有公用军毯,被褥二事,亦可赠君。”恨水感泣,至无可言喻。古人谓推衣衣我,不是过也。旋以君之介,为老友名记者秦墨哂君助理笔墨,稍可自活,而读书终无望,君乃为之叹息不置。时恨水穷,君亦仅足自给,非在学校。早起,仅苦茗一壶,烧饼油条一套。或至黄寺督练处,或至学校,来回数十里,风雪交加,无不步行。其勤苦又如此。
由此可知,张恨水的北上京城,以及到北京后的生活,最初都靠了王夫三的慷慨援助,第一份工作也是王夫三帮助联系的。来北京之前,为了筹集路费,他把冬天穿的皮袍子送进了当铺,还从一位卖纸烟的桂家老伯那里借了些钱(一说10元)。他是搭乘津浦线列车赴京的,刚到北京时,就寄居在王夫三所住的歙县会馆,不久则迁往潜山会馆。王夫三把当时负责《时事新报》驻京记者办事处的秦墨哂介绍给他,而这个办事处只有秦墨哂一个人。对于张恨水的到来,他表示很欢迎,工作是每天发四条新闻稿子,新闻来源由办事处提供,月薪10元,如果稿子多,还可以外加。他还预支了一个月的薪水给张恨水。拿到钱的张恨水马上赶到邮局,给芜湖那位借钱给他的桂家老伯寄去10元钱。
就“北漂”而言,张恨水算是幸运的,初来北京,不仅有住处,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薪酬虽说不多,却也足够应付会馆的饭钱和房钱,而且,“一切不用自己操心,自己可以用功,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全书》。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阙。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但他似乎已经忘了来北京的初衷,是要进北大读书的。有一天,他在交过房钱、饭钱之后,还剩下一块现大洋,怎么花呢?“恰巧这时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合上演,这当然是好戏,我花去了身上最后一块现大洋去饱了一下眼福耳福”。
这是张恨水一生中不多的“有钱”而任性中的一次。他在芜湖办报期间结识了一个朋友,叫方竟舟,也在报馆工作,是个年轻的老资格,后来与张恨水因办报而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成舍我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引导他走上新闻之路的启蒙老师,就是方竟舟。这天,方竟舟来到张恨水居住的潜山会馆,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口袋里听不到钱响了,大概缺钱用了吧?有个朋友在《益世报》做事,想找一个人打下手,你去不去?
张恨水后来回忆,他在秦墨哂那里,“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而“在《益世报》是晚间十时到天亮六时”, 时间既然可以安排,而他又“很愿意兼个差事,就答应了”。很愿意的原因怕是10元钱在北京生活总是捉襟见肘,他需要另外开辟经济来源。而更深层的原因显然是家里弟妹们都进了学校,越发需要他的经济援助。于是,他便进了《益世报》,去做成舍我的助理编辑,月薪30元。“说是助理编辑,其实是校对,我的职务,乃是看大样”, 多年后,张恨水还特意作此说明。
关于张恨水与成舍我的相识,还有一种略带戏剧性的说法,中间人也是这位方竟舟君。据说,他来到张恨水的住处,随手拿走了张恨水刚填好的一阙《念奴娇》。过了几天,他又来见张恨水,进门就说,那阙词被一位朋友看到了,大为倾倒,读其词,便想见其人。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他们因此而订交,合作长达十年之久。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天,他们在上海《立报》还曾再度合作,由张恨水出任该报副刊《花果山》的编辑。这阙词七年后发表于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晚报》副刊《明珠》:
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憔悴旧时歌舞地,此恨老僧能说。旭日莺花,连天鼓吹,霎都休歇。凭栏无语,孤城残照明灭。
披发独上西山。昂头大笑,谁是封侯骨?斜倚长松支足坐,闲数中原豪杰。芥子乾坤,蜉蝣身世,坠落三千劫。怆然垂涕,山河如梦环列。
这是一段很不错的文坛佳话,我们当以“姑听之”而对待之。实际情况如何呢?民国七年(1918),成舍我辞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职务,来到北京,初衷也是入北京大学深造,因无中学毕业文凭不能报考,他便主动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蔡元培,陈述自己的求学愿望,请校长给予通融。蔡元培读了他的信,觉得这个青年文笔通畅,言之成理,故准其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旁听生。这里可以看出他与张恨水的不同。为了维持生活,又请李大钊介绍他到《益世报》工作,而且去了就做总编辑,写社论,编副刊,看大样,就一个人。北大旁听期间,他已感到很累,担心身体吃不消。民国八年(1919)九月,他考取了北大正式生,更感到个人精力的不足,不得不向经理杜竹萱请求增加人手。在得到杜经理的谅解后,他开始物色能够帮他分担工作的人物。
方竟舟之于成舍我,不止是他新闻从业的引路人,当年,他父亲成心白因舒城监狱囚犯暴动一案,遭人诬陷,正是方竟舟的父亲,时任上海《神州日报》驻安庆访员的方石荪,多方调查取证,并由其子方竟舟写成文章,在报上披露了囚犯反狱的真相,为之洗刷了不白之冤。他们这种不一般的交情,自然可以让方竟舟觉得有义务帮他“找一个人打下手”;而方竟舟的心里恰好便有张恨水这个人,且了解他的才学,知道他眼下的窘迫,所以敢直接问:“你去不去?”而成舍我既在《民国日报》做过编辑,又与张恨水的故交刘半农打过交道,大约对张恨水也曾有过耳闻,接受他并不困难。
就这样,张恨水进了《益世报》。这是一家天主教报纸,创办人是比利时籍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神甫雷鸣远,主报设在天津,北京是它的分馆,由杜竹萱担任分馆经理。多年后,张恨水还记得当时的情形:“除了总编辑成舍我外,有吴范寰、盛世弼、管窥天和我几个编辑,还有两个校对,另有主笔一人,每天做一篇社论。”张恨水的工作是负责看大样,后来,看大样又增加了一个人,工作减少了,月薪也减少了,减为25元。
这样维持了大约一年之久。工作之余,他还在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自修英文。他的嗓门本来就很大,偏又喜欢高声朗读,终于引起同院住着的经理新太太的反感,于是,杜经理调他担任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他便从位于新华街南口的益世报社搬了出去。恰好这时秦墨哂办了一家世界通讯社,约他做总编辑,因为有房子住,又有水电供应,可以解他的燃眉之急,他便欣然接受了。不过,谈起那时候的通讯社,他却显得十分无奈,“一个新闻机关,没有邮电的新闻来源,也没有外勤记者。除了社长在茶余酒后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新闻而外,并无新闻稿子供给”。他问自己,“我这总编辑是怎样的当法呢?我没有那胆量天天造谣,我也不能把我所得的一点新闻,全部送给通讯社。我得了社方的谅解,只是找些内地各省来的报,改头换面,抄写几段。这自然是不忠实的。但绝对没有造谣,倒也问心无愧”。就这样干了几个月,他决计不再干这闭门造车的新闻,又从这里搬走,回潜山会馆去住了。
他担任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任务是每两天写一篇通讯,薪水也补足到30元。对他来说,不必每天夜里看大样,其实是一种解脱,使得他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所以,当芜湖《工商日报》请他担任驻京记者时,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期间,他结识了几位上海记者,于是,《申报》和《新闻报》也来约他写北京通讯。他后来回忆道:“这两家报馆,对于北京通讯,极肯花钱,一经取录,每篇通讯拾元。材料好,写上篇通讯,是不会费一小时以上的工夫的。我也为了人家的报酬丰厚,抱定不拆烂污主义,有材料才写,没有材料决不敷衍成篇。而且写的时候,将一篇文言,总写得它十分清楚流利。于是在‘新’‘申’两报方面,信用都很好,写去的通讯,很少不登的。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收入算是相当丰厚了,在当时,这也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数目,当然,他也做得相当辛苦,每天从“上午九点钟起,到下午五六点钟止,我少有空闲的工夫”,他这样说,“由民国八年(1919)秋季起,到民国十年(1921)冬季止,我就这样忙下去。其间只是十一年(1922)的旧历年,我回了一趟芜湖,探访母亲,此外没有离开北京”。
他这样忙,就是为了给弟妹们筹措学费。那时,他已托二弟把家眷送到芜湖居住,郝耕仁的女儿郝君仪回忆往事时说:“恨水先生到北京在《益世报》当记者,两三年后收入渐丰,一九二二年他托他二弟把家属接到芜湖安家,由我父亲照料。我父亲也把母亲和我接到芜湖住家。父亲为了照顾方便,就把两家合为一家,在芜湖太平街租了一所住宅,雇了一个女佣,在一锅吃饭。恨水先生一家六口(他母亲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及一女眷)。”这当然会增加日常生活的开销,而弟妹们读书更需要一大笔钱。张恨水深知失学的痛苦,所以,他绝不肯让弟妹们失学,他说:“所以我把在北京得到的薪资,大部分汇到南方去,养活这个家,也唯其如此,我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没有心情,也没有工夫,再去搞什么文学。”
作为长子,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张恨水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兴趣和志向。那几年,除了民国十一年(1922),应芜湖朋友之邀,写了一部表现安徽自治运动的白话章回小说《皖江潮》,并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外,再没有写过小说。至于到北京大学旁听一事,自然更不再提起了。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