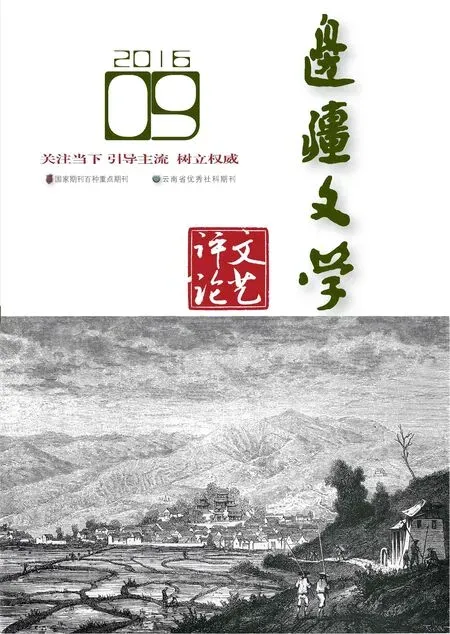《海滨故人》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困境解读
◎段晓丹
《海滨故人》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困境解读
◎段晓丹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唤醒了一批女青年的个人意识,她们逐渐走出封建传统的桎梏,走出家门,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与事业,以前不曾察觉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由旧而转入新的进程中暴露出来。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手写我口”,创作出一大批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如陈衡哲《小雨点》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冯沅君《卷葹》凌叔华《酒后》等,庐隐也是这批女作家中的佼佼者。茅盾在《庐隐论》中指出:“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1]这只“苦恼的夜莺”唱着忧郁的歌,“垂泪”“落泪”“哭泣”之类字眼频繁出现在文本中,庐隐的写作以细腻、丰富的女性心理描写见长,表现了女性个人意识觉醒后渴望着实现自我价值和自由之爱,以及在这追求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个人理想与外界压力的冲突,对于爱情的困惑与彷徨,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事业与家庭之间的两难选择和对未来的憧憬与忧虑等等。
一、个人意识的觉醒
《海滨故人》的几位主人公都是青年人,青春期和新婚后关于爱情的琐碎幽微体验处于文本情节绝对的中心地位,“导向婚姻的事件或是摧毁爱情的事件占据了有意义的事件的位置”[3]宗莹虽然和师旭结婚了,然而也赔了许多的眼泪,行动改了前态,病后精神更加萎靡,生育小孩后,更不能出来服务了。婚前的雄心壮志,结婚后已消磨殆尽。婚前因为追求自由的爱情受折磨,而婚后又失去事业心,就像伍尔夫所表述的,“因为她每天都做饭,洗盘子和杯子,送孩子上学,然后送他们走向世界。这一切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一切都消失了”,[2]这是宗莹品尝的爱情与事业的悲剧。云青放弃了和蔚然的爱情,埋首家庭,侍奉母亲,教养弟妹,把自己置于无地。一颗失却自我的心,如何能够奢谈快乐?因此当面对挚友时,云青借小说《消沉的夜》表露出自己真正心迹。这千回百转的愁肠,牵绊着云青,而她始终不能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只是默默地拿起家庭伦常孝悌之义来障目,自欺欺人,暗自饮泣。因为传统与家庭的束缚,失却爱情及至失却自我,这是云青的悲剧。看似最幸运的玲玉也被设置了一个尴尬的背景,她所恋的剑卿是结过婚的。强加于剑卿的旧式婚姻几乎要断送了三个青年的幸福,幸运的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最终摆脱了困境走到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玲玉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我们都有事业上的安慰,对于这些事都可以随便些。”这些话渗透着她觉醒了的女性意识,追求爱情,但不困于爱情,努力寻找其他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作者也正是要借此言明自己的观点,爱情如此脆弱,些微的风浪便使它湮灭,因此女性必须奋起,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个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3]像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子”所传递的象征意义,要想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庐隐在《花瓶时代》得出的直接结论是:女人不能满足于做花瓶,要做人,要有独立的人格。如果说女性在爱情中的求索终究是要幻灭的,这个观点是庐隐开出的一剂药方,而这也正是她女性意识觉醒最直接的表现,她在试图建立女性自己的话语主题。
二、自白体的意义指向
《海滨故人》主要是围绕五位女性的爱情故事展开,文本中心人物的思想没有以作者的声音直接体现,而是设置了露沙这一角色,作为这群女性的核心人物。露沙与庐隐有着相似的身世背景,作者对她投入了更多的目光,将她设置成一个性格鲜明敢爱敢恨的女性。《海滨故人》的文本即是罗瑟琳·科渥德所说的“准自传式结构”[4],庐隐将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成长经历编织到文本之中,注重描写女性的内部世界,大胆写自我,刚强的露沙带有鲜明的作者个人印记。露沙在给友人云青的信中写到“在事实上我没有和他发生爱情的可能,但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外来的桎梏,正未必能防范的住呢!以后的结果,是不可预料,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罢了。”小说中的露沙除了在最后辞别的信中谈到了同梓青的爱情以外,这就是她最直接地向外界所宣告的爱情观,联系庐隐第二段备受争议的婚姻,可以说这正是她用露沙的话语来传递自己声音,露沙表现出的爱情观,很大程度上正是庐隐的爱情观。露沙面对爱情有怀疑,也有消极,她虽没有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勇敢,但也没有妥协,相信爱情能够超越束缚,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中挣脱出来到喊出“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勇敢宣言,是自由女性发出的先声。
传统的“自白体”已在小说内部出现,它尤其受到了叙述的重要性的影响,这种叙述将一系列事件和经历组织起来并赋予其意义,指向一个有意义的结论。[3]文本的几位女性都遭遇了爱情、事业的失败,最后露沙更是不知所踪,这样的情节指向的结论是作者已经意识到,这时代的爱情悲剧,不仅发生在旧式女性身上,也在觉醒了的新女性身上上演。无论新旧,女性总是被束缚、被定义和被选择,无法掌控属于自己的幸福。虽然时代早已变化,然而寻求自由的出路依旧是布满荆棘,如此艰辛。一方面是想要坚守对自由爱情的坚信,另一方面却是现实中理想的幻灭,使得作者备受打击而陷入困境之中,犹如露沙在沙滩上所结之庐,凄清孤独。
三、建立个人价值的困境
庐隐的作品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作品中少有男性,通常只是不怎么出场的配角,角色演绎也多为负面形象。“在庐隐的作品中,男人只是作为一个给女人制造痛苦的小丑出现的。当他们完成了给女人制造痛苦的表演后,便匆忙地从前台溜走,或者说庐隐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划掉,不肯让这些男人在她的作品中多留片刻。”[5]在代表作《海滨故人》的开场,几位女性在海边自由畅快的生活是庐隐作品中少见的恬静温馨的场景,而这场景里没有男性的存在。在假期结束回归社会后,她们身边都出现了男性,却也都陷入了苦闷之中。
20世纪70年代中叶,法国评论家埃莱娜·西苏指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写作被视为知识界的活动,与女性无缘。伍尔夫也指出,“直到简·奥斯丁的时代之前,小说里的所有伟大女性不仅是由男性来予以理解,而且还只是由与男性的关系来予以理解,而那又是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一个多么小的部分……”[4]庐隐在《海滨故人》中用自己的笔触塑造了不同于以往文学中常见的妇女陈规形象,女性不再仅仅是片面化天使型女性或者丑化的魔鬼,而是有着独立的思想,思考人生和爱情。在这一阅读与写作的革命性行为中隐去了男性,以此形成了对男性话语的质疑与冲击,成为她建立自我话语系统与主题的切入点,为了表现对女性个人价值的探寻,女性主义追求与社会环境的冲突成为了写作的中心要素。《海滨故人》中所描述的女性都是美丽的,聪慧有才情的,然而她们仍是遭遇了爱情和事业上的失败,这不是她们自身的问题,而是文本所描述的时代环境的原因。
有的评论认为文中人物关于知识的责问,是消极落后的表现,是思想上的倒退,真的是这样吗?文本中露沙的确发出过这样痛苦的追问:“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然而,她与梓青恋情正是由于学习了新知识产生了觉醒意识,有了思想上的契合后彼此认同,才走到一起。因此如果没有接受新思想的启蒙,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因缘际会。而这种能产生精神共鸣的爱情,也恰恰是露沙所追求的。而在现实中,庐隐本人也是这样,她与郭梦良相爱,冲破束缚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如果没有接受新思想,她或许像云青一样无力去面对这一切。虽然作家以抱怨的口气来责问知识,这只是一个人在思想上的苦闷难以派遣时发出的一句叹息,如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所论述,人的思想会有动摇的时刻,保尔会想自杀,玛柳卡特也会爱上本应被消灭的中尉。露沙的困惑正是因为她觉醒了,拥有了自我意识,确信知识有伟大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然而觉醒的她却仿佛因知识而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们都明白,这不是露沙的错,也不是知识的错,而是时代的苦闷,周遭少有能理解她的人,于是作者只能用对知识的追问来表达自己所处的困境,同时借此发出实际上更为深刻的对时代的追问,渴望有人能够关注与理解这个时代里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困境。再如宗莹,“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只过我六七年前的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来,看看不相干的闲书,作两首滥调的诗,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从四德的观念,那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没有什么苦恼了!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知识,叫我屈服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的到!”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但是却又被所谓的“知识”拖下烦恼的深渊。然而,如若让她重新选择,她真的会选择做一个安分的旧式小姐吗?他们真的会忍心放弃享受自由的生活而选择看闲书作滥调诗,且“没有一点别的思想”吗?海滨度假时五人赏月作诗,歌咏吹箫,快乐逍遥,与这段话里的“闲书”“滥调”鄙夷语气对比,就可以看得出宗莹的潜在的思想还是抗拒这种没有思想的生活的,只是被烦恼和无助蒙蔽了双眼的她,四下里找不到可以求助的对象,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能自相矛盾对“知识”发问,得出了模糊做人的妥协。
觉醒了的个人意识,刚刚萌芽,便在家庭代表的强大传统道德规范、伦理纲常力量的压迫下,开始枯萎了。“云自幼受礼教熏染。及长成已经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所以云青最终选择放弃抵抗,自愿为家庭牺牲。在家庭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对抗中,传统文化就这么轻易的胜出了,纵然已经觉醒,但仍逃不出亲情的网,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女性想要冲破层层的束缚,真正的践行自己的意愿是多么的困难,女性的平庸实在不在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时代和社会强加的符号。文本的中心人物都经历了根本上影响其生活或转变其态度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她们成为了有知识、有智慧的女性,有了明确的意识形态,而文本中她们的失败则反映了刚刚走出封建泥沼的女性普遍共有的迷茫、徘徊与无力感,作者对这种无力感的揭示,也正是一种打破困境的努力。苏雪林曾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 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出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处。”[6]
四、结语
“把自己对人生的探索,对理想的追求让笔下的人物去实践;把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探索无所得的疑惑、孤独、傍徨、苦闷的情绪完全寄之于笔下的人物情感,正是文学,形象而真实地记载和再现当时那批不满现实,积极探索新的人生的垦荒者们的思想沉浮和人世沧桑。”[7]这段评论正是庐隐作品的真实写照,文本中的各色眼泪饱含了作家对时代、对社会和对女性命运的追问、反抗以及深深的无奈。庐隐作品的不足之处,即茅盾所谓的“庐隐的停滞”[1]106。她似乎只是在一个圆形的轨道上运转,始终没能打破角色的陈规,没有脱出个人主观的心绪。但是,作为一个新时代之初的女性,她毕竟勇敢地走入了那间“自己的房子”,言说着自己,表现着时代的一个缩影,用她觉醒了的个人意识给后继者以启示,就像她自己所说,“我在那繁星之中,找到最小的一个,代表我自己,但是同时我又觉得我不止那么一点。”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邓邵生
【注释】
[1] 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01.第106页
[2]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I)[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01.第570页
[3] 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庐隐选集(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31页
[4] (英)罗瑟琳·科渥德.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M]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第77页
[5] 张根柱,曹允亮.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及其现代意义[J].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总第198期.第101页
[6]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J].当代.2000年第6期.第193页
[7] 林丹娅.试论庐隐创作个性中的“自我”[J].福建论坛.1983.03.第105页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