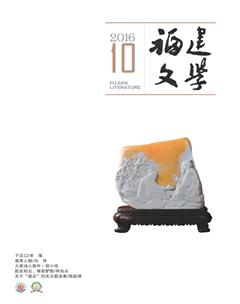关于“锅庄”的无主题变奏
◎陈歆耕
关于“锅庄”的无主题变奏
◎陈歆耕

一
这真是一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
走进这片土地,居然一次次萌发想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理智又告诉我,这是不现实的!我非如作家阿来那样生于斯长于斯,缺少在藏区生活的丰富的体验和经验。但这片土地上,无数迷人的故事,如同那奔腾不息的金川江水,不断地冲刷着我的大脑屏幕,飞溅起如雾如梦般灵感的水花。
生活经验和体验,对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四川阿坝州的金川归来后,我一直在读阿来的两部主要作品,一为非虚构的历史纪实《瞻对》,一为他的成名小说《尘埃落定》。看《瞻对》,我的目的在避免我这篇关于金川的文字,在涉及史料时与他的作品重叠。因为他所写的“瞻对”(今日名为“新龙”县),距金川仅有五六百公里;看《尘埃落定》,则想从中找到一点川藏地区生活的质感。我发现,如想寻找小说的感觉,对于我这样浮光掠影的过客,是非常困难的,也并非靠阅读大量的史料能够弥补。这部小说,在它刚问世时我即读过,留下记忆的是当时阅读的神秘感,对其中的故事人物情节已经淡忘了。近日又打开,用写作者的眼光重读。阅读告诉我,生活经验常常无法用想象来替代。第一节:“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吁吁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听说过贵妇用牛奶洗浴传闻,但在川藏地区的一位老年女性用牛奶浸手保养皮肤,却让我难以想象。因刚去过金川,我判断,这大概只有土司家的女人才有可能如此奢华吧?果然,“母亲”就是土司太太。
再读第2页:“母亲打开一只锡罐,一只小手指伸进去,挖一点油脂,擦在手背上……屋子里立刻弥漫开一股辛辣的味道。这种护肤用品是用旱獭油和猪胰子加上寺院献上的神秘的印度香料混合而成。”我闻到了一股辛辣的气味,但我绝对想象不出土司太太使用的“护肤品”,会散发出这种怪异的味道,以及这种怪味的成分。很多构成生活质感的“经验”,往往是想象力无法“填充”的。今天的科技发达到,让很多人觉得有了“百度”,可以找到无所不包的知识,似乎当一个学问家很容易。但构成生活质感的情感体验和经验,“百度”先生如何提供?
因此,虽然有写小说的冲动,但是否真的动笔写小说,我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心。那就先写一篇涂鸦式的短文,也就是这篇非虚构的《关于“锅庄”的无主题变奏》。
二
这片土地如何神奇而又神秘?我们先从地理层面看看。
在李菲博士的论著《嘉绒跳锅庄》中,对这片土地有一段描述,站在嘉绒墨尔多神山巅峰俯瞰:“由五条河流和五条山脉形成了一朵‘莲花’图案。”“五条河流从东沿逆时针方向依次为大渡河上游两大支流小金川、大金川,以及革什扎河、东谷河、大渡河;五条山脉从东沿逆时针方向依次为墨尔多山、白菩萨山高顶梁子、党岭斯达纳山、卜角顶、莫日山。”她所描述的这朵“莲花”呈现在甘孜州丹巴县境内,而其水系和山脉都与阿坝州的金川县紧紧相连,墨尔多神山矗立两县之间,金川就在这朵莲花花瓣的边沿上。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拥有共同的文化形态之一:嘉绒锅庄。
这里碰到两个概念,“嘉绒”与“锅庄”。
先说“嘉绒”:根据李菲博士论著中提供的研究成果,关于这一概念,在民间和学界有七种不同的解读,都有各自的依据。笔者不想在这里一一罗列。我喜欢其中的一种富有诗意的说法:“因其地群山环抱江河汇流,宗教界将境内墨尔多山奉为群山之主,其山全称为‘嘉莫·墨尔多’,将其山名变译称为‘嘉莫绒’或‘嘉尔木戎巴’,‘嘉绒’便是这些称谓的缩写或简称。”好,我们可以把“嘉绒”看作是一个与墨尔多神山相连的地域概念。
再说“锅庄”。从字面看,是灶台、锅台?是,又不是。是锅台,也不是我们内地汉民族使用的锅台,因为建在家中的锅台,是无法燃烧篝火,然后众人围着篝火翩翩起舞的。这里是指早期藏区牧民使用的锅台,在野外,用几块石头搭起来,铁锅就架在石头上,然后下面燃烧树枝木柴,藏民们在节日或举行某种庄重仪式时,便围绕锅台和熊熊燃烧的篝火跳舞。后来就逐步演变为一种舞蹈形式的代称。其实,“锅庄”是普遍流行于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舞蹈形式,而“嘉绒锅庄”是指流行在嘉绒藏区的舞蹈。不同地区的“锅庄”,它的文化指向,它所体现出的宗教内涵,它所折射出的文学文本意义,是有区别的。就如不同民族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一样,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不同种族的遗传信息和密码是复杂而多义的。
在今日,跳锅庄甚至不仅仅在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在我生活的南方都市,也常常看到市民们伴随《跳起欢乐的锅庄》舞曲,将“锅庄”演变为纯粹以锻炼身体和娱乐为目的的广场舞。
丙申初春,从四川阿坝州的金川县归来,当我对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川“马奈锅庄”有所了解、理解后,每每在南方都市街区听到熟悉的锅庄曲调,看到不那么标准的锅庄舞步,就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心想,锅庄的魅力是永恒的,对它保护或不保护,它都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谁不跳舞,谁就不懂得生活”——公元2世纪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歌词如斯唱道。
在人类语言文字尚未出现时,舞蹈开始了;在人类语言文字无法抵达之处,舞蹈开始了。
世界最权威的舞蹈史研究学者库尔特·萨克斯认为:
“舞蹈是一切艺术之母。音乐与诗歌存在于时间;绘画和建筑存在于空间,只有舞蹈存在于时间同时也存在于空间。”
“舞蹈打破了肉体和精神的界限,打破了耽溺于情欲和约束举止的界限,打破了社会生活和发泄个人特性的界限,打破了游戏、宗教、战争与戏剧的区别,打破了一切由更为高级文明形成的各种界限。”
“舞蹈实际上就是拔高了的简朴生活。”
金川之行,为我创造了直接体验一种具有独特风情的舞蹈形态的机会,它就是——马奈锅庄。
三
丙申三月某日,在去金川马奈乡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关于“马奈锅庄”的文字介绍。
在清代的诗文中,有多首诗写到了跳锅庄:李心衡的诗《仙坪跳月》中有“连臂踏歌”的字眼;在胡经德的诗《跳锅庄》中有“舞态回环抑复扬”的描述。在李心衡记录金川风情风物的著作《金川琐记》中,专有一节写到跳锅庄:“俗喜跳锅庄嘉会,日里当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属,罄家所有,杂佩其身,以为华赡,男女纷沓,连臂踏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调诘诎,无一可解,然观其手舞足蹈,长吟咏叹,又似有一定节奏……”这位汉族文人的记载颇有趣,他老先生不懂藏语,固然听不懂他们唱些什么,至于舞蹈形态,除了“连臂而歌”,他也体会不到那种踏步独特的节奏美感。
我不能断定他们写的特指马奈锅庄。马奈锅庄与整个嘉绒藏区的锅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还是应该把马奈锅庄放到整个嘉绒锅庄的体系中来考察。当然,我们可以把马奈锅庄看作嘉绒锅庄的重要源头或精华。有一首锅庄词唱道:“踩蘑菇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生长它的土壤;跳锅庄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产生它的地方;欢乐的锅庄来自哪里?上游马奈是它的家乡。”
在马奈乡的“马奈锅庄”讲习所,我又仔细观看了那些关于这种舞蹈的历史、形态特征的图片实物展示。我想,如果我这里哪怕用华丽的文字,再来把相同的内容描述一遍,对于读者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对于金川熟悉这种舞蹈的读者,他们会觉得我的文字是苍白的,而对于不熟悉这种舞蹈的读者,他们也很难从文字中找到为之怦然心动的感觉。如果谁想了解这种舞蹈的知识,那就请教“百度先生”好了。当然,如果要从高深的学理上考察“马奈锅庄”,不妨研读李菲博士的论著《嘉绒跳锅庄》,这部专著让我感到惊诧:一种诉诸肢体的舞蹈,居然被她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得那么深奥。
说内心话,尽管马奈乡的最高长官王庆华先生亲自为我担任解说员,我也无法感受到马奈锅庄鲜活的魅力。“纸上得来终觉浅。”古人的话是千古不衰的箴言。
我向王庆华先生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一两位会跳锅庄的美女来教舞,他说年轻的美女都离开这偏僻的山村,外出就学或打工去了,“资深美女”可以找到几个,吃过中午饭可以请她们来教你跳锅庄。
正说着话,忽然听到有音乐声传来,转首一看,对面是乡中心实验小学,孩子们正在伴随音乐跳舞。这里学校的课间操是用跳锅庄舞来代替的。但孩子们是散开的,不是正式的跳锅庄形态的手拉手式的圈舞。而舞步和甩手的姿势,却是十足的锅庄味道。我兴味十足地欣赏着孩子们的锅庄课间操。孩子们看到一个陌生人眼睛盯着他们看,用手机拍照,在踏步、甩手的同时,稚嫩的脸上露出几分腼腆的笑意。学校教导主任走来,知道我是来采访的作家,就说这不是正式的锅庄舞,如果你要看,她组织孩子们为我表演一场。
太好了。于是课间操变成了为我特意展示的锅庄舞。十多个女生组成一队,十多个男生组成一队。这仍然不是正式的锅庄舞的形态,孩子们只是向我呈现锅庄舞的一些基本样式。马奈锅庄分两种,一种叫大锅庄(藏语:达尔嘎底),一种叫小锅庄(藏语:达尔嘎则)。大锅庄只有在盛大的节庆或举行某种隆重的宗教仪式时,才会举行,其特征是跳舞者须按照要求盛装出席,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端庄隆重,气势壮阔;而小锅庄则属于民间自发舞,随时随地可跳,人数场地不限,二三人,树下,河畔,石间,青年,老年,男女,可随性起舞,表达收获的喜悦、婚庆的快乐、爱情的狂野……小锅庄是藏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野,从本质到形态都有相互交融的地方。舞者都是嘉绒藏民。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锅庄是他们表达情感信仰的肢体语言。
在舞蹈开始前,举行授帕仪式,女领舞向男领舞献哈达,没有哈达就用一方手帕代替了。此时男领舞要双脚下蹲,行三拜之礼。这一小小的动作,最能说明嘉绒锅庄带有古东女国崇尚“女尊男卑”的独特风情。孩子们的锅庄表演让我痴迷,我几乎想扔下手中的拎包,也插入到孩子们中间,与他们一起踏步、甩手、歌唱……让我感到诧异的是,那个领舞的小女生,淳朴漂亮且不说,肤色之白如同直射的阳光令人炫目。她让我想起了金川山间看到的雪梨花,花瓣上覆盖着尚未完全融化的有些晕黄的雪,白皙的花瓣隐现丝丝若有还无的红色脉络,在料峭的三月寒风中颤颤悠悠,柔弱却又倔强……
这里的海拔高度有三千多米,由于紫外线的照射,人们的皮肤普遍黝黑。但居然也有肤色如此皎白的女孩,可以化紫外线为增白的营养素,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更让我相信,乾隆年间出生在这里的美女阿扣,人们描述她的肤色如何如何嫩白是可信的。
四
写锅庄,为何要写到乾隆年间的美女阿扣?因为美女阿扣把嘉绒锅庄的美和魅力,推向了极致。而阿扣又把锅庄赋予她的美渗透到嘉绒山脉和流水之中。这样一种美产生的辐射力,曾经改写了金川的历史,影响了嘉绒藏区从土司头人到藏民的命运。
生活在金川马尔邦的年逾古稀的老人张诗茂,只要你跟他谈嘉绒历史,谈锅庄,他必然要谈到阿扣。因此,阿扣是本文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而写到她,笔者的热血几乎也要飞扬起来了。阿扣并非纯粹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在清代的野史中曾有文字记载。最著名的是那篇作者不详的文章《金川妖姬志》,此文被国学大家辜鸿铭发现,编入了《清朝野史》中。
写此文的显然是清代官员,语含贬抑。“姬”虽是古时对妇女的美称。但连上“妖”,就有些不那么友好的意味了。但从另一面也可理解成,此女是具有怎样的诱惑力。在《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可爱的美女,也是由动物成“妖”成“精”演化而成的。因此,“妖姬”二字,并不会让我对阿扣产生任何的不良感觉。
美女不罕见,美而近乎“妖”,则是百年千年难遇的极品。在嘉绒藏民心中,阿扣是圣洁无瑕的,他们称她为“玉观音”。传说她原是观音菩萨莲花座前的一个玉瓶,沐浴日月精华而转世投胎到人间。
阿扣是如何美呢?皮肤嫩白到何种程度呢?或用现代人的话,她是如何性感呢?遗憾的是那个年头,没有照相技术,藏区也没有画师,无法让我们从图片或画像中一睹她的芳容。我想,用已有的词汇诸如“倾城倾国”“沉鱼落雁”之类来描述,不会让人有什么直观的感觉。这类形容美女的词用得实在太烂了。龚自珍用诗句描写一位他心仪的美女:“一队画师其敛手,只容心里贮秾春。”是说一队技法高超的画师,面对那位美女不知从何着笔。色彩和线条,难以描画出她美的神韵。《金川妖姬志》对阿扣姿色的描述也仅两句:“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莹白为番女冠。”究竟是如何美,我也寻觅不到更精确的语汇,但可以用事实来呈现——
土司头人,为获得她的“美”,不惜刀枪火拼;
大清帝国的将领见了她,敢于将皇帝老儿的圣谕弃之一旁,而将她的枕边风,视为最神圣的指令;
为了她,达官贵人竟愿意爬狗洞钻沟壑斯文扫地;
那些驰骋疆场的清军将士,见了她,举刀剑的手臂忽然酥软,蹬马鞍的脚失去知觉……这样的女子可以“秒杀”世间所有男人,所向披靡,横扫千军!
她的美与她高超的舞姿又是相伴相随的。锅庄舞自然是她的拿手好戏,独舞也自是一绝——
她的舞姿,曾经牵动了整个嘉绒藏区土司和藏民的目光;
她的舞媚,曾经使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变得诡异莫测;
她的舞影,曾经消弭了征讨方和被征讨方的刀光剑影……
金川有此女中极品,是否与这里曾是古东女国的地域有关?有待考证。但我从民间传说和有关史料上看到,古东女国盛产美女,曾经美女如云。其中有什么奥秘?著名藏学专家李茂先生提供了一个说法,公元6、7世纪,东女国最早存在于西藏昌都地区,“专家们通过在中路乡克格依村的考察,一致认定:公元8世纪末,东女国王室发生内乱,男人篡夺了王权,女王冒着生命危险,携带旧僚巧妙逃离到金川,并在金川人的帮助下恢复了王室,东女国因此在金川复兴。复兴的东女国曾辉煌一时,但很快被历史的长河淹没。其直接原因估计是女王自己造成的:女王有一个让生下来的女子十分漂亮健康的祖传秘方,因此国内美女如云,周围其他国家为了争夺这些美女,搅得东女国鸡犬不宁。据传乾隆皇帝打金川导致古东女国的最后灭亡。”
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秘方,能够在服用后生出漂亮女子来?如果放在今天,世界首富不是比尔盖茨,而是这位女王了。但常言:最美丽的最危险。东女国的美丽药方,成为葬送自己命运的“毒药”;而阿扣年仅29岁,就魂归天国……
金川阿尔邦的老人张诗茂对阿扣的早夭有他更为深刻的看法:美,不是阿扣的错;而是那些臭男人太贪色了,他们无一不是好色之徒。
五
世界上最悲催的是什么?美的毁灭!
阿扣姑娘29岁死于非命,是流传在嘉绒藏区的最为悲催的故事。墨尔多神山曾为之垂首,金川江水曾为之泣血,琼鸟的羽毛曾化作漫天飘落的雪花……
乾隆皇帝派兵两征金川,曾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十大武功之一。第一次派兵征讨金川与阿扣有关,而战争的终结也与阿扣有关。从乾隆十一年(1746)至乾隆十四年(1749),这场战争历时4年,在金川这个弹丸之地上,清廷共用兵75000人,耗银2000余万两。虽说战争的引发和进程都与阿扣有关,但战争引发和耗时、耗力、耗财的责任,却不应归罪于阿扣。
美丽——难道也是一种错误?
阿扣,其名在嘉绒语中含义为“心肝宝贝”。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女儿,因其天生丽质聪明伶俐而得到整个族群的宠爱。在藏区土司中,他们相互间通过联姻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几乎是最为老套的方式,无论是儿子娶妻,还是女儿择婿,精心选择的对象,大都与爱情无关,而跟家族势力的扩展有关。因此,土司家族的兴衰,就常常与这个家族男人精子的质量、数量成正比。妻妾成群对于土司头人不难,但要生出一窝窝强悍的儿子和美貌女儿来延续家族的兴旺,却常常不是主观能控制的。
阿扣的命运也受到这“土司思维”的影响。看起来上下人人都爱她,但却无人尊重她心中所爱。她按照父母之命嫁给了小金川土司泽旺。魏源在《乾隆初定金川土司纪》中记载:“莎罗奔以女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这里对泽旺的描述,只用了一个字“懦”。甭管我们对这个字如何理解,反正事实是阿扣不爱泽旺,导致夫妻不和。现代学者称,阿扣因对丈夫不从,而遭到百般凌辱。魏源说泽旺“为妻所制”未必是实际情况。阿扣回娘家告状,莎罗奔则勃然大怒,派人将泽旺劫持到大金川,并夺其印信。这下事情就闹大了,家事演变为国事。大、小金川土司,都是朝廷命官,岂可相互吞并?乾隆闻奏大怒,下诏云贵总督张广泗率兵征讨大金川。官军分两路打金川,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金川一带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土司武装人员又可据“碉楼”作抵抗,张总督3万兵马,损兵折将,劳师糜饷,持续两年多,久攻不下。皇帝急了,又派大学士纳亲视事,并重新起用大将军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自效。”这三位高级文臣武将,在征讨金川过程中,因各种机缘被阿扣所迷,他们的心思不在如何平定金川上,而是绞尽脑汁要将阿扣的玉体拥入自己温软的褥衾内。这三个男人围绕一个女人之间发生的明争暗斗,足可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笔者不想在这里费太多笔墨。这里,只提供几个在阅读史料时映现在脑中的场景:
——岳钟琪至张广泗大营视察,发现张总督正在营帐中,一面享受美酒佳肴,一面观赏美女阿扣的舞姿。阿扣跳的是什么舞呢?锅庄?某种自创的独舞?是什么舞或许不重要,只要是阿扣的表演,无人不被醉倒。
——阿扣对岳钟琪情有独钟,夜里带着使女逃往岳钟琪大营,被岳钟琪藏于深山丛林中,两人频频幽会,岳将军哪里还有心思打仗。
——纳亲大人派人察知后,将阿扣诱至自己帐下。大学士一见阿扣即两腿酥软,似乎以往的人生皆白白度过,天高皇帝远,且先喝了这杯“美酒”吧。
——岳大将军为重新夺回所爱,夜里只带数骑,潜往勒乌围密林中袭取阿扣,未想到被莎罗奔的巡逻兵发觉并扣留,岳大将军贿赂看守士兵才得以逃脱,连爬带滚,逃回本营,斯文扫地且不论,还差点掉了脑袋。
……
请读者通过这些简短的文字来想象一下,再现一下这些文字背后的细节和意味,会比我来描述更精彩。比如那个岳大将军,侥幸从莎罗奔士兵看押处逃出时,该是如何的狼狈、猥琐?那个威风八面、驰骋疆场、一呼百应、道貌岸然的大将军,为了一个女人,居然颜面尽失,堕落成鼠辈。呵呵,真是可怜而又可笑啊!
在这几位朝廷命官中,最让我感到可恶而不能容忍的乃岳将军也。请看下文。
六
这场关系错综复杂的征讨金川大战,与阿扣有关联吗?有,也可说没有。
阿扣的美,延缓了战争的进程,客观上起到了救护乡亲们免遭官军屠戮的作用。可这场战争的结束,却以阿扣生命的终结作为代价。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白居易生活年代之前,他的《长恨歌》的主角,不会是大唐贵妃,而应是这位阿扣了吧?
再说岳钟琪,岳大将军。
在清军征讨金川久攻不下,皇帝对军情实况疑云重重之际,这位岳大人将军情密奏乾隆,其结果是皇帝大怒,“掷尚方宝剑斩张广泗于御前,并赐纳亲速死。”此二人死不足惜,关键是由此而置阿扣于死地。皇帝派大学士付恒赴金川军营,挂帅升帐,第一件事就是“立斩阿扣”。据传,在阿扣被斩时,天空愁云惨布,似有一口黑色的巨大的铁锅要倒扣下来。“索乌山男女二神着金盔金甲立于云端,双目如电,怒视刑场,吓得刽子手弃刀而逃。付恒见状也吓得魂不附体,遂焚香祷告,亲自斩阿扣于营前。”
这个岳大将军为了自保,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责,竟借皇帝之手,残忍地断送曾为他付出情感的年仅29岁的美丽的阿扣,这个男人还是男人吗?
从此,嘉绒藏区失去了人人喜爱的“心肝宝贝”、锅庄的领舞人。
七
锅庄的另一位领舞美女,在乾隆二次征讨金川后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里是一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同时,这里又是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且不论朝廷与藏区土司之间发生战事,就是在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展部族势力范围,也经常发生战乱,导致相互杀戮。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金川大小土司之间战乱不断,第二次派兵征讨金川。这仗前后打了13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结束。清廷投入兵力近20万人,耗银7000余万两,阵亡官兵27500人,而大、小金川幸存民众也仅剩万余人。原本牛羊满山坡的繁茂山寨,成为人迹罕至的荒山僻壤。
乾隆这次征讨金川战争进程中,并未有美女卷入。在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改变了部落命运的又一位美女,她的名字叫阿凤。关于阿凤行迹,未见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她的天生丽质以及改变部族命运的行为,却刻印在世代嘉绒藏区百姓的口碑上。
战争虽然结束了,嘉绒藏区的百姓却进入了另一种磨难。这种磨难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和痛苦,并不亚于兵戈杀伐。为使金川地区不再发生战乱,皇帝对居住百姓的种族进行了分流改造。很大一部分金川藏民被迫离开故土,被迁押至北京的郊区,安置在香山法海禅寺南沟阳坡上,让他们住在“孤燕檩单椽子”的简陋寨子里,地位列在八旗之下,将他们当作最劣等的奴隶对待。据传,还令人诅咒这些曾与官军作战的藏民200年后灭绝。可以想象,这些远离故土,生活在遭受歧视、辱骂、陌生环境中的普通藏民几乎日日以泪洗面。
改变他们命运的来自一个偶然的机缘。乾隆到香山八旗兵营观看将士操演,夜宿香山行宫。晚膳时,令宫女歌舞助兴,可那些慵懒惯了的八旗女子,实在表演不出像样的歌舞来。有人推荐金川藏女阿凤,称她美若天仙、能歌善舞,这个风流皇帝神经立马就兴奋起来。接下来的场景,未见有任何史料描述,只能凭借我们的想象了。阿凤是如何美?阿凤和她的女伴表演了哪些歌舞?其中有无表演嘉绒藏区最有特色的锅庄?在群舞和圈舞后,是否表演了她自创的独舞?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反正阿凤凭借她的姿色和出色的歌舞才能,彻底把皇帝的心俘获了。皇帝端起的酒杯,忘了往唇边送了,眼睛随着阿凤的舞姿旋转。从这一晚起,“六宫粉黛无颜色”,皇帝独钟此阿凤。
这位风流大皇帝显然真的痴迷阿凤独特的风情无法自拔了,他不满足于一夕之欢,居然要违背不得与外族通婚的祖训,要册封阿凤为妃。对此,那些维护满人族规的大臣激烈反对,皇帝大怒,执意要将阿凤纳入宫中,让她成为正式的宫妃成员之一。有大臣在祖训与皇帝的欲求间寻求平衡,献妙计曰,先改阿凤所住的寨为正黄旗小营,阿凤成为上三旗的女子,皇帝就可以迎娶阿凤为妃了。于是,阿凤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乾隆的宠妃。
金川藏民地位的提升,得益于阿凤。而藏民生活的改善也得益于阿凤。当乾隆在枕边问阿凤有什么要求时,她不求位,不求宝,不求宠,只提出请圣上善待她的那些父老乡亲。乾隆当即应允,将金川藏民的正黄旗营寨迁至沟北阳坡,为他们重建了新居,并特意建石碉,满足他们的思乡之情。金川藏民因阿凤的“枕边风”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可以想象,阿凤在金川百姓心中的美,就不仅仅是她的肤色如何,五官如何,舞姿如何了……
她是金川藏民心中的又一尊“玉观音”。
写到这里,笔者突发奇想,如果清廷官军第一次征讨金川,乾隆皇帝能够亲率大军前往,圣上就有机缘目睹阿扣那无法抗拒的风姿,那么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完全被改变,金川藏区百姓的命运大概也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结局吧?
可以断言,这个风流皇帝在面对一位千载难逢的美女时,不会比他手下的那几位大臣更理智。由于皇帝拥有至高权力,那些将军、大臣,无一人敢与皇帝争宠;阿扣的锅庄、“枕边风”,也一定能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消弭那场战争带来的祸害;阿扣自身的命运无疑也会发生变化……
八
面对这片土地上的战乱与灾难,面对那些在苦难中仍然生生不息的生命,我愿对苍天一遍遍地祈祷——
愿人间化兵戈为“锅庄”。
愿人间永远只有“锅庄”,而无杀戮。
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都是无比珍贵的。虽说每个人都是时光长河中的匆匆过客,但我们应该相互呵护,让生命在宇宙循环自然生态中走完她应有的旅程。
让我们挽起手臂,跳起心爱的锅庄,让爱与快乐永驻心间!
马奈乡王庆华先生真的为我请来了锅庄的指导老师,几位“资深美女”。她们都是面容慈祥的大娘。还有“资深帅哥”,他们是几位满脸褶皱的老汉。跳锅庄必须有男女两队人,围圈而舞。两位老汉,从两旁握着我的左右手,他们的手厚实温暖,对面是两位大娘。随着一声口令,我们一边清唱一边跳起来,歌声飘荡在溪谷山涧。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双脚踏步总无法与他们的节奏吻合,但快乐的阳光洒在每个舞者的脸上……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