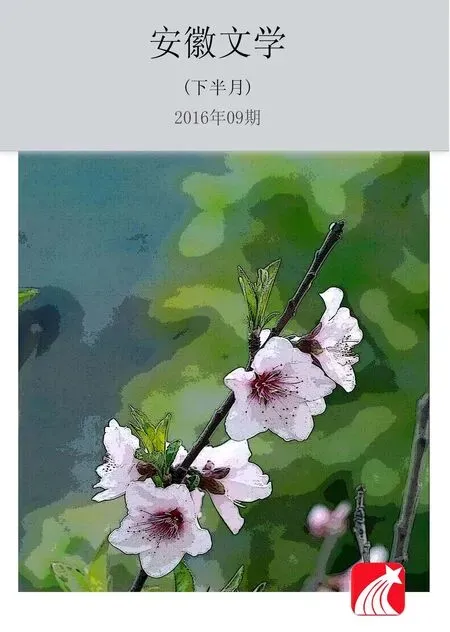从读者反应批评解读阿特伍德的《盲刺客》
左万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从读者反应批评解读阿特伍德的《盲刺客》
左万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强调文学作品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分析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中不同文本的重叠与空白,解读小说意义的开放性及不确定性,探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文本的互动交流关系。
《盲刺客》读者反应批评 读者 阅读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强调阅读以及意义的生成过程,而不仅仅关注文本本身。它以读者为中心,着重探索读者与作家、作品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强调读者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之一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强调读者对作品的反应以及对意义的重新建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空白。
正如书页上语符与语符之间的空白一样,文本中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一个章节与另一个章节之间也存在“空白部分”。这种空白并不是纯粹的“无”,而可看作是不断进行无中生有的机制。对于读者,这种空白是一种动力因素,召唤和吸引读者去想象、去填补,从而使文本各个间隔的成分相互组成连贯的有意义的单元,进而重构出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形象。
同时,这些“空白”也是作品向读者提出的问题。读者依据作品在上述连续不断的有机联系中所形成的一定关系,赋予作品意义。换句话来说,文学作品的任务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把回答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根据伊瑟尔的观点,文学作品应是文本和读者想像相遇的结晶,因此,一个没有空白或者空白不足以引起填补冲动的作品是自我窒息的作品,是没有生命的作品。
一 《盲刺客》中的空白艺术
《盲刺客》是当代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结构犹如俄罗斯套娃:叙述者爱丽丝·蔡斯在去世前的一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记录下了她当下的生活以及对过去的回忆。同时,小说中又完整再现了署名为劳拉·蔡斯,即爱丽丝妹妹的同名小说《盲刺客》(以下简称“劳拉的《盲刺客》”,以示区别)。此外,整部小说中还节选了不同时期的各种相关新闻报道。
从爱丽丝的自述伊始,读者被告知“在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6]而随后引用的新闻报道则称劳拉是“意外死亡”。正当读者疑惑劳拉的死因时,署名为劳拉·蔡斯的小说《盲刺客》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爱丽丝的自述中。劳拉的《盲刺客》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无名的男女主人公 “他”和“她”在不同的租住地点秘密幽会。同时由于劳拉的《盲刺客》省略了太多东西,包括人物的身份,故事的背景以及情节的来龙去脉,读者从故事的叙述中只能得到关于男女主人公有限的认识:“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而“他”是一个穷困潦倒、东藏西躲的穷小伙。就小说本身而言,如此多的省略和空白,使得劳拉的《盲刺客》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读者可以凭经验去填充、想象空白的部分,做出各种判断和猜想,构想自己的“他”和“她”的故事。
根据传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经验,读者会自然而然地把劳拉小说中的“她”认为是劳拉本人:没有什么能比自杀前的遗作足以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了。而爱丽丝的回忆成为打开劳拉《盲刺客》的钥匙:劳拉从小就被认为是一个敏感、乖戾、古怪的女孩。一个“古怪”的女孩能做出打破禁忌的事,也是在读者的期待之中。
一次劳工节野餐会上遇到的年轻男子亚历克斯·托马斯是爱丽丝回忆中唯一与劳拉有关的男人:两人在野餐会上在一见如故,期间,姐妹俩和亚历克斯还被当地记者偷拍了一张照片,而且劳拉设法得到了照片底片。随后小镇上出现了劳拉与亚历克斯的流言:两人被看到“一起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在市政厅旁的阵亡纪念碑附近,倚在喜庆桥的栏杆上”。所有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显示了一个隐藏的信息——劳拉可能在同一个男人约会。
而爱丽丝的记忆碎片“巧合”地重现在劳拉的《盲刺客》中:读者惊喜地发现类似野餐会上三人被抓拍的照片出现在小说的引子中,而且被“她”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他”和 “她”在公园的长椅上约会;“他”和“她”在桥下激情幽会;每次约会后“她”总是匆忙离开,等等。在这种交替出现的对话和交流中,爱丽丝的回忆和劳拉的《盲刺客》似乎不断证实着读者的猜想:劳拉就是小说中的 “她”;亚历克斯则是小说中的“他”。这样,读者眼中模糊的、黑白照片似的劳拉的《盲刺客》随着爱丽丝回忆片段的着色而显现出色彩,劳拉的形象也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
但是,这样的证实却在自述即将结束时被爱丽丝自己否定:“至于那本书,劳拉一个字也没写过。……在我那些漫长的孤独的夜晚,当我等候亚历克斯回来,以及后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自己把书写成了”。爱丽丝才是小说中的“她”,而亚历克斯仍然是小说中的“他”。至此,读者之前所有的记忆被迫重新书写:是爱丽丝珍藏着两人的照片;是爱丽丝在公园的长椅上和亚历克斯约会;是爱丽丝在桥下和他激情幽会;是爱丽丝总是约会后匆匆离开。
二 读者的期待视野与《盲刺客》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期待视野”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的显现方式具有定向性期待,即一部作品对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的定向或现在结构,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理解过程”[7]。在《盲刺客》的阅读中,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不断被超越的:各个人物形象随着文本间的交流被不断补充和修正。已有的阅读经验和即成的心理图式让读者从爱丽丝的回忆中对劳拉树立起了一个叛逆的富家女形象,但直至回忆末读者才从劳拉生前留下的练习本中获得了解劳拉的第一手资料,随之颠覆了之前对劳拉的记忆。
在劳拉生前留下的数学本上记录了一列日期和一些词。第一个日期是爱丽丝从欧洲度蜜月回来的日子,而最后一个日期是劳拉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三个月前。与日期相对应的词包括地名(阿维隆庄园、向阳游乐园、“忽必烈行宫”、“玛丽女王”号、纽约、“水妖”号、多伦多)、“没有”(No,no)和字符“X”、“O”。看似毫无关联的日期和词却讲述了劳拉被理查德,即爱丽丝的丈夫,诱奸以及怀孕的全过程。尽管爱丽丝的回忆中出现过劳拉提及的地名,但读者很难从她的自述中读到理查德对妹妹劳拉诱奸的正面暗示。这种意向性关联物的非连续性可以称为“空缺”。空缺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这种结构机制可以不断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野。此时,读者需以文本中写出的部分为依据,填充作品中的空白,构建文本的意义。
从劳拉的记录中,读者可以判断自从爱丽丝从欧洲度蜜月回来,丈夫理查德就已经在不断勾引劳拉了,但遭到劳拉的拒绝(Avilion,no,No,No)。直到爱丽丝一家在阿维隆庄园度假时,在一次午餐上理查德提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和保释了卡利斯塔,亚历克斯的朋友。而爱丽丝对当时的回忆是她“没来吃午饭,一个人端着杯咖啡去了码头”。当爱丽丝提出要去码头陪劳拉时,理查德的反应非常强烈,并建议让劳拉“自己排解那些令她苦恼的事”。后来劳拉不经意向爱丽丝提起亚历克斯,并说“反正他们还没抓到他,否则我们早就听到风声了”。从爱丽丝看来,劳拉的异常是对亚历克斯的眷恋,仅此而已。不久爱丽丝看到劳拉和理查德俩人乘“水妖”号下水,天真地以为劳拉已和理查德冰释前嫌了,却发现事后“只要劳拉一进屋,理查德准会马上离开。他倒反而怕她似的。”但当读者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填补其中的空白,会得到这样一个故事:理查德保释卡莉斯塔,其实是为了得到亚历克斯的下落,并以此为条件要挟劳拉;而劳拉担心亚历克斯被捕,自愿与理查德达成三方协议,以自己的身体换取亚历克斯的平安。“水妖”号即是劳拉被诱奸的地方,X既可以理解为sex的缩写,也可以理解为性交的符号。随着细节的逐渐串联,一个不一样的劳拉的故事被读者逐渐补充完整。与姐姐爱丽丝回忆中古怪、难以理解的劳拉不同,她是一个忠于信仰的女孩。对于爱情,她相信默默付出,所以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得爱人的生命;对于上帝,她相信牺牲,所以会试图用自己的生命换得母亲的复活;对于亲人,她相信信任,所以在被理查德送到精神病院接受堕胎手术时仍然把姐姐爱丽丝作为最信任的人,写信求助。当所有的信仰都破灭时,劳拉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开车冲下了桥。在读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到与文本的交流,填补空白,构建劳拉故事的过程中,爱丽丝的期待也是不断被打破和超越的:在爱丽丝自述里一个看似与世无争、心如死水、中规中矩的上流社会贵妇,却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姐姐、一个激情似火的情妇、一个充满心机的女人。
三、结语
在小说《盲刺客》的阅读中,读者需要积极主动与小说互动,通过不同文本间的互文,填补空白,完成文本的再创造。由于小说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文本的终极意义已不复存在,读者的想象和个性化的阐释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阅读成为一种小说意义产生的方式。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M].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M].韩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侯素琴.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理论与文学批评异同分析[J].理论导刊,2009(4):111-112.
[5]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左万芳(1987-)女,湖北潜江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