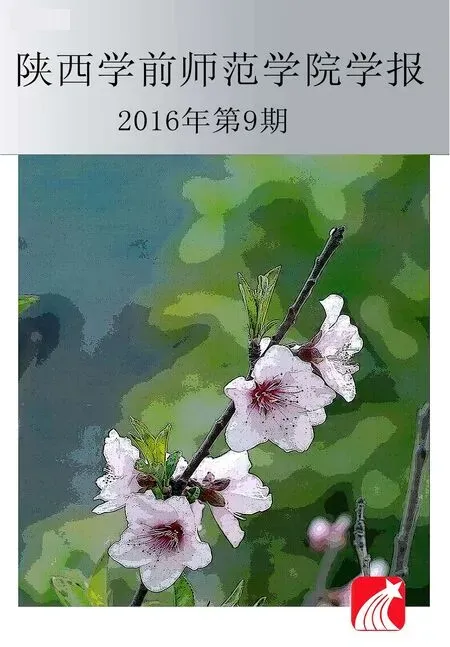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看元代社会
刘方园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看元代社会
刘方园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710000)
武汉臣的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不仅是一部描述家庭内部争端的家庭伦理剧,更是一部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社会风俗剧。元代小商人处境的艰难,宗族内部的财产继承制度,元蒙民族统治下的民族信仰,祭祀传统,以及一夫多妻制、赘婚制等婚姻状况,皆在剧中有所反映。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小商人;继承;祭祀;婚姻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9.028
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是武汉臣现存的唯一一部杂剧。该剧讲述了富商刘从善年轻时走南闯北,积累下万贯家私,老来却无子嗣继承,侄儿引孙因父母生前与婆婆李氏有隙,被赶出刘家,侍婢小梅幸而怀孕,却被觊觎刘家财产的女儿、女婿设计送走。无奈之下,刘从善将家产交给女婿张郎掌管,自己散财布施,积善行德。寒食时节,女婿张郎执意先上张家祖坟,使得刘从善夫妇深有所悟,认识到“女婿终归是外人”,从张郎手中骗回了“掌管家财的十三把钥匙”,交给侄儿引孙掌管。女儿引张怜悯父亲无子,在刘从善寿辰之际,带回了偷偷寄养在东庄姑姑家的小梅,以及小梅生下的儿子,父子相认,刘从善喜出望外,将家产侄、女、儿三人均分。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的一个特殊时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共处,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形成了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而最能反映这种社会文化的就是根植于元代下层民间社会的土壤之中,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和世俗风貌的元杂剧,正如吕天成在《曲品》中描述的那样,戏曲“描画世情”,“凑拍常语”,“有意近俗”[1]。《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描摹了元代真实的社会百态,通过对其分析,我们可以对元蒙民族统治下的社会文化有更好的认识。
一、小商人的处境
在元代,统治者对经商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减轻商税、给予贷款,供给衣食,保护商旅安全,提高商人的经济、政治地位等。因而民间弃儒经商的人较多,并且许多人依靠经商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然而,即便如此,谋取暴利的大多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官僚,以及蒙古、色目等上层阶级,一般小商人只能游走于商业边缘,靠自己辛勤操劳谋得些许利润,并且经商的过程十分艰难,甚至有时担着生命风险。剧中,刘从善曾描述到小商人经商的艰难:
(正末唱)哎,钱也,我为你呵,那搭儿里不到,几曾惮半点勤劳。遮莫他虎啸风崒律律的高山直走上三千遍,那龙喷浪翻滚滚的长江也经过有二百遭,我提起来魄散魂消。[2]2200
刘从善幼年经商,走南闯北,泛海渡江,积累下十多万贯家私,是民间百姓经商成功的典型,然而,对传统“士、农、工、商”身份地位的追从却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结,即使是在元代,科举时兴时废,儒生地位低下,他仍难以正视自己的经商身份,反而时常困惑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失落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身价值感的迷茫。
当侄儿引孙想要借点本钱做买卖时,他立即给予劝止,教导侄儿经商不如读书好,并恳切地发表了一段经商与读书的见解:
(正末唱)我道那读书的志气豪,为商的度量小,则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争似那勤学,为商的小钱番做大钱,读书的把白衣换做紫袍。则这的将来量较,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妆幺。有一日功名成就人争羡,(云)头上打一轮皂盖,马前列两行朱衣。(唱)抵多少买卖归来汗未消,便见的个低高。[2]2204
刘从善认为商业是社会的最底层行业,走仕途,功成名就、改耀门庭才是正道。在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经商的自卑感,认为自己所得不正,是折损子孙的行业,甚至将自己老来无子与往年经商不正联系起来:
(正末领丑兴儿上,云)……我想人生在世,凡事不可过分,到这年纪上身多有还报。则我那幼年间做经商买卖,早起晚眠,吃辛受苦,也不知瞒心昧己,使心用幸,做下许多冤业,到底来是如何也呵![2]2192
元蒙民族统治者从马上得天下,虽然在地理上占有了整个中国,但是其落后的草原文化显然难以适应中原文明的发展步伐。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将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手中,广大的汉人、南人根本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进入社会上层,且自隋朝就开始的科举取仕在元朝几乎不存在,仅有的几次也无非是粉饰太平的装点,根本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此,则众多的儒士沉溺于社会底层,无所事事。另一方面,野蛮、落后的草原文化使得蒙古的王公、贵族、大臣在得到政权之后,不知道发政施仁、巩固统治,反而沉溺于中原地区的歌舞声色、酒足饭饱中,难以自拔。他们把从全国各地掠夺来的财产、工匠,伶人集中在大都、杭州等地,造成这些城市的人口迅速增加,商业膨胀,都市经济畸形繁荣,许多入仕无门的知识分子从而转投商业。
然而,即便统治者对儒家文化如此轻视,也并没有因此消解根植于中国文人心中几千年的崇儒倾向,反而给他们带来的是更多的迷茫与困惑。就如同弃儒经商后的刘从善一样,一方面,他通过经商积累下巨额财富,改变了家庭条件,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另一方面,他又看不起商业,认为不如读书好,并痛恨自己往年经商折乏的老来无子,这种徘徊于出仕与经商之间的矛盾心理正是元代社会底层文人们的普遍心态。
二、宗族制度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同时也是一部反映宗族制度的教科书。剧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刘从善亲生的女儿、异姓的女婿、同族的侄儿、庶出的儿子在继承财产方面的先后顺序,而这种财产继承的顺序正反映了宗族内部亲疏关系的远近。
刘从善家庭矛盾最大的根源就是其老来无子,财产无人继承。对于无子嗣继承财产的情况,汉族传统和蒙古族的宗族制度是一致的。汉族规定,若财产无子嗣继承,要全部上交宗族。蒙古族规定,在无任何人继承财产的情况下,除少部分留给未亡人外,大部分则捐给寺庙或所在的旗仓。刘从善对此显然心有不甘,欲“散家财”,向天求子。剧中,刘从善有两次大的义举,一是焚烧债券,二是开元寺散财。前者则是消“六十载无儿冤业”的酝酿,后者则是“要问天公赎买一个儿”的真心忏悔。关于施散家财,汉族传统宗族制度中早有此传统,《仪礼·丧服》中说道:“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3]这是一种维护宗族内部团结的方式,同蒙古族的财产若无继承人,则捐赠给寺庙或所在旗仓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暗含着保护宗族内部财产不外流的因素。此外,汉族的宗族内部还设立有“义田”“义庄”“义宅”“义仓”“义冢”等公共设施的传统,由专门人员管理,群众监督,在每年青黄不接的三月、秋凉已至的九月和十月秋收之后,为同宗族的人提供救助,并且捐施的对象一般是宗族、亲族、九族,[4]从刘从善在开元寺散家财,同宗族的刘九儿来乞讨,可见在元代社会下,源于汉族的宗族制度仍有很强的凝聚力,要求同宗族的人要相互救助。
但同时,汉族和蒙古族的宗族继承制度又规定,若没有子嗣继承财产,也可以从同宗族中过继,但过继的子女严格讲究血源的纯洁性,亲同族,薄异族。并且在这方面,蒙古族的制度更能为严格,甚至严格禁止蒙古贵族过继异族子女。这也是剧中刘从善一直倾向于侄儿引孙的缘故,引孙与刘从善是同宗族内部的伯侄关系,且引孙父母双亡,对于无子的刘从善来说是继承财产的最合适人选。然而,刘从善还有一女儿引张,且女婿张郎入赘刘家已十年,早就期盼着继承刘从善的财产。在元代社会,女婿张郎继承刘从善的财产是有其合理性的,不仅我国汉族传统宗法制中规定入赘女婿可以继承女方家的财产,就是在蒙古族继承制度中也有此规定。蒙古族的财产继承制度规定,在无子嗣又无抱养继子的情况下,其财产的继承顺序是:胞兄弟,亲生女儿、叔伯兄弟、养老女婿、最后是远亲族外甥。张郎是刘家的养老女婿,这是得到刘从善认可的,因而,无论是按照汉族制度,还是蒙古族制度,张郎都有理由继承刘家财产,从张郎很早就掌管刘家家私来看,刘从善夫妇最早也是有此打算的。如此,则女婿张郎与侄儿引孙势均力敌,但是张郎显然高兴过早,在寒食上坟时,忘了自己的入赘身份,先上张家祖坟,导致刘从善夫妇改变心意,将家产重新交给侄儿引孙掌管。刘从善夫妇能够随意地挑选继承人,正是元代这种多民族并存的情况下,宗法制度较为灵活的缘故。
在剧末,女儿引张为了挽回父亲心意,带回了小梅姨姨,以及小梅产下的儿子,刘从善巧妙地将家产三分,侄、女、儿各得一份,可谓是一个创举。一方面,按照汉族的传统,女儿不享有财产继承权,刘从善已经有了亲生的儿子,照理说有了合法的继承人,不应再分给女儿财产,而在蒙古族的继承制度中,女儿同样是享有继承权的,未婚子女可以带财产出嫁,已婚子女也可以分得一点。而刘从善在此就是沿用了蒙古族的传统,也分得女儿一份,这显示了在元蒙民族统治时期,汉族民间百姓的生活还是受到蒙古族风俗影响的。另一方面,小梅之子是庶出,在蒙古族的继承制度中,庶出之子,无论男女,都没有财产继承权,但在汉族的宗族制度中,财产先由嫡长子继承,若无嫡子,则由庶子继承,刘从善给庶出之子也分得一份财产,可见其又延续了汉族的财产分配制度。
如此,则不能单方面地说元蒙民族对汉民族的统治是蒙古族文化吸收汉民族文化的过程,也应该看到,这种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既有汉民族吸收蒙古族的成份,也有蒙古族吸收汉族文化的成份。
三、民族信仰
元蒙民族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教信仰政策,而是多种信仰制度并存。传统各民族的对天崇拜,以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并相互影响,形成了元朝历史上一个思想大融合时期。
在剧中,最明显的就是刘从善通过舍散家财,终得“天赐一子”。这种“天赐子”的信仰,不仅来源于汉族人民对天的崇拜,也来源于蒙古族对天的崇拜。在汉民族信仰中,天是最高的神,掌管一切,且天和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人亦能感动上天。祭天是华夏族最隆重的仪式,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受宠的人称为天之骄子,婚丧嫁娶要先拜天地,逢年过节要祭天拜祖等等。而在蒙古族中,同样视天为一切万物的主宰。蒙古族尊称天为“腾格里”,祭天是蒙古族的传统,在元朝在中原立国以后同样如此,《元史·郊祀志》里就记载有元代帝后祭天的情景:“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岁甲寅,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丁巳秋,驻跸于军脑儿,皆祭天于其地。世祖中统二年,亲征北方。夏四月己亥,躬祀天于旧桓州之西北,洒马湩以为礼,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皆如其初。”[5]1781
元蒙民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元史·祭祀一》记载的:“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5]1780说的即是萨满教。萨满教崇拜各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崇拜“长生天”。在早期,萨满教在蒙古社会是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但随着元蒙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对宗教兼收并蓄,由《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的元大都里有“基督徒”、“寺庙”、“回回”、“巫师”等,即可知元代的宗教信仰制度是多么得复杂。随之而来的是萨满教的势利渐渐弱化,而在汉族地区流行已久的佛教、道教则渐渐渗入到元蒙民族社会文化中。
剧中,刘从善对自己老来无子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自己往常不尊重僧道所致,因此要舍散家财,悔罪神灵:
(唱)……往常我瞒心昧己,信口胡开,把神佛毁谤,将僧道抢白,因此上折乏的儿孙缺少,现如今我筋力全衰。人说着便去,人唤着忙来,看经要灭罪,舍钞要消灾……[2]2193
刘从善对积善行德、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深信不已,就连散家财也是在佛教寺院中,正反映了即使是在蒙古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佛教思想仍然在元代社会民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四、祭祀传统
蒙古族传统的祭祀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元史·祭祀六》记载有蒙古贵族旧时的丧葬情况:“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5]1925
自蒙古入主中原,这种传统的祭祀方式已渐渐被抛弃,武汉臣在《老生儿》中,描述了元代统治中原时期,刘从善一家寒食上坟的状况。剧中写道“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关于清明、寒食上坟的传统,汉族传统的经书《礼记·祭义第二十四》,记载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6]1310汉族祭祀有时间规定,不能太繁,也不能太疏,清明、寒食时节,季节变化引起人内心感时念亲之情,是最佳祭祀时间。祭祀仪式也极为讲究,婆婆李氏就曾描述道祭祀的景象,“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馒头,春盛担子,红干腊肉,盪下酒,六神亲眷都在那里,则等俺老两口儿烧罢纸要破盘哩。”祭祀时,要搭好祭棚,宰羊、漏粉,蒸好馒头,准备好春盛担子、摆好红干腊肉,烫好酒,家族成员要聚集一起,烧完纸钱后,大家还要“破盘”,即分享祭品。即使在贫穷人家,祭祀时也要“烈些纸钱,添些土儿”,就像引孙上坟时,“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濡喏,讨了这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这半瓶儿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害怕公公婆婆和父亲母亲为一个馒头分不均,又将一个馒头分作两半,可谓滑稽。
汉民族在祭祀时,奉行“死者为大”的原则,在与婆婆拜祭祖坟时,刘从善就劝导婆婆要拜祭辈份低的引孙爹娘,“他活时节是咱的小,他今死了,也道的个生时了了,死后为神。”《礼记·祭义》“第二十四”中写道“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悽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6]1325《礼记》认为人死为鬼,其气为神,鬼神合一,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敬畏之情。元蒙民族同样也对逝者充满敬畏,尊其为神,萨满教的教义中就包含着对先祖的崇拜。同样,《元史·祭祀一》里记载的:“天子亲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5]1782同汉民族的信仰也是一致的。
元蒙民族发源于草原,因地势皆平坦,故对墓地的选择则没有严格的要求,正如前文材料中所引述的那样,棺柩至所葬陵地,按照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而这种传统在元蒙统治时期,根本不可能实行下去。传统汉民族文化认为:同族的人,血脉相连、骨肉相通,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剧中刘从善的太公、太婆、父亲、母亲、弟弟、弟媳都葬在一处,并且,墓地的选择也要讲风水、顺阴阳,刘从善因为自己无子,便选了一块下洼水渰的绝地,着实可笑,他解释道“则俺这一双老枯桩,我为无那儿孙不气长。百年身死深埋葬,坟穴道尽按着阴阳。咱两个死时节便葬在兀那绝地上。”可看出,在元蒙民族统治下,汉族人民仍沿袭了其固有的丧葬传统。
五、婚姻习俗
《老生儿》中涉及的婚姻关系主要有两个,一是刘从善的正妻李氏和妾小梅,一是独生女引张与赘婿张郎。关于婚姻的描述,《礼记·昏义第四十四》中有表述:“昏阴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6]1618刘从善有一妻一妾,是典型的富户家庭,他与正妻感情甚笃,但只生的一个女儿引张,侍妾小梅怀有身孕,母凭子贵,被纳为妾。这种妻妾并存的家庭在古代社会甚为普遍,元代统治者虽多次加以干预,禁止一夫多妻,但收效甚微。小梅本身地位低下,只是一个贴身服侍主人的侍婢,但是因为怀有刘家子嗣,承担着刘家宗庙后继的重任,而成为刘家内部纷争的关键人物,但是,小梅在刘家其实就是家产争夺的一颗棋子,该出现时就出现,不该出现时就消失,张郎因为小梅怀有身孕,想早早“所算了”她,便联合妻子伪称小梅配绒线去,怀空走了,轻而易举就将小梅送走了,这样就扫除了女婿继承刘家财产的障碍,当侄儿引孙夺得刘家财产继承权时,女儿引张又将小梅送回,这样小梅所生儿子则是合理的继承人,轻易就将引孙的继承人资格排挤掉了,小梅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甚至是外姓的女婿也可以决定她的去留,她在刘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即使女婿张郎不算计她,还有婆婆李氏,刘从善早已向婆婆李氏交代过,只要小梅生下儿子,要典要卖,到时候全凭婆婆处置,小梅在刘家的价值就是肚里的孩子,这也是古代妻妾并存家庭中妾的依靠,因为生下孩子,而在夫家有一席之地,假若无子,地位连奴仆都不如。
元代赘婿婚盛行,并且赘婿形式多样,这在《老生儿》中可以明显看到。张郎入赘刘从善家已经十年,常住刘家,甚至连怀孕的小梅姨姨和同宗的侄儿都被他赶出刘家,并且还一度执掌刘家的家私,其精明、狠毒可见一斑,他早已算好了刘从善寸男尺女皆无,入赘刘家图的就是刘从善的家产,并将己姓改作刘姓,自称“刘张员外”,因此,张郎所代表的是元代抱财女婿与养老女婿两种类型,此外,元代还有出舍女婿、归宗女婿等类型,出舍女婿即男女双方约定年限已满或其他原因,婿带妻室,另立家户,与妻家析居营生者,归宗女婿即期限满后或妻亡后回父家。[7]这皆反映了元代婚姻习俗的多样化。元代将赘婿称作“补代”,即养老送终,补其世代的意思,剧中刘从善说道:“我在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汉三十载。无倒断则是营生的计策,今日个眼睁睁都与了补代,那里也是我的运拙时乖。”刘从善不甘心将家产交给女婿,并对其常怀戒心,可见,元代赘婿的地位并不高,大多受人轻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杂剧作为元曲的一种,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艺术上的饕餮盛宴,更是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高感胶片。
[1]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2]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洪迈.容斋随笔[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4]刘毓盘.词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5.
[5]王寂.拙轩集[M].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6]张璋,等.历代词话(下) [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7]王寂.拙轩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李兆平]
The Society of Yuan Dynasty Reflected by A Rich Old Man’s Son
LIU Fang-yu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China)
ARichOldMan’sSonis not only a family moral drama that describes the domestic disputes of a family, but also a drama that reflects the social customs of Yuan Dynasty. Social realities and practices, such as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that the small traders lived in, the property inheritance system in clansmen, national beliefs under the reign of Mongolian nationality, practice of sacrifice and marriage system, can be seen from the drama.
ARichOldMan’sSon; small trader; customs; sacrifice; marriage
2016-03-02
刘方园,女,河南洛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学·艺术研究
I207.37
A
2095-770X(2016)09-01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