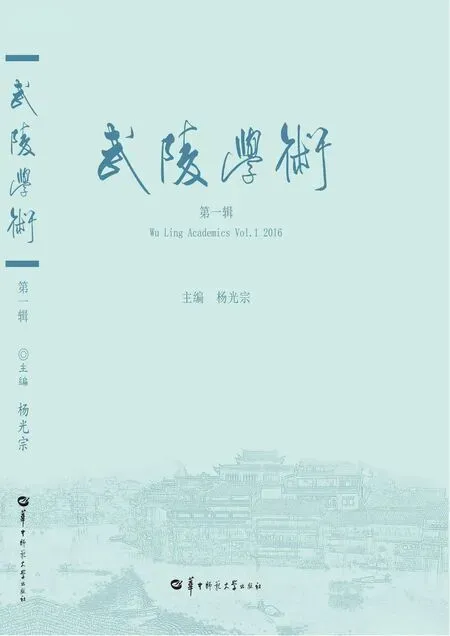概念结构及其对语义和句法的制约*
惠红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概念结构及其对语义和句法的制约*
惠红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概念是相互依存的思维形式,它来自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并在根本上受文化的制约。概念结构可以从概念要素和概念关系两个方面理解,它广泛影响着语义搭配,句法成分的隐现、功能和指向,以及句法结构的可能类型。
概念结构文化制约语义句法
1. 概念是语言认知研究的重要环节
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必然关涉极其复杂的概念系统,即使日常生活的简单会话也是如此。比如当我们看到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植物时可能会问“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一般不会问“这是什么动物”,除非问话人的概念系统已经紊乱。之所以会这样提问,是因为我们已经将真实世界中的事物归于植物、花、树、草以及动物等不同概念范畴。换言之,我们通过语言来呈现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世界时必须要通过概念的作用。我们首先要通过概念系统来判断所看到的是植物而不是动物,接着需要通过概念系统来判断所看到的是这一类植物而不是那一类植物。在整个判断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通过一个一个的概念,而且还要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所看到的是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对概念的认知不但涉及如何认知世界,也涉及如何将这种认知成果展现在语言世界中。因此,概念研究是语言认知研究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每个孩子共同经历的认知发展过程足以证明,人的知识体系是以概念为核心的*贺文、危辉:《概念结构研究综述》,《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0年第1期。。语言中存在着无数的概念,对这些概念及其结构的研究是语言认知研究中极其重要而关键的环节。我们认为,概念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思维形式,它来自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概念存在于人类的认知系统中,是人类知识的组成部分;它随着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能力而不断发展变化。在认知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地获取新概念,寻找、确定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但由于概念所反映的外部世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变化,而某一概念所对应的外部世界的对象都有其独特性,因而当反映外部真实世界的概念进入语言世界时必然有其独特的具体化,从而使概念总是处于某种变化之中,甚至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概念。
2. 概念结构的研究
关于概念结构,Jackendoff认为,它是存在于语言信息和心理信息(视觉、听觉、味觉、动觉等)之间的两种信息共存的层次;它必须有强大的表达能力,以便有效处理被语言感知到的所有事物以及所有的表达形式,因此还需要设定一套概念合适性规则(conceptual well-formedness rules);就语义理论和概念结构的关系而言,概念结构是比语义结构更高的一个层面,语义结构则是一种简化的概念结构*Jackendoff,Ray.Semantics and Cognition.The MIT Press,1983:6-19.。程琪龙认为,目前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还很难证明Jackendoff假设的全部内容;可望而又可即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能和句法、语音等语言子系统连接的概念系统(包括概念结构),使概念系统能作为事实推理的输出和输入,并进一步探索概念结构和常识的关系;与此同时,概念结构也应考虑它和其他认知系统,尤其是和视觉系统连接的可行性*程琪龙:《“概念结构”探索》,《语文研究》,1996年第1期。。
Jackendoff进一步指出,概念结构受概念格式化规则和推理规则的制约,它与句法结构、观念、行动等相互影响;概念结构与音韵结构、句法结构共同构成语法组织中的三个自主结构,由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将它们联成一个整体*Jackendoff,Ray.Semantic Structures.The MIT Press,1990:8-17.。戴浩一认为,Jackendoff一系列著作中的概念结构和句法结构都是各自独立自主的系统,互相不影响,而形式结构与概念结构之间的投射也是任意的,不会受到文化及经验的影响;然而,汉语的实例证明,“概念结构”会深入影响“句法结构”,因为“概念结构”会受到文化经验的影响,因而“句法结构”也会受到文化经验的影响*戴浩一:《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当代语言学》,2002年第1期。。
程琪龙认为基本概念结构有两个:时空关系概念结构和指向关系概念结构。同时,基本概念结构有三个条件:(1)它解释的是概念及其结构的异同,而不是表层句法结构的异同;(2)它是有普遍意义的,不存在有具体语言倾向的概念结构;(3)它可以延伸到具体概念结构,并最终体现成句法结构*程琪龙:《试论语言的基本概念结构》,《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3期。。
我们认为,概念结构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概念要素,即构成一个概念所可能包含的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真实世界,并对应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存在;一类属于语言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某种存在的主观性认知。如“人”这一概念中,动物类的特征构成来自真实世界的概念要素,价值伦理类的特征则构成语言世界的概念要素。真实世界和语言世界的概念要素都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一个历时的过程,是随着认知的发展而不断构建出来并加入这一概念中的。因此有些概念要素只存在于语言世界,无法在真实世界找到相应的存在,如语言中的助词、介词、语气词这类概念要素。可以这样认为,所有的概念要素都存在于语言世界,但不一定存在于真实世界;即从真实世界到语言世界中增加了一些概念要素。(2)概念关系,即概念要素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在真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中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应该是可以穷尽的。如汉语中,“猫”“吃”“鱼”这三个概念可能形成的结构有“猫吃”“鱼吃”“猫吃鱼”“鱼吃猫”“猫吃猫”“鱼吃鱼”等;而它们可能的扩展结构则会更多,甚至无法穷尽。虽然真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实际关系无法穷尽,但是其组合的结构类型在一种语言,或在整个人类语言中却应该是可以穷尽的。概念结构中的概念要素和概念关系基本对应于语言研究的两个层面:语义和句法。从这个角度说,概念结构是连接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枢纽环节,因而在语言认知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3. 概念结构的文化制约
解释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之中*Walker,Galal.Performed Culture:Learning to Participate in Another Culture.In Walker,Galal (ed.)The Pedagogy of Performing Another Culture.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同时,文化规范行为,为我们提供认知特定世界里的事件和事物的方法;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文化是个人的行为,该行为在特定情境中被自己和他人理解*Walker & Noda.Remembering the Future:Compiling Knowledge of Another Culture.In Walker,Galal (ed.)The Pedagogy of Performing Another Culture.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50页。。在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结构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也必然由于解释者和接受者的个体性而表现出个体性。我们可以通过宋代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一诗来对这一点做进一步的形象解释。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根据诗的意境,我们可以说“岭”就是“峰”,“峰”就是“岭”,因为虽然观察的角度不同,但二者所指的观察对象相同,都是庐山;我们也可以说“岭”不是“峰”,“峰”也不是“岭”,因为二者的观察角度不同,因而实际看到的庐山景象并不相同。这正是认知独特性的形象反映。关于认知的这种独特性,威廉·冯·洪堡特也曾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脸型的独特性取决于所有部位的总和,同时也取决于每一个人的眼光。正因为这样,同一张脸才对每一个人都显得不一样。”*[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
上述观点似乎表明,真实世界在每个人眼中都不一样,人并不能真正认知真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讲,确实如此。Jackendoff利用对四个不同图形的认知过程来说明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和投射世界(The Projected World)之间的不同:

对图1而言,其中的四个点虽然没有连线,但是人们会自然地将它看成一个正方形。对图2而言,如果关注其中的白色部分,图像就可以看成一只花瓶;如果关注其中的黑色部分,图像则可以看成面对面的两张人脸。图3则既可以看成一只鸭子,也可以看成一只兔子。图4中,本来一般长短的两根线段,由于在它们的两端分别加上了方向相反的箭头,看起来却并不等长。因此,Jackendoff认为,人并不能感知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Jackendoff,Ray.Semantics and Cognition.The MIT Press,1983:23-26.。
很显然,因为概念构建的世界加入了主体的认知因素,所以它和真实世界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并不能感知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Jackendoff理论中所谓的投射世界大体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和认知构建的世界,即概念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语言世界。虽然语言世界和真实世界有一定的不同,但是二者毕竟同源,就像“岭”和“峰”的关系一样,因此二者都具有确定性,是可以感知和认知的。对概念结构来说,某种文化的所有认知主体都可能影响到它,但事实上我们无法获得某种文化的所有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果。我们也无法从自发的语篇中获得有关意义的充足信息*Matthewson,Lisa.On the Methodology of Semantic Fieldwor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Vol.70,2004,10.4:369-415.,而只能通过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获取某种文化的认知共性,进而获得与之相关的概念结构。同时,因为概念结构中不断有新颖而动态的结构呈现*Fauconnier,Gilles.Compression and Emergent Structure.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05,6.4:523-538.,所以只有考察语言中因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的独有特点,才能够对该语言的概念结构做出准确的描述,并对该语言的语法规律做出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解释。在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文化特征不但影响了概念结构的最初形式,也会给语言使用者的概念结构中不断地加入新的要素,从而形成新的概念结构。因此,语言的语义和句法都无法摆脱概念结构的基本限制,无法摆脱文化及历史演变的“约定俗成”的基本限制。
4. 概念结构对语义的制约
概念结构对语义的制约非常明显。这种制约能够在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汉语方言在量词使用上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在同一量词在不同方言中能够修饰的名词具有明显差异,如名量词“张”“条”“根”“只”“块”“把”“本”“部”“支”“头”等在汉语各方言区修饰的对象都有非常大的差异。以名量词“张”为例(参看《汉语方言大辞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4月第1版,第2953—2954页):“一张腿(山西汾西);一张厝(房子)(福建仙游、莆田);一张车(湖南长沙);一张汽车(浙江金华岩下);一张山(江西宜春);一张拖拉机(江西高安老屋周家);一张汽车、一张拖拉机(云南玉溪)。”以名量词“根”为例(参见《汉语方言大辞典》,第4600页):“一根被子、一根腿(山西太原、榆次、太谷);一根裤子、三根蛇、一根牛、两根羊、三根树子、几根葱(四川成都);一根毛巾、一根猪(四川仁寿);这根人、你的这根朋友、一根问题、两根手、一根眼睛、三根脚(云南蒙自);那根人、一根船、一根鱼(云南建水);一根麦子、一根珍珠(山西太原);一根絮(棉絮)、一根睏簟(睡席)(安徽绩溪)。”另一方面表现在普通话和方言在通用个体量词选择上的差异。虽然普通话中公认的通用量词是“个”,然而“个”却并非所有方言区的通用量词。如湖北通城方言、湘方言、福州方言、吴语的通用量词是“只”*详见万献初:《湖北通城方言的量词“隻”》,《方言》,2003年第3期;姜国平:《湘语通用量词“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邓开初:《长沙话中缺乏语义分类功能的量词“只”》,《船山学刊》,2008年第3期;陈泽平、秋谷裕幸:《福州话的通用量词“隻”与“個”》,《方言》,2008年第4期;严宝刚:《吴语通用量词“只”探源》,《才智》,2009年第17期。,陕西关中方言的通用量词是“”,陕西洋县方言的通用量词则是“块”。
概念结构对语义的制约也能够在不同语言功能相似的词语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汉语和英语在计量动物群体时所使用的量词(或分类词、名词,这一点下文还要讨论)就存在鲜明差异:
一群羚羊:a herd of antelopes一群蚂蚁:an army of ants
一群蜜蜂:a swarm of bees一群小马:a rag of colts
上举各例中,汉语仅用“群”来修饰限制“羚羊、蚂蚁、蜜蜂、小马”等所组成的群,英语则分别使用herd、army、swarm、rag四个词语来修饰限制antelope、ant、bee、colt所组成的“群”。这说明,汉语和英语对真实世界中这四种动物的群体关系有着不同的认知,基于这种认知所形成的概念结构进而影响和制约着语义之间的搭配。汉语中,真实世界中不同动物群体的概念对应着语言世界中的同一个概念要素“群”,因而汉语的“群”可以指称人的群体,也可以指称动物的群体。英语中,真实世界中不同动物群体的概念对应着语言世界中的不同的概念要素,因而英语中人的群是“group”,动物的群则可以分出“herd、army、swarm、rag”等更小的类。汉语和英语中也有与“群”相反的情况,即英语中是一个概念要素,而在汉语中则是几个不同的概念要素。如:
a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a piece of bread 一块面包
a piece of string一根绳子a piece of broken glass 一片碎玻璃
a piece of text 一段文章three pieces of fruit 三个水果
a piece of advice一点建议a single piece of jewelry 一件首饰
从概念要素的角度看,客观世界的“群、条、块、片”等,在汉语中是从名词非范畴化为量词的,并用来修饰限制名词的数量;而类似概念要素在英语中则是作为可数名词来修饰限制名词的数量。从术语接受的角度看,汉语量词这一术语已经被大型专业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5版)收录;而classifier(分类词)这一术语,一些大型的专业英语词典(如《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英英·英汉双解)(第四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则并未收录。进一步看,量词、分类词、名词虽然是三个不同的词类,然而它们在语义上却具有相同的限制功能,即都能够用来限制事物的数量;而个中原因则在于它们在概念要素上具有相同之处,即它们在概念表达上的邻近性和相似性。这种概念表达上的邻近性和相似性在限制语义搭配的同时,也限制着语义演变的方向,即词类非范畴化的方向。如汉语的“流、级、类、等”等量词非范畴化为“流、级、类、等”等区别词*惠红军:《汉语量词研究》,四川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汉语量词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5—220页。;“十分、一下、一把”等数量结构非范畴化为“十分、一下、一把”等副词*参见惠红军:《汉语量词研究》,四川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汉语量词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5—220页;惠红军:《数量结构“一把”的非范畴化现象探析》,《现代语文》,2010年第24期;惠红军:《数量结构非范畴化为副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相反的非范畴化方向。
因此说,对于真实世界的同类现象,语言中存在着不同的概念化结果,形成了不同的概念要素。这种概念化的不同也能够通过语言中的词语借用可窥一斑;因为对于一种语言中那些具有文化特征的词语来说,另一种语言中往往缺少对应的概念,所以在找不到最佳匹配的词语时往往采用音译的方式借入。如汉语的“风水”“阴阳”“功夫”“道”等,在英语中的借词形式分别是“feng shui”“yin and yang”“kung fu”“Tao”,都是采用音译的方式;而且“风水”一词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如“feng shui a room”,即“看风水”。但是,这种音译借入的情况也会发生分化;因为随着认知的发展,人们会采用母语的概念对一些最初使用音译方式借入的概念进行完全的母语化改造。如汉语近代以来的一些音译词,如“葛朗玛(grammar)”“英拜儿(empire)”“水门汀(cement)”“麦克风(microphone)”“德律风(telephone)”“赛因斯(science)”“德莫克拉西(democracy)”等,最后都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而完全汉语化为“语法(grammar)”“帝国(empire)”“水泥(cement)”“话筒(microphone)”“电话(telephone)”“科学(science)”“民主(democracy)”*对于这些词的来源依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科学”一词,马西尼认为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高名凯、王力等则认为是日语的原语借词。“民主”一词,马西尼认为是汉语的仿译词,而王立达和高名凯等人则认为是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水泥”一词,马西尼认为是汉语新词;虽然与日语借词“混凝土”并存,但它现在是表示“cement”最为常用的词。(参看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25、230—231、241页。)。除此之外,不同语言对外语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一般也都是采用音译的方式,其原因都是这类词语中所隐藏的概念在母语文化中找不到恰当的对应概念,如英文中的姓氏Carpenter、Kissinger,汉语就音译为“卡朋特”和“基辛格”,而不能意译为“木匠”和“接吻的人”;对汉语中的姓氏“钱”和“马”,英语则音译为“Qian”和“Ma”,而不能意译为“Money”和“Horse”。
5. 概念结构对句法的制约
概念结构不但制约着语义的理解及其搭配,而且也制约着句法结构,包括句法成分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继续以上文所谈到的量词以及数量结构为例来分析。由于概念结构的制约,不同语言中能够出现在数量结构中的句法成分会因此而不同。如汉语的数量结构在表示数量“一”时,使用的语言单位是数词“一”;英语则可以使用数词“one”,也可以使用冠词“a、an”。汉语的数量结构中,可以出现助词“的”,但“的”的出现与否有一定条件;如助词“的”一般不能出现在“一群羚羊”中,但可以出现在“成群的羚羊”“一群一群的鸭子”中,也可以出现在“一屋子的人”“一篮子的板栗”“一身的病”“满眼的泪水”等结构中。汉语的数量结构中不能出现任何介词,但英语数量结构中则必须出现介词“of”。再进一步说,汉语的结构助词“的”不能单独成句,而英语的“of”则可以单独成句。
概念结构对句法结构的制约还表现为对同一语义成分的不同句法功能的限制。我们这里以汉语的定语、状语、补语三种句法成分的有序变换为例来进行分析。现代汉语中,有些句法成分在词汇形式上完全一致,但却能够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充当定语、状语、补语。如:
明晃晃的手电筒光束射得中国医生睁不开眼。(《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
只见头顶上明晃晃飞来一把斧头。(马峰《吕梁英雄传》)
晚上宿营时,负伤的左臂肿得明晃晃的。(刘秉荣《红军长征中的三位断臂将军》)
其中,“明晃晃”能够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分别充当定语、状语、补语,其原因在于它既是事物的一种特征,如“光”的特征;也可能是伴随动作的某种状态,如“明晃晃飞来”;也可能是动作产生的某种结果,“肿得明晃晃的”;因而“明晃晃”能够在句法结构中有序变换,充当定语、状语、补语等不同句法成分。这种情况在近代汉语时期就能看到,如:
那梢公便去艎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水浒传》第36回)
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打鱼的,都手里明晃晃拿着刀枪走来。(《水浒传》第19回)
原来那里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西游记》第52回)
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酽酽的沏上茶来大家吃了。(《红楼梦》第8回)
替老爷快倒一杯酽酽儿的清茶来。(《孽海花》第10回)
汉语时间性量词短语的语义双指现象也能够反映出概念结构对语言单位充当句法成分的限制。汉语中的“下了一场大雨”“发了一顿脾气”“请一年假”这类结构中的量词在语义上同时指向动词和名词,形成了一种语义双指结构。惠红军对这种语义双指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一场”“一阵”“一年”这类量词短语都能够表达时间,是一种时间性量词短语;这类时间性量词短语之所以会出现语义双指,主要原因在于其称量对象“下大雨”“发脾气”“请假”等都是“事件”;而事件或事件范畴(event category)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对象,它涉及动作、事物在时间上的持续互动,因此既有动词性的一面,又有名词性的一面。其中的动词都具有持续性,名词都具有明显的变化性。时间的延续是事物变化、存续,以及事件和动作发生、延续的基本特征。时间性量词短语、延续性动词、变化性名词都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延续]。因此“下了一场大雨”这类结构中,由于[+延续]语义特征的存在,时间性量词短语向前可以指向动词,向后可以指向名词,同时称量动作和事物延续的时间长度,从而形成语义双指的现象;而非时间性数量短语则不会形成这样的语义双指结构*惠红军:《时间性量词短语的语义双指》,《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概念结构不仅制约着句法结构如何呈现,也同样制约着句法结构的可能形式。以数词、量词(分类词)和名词三者所形成的句法结构为例,从组合的角度看,数词、量词和名词会有六种可能的语序结构:
Ⅰ数词+量词+名词Ⅱ名词+数词+量词
Ⅲ量词+数词+名词Ⅳ名词+量词+数词
Ⅴ量词+名词+数词Ⅵ数词+名词+量词
Greenberg认为,只有前四种结构是可能的数词分类词结构(numeral classifiers construction)*Greenberg,J.H..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Universals,9:1-39.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Stanford University,1972.Also in K.Denning and S.Kemmer(ed.)On Language: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Greenber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66-193.;语序Ⅰ和语序Ⅱ相对于语序Ⅲ和语序Ⅳ更常用,语言也允许在语序Ⅰ和语序Ⅱ之间有序转化*Greenberg,J. H..Dynamic Aspects of Word Order in the Numeral Classifier. In Li,Charles (ed.)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5:27-43.Also in K.Denning and S.Kemmer(ed.)On Language: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Greenber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227-240.。数词分类词即本文所讨论的量词。实际上,量词与数词、名词的可能语序类型多于Greenberg(1975)所预测的四种,因为我们能够在壮语、布依语、莫话、甲姆话、毛南语、苗语等语言中发现语序Ⅴ“量词+名词+数词”*参见张元生:《武鸣壮语名量词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吴启禄:《贵阳布依语》,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14、117页;马学良:《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43页;马学良:《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45页;张景霓:《毛南语的量词短语》,见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9、302页;罗安源:《松桃苗话描写语法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壮语(张元生,1993):
块 肥皂一 块 糕一
布依语(吴启禄,1992:114,117):
tu2mu1diau1一头猪ba1sa1diau1一张纸
只 猪一 张 纸 一
莫话(马学良,2003:743):
只 马一
甲姆话(马学良,2003:745):
ka1ni1deu1一条河
条河一
毛南语(张景霓,2005):
把刀 一 个 碗一
苗语(罗安源,2005:80):
a44ntu54wu35a44na42m22qwen44a44!
那 条河一 那么 宽啊
那一条河那么宽啊!
虽然“量词+名词+数词”结构中的数词都是“一”,但这可能是这种语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语序Ⅵ“数词+名词+量词”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根据所看到的语序结构类型,我们发现,数、量、名的语序不仅能够在语序Ⅰ和语序Ⅱ之间有序转换,而且还能够在更多的语序之间有序转换。如汉语的数、量、名能够在语序Ⅰ“数词+量词+名词”和语序Ⅱ“名词+数词+量词”之间有序转换,布依语、壮语、苗语能够在语序Ⅰ“数词+量词+名词”和语序Ⅴ“量词+名词+数词”之间有序转换,傣语能够在语序Ⅱ“名词+数词+量词”和语序Ⅳ“名词+量词+数词”之间有序转换。而有的语言的数、量、名所形成的结构还能在三种语序结构中有序转化,如临高话*黄平:《汉藏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37页。能够在语序Ⅰ“数词+量词+名词”、语序Ⅱ“名词+数词+量词”和语序Ⅳ“名词+量词+数词”三种语序中有序转化:
数词+量词+名词
tam213hu55nok55三只鸟vn33na33lk55nk33两个孩子
三 只 鸟两个孩子
名词+数词+量词
nok55tam213hu55三只鸟11vn33bn55na24两个人
鸟 三 只 人 两位
名词+量词+数词
树 株 一刀 张一
数、量、名的语序结构呈现这种分布的原因,我们认为是距离象似动因的制约,而距离象似动因则受制于概念关系的制约。在已经发现的五种语序结构中,Ⅰ、Ⅱ、Ⅲ、Ⅳ四种语序都可以看成数量结构和名词的语序,即数词和量词首先组成数量结构,然后这个数量结构或者位于名词前,或者位于名词后,从而形成不同的数量结构;不同的是其中数词和量词的语序变化,即或者是“数词+量词”,或者是“量词+数词”。但Ⅴ、Ⅵ两种语序则不同,数词和量词分别置于名词的两边,二者在句法结构上的距离明显加大,概念关系明显疏远。数、量、名的可能语序结构与实际观察到的语序结构的差异说明,这类结构中的数词和量词之间的概念关系更为密切,二者的句法距离应该最短,因而在句法结构中它们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移动。如果要使数词和量词的概念关系变得疏远,使二者的句法距离加长,那么这样的结构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因而Ⅴ、Ⅵ是较为少见的两种语序,而且实际上语序Ⅵ目前还没有看到。
数、量、名语序的多样化反映出,概念之间可能的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但是有些组合常见,有些组合不常见,这能够反映出概念关系的远近变化,而这种远近变化则体现为语言层面的距离象似原则。这种基于概念关系的距离象似原则也会影响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如多层定语或多层状语的排列顺序。
6. 余 论
上面的讨论启发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对于语言中的各个概念要素,哪些会在句法结构中出现,哪些不会在句法结构中出现,其中的限制性条件是什么?句法结构中能够同时出现的概念要素有多少?这些能够出现的概念要素有哪些可能的语序序列?这些语序序列与概念结构之间又有哪些对应规则?
上面的讨论还明确了这样的看法,文化对概念结构的制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表现却千差万别。概念结构所受到的文化制约也会随着文化的发展演变而变化,并最终会对语言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正如沈家煊(1994)所说的那样,对句法的分析不能脱离语义;而对语义的描写又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度的知识系统。我们认为,这个知识系统的核心正是概念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概念结构的研究正是语言认知研究中一个极有价值的领域。
本文是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740046)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J02)的部分成果。
惠红军(1970—),男,陕西蒲城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兴趣为汉语语法史、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认知类型学、对外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