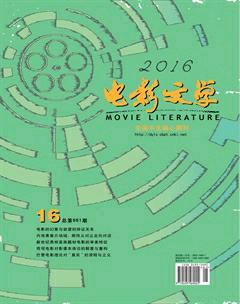《消失的爱人》的叙事伦理
池丽霞
[摘要]《消失的爱人》是美国著名导演大卫·芬奇的作品,影片在上映之后引发了人们关于婚姻等问题的持久热议。“叙事伦理”则是西方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学科,意在探究作品中的伦理效果是如何在叙事中实现的。《消失的爱人》关注着人的生存法则、道德行为与伦理诉求,其中存在着隐形的道德尺度,是应该置于叙事伦理的层面来进行讨论的。文章即以此入手,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两性伦理三方面,分析《消失的爱人》的叙事伦理。
[关键词]《消失的爱人》;大卫·芬奇;叙事伦理
《消失的爱人》(Gone Girl,2014)是美国著名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根据女作家吉莉安·弗琳的同名悬疑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电影以女作家艾米失踪,艾米丈夫逐渐被各种证据指为杀人凶手开始,随着真相层层揭开,两人真实而残酷的关系也展现在观众面前,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电影也在上映之后引发了人们关于婚姻等问题的持久热议。芬奇利用各类视听元素将小说中的暗黑、压抑、惊悚气质进行了强化,在影像设计上芬奇则延续了自己在《纸牌屋》(House of Cards)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贯冷静而简洁的风格,以保证电影无论是从结构到细节,抑或是从场景到段落剪辑,都呈现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而电影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艺术的一种,上述元素皆是服务于叙事的。“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是西方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学科,它最早由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即探究作品中的伦理效果是如何在叙事中实现的。《消失的爱人》关注着人的生存法则、道德行为与伦理诉求,其中存在着隐形的道德尺度,是应该置于叙事伦理的层面来进行讨论的。
一、《消失的爱人》中的社会伦理
英国学者米切尔曾经指出:“社会一词是社会学词汇中最不明确和最普通的名词之一。它可以从表示没有文字的民族到表示现代工业民族国家,或者从一般的泛指人类到表示较小的有组织的民族群体。”可以说,社会一词的外延是十分广大的,任何人与他人在进行互动时,某种具有稳定关系的人的集合体都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便是作为个体的“人”与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关系,以及个体本身的自我认知、自我价值判断,这些都可以被视为社会伦理问题。《消失的爱人》之所以引起热议绝不仅仅是因其对婚恋问题进行了探讨。单纯就对婚姻的复杂性和绝望性的表现这一点来说,《消失的爱人》实际上并不比萨姆·门德斯的《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1999)和《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2008)更为优秀;《消失的爱人》也不应该仅仅被视作一部悬疑电影,就对悬疑的设置而言,芬奇早已在《十二宫》(Zodiac,2007)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消失的爱人》选择在叙事进行不到一半时就抛出了“罪案”的“真相”,从而过早地结束了悬念。而电影基于畅销小说改编这一点也注定了电影无法靠悬疑叙事取胜。事实上,《消失的爱人》与芬奇的另一部佳作《七宗罪》(Se7en,1995)更为接近,导演只是借用了罪案的外壳,来探索人性与社会的深层问题。
(一)艾米的身份迷失
身份迷失问题是当代人的困扰之一,同时也是《消失的爱人》中悲剧的根源之一。之所以笔者认为《消失的爱人》所探讨的并非单纯的婚姻问题,正是因为整个故事实际上都与女主人公艾米的心理问题有关。作为一个拥有名校心理学学位的女性,她深谙如何利用话语控制他人,为他人设下陷阱,给他人制造心理刻板印象,从而扮演各类能使自己获益的角色,而艾米最擅长扮演的便是弱者。由于艾米的心灵早已扭曲,即使她没有踏入婚姻的殿堂,电影中的惊悚故事同样可以发生在艾米与他人身上。而事实上,艾米也确实在结婚前就通过扮演被强暴的女性而成功使自己的前男友背负了多年的性侵罪名。而艾米本人之所以热衷于这种扮演行为,实际上还是在于自己身份的迷失。艾米及自己的父母都是知名人物,她是儿童读物《了不起的艾米》的原型,必须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知书达理、温柔乐观等优点,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大众情人式的“美国甜心”。这其实没有导致艾米在自我认同上出现偏差,她深知他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艾米,自己也能在本性与扮演之间转换自如。陷入“迷失”的实际上不是艾米本人,而是注视艾米的人们。如坚信艾米是忠贞贤妻,认为尼克是个负心混蛋的邻居诺伊尔,便是芸芸庸众的一个缩影。
(二)媒介与受众的众声喧哗
当代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众除了利用媒介获取信息之外,更利用媒介获取娱乐。而意味着话语权的媒介则往往由中产精英所掌握,大众很容易为媒介所引导,进入一场又一场话语狂欢中,如尼克在“负心汉”形象被曝光之后迅速陷入媒介解析的泥淖,大批媒体日夜守候在其家门外,电视台则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提高收视率,不断邀请专家分析尼克杀妻的可能性等,此时受众所呼唤的其实早已不是真相。艾米正是深知媒介话语导向的作用才扮演成遭受家暴的怀孕妻子,而尼克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也通过在电视访谈节目上扮演沉痛悔过的丈夫来挽回形象奋起反击。受众对于尼克的印象迅速被媒介固定又迅速为媒介扭转,这无疑是电影最大的讽刺。而电影有意设置了一个与艾米一起看电视的女孩,出身底层的女孩一语戳破艾米在媒介上的伪装,甚至通过打劫艾米的钱将算无遗策的艾米逼入绝境,生存的压力使这一女孩无暇加入狂热群众的围观中,反而更能看清真相,可以说这一形象是整部电影中最为清醒的角色。
二、《消失的爱人》中的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也是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内容。《消失的爱人》中的家庭伦理主要有两类:一是亲子伦理,二是手足伦理,这二者都是文学与戏剧艺术中进行家族叙事时屡屡涉及的伦理类型,对它们的处理也可以体现导演的价值取向与艺术匠心。
(一)亲子伦理
电影中艾米与尼克都有各自的父母,然而他们在处理亲子关系时几乎都是失败的。“理想之母”的角色在《消失的爱人》中是缺席的。尼克的母亲在电影开始时就已经因病去世了,从后面尼克在律师的训练下上电视节目的情节可以看出,母亲已经成为尼克用来标榜自己“孝顺”的一个符号。而实际上,尼克母亲可以说是尼克夫妇关系失和的导火线之一。正是打着照顾生病母亲的借口,尼克说服已经习惯了纽约大都会生活的艾米与自己搬到乡下小镇来开始艾米难以适应的生活。尼克的父亲则因为年迈痴呆而出现在警察局,与自己的儿子只有一墙之隔,随后尼克将父亲送回养老院。在尼克为数不多的与父亲接触的画面中,观众看到的是尼克的毫无耐心。而尼克一年仅仅探望父亲一次也成为他后来遭到口诛笔伐的弱点之一。
而艾米的父母则在电影中出现多次,他们的形象承担了塑造艾米阴暗家庭氛围和性格的任务。艾米拥有远胜于尼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拥有风靡全美的漫画《了不起的艾米》的版权。对于艾米,艾米父母从来没有给予过她无条件的爱,并且对艾米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如要艾米接受记者采访等。艾米仅仅是“了不起的艾米”的原型,是在处处圆满的“了不起的艾米”衬托之下的残次品(如不会拉大提琴,不会打排球等)。艾米很清楚父母对自己的真实态度,也已经习惯了父母在媒体面前表演式的生活方式。这种亲子伦理直接影响了艾米的两性关系:一方面她迫切地期待丈夫能够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爱自己的缺点与阴暗面,一旦发现自己得不到这样的爱时,她便会惩罚对方;另一方面,从小形成的表演人格又使艾米有意无意地在与尼克初识时看透对方的心思而将自己扮演为对方想要的“Cool Girl”。这种表演实际上正是艾米父母长期将艾米打扮成“美国甜心”后的一种自然延续。
(二)手足伦理
电影中的手足伦理则是由尼克兄妹来体现的。尼克与双胞胎妹妹玛格之间的感情也是尼克在事发之后遭到攻讦的弱点之一,尼克甚至在机场听到陌生人嘲笑他们为兄妹乱伦。在小说中,弗琳用大量文字介绍了“我”与玛格的关系,“我”对玛格的依恋之情。尼克与玛格并没有肉体上的乱伦关系,这也是尼克为何在机场会十分愤怒的原因,但是在精神上,两人又对彼此确实有着畸形的依赖。在电影中,芬奇用不少细节将弗琳的文字具象化了。如电影一开始便是尼克与玛格一起在酒吧无所顾忌地表达对艾米的不满。玛格的酒吧是在艾米出资帮助下开起的,玛格却对艾米没有任何感恩之情,相反总是以自私、低俗的腔调诋毁艾米。又如,玛格自己没有恋人与朋友,在发现尼克确实出轨后的恼羞成怒,以及在电影结尾时两人拥有一段暧昧不清的对白,尼克决定留在心如蛇蝎的艾米身边,玛格为此崩溃痛哭,尼克恳求玛格陪着他,玛格则流着泪说他们早在没出世前便彼此陪伴了。对于早已在《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1999)中尝试过精神分裂叙事的芬奇来说,玛格除了是原著中的角色以外,实际上还承担着尼克的另一重人格。电影中已经交代了两人因为是孪生兄妹而有心灵感应,当尼克决定继续自己窘迫的处境后,玛格的崩溃实际上也是尼克内心隐忧的反映。
三、《消失的爱人》中的两性伦理
两性伦理则是整部电影中负载着戏剧张力的伦理类型,也是艾米的主要伦理诉求。电影中与艾米发生两性关系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其丈夫尼克,另一个则是她的高中男友德西。
艾米与尼克的关系经历了初见时彼此对形象的伪装以及婚后真面目的暴露,直至彼此伤害,尼克出轨,艾米伪造家暴与他杀,最终两人又选择继续在扮演中继续生活,甚至还要生儿育女这一过程。婚姻在电影中呈现为一种压抑的态势,两人都极为自私且自怜,在是施害者的同时又是受害者。艾米最终没有因为杀人而被绳之以法,尼克也没有揭露艾米,整个婚姻成为一个牢笼锁住两人,当两人面带微笑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电影传递出来的婚姻的绝望感,实际上要远比电影开头时更为强烈。在影片开头,两人正在谈论离婚,虽然记恨彼此,但此时这段婚姻仍然有结束的可能。然而在结尾时,离婚的可能已经不存在,尼克已经明明知道身边人具有蛇蝎心肠却无法离开,还需要在未来强颜欢笑,在恐惧与虚伪中度过余生。两个人已经比电影开始时更憎恨彼此,却又要扮演得更爱对方,婚姻成为“无期徒刑”。而电影在结尾时的漫长也给予了观众一个沉淀思绪的时间,让观众感受到片中人的身心俱疲。
德西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出于情节的需要,使艾米在被抢劫之后能有一个容身之所和替罪羊,最终顺利回到尼克身边。德西之所以被艾米杀死,除了他知道艾米还活着的真相以外,还与德西比艾米更为强烈的控制欲有关。电影中,芬奇多次表现了德西对艾米无处不在的控制,如不由分说地拿走艾米手中的平板电脑,在湖边小屋的所有出口都装上摄像头,在性上采取主动、逼迫的姿态等,这些对于德西形象的完善都显然比仅仅把德西塑造成一个痴情的、轻信的牺牲品角色更容易激发观众的思考,从而达到叙事的伦理效果。
大卫·芬奇的电影往往能够在保证商业回报的同时,又不忘在电影中注入人文关怀精神。《消失的爱人》亦不例外。从对《消失的爱人》的叙事伦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电影作为叙事艺术的一种,其叙事文本是可以用叙事伦理理论进行解读的,而叙事伦理本身也对当今社会有着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河北省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专业写作名词化研究”(项目编号:2015YYJG067);防灾科技学院2015年院级教育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JY2015B14)。
[参考文献]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01).
[2] 胡荣.社会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焦国成.论伦理——伦理概念与伦理学[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4] 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比较论纲[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