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一环
——安达卢斯俚谣
宗笑飞
世界文学
被忽略的一环
——安达卢斯俚谣
宗笑飞
阿拉伯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后,安达卢斯地区(包括今西班牙大部及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有了自己崭新的文学形式,从而改变了西哥特王国的文学形态。首先是阿拉伯悬诗的变体:彩诗,然后便是东西混血儿:俚谣。后者不再延用古典阿拉伯语,而是安达卢斯阿拉伯语和拉丁方言杂糅的产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俚谣是近代西方民间文学的最早表征之一,为西班牙文学乃至普罗旺斯民歌奠定了基调。
东学西渐;俚谣;西班牙谣曲
精神文明总是步履蹒跚,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梗阻和倒退。罗马帝国消亡后,日耳曼人在南欧建立的东、西哥特王国几乎一夜之间回到了“蛮荒”(又称“黑暗”)时代。因此,东、西哥特时期几乎没有产生像样的文学。而近代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国文学几乎是在阿拉伯人的刺激下从头开始的,口口相传的民间谣曲就是其初始阶段的不二选择。
然而,囿于俚谣是东西文化杂糅的产物,西方乃至一般阿拉伯诗人、学者皆对其表示不屑。最早持否定意见的是安达卢斯中世纪文学史家伊本·赛义德(,?-一二八六)和伊本·赫勒敦(,一三三二-一四〇六),后者在其《绪论》()的末章中对俚谣进行了贬斥。同样,阿卜杜·阿齐兹·艾哈瓦尼()也在一篇题为《安达卢斯伊本·赛义德〈奇谈节选〉》(“”)的檄文中完全无视俚谣的价值,并全盘接受了伊本·赫勒敦关于俚谣的评骘和伊本·赛义德的否定观点。艾哈瓦尼还在《绪论》和《奇谈节选》的注疏中对二者有关俚谣的评述进行了比照,认为二者言之有理,而且一脉相承。伊赫桑·阿巴斯甚至断言俚谣的语言是彻头彻尾的方言俚语,“还不时夹杂着一些罗曼司词汇”。①总之,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皆以清教徒式的矜持或古板轻视俚谣,他们对任何民间文学或口传文学漠然相向、不以为然。及至十六世纪依然如此。
西方学界视这一“道统”为圭臬的也大有人在。一九三三年,最早研究俚谣的德国学者尼克尔在《伊本·古斯曼〈歌谣集〉》中就曾援引科林的话说,俚谣“只不过是以西班牙本地方言而非古典阿拉伯语创作的彩诗”。①转引自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Richmond:Curzon Press,2011,p.31。此外,斯特恩于一九五一年撰文称俚谣为“类彩诗”,“是在彩诗转化为阿拉伯安达卢斯方言的过程中形成的”。②转引自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Richmond:Curzon Press,2011,p.31。长期以来,学界几乎一概排斥方言俚语和口传文学,而俚谣作为民间小曲,自然不登大雅之堂。人们还常拿伊本·宰敦的经典写作来反衬伊本·古斯曼的俚谣,甚至通过一个词汇在俚谣中重复使用的频率,来判断它是否符合经典阿拉伯语诗歌的规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学者对上述陈见提出了质疑。艾布·海达尔在其《西班牙-阿拉伯文学与早期普罗旺斯民歌》(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中曾举例说明俚谣对西方文学重新的发轫至关重要。在新版《伊斯兰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中,科林也明确肯定了俚谣的功绩,认为后者并未脱离古典阿拉伯语,而是其口语化变体。加西亚·戈麦斯则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三卷本《古斯曼全集》(Todo Ben Quzmān)中,就俚谣的语言是否纯属安达卢斯方言这一问题表达了更为鲜明的态度,修订了他之前的观点,谓“事实上,伊本·古斯曼无疑经常使用古典阿拉伯语。我们甚而可以大胆推说,使用古典阿拉伯语乃惯性使然。反之,伊本·古斯曼的安达卢斯方言同样与生俱来、无可避免”。③García Gómez:Todo Ben Guzmān,vol. III. Madrid:Editorial Gredos,S.A. 1972,p19.
如今,学者们开始越来越重视俚谣的价值,有关研究方兴未艾。人们发现俚谣的语言并非全然来自安达卢斯方言,它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古典阿拉伯语及其变体。俚谣大师则多为精通经典阿拉伯文学的饱学之士,他们不仅能背颂长篇累牍的古典韵律诗,而且艺术造诣较之任何同时代的东方大师毫不逊色。换言之,他们并不都是下里巴人,而是重视下里巴人和民间艺术的安达卢斯本土诗人。因此,研究俚谣不仅有助于了解安达卢斯文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厘清它与近代西方文学,尤其是早期口传文学、民间文学的某些因缘。
一、俚谣的由来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俚谣并非无根之萍。它与丰厚的东部阿拉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八世纪,安达卢斯地区的阿卜杜·拉赫曼一世自立为艾米尔,在西班牙建立了阿拉伯后伍麦叶王朝。此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东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进入鼎盛。西部后伍麦叶王朝一方面急于与东部抗衡,发展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东部学习,特别是继承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在此,首当其冲的便是借鉴阿拉伯诗歌传统,并加以改良。彩诗和俚谣就被众多阿拉伯文人视为东部诙谐文学的西方奇葩,它们不可避免地吸纳或者催生了西方的民间文学。
其次,早在彩诗和俚谣产生之前的公元八-九世纪,以艳情诗和各种打油诗为标志的诙谐文学()就已兴盛于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时人普遍认为文学作品必得趣味盎然,有娱乐功用,否则就没有受众。因此,十一、十二世纪安达卢斯诙谐文学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公元九世纪,文学巨擘伊本·古太白(,八二八-八八九)就曾在其《故事源》()序言中解析了诙谐文学的特点和价值,并一语道出了俚谣的本质。他固然不像先于自己的贾希兹(,伊历一五九-二五五/公历七七五-八六八,公元八-九世纪伟大的阿拉伯文人,文风诙谐犀利)那样诙谐幽默、生性奔放,而是以严谨著称,却也认为作家可以采用轻松幽默的方式以吸引受众:“辱骂和斥责人们的幽默,那才是非法和不道德的。所有这些(幽默)在法拉兹达格的诗中很少见到,但后者恰恰不敬女性。而我,决不允许你们使用这类不严谨的语言,除非是讲述各类或长或短的故事。”④他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字字合规,就失去了自我和魅力,读者读其作品也会觉得索然寡味。
此外,早在彩诗和俚谣出现之前,《故事源》就在安达卢斯地区非常流行。伊本·拉比《罕世璎珞》的主要素材和灵感来源即是《故事源》。《故事源》共四册,分十卷。每卷论述一个专题,是一本论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巨著。其篇目依次为:君王篇(一译统治篇)、战争篇、政治篇、本性与卑劣篇、学问与阐述篇、修行篇、兄弟篇、需要篇、食品篇和妇女篇。在君王篇中,作者谈到了君王应有的举止、应行的策略。伊本·古太白在书中经常援引他人的言行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场白常常是:“我从某某书中读到过这样的话”/“我从一本印度书中读到过(这句开场白在书中尤为常见,说明《故事源》受到印度文学影响很大)……”/“我在《新约》中读过……”等等,颇有佛经中“如是我闻”的意味。《故事源》一书是当时阿拉伯、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而《罕世璎珞》则将故事分为二十五个部分,并与《故事源》相同,将关于国家和战争置于首篇,而将食物和女性置于末篇。其次,在行文方式上,《罕世璎珞》也大抵效法《故事源》,但这是另一个话题,本论文不再讨论。
回到东部诙谐文学,其主要代表文人除了以上提到的贾希兹、伊本·古太白之外,还有阿拔斯时期的酒诗人艾布·努瓦斯。艾布·努瓦斯据说曾创作一万两三千首联句“”诗,且内容、题材各不相同,主要有颂诗、挽诗、情诗、讽刺诗、劝世诗等几大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其咏酒诗,这也为他赢得了“酒诗人”的美誉。其中最能体现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和谐趣意境的当属其艳情诗、讽刺诗和咏酒诗。西班牙伊斯兰时期,艾布·努瓦斯的诗歌受到安达卢斯诗人的推崇和追捧,人人都竞相效仿。谁的诗歌如果被指有艾布·努瓦斯之风,那便是平生得意之事。
此外,《一千零一夜》以及各种阿拉伯民间笑话和玛卡梅的广为流传,也对安达卢斯诙谐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千零一夜》以及各种阿拉伯民间传说在安达卢斯时期尚未定型,其对俚谣的影响或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中。而玛卡梅则比较特殊。公元十至十二世纪,玛卡梅体小说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其思想内容、创作方法和语言特征已臻完善,并开始产生变异。早在九世纪玛卡梅问世之时,其主要目的是教授阿拉伯语(可参见赫迈扎尼《玛卡梅集》),因此多选用趣味性强、幽默诙谐或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内容则以反映下层百姓生活为主,间或有讽刺统治者昏庸、世风凋敝的文字。但语言上,赫迈扎尼则竭尽雕琢之能事,在韵律、对仗方面也非常讲究,其旖旎的语言风格甚至颇有卖弄学识之嫌。而自哈里里开始,玛卡梅的故事情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故事内容也更加丰富、完整和饱满,也更利于反映底层生活。但总体说来,后者的语言仍略显艰深玄奥。公元十至十二世纪,与彩诗相仿,安达卢斯的玛卡梅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但语言仍延续前人的创作风格,此时兴盛的彩诗也多采用古典阿拉伯语。在这种情形下,俚谣作者们便有意使用方言、土语,甚至某些粗俗鄙陋的语言以抗衡雕琢旖旎的文风,从而对传统写作形成一种“反动”。
在艾布·海达尔看来,迄今为止东西方学者都很少视俚谣为值得钻研的课题。自十六世纪贾马里亚·巴别里(Giammaria Barbieri,一五一九-一五七四)以降,西方学者对彩诗和俚谣的所有兴趣几乎仅限于它们能为十二世纪普罗旺斯民歌和阿基坦宫廷情诗(Aquitaine court poetry)提供哪些可能的注解。换言之,这两种诗歌形式之所以被研究界所重视,是因为它们或有的文学史价值:它们是近代西欧文学发轫的渊源与研究“基数”。①Abu 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Richmond:Curzon Press,2011,pp.33.
西班牙-阿拉伯俚谣于十二世纪达到顶峰。时值游吟诗人(Juglares或Trovadores,后者据说直接源自阿拉伯语“”的组合,意为边歌边舞)成为诗歌、音乐乃至各种民间文艺的传播者。而且,他们不仅在民间,即或在伊比利亚北方基督徒宫廷之内也充当了时鲜艺人的角色。他们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上至王公贵胄,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对其馈赠津津乐道。梅嫩德斯·皮达尔(Menéndez Pidal)有一部描写这些江湖艺人的著作,将后者誉为“诗艺传播者”。①Menéndaz Pidal:Poesíajuglarescayjuglares:aspectos de la historia literaria y cultural de España,Madrid:Espasa-Calpe,1975,p.100.简言之,游吟诗人以歌咏、音乐,抑或形形色色举止夸张的行为艺术如戏仿、舞蹈乃至杂耍取悦观众,同时为他们带来各色故事、新闻。
海达尔断言,在西班牙基督徒王国,游吟诗人和俚谣作者是可以划等号的。这一观点来自他对伊本·古兹曼的了解。
二、俚谣的形式与内容
俚谣韵律专家戈顿(T. G. Gorton)曾说:“如果没有伊本·古兹曼的一百九十三首俚谣的发现,这种诗歌形式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名词。”②Gorton:“The metre of Ibn Quzmān:A Classical Approach”,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 VI,1975,p.1.此言可谓不虚。伊本·古兹曼的作品充分体现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无论就语言、内容,还是韵律、风格而言)。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歌谣集》决定了同时期乃至后来俚谣的发展向度。
一八九六年,伊本·古兹曼《歌谣集》(或曰《俚谣集》)的一百四十九首俚谣手稿副本由德国学者大卫·德·古兹伯格(David de Gunzburg,一八五七-一九一〇)在彼得堡发现,并付梓出版,从而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歌谣集》始终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迄今仅有极少数西方学者视若珍宝。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伊本·古兹曼的《歌谣集》大多以安达卢斯方言写成,这使得许多阿拉伯学者并不关心,甚至认为它难登大雅之堂;二是在东方学者的脑海中,始终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俚谣和彩诗是东西方文化的混血儿,既不算东,也不算西,进而将其视为另类()。不过,近年来情况正在改变,阿拉伯学者开始翻译、研究《歌谣集》。自一九九五年埃及首次出版伊本·古兹曼《歌谣集》全本之后,这部“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俚谣集”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在西方,自一九三三年德国东方学者尼克尔出版《伊本·古兹曼〈歌谣集〉》一书以降,由他翻译注疏的《歌谣集》拉丁语版本——序言则保留了原来的语言——也相继出版。之后是一九七二年西班牙学者加西亚·戈麦斯的《伊本·古兹曼研究大全》。编者根据伊本·古兹曼俚谣的不同手抄本,将有关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但由于年代久远,不少手抄本存在着诸多错误,致使戈麦斯的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给后来的解读和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一九八〇年,马德里西班牙阿拉伯学院教授韦德里科·库林特(Corriente,Federico)出版了阿拉伯文的《伊本·古兹曼〈歌谣集〉:文风、语言及韵律》(),该书第一次从安达卢斯方言的角度分析了伊本·古兹曼的特点。二〇〇一年,阿拉伯裔美国学者艾布·海达尔出版了《西班牙阿拉伯文学与早期普罗旺斯诗歌》一书,并辟专章纠正了戈麦斯著述中的讹误,同时分析了伊本·古兹曼俚谣的语言风格,是推进俚谣研究的重要一步。
一八九六年发现的一百四十九首俚谣,加上后来的收集、整理,伊本·古兹曼流传至今的俚谣共有一百九十三首,均被收录在他的《歌谣集》中。这些都是研究安达卢斯通俗文学乃至社会、民风的重要资料。基于此,本文便以《歌谣集》为例,来分析俚谣的语言、形式及韵律特点。
伊本·古兹曼(一〇七八-一一六〇),生于科尔多瓦,出生世家,被视为安达卢斯东西方混血文学的代表和俚谣的集大成者。据说,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塞维利亚度过,且地位显赫,但仕途不济、命运多舛。作为诗人,他一直标新立异、不同凡响。因此,在众多文人竞相效法东部阿拉伯文学或大量创作彩诗之际,他却选择了俚谣,并且以安达卢斯方言进行创作。这也使得他一跃而成为“”(俚谣泰斗),同时奠定了其在安达卢斯文坛不可或缺的地位。如此,他的俚谣不仅在安达卢斯地区流布甚广,而且一直流传(返销)到东阿拉伯地区。他也因此被视为唯一可与东阿拉伯帝国文豪艾布·努瓦斯遥相媲美的时代翘楚。
关于伊本·古兹曼的外貌,我们无从查考,只能根据他在一首俚谣中的自诩演绎推断:金发碧眼,体量伟岸,身材高挑,体格强健:
你且看我,身形挺拔,
双臂修长,金发碧眼,
神清目朗……
有学者故而指他是东西混血儿,并认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精通安达卢斯拉丁方言。但苦于没有证据,这只能流于猜度。另一方面,诗人生活考究,衣必光鲜,居必广厦,食必丰美;对朋友他一诺千金、重情重义。这些特点,都可以在他的俚谣中窥见一二。
首先,伊本·古兹曼的俚谣在主题上延续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传统。自蒙昧时期起,赞颂即被视为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基本主题,或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因此,颂诗在阿拉伯传统诗歌中比比皆是。它们有利于记录、研究阿拉伯历史;记述统治者的功绩和宫廷生活;展示学者们的学识智慧。颂诗内容一般由两方面组成:第一类不外乎传统颂诗,其赞颂对象多为统治者或是王公贵胄,诗人歌颂他们的慷慨、仁慈、英勇和宽厚等高贵品质。诗人甚至以此为谋生之计,期待获得被赞颂者的赏赐。第二类则是矜夸类颂诗,或矜夸自己的风雅俊朗;或矜夸部族首领、同道的骁勇彪悍;以及描述争战场面的壮烈等等。彩诗在安达卢斯地区兴起后,基本延续了这个主题,俚谣也不例外。在《歌谣集》中,称颂统治者、执法者、王公贵族以及伊玛目等教长的颂诗就有近四十首,占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在一首颂诗中,伊本·古兹曼写道:
世间王公,众人福祉
血统高贵,强健身体
尊贵荣耀,无人可比
倾其所有,何谈悦己
乐善好施,换来谢意
……①?这首诗据说是为了称颂某位名叫阿布·伊斯哈格·本·穆瓦萨里的权贵。
第二类颂诗,即矜夸类颂诗,在《歌谣集》中也十分常见。伊本·古兹曼对自己的外貌赞赏有加,几乎达到了自恋的程度。前面所引其自诩俊朗的俚谣即是显证。关于性格,他也曾不无矜夸地写下了:
我恰似镰刀一把,
正直似利刃弯弯。②转引自 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Richmond:Curzon Press,2011,p.35。
伊本·古兹曼及同时代俚谣诗人大都放浪形骸,并以此为荣。他们甚至大肆渲染自己的放荡行为,丝毫不觉得羞赧。这几可谓俚谣诗人的共性特征。即使在俚谣的另一重要主题——挽歌当中,诗人也毫不掩其诙谐乃至略显轻浮的本性。例如,在其第八十三首俚谣第十四节中,伊本·古兹曼是如此缅怀先君的:
自你走后,众人无依,
好似秃头,虱子戚戚。③转引自 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Richmond:Curzon Press,2011,p.35。
除了颂诗、挽歌之外,俚谣的另一个主题便是爱情。这在《歌谣集》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总体说来,《歌谣集》即是颂歌、挽歌和情歌的集合,几无例外。一首歌颂梦中情人的谣曲这样写道:
我的心上人呀,你伤透我的心。
我心已破碎呀,你是否会知情?
……
我的心上人呀,那日三生有幸,
得睹芳容若锦,胜于明月初升。
恰似春光满园,你是美丽化身,
鲜花权作地毯,在你脚下延伸,
……
美轮美奂之身,真主赋予卿卿,
姣妍无与伦比,而且永远白净。①
要之,俚谣的主题一方面延续了传统阿拉伯诗歌的主题,另一方面又明显加入了新的元素如语汇、旨趣和意境。也正是这种新的写作风格,使得俚谣独树一帜,成为阿拉伯诗坛玲珑璀璨的明珠。
这种新的写作风格的首要体现,便是其语言。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中曾经说过:一个人有可能言不由衷,“但是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②[德]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第3页,印芝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虽然他说的是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式语言风格,但我们可以进行类似的推理:一个人使用的词汇可能会有变化,但整体风格却无法掩盖其性格特征,亦即人们常说的“风格即人”。
俚谣的第一个语言共性便是方言。有学者认为它是纯粹的安达卢斯俚语,夹杂了大量的罗曼司语元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俚谣的语言并非纯粹的罗曼司俗语,而是一种阿拉伯古典语言的变体。它灵活多变,不受古典阿拉伯语语法的束缚,更能体现幽默、诙谐的风格,也更适合表达安达卢斯普通民众的情感与心理诉求。
且看一句早期的匿名俚谣诗句:

(我饮酒来船为皿,敲起鼓来拨动琴。)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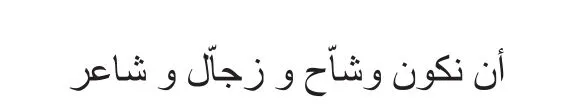
……
(丰功伟绩的创造者啊,我们这些彩诗作者、俚谣手和诗人……不会有损你的威仪)④
也正因为如此,俚谣往往受到传统阿拉伯学者文人的诟病,被指韵律松散失规,语言简单粗俗。他们认为这样的作品实在难登大雅,从而将其从文学史中抹去。而事实上,许多作者如伊本·古兹曼,对古典阿拉伯语的精通程度当不亚于穆泰奈比或艾布·努瓦斯。他们语言之丰富、骈偶之旖旎、对仗之考究非同时代其他诗人可比。他们对古典阿拉伯诗文的娴熟则几乎到了可以信手拈来的地步。譬如,《歌谣集》序言便是一篇美轮美奂的阿拉伯骈文。而俚谣作者之所以乐于大量采用诙谐、幽默的方言俚语,则大抵是因为后者符合他们表达的旨趣。有诗为证:
这首俚谣多么鲁莽,
闻者听了如此癫狂
最好还有乐器相伴
来点儿当!当!当!①穆德哈里(Mudghallīs)俚谣,转引自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p.35。
此处且援引艾布·海达尔博士的一段引文,来表明俚谣作者大量采用方言俚语进行创作的初衷。这段引文出自摩洛哥拉巴特公共图书馆的第D985号手稿,作者据说是十三世纪一位名叫阿布·雅赫耶·欧拜德拉·扎杰里(,?-一二九四)的文人。他在手稿中写道:
我将作品分为两部分,目的有二。第一部分我认为适宜颂扬先知(愿他平安)的传统。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会令读者获益匪浅。这部分我以经典阿拉伯语写成,语言优美,娓娓动听,并且引用大量的阿拉伯语格言、警句以及前朝大师们的精美演说。我选择它们,是因为其教化功用,且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其二,本书的第二部分使用下里巴人的俗言俚语和乡村野夫的恶言谩骂。它们尽是些通俗的、不合时宜的阿拉伯土语和滑稽笑话,是常年挂在人们嘴边的方言俚语,有些甚至尚未摆脱动物的粗野,其趣在于使听众开怀大笑。要是我用经典阿拉伯语来呈现后半部分的内容,那对我而言将更为轻松容易。但那样会使它失去原有的色彩和滋味。所以,我保留它们的原汁原味,以为不失其趣。它们足以帮助人们消解愁闷、转苦为乐,变他们的紧张和压力为轻松和愉悦。②转引自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p.38、p.95、p.95.
这段话道出了俚谣创作的初衷和本质,也写出了俚谣作者们的难言之隐和尴尬境地。
俚谣的另一个语言特点是大量使用指小名词。据统计,在伊本·古兹曼《歌谣集》中,指小名词的使用多达近二百次,其中许多指小名词的单个使用频率也在十次左右,例如(有“小事、一会儿”等意,竟出现了多达十次),(饮料的指小名词,可理解为“喝点小酒”、“小酌两口”,出现了六次),(“小俚谣”,出现了六次)等等。这些指小名词的频繁使用有亲昵(如前引诗中出现的)、调侃、打趣的意味。有学者甚至认为,伊本·古兹曼使用指小名词,是受到了西班牙本土拉丁俗语的影响,因为阿拉伯语在进入安达卢斯之前是没有指小名词的。而伊本·古兹曼作品中的相关指小名词在同时期及之前的安达卢斯阿拉伯文学作品中也很少出现,倒是在同时期的罗曼司语中一直大量存在。对于此观点正确与否,需要从专门的语言学角度,对安达卢斯之前的文学文本作大量考证来研究解决,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伊本·古兹曼时期,指小名词的使用频率确实有了质的变化,且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这在拉丁俗语西班牙语中至今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古兹曼之后,阿拉伯语的指小名词与西班牙语中的指小名词相互交融,就很难确定孰先孰后了。例如,西班牙语中的指小名词“albufera”(滨海湖),就显然是阿拉伯语指小名词的音译。类似例证还有很多。总之,指小名词的使用,成为了俚谣语言的又一大特征。如前所述,作者常借此表达亲昵、爱恋。且看伊本·古兹曼的小诗:
(这首小小俚谣哦,出自我破碎的心)
说到俚谣,伊本·古兹曼几乎言必用“小俚谣”这个词,以表达他对俚谣不无自豪的爱恋,他甚至在第六十五首俚谣末尾说:“和这首诙谐小诗相比,所有诗歌都一无是处”。
除了指小名词(也作小化词,西班牙语中多表示亲昵),伊本·古兹曼还十分钟情于使用另外三个词汇:“”(插科打诨或戏谑逗乐)、“”(放浪形骸或风流成性)以及“”(暗藏玄机或话中有话),这三个词几乎成了他的标志语。④转引自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p.38、p.95、p.95.“风格即人”,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他自身放浪不羁的性格特征。
他反复强调,放弃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就等于让他放弃他的艺术感觉。他甚至在这样的表述之前加上强调语气的经典阿拉伯语,以及限制性小品词(同样是经典阿拉伯语“”,意在强调其对放浪生活的重视):(第九十首俚谣,第一节)
(倘疯狂赐予我放浪之路)(第二十五首俚谣,第二节)
(忙忙碌碌皆为放浪形骸)①转引自Abu-Haidar:Hispano-Arabic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Provençial Lyrics,p.36.
更有甚者,海达尔在摩洛哥第D985号手稿中发现了这样的诗句,他认为这样的语言几近厚颜无耻,粗俗鄙陋:

(人若倒霉,下身都能将自己绊倒)②这里的“下身”具有性指涉。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手稿中出现的另一句谚语,其含义与上述诗句大同小异,而语言则显得典雅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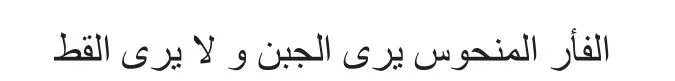
(倒霉老鼠,只见奶酪,不见有猫)③见手稿,第235页。
由此,可以看出,俚谣首先是一种“诙谐文学”(),它以它的滑稽、通俗(有时甚至不乏粗俗),实现了“贵族与下里巴人的耦合”:借艺术之名“率性而为”。④Menéndaz Pidal:Poesíajuglarescayjuglares:aspectos de la historialiterariay cultural de España,p.101.
三、西班牙古典谣曲
生活化语汇的使用为伊本·古兹曼的俚谣奠定了诙谐、滑稽、放浪不羁的文风;而在俚谣格律方面,他不仅进一步改良了阿拉伯诗歌,也对日后西班牙谣曲,尤其是西班牙谣曲的韵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先说内容。首先是作为彩诗衍生物的缀诗——哈尔恰,特别是罗曼司语哈尔恰,它完全具备了俚谣的世俗化特征,譬如以下几首:
一
依汝所愿,姐妹们哦!
我如何才能免灾祛难?
没有情哥我不活:
他的踪迹何处觅?
二
若是好男悦我,
亲吻两串珍珠,
在我樱桃嘴中。
三
情哥哥快来呀!
你若撒谎逃避:
必遭电打雷击,
快快到我怀里!
四
你知道,我的爱,
没有你,我会殁;
我的爱,快来呀:
不见你,我无眠。
五
珍珠口衔,
津似蜜甜,
来吻我吧!
入我怀抱,
和我一体,
恰如昨昔。①转引自Frenk:Las jarchasmozarabes y loscomienzos de la líricarománica,第112页。
这样大胆热辣的情感表达,在西哥特拉丁时期是难以想见的;即或坊间曾经有过,也早已被强大的宗教神学所淹没,或谓阉割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一首类似的西哥特拉丁情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异现象。
至于后来的罗曼司谣曲则更是充满了俚谣的世俗化特征。譬如葡萄牙-加利西亚的“情人谣”:
情哥哥,我该怎么办?
难道你不管我死活?
我爱你却无好结果。
我的爱饱受重创!
啊咿呀,愿主保佑!
他怎知我多爱他!
啊咿呀,愿主保佑!
母亲呀,我该怎么活?
我无眠,并将永无眠,
只因我的爱他在宫廷,
让我翘首等待多熬煎。
一天,情哥哥离开此地,
不再回来,我不得而见。
妈妈呀,我要呜呼哀哉。
而所谓的维良西科——卡斯蒂利亚村民谣或山民谣——则庶几是俚谣的罗曼司语翻版,故而也常常直接被称为俚谣。以其最初的表征为例,则几乎与哈尔恰并无二致:
哈尔恰维良西科
二二
我的心已经走了:我爱走了,母亲,
拉布,他还回来?去了遥远的地方:
亲亲让我心疼痛!我却不能将他忘。
我的心病何时愈?谁能唤他往回转?
三三
汝若爱我,你若爱我,
好男人哦,我的夫人,
汝若爱我,你若爱我,
给我一个(把你给我)。我心好逑。②所不同只是哈尔恰多为女性口吻,而维良西科则是杂糅的。转引自Frenk:Las jarchasmozarabes y loscomienzos de la líricarománica,p.144.
以类别来看,西班牙古典谣曲主要内容可按题材分为:
(1)古代历史(即前西班牙历史);
(2)西班牙(或葡萄牙)历史;
(3)骑士传说(如熙德、罗兰、特里斯当、兰斯罗特传奇);
(4)歌颂历代国王或王后;
(5)爱情;
(6)虚构故事(如《女兵谣》“La doncella guerrera”、《夫记谣》“Las señas del esposo”等);
(7)圣经故事;
(8)希腊罗马历史及其神话故事;
(9)宗教故事;
(10)“摩尔人”和“光复战争”。
再说形式。传统阿拉伯诗歌对格律的要求十分严格。悬诗以降,阿拉伯古诗便形成了大致十六种格律,如长律(,八音步格律)、延律(,六音步格律)等,而且基本采用一韵到底的形式。到安达卢斯时期,彩诗开始采用变韵的方式,形成灵活多变的多韵体诗。伊本·古兹曼更是在彩诗的基础上创造了多重格、多重韵。其中既有传统的八加八
一一
妈妈呀,我当何如?我的妈,我不知
情哥哥已在家门口。是否替他把门开。格,也有六加六格,甚至四加四格,押韵方式也更加自由。
西班牙谣曲所遵循的八加八格和六加六格、偶句押韵方式,固然有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印迹,但显然更加受惠于伊本·古兹曼这个“近亲”。十九世纪,人们发现后者的手稿时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西班牙古典谣曲的所指“Cancionero”直接来源于他的同名诗集。当然,囿于政治、历史、文化和宗教等诸多原因,西班牙基督徒在“光复战争”期间就已启用“Romancero”这一词汇以取代“Cancionero”,尽管后者更具有生命力。因为“Romancero”源自罗曼司语(Romance),无法涵盖所有谣曲。而“Cancionero”则不仅是罗曼司语,而且指代所有歌谣。而伊本·古兹曼的《歌谣集》之所以被翻译成“Cancionero de Ibn Guzmān”,显然是因为最早翻译其谣曲的文人认为他的诗歌与西班牙早期谣曲有源流关系。
伊本·古兹曼早期俚谣有单句诗和联句诗两种,单句诗多为两节或三节,押韵方式为aaad,bbbd,cccd或aaaad,bbbd,ccccd。如他的一首歌颂是这样的:
像光芒面对纷扰(a)
太阳也格外明朗(a)
皓月为其添俊朗(a)
伊本·艾布拉什啊(a)
能消除所有困窘(d)
这姿容令人迷恋(b)
谈吐优雅让人念(b)
如你渴望甘甜水(b)
他会带你至泉涌(d)
话语似黄昏明日(c)
我等众人却沉默(c)
只因这仅是开始(c)
人们敌意来面对(c)
离去却成其朋友(d)①
他的联句诗则采用偶句押韵的形式,诗的末句换韵,如ab,cb,db,ed。 而联句多诗节的作品,其押韵方式则为:ab,cb,db,ed ;gf,hf,if,jd ;kx,lx,mx,nd……。众所周知,拉丁诗歌是有格(律)而无韵的,其格律由音节和重音搭配而成,恰似我国古典诗词中的平仄;而西班牙古典谣曲从一开始就既有格律又有韵脚,不啻是受了伊本·古兹曼的影响,自然也是整个阿拉伯古典诗歌传统的赓续。我们来看看下面这首伊本·古兹曼的俚谣:
我对你夸拉比阿(a)
皮肤洁白又粉润(b)
他乃众民之领袖(c)
容貌清朗又英俊(b)
品性高雅且聪慧(d)
见之犹如沐春风(b)
学识丰富且深邃(e)
见了仇敌也慷慨(d)②
而一些罗曼司语情歌显然也具备了这样的格律形式,每行由(六加六)十二音节联句组成,偶句压韵。这正是中世纪晚期西班牙语谣曲的主要特征:
理性丧失殆尽,巨大声望所致;
觊觎伊人美貌,施展手段有技。
你是麦加之幸,我正为你而疾!
使出浑身解数,吟出无数颂诗。
你却离我而去,牵手欢愉已毕?
亲爱的人儿哦,我罪何至于此?
遥想昔年如昨,相逢何必相识,
亦歌亦舞尽兴,但见幸福无际。
我愿为伊而生,尽管身世卑微;
经过不懈努力,总能出人头地。
惜我青春年少,远别乡亲故里;
千里万里行程,朝着圣地迁移。
千难万难何惧!朝朝沐浴更衣,
夜夜美梦似真,痴心日复一日。
那是美妙时光,我心紧随我意,
今天爱上娇娥,明天还有更丽。
……①Francisco Reina:Poesía Adalusí(需要添加补字图),Alicante:Universidad de Alicante,2004,pp.503-504、pp.509-510;其忠实的西班牙语译文或为:Perdí la razón,teniendo gran honra;Que obró a su sabor,por una coquta. ¡Ternera de Meca,por ti me muero! De ti mi loor,toda hora renuevo. ¿Tu mano por qué soltóme tan pronto? ¿Qué hicieronse,di? Cariño y afecto.……
另有一些十六音节以八加八形式出现,偶句押韵。如:
爱情分明似那重负,没人能够肩负长久!
英俊小伙奋勇向前,美名可用性命换取。
当知有否爱情秘诀,相爱之人眉目倾诉。
明眸难藏内心感悟,巴别通天之塔仿佛;
骄傲矜持逃遁一空,爱情来时理智全无。
绵绵乡思了无尽头,你可知道你心如缚?②Francisco Reina:Poesía Adalusí(),Alicante:Universidad de Alicante,2004,pp.503-504、pp.509-510;其忠实的西班牙语译文或为:Perdí la razón,teniendo gran honra;Que obró a su sabor,por una coquta. ¡Ternera de Meca,por ti me muero! De ti mi loor,toda hora renuevo. ¿Tu mano por qué soltóme tan pronto? ¿Qué hicieronse,di? Cariño y afecto.……
前面说过,由于在阿拉伯人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之前,拉丁诗人的作品有律无韵,而西班牙早期谣曲既有律又有韵,正是受到了阿拉伯安达卢斯诗歌的影响,作为个中桥梁的伊本·古兹曼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仍罕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赜考究。因此,我的方法是择其与西班牙罗曼司谣曲的相同相似之处进行平行比较。
在西班牙,谣曲又被基督徒称为罗曼采,与罗曼司(Romance)本是同源同宗的并蒂莲。它们一而二,二而一,难分难解。随着“光复战争”的节节胜利,战争中流传的各种消息和传说成为行吟诗人的主要游唱内容。它顺应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同时,基督教王国的后方生活也为这些谣曲的传播者提供了想象的余地。他们迎合不同地域的信息诉求和审美需要,不断翻新内容,从而催生了大量的谣曲和更为众多的谣曲变体。
古典谣曲(Romances viejos),又称古罗曼采,是西班牙语文学的最早表征之一。它口口相传,变体众多,且极易散佚,因而发轫年代难以查考。也许它们与流行于公元十至十二世纪的哈尔恰或十二、十三世纪的俚谣等抒情色彩浓郁的民歌民谣,以及同时期的英雄传说等有渊源关系。它们多以佚名散篇的形式通过行吟诗人的游唱在民间流传,不少篇什被巴埃纳(Baena)、埃尔南多·德尔·卡斯蒂略(Hernando del Castillo)收入《歌谣总集》(Cancionero general 一五一一-一五四〇),③主要为14至16世纪署名诗人的作品,是谓“新谣曲”。一六〇〇年又由路易斯·桑切斯(Luis Sánchez)汇编成册,谓《谣曲总集》(Romancero general)。④《谣曲总集》除收录古典佚名作品外,还有一些14至16世纪署名诗人的作品。后者展示了西葡两国的古典谣曲及其主要变体,但规模不及前者。这些歌谣及其变体(或变奏)是西葡两国的文学宝藏,也是西葡罗曼司语的载体和表现。
在西班牙语中,罗曼采专指十六音节(少数为十二音节)谣曲。每句一分为二,押尾韵,但有时也有押中韵(即前半句同样押韵)的情况。而一般歌谣是比较自由的,音节和押韵方式各不相同。
多数谣曲都有一些变体,有些可谓变体众多。比如《女兵谣》,它表现了西班牙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摩尔侵略者的英勇气概,内容同我国的《木兰诗》如出一辙:
为抗击摩尔人入侵,国王他派人来征兵。
马科斯自叹年事高,膝下无子又添烦恼。
小女儿前去把名报,她替父从军志气高。
父亲嫌她是女儿装,她脱了红装换武装。
父亲嫌她小辫儿长,她拿起剪到把发断。
姑娘举枪把战马跨,英姿飒爽要上前方。
临别她想起事一桩,要求父亲把名号换。
“就用马科斯你父名,英勇杀敌把功劳建。”
万马军中小马科斯,南征北战她名远扬。
有位王子爱上了她,怎么看她也不像男。
王后教他要细端详,以免出错太难收场。
“你把她带到大市场,试试她喜欢哪一样。
如果她真是女儿身,定会流连那花衣衫。”
马科斯不爱花衣衫,一心只要那销魂枪。①转引自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第23-2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以上西班牙谣曲是我从现有西班牙文学史料中攫取的。其中最后一首的不同变体多描述女兵同王后及王子的机智周旋,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相同人物、类似故事的不同感受。由于它们的形态生动自由、风格简洁朴素,谣曲一直受到后世诗人和读者的喜爱。从十五世纪的希尔·维森特(Gil Vicente,一四六五-一五三六)到十七世纪的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一五六一-一六二七)再到二十世纪的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一八九八-一九三六),谣曲作为一种独特的诗体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
和上述古典谣曲同时流行的还有一些表达人之常情的民歌(Canción,也有人称之为抒情诗)。它们大都短小精悍,脍炙人口。比如有一首描写俘虏心境的歌谣,充满了艺术魅力,但韵律有异于上述谣曲,倒与伊本·古兹曼的某些情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月呀五月,
天气热起来,
麦子正拔节,
花儿遍地开。
云雀唱得欢,
夜莺打擂台。
情人成双对,
相爱多自在。
不知白天去,
凄苦我一人。
牢房独自捱,
不知黑夜来。
幸好有小鸟,
清早唱开怀。
箭手射杀它,
天理尚可待?②转引自董燕生《西班牙文学》,第1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这些歌谣或曰歌曲以及曾经提到的缀诗——哈尔恰和罗曼司谣曲共同缔造了西班牙语的早期文学。它们颇似我国古代《诗经》中的某些篇什,是罗曼司语系的早期文学表达。众所周知,古代谣曲大都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蒙昧时期,而具有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一般西方基督徒在逐渐失去了高高在上的拉丁文之后,其对古典文学的疏虞也在全面的文化退化中使自己沦落到了重新因循口口相传的歌谣传统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在十一至十四世纪罗曼司谣曲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而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涨和罗曼司语的普遍生成,西班牙语文学在反弹中迅速崛起。
简而言之,在上述以题材划分的十类谣曲中,相当一部分(或谓绝大多数)属于边境谣。它们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长期争斗的结果,也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融的结果。由于产生年代的相近性,格律的相似性,以及内容的相关性,我们不难看出伊本·古兹曼的《歌谣集》对西班牙古典谣曲的多方面的影响。然而,苦于年代久远,以及中世纪文学创作常采用匿名方式,对于其中的交互影响我们大多只能通过文本的平行比较方式来进行推导和论证,期待后续的研究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和推进。
宗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