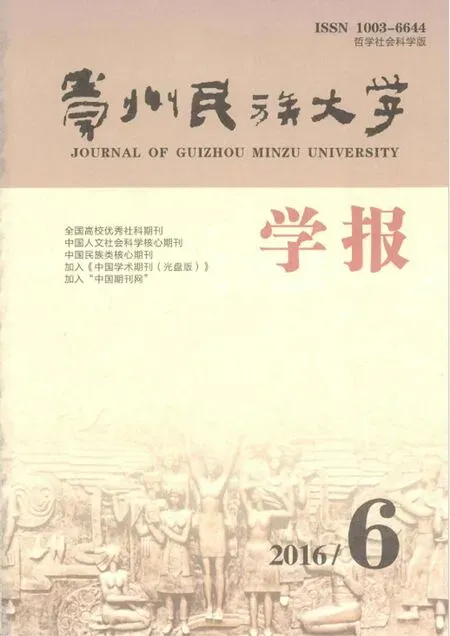论错层式间接相关转喻及认知模型 ———以“一挑田”类现象为例
赵 宏,何 英 楠
论错层式间接相关转喻及认知模型 ———以“一挑田”类现象为例
赵 宏,何 英 楠
一般的转喻都是本体和喻体直接相关。我们在多种资料中发现了“一挑田”类特殊的转喻现象。“田”不能用“挑”来衡量,“挑”与“田”不能直接相关,也不能与“亩”直接相关。 “一挑田”类转喻具有间接相关性与错层式搭配性。所谓间接相关,即本体和喻体之间隔着一层关系;错层即搭配的概念不在一个层次上。据此,我们给出了错层式间接相关的显示具体步骤的认知模型。错层式间接相关转喻认知模型产生的根源是独特的认知语境。
错层式间接转喻;一挑田;认知模型;认知语境
作者赵宏,男,汉族,安徽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 贵阳 550025);何英楠,女,汉族,河北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引言
当前,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成为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人类对认知的研究,必然涉及各类认知模型,转喻是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所论“错层式间接转喻”,涉及转喻的类型及认知模型。庄冬伟(2009)《转喻研究综述》说,有的以邻近性为出发点结合原型理论,将转喻分为空间、时间、行为或事件过程、集合四大类;有的以框架理论为基础联系邻近性原则同时也结合原型理论,将转喻总分为共现和顺承两大类。[1]陈香兰(2013)《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介绍说:有的根据抽象程度将转喻分为高层转喻和低层转喻,高层转喻和低层转喻又分别分为命题转喻和情景转喻。[2]P12-13Peirsman和Geeraerts(2006)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部分与整体、时间部分与整体、方位与所在、先前与后果、单个实体与总体、上位词与下位词等23种转喻模式。不同的转喻模式,也可看做转喻的分类。[3]P21-22
已有的转喻研究,无论如何分类,都离不开“邻近性”,即喻体和本体是直接邻近的,也即源域和目标域、本体和喻体直接相关,而且给出的认知模型一般是很简略的。
我们在多种资料中发现了“一挑田”类特殊的转喻现象。“一挑田”类短语,是一种名量结构,可从名量结构非常规搭配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此角度研究也涉及转喻,而且一般名量结构也是本体和喻体直接相关。胡金梅(2010)《名量非常规搭配的认知解释》说:转喻的功能主要在于能够让我们用一个实体来指称别的实体,其实现的形式是通过视角化来突显要表达的意义。所谓“视角”,是指人们对事物描述的角度。转喻的视角化主要有“成分视角化”和“含义视角化”。[4]例如:一尾鱼、一碗饭、一粒球等。在此类例子中,量词“尾”和“鱼”直接相关;“饭”盛到“碗”里,直接相关;“球”是圆的,“粒”作量词一般是用于圆形或接近圆形的物体,其作为量词的描写性与“球”直接相关。
“一挑田”类现象,可看做“挑”等作为量词替代了与“田”常规搭配的“亩”等量词,“多少挑田”替代了“多少亩田”的说法,应看作转喻。但是,“田”却不能用“挑”来衡量,“挑”与“田”不能直接相关,也不能与“亩”直接相关。可见,“一挑田”类转喻是一种特殊型的转喻,下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一挑田”类转喻的特殊性
(一)“一挑田”类语用现象
之所以说“一类现象”,是因为这种用法在多地汉语方言中出现,而且除了“挑”外,还有“背筐”、“斗”、“斤”等。如:
(1)在平坝地区,土地已相当集中,拥有数百挑至千挑以上的地主已不少。清成嗣年间,摆略(今独山基场)地主蒙德鲜占有一千多挑田,烂土地主张炳四则拥有九千挑之多。[5]P482*此处的“烂土”为地名,三都水族自治县属贵州省。
(2)六组吴文才马上提出反驳:“王树清虽然只种了十多背筐包谷土,但他做生意,家里人又少,他在二等的话,那没得三等的了。”*此处“土”指坡地。[6]P46
(3)鸦片盛年一担田约产300两,枯年200两。价格每两制钱80~120文。我们假定每担田平均产250两,平均每两价格100文,那么共计约25,000文。[7]P155
以上“挑”、“筐”、“担”等是容器,是转移东西的工具,也用于计算东西多少的量词。但“田地”是不可能直接用“筐”来装或者“挑(担)”的。
(4)1945年2月24日《新华日报》报道,在重庆巴县一带,“在战前的时候,每担押金有限,很少超过一锭银子(每锭银子折合法币14元)的金额,现在则一石田的押金可以增加到3 000到5 000元的巨款。”[8]P346
(5)庄官由富裕的地主充任,任期两年,期满更换。产粮一石的田,收租八斗。[9]P218
(6)周桂春家在山深林密的大面山,家境向来贫穷,并无一斗田一亩岭,全靠打野味,傲笋干籴米度日。[10]P34
(7)他到山后请来几位亲戚帮忙,砍来武竺山的竹木扎排、挑土。大家忙了一整天,还没有造出一升田。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一石相当于现在的六亩。[11]P126
以上“石(dàn)”、“斗”、“升”等是计量粮食的量词,“斗”、“升”也是工具,装粮食的容器。“田地”也不可能直接用“石(dàn)、斗、升”来衡量。
(8)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没收了封建土地3656万多斤(当地是以斤计亩),分给了 65 580个(占全县人口 68%) 少地、无地的农民。[12]P41,152
(9)这里水田的面积单位,过去是以斤或以担计算的,一担为100斤。田面400斤约合一亩。一般来说,田面1,000斤,地主要收租500斤。[13]P215
“斤”是用于计算物质重量的专用量词,但是田地不可能直接论斤来称重衡量。关于“斤”与“田”的组合,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这种组合使用与中国1956年代大跃进时期人们所说“万斤田”有差别。大跃进时期人们所说“万斤田”指一亩田地能产万斤粮食,即“亩产万斤”,那是一种做假虚夸的说法。这里所举“斤”与“田”的组合,在有些方言中是用于直接计算田地的多少。
以上“挑”、“石(dàn)”、“斤”等多种量词与名词“田”、“地”的搭配组合中,以“挑”具多,我们以“挑”为代表,统称“一挑田”的变异组合。说“挑”、“斤”等量词与名词“田”、“土”的变异组合是一种语用现象,是因为,从地域上看跨度较大,涉及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汉语方言;从使用时间上看跨度也较大,有历史典故与传说中的,有些地方在改革开放后还在使用,如:
(10)有网友向四川省领导留言,……“我家的田被村里承包给别人种植藕,合同期满就返还农户,现在田地根本无法耕种,而且我给村里的田是10挑,现在村里只返还了我3挑半。”(《人民网-地方领导》,2012年05月29日。)
以上例子具有以下共同性:
“挑”、“筐”、“担”、“石(dàn)”、“斗”、“升”、“斤”都不是面积量词,又都替代了“亩”类面积量词。
(二)可由认知模式证明“一挑田”说法属于转喻
“挑”、“斤”等作为量词替代了与“田”常规搭配的“亩”等量词,“多少挑田”替代了“多少亩田”的说法,之所以看作转喻,可由认知模式证明。现在一般认为,认知模式有如下四种:
命题模式:表明概念及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结构。如一个描述关于“火”的命题模式:“火是危险的。”命题模式是一个判断事物某方面真或假的陈述,一般形成主谓宾结构的陈述,典型形式为判断句。“一挑田”等是名量结构,不是命题模式。
意象图式模式:所有意象图式都涉及空间结构,所以凡是涉及到形状、移动、空间关系的知识是以此模式储存的。人最初的经验就是空间经验,基本的意象图式就是空间图式。如,“把肚子喝涨了。”“把酒装进坛子里。”等。这些基本的空间概念和结构又通过隐喻成为人们理解其他概念的基本模式,如,“这人不听劝,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在这种空间结构模式中,量、名的搭配是讲理据的,如“一坛酒。”“酒”是可以装进坛子里的。“田地”却不可以“挑”起来,也无法装进筐子里。
隐喻模式:一个命题或意象图式模式从某一认知域投射到另一认知域的相应结构上就形成隐喻模式,此模式的关键是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如,“李同学基础不扎实,研究生没考上。”“基础”一词本是房屋建筑方面用词,指前期的地表以下的对地表以上墙体起承托稳定作用的部分,没有这一部分或这一部分没有做好,房屋、墙体便会倒塌;“基础”一词用于学习、考试,指其相关的前期知识,前期相关的知识没有学好,后期的学习、考试便有困难或不会成功。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筐”、“斗”等容器与“田地”、“亩”不存在相似性的问题。
转喻模式:在上述某种或多种模式基础上,使其中某个成分与另一成分发生联系,如在一个表示部分—整体的图式模式中,使一个部分转到整体的功能,从而使部分能够代表整体,此模式的关键是相关性。如,“大鼻子走了。”“大鼻子”是人体的一部分。部分与整体是相关的。产地和产品也是相关的。如,“喝啤酒吧,茅台没有了。”“茅台”本是一个地名:茅台镇,是茅台酒的产地,这里指代“茅台酒”,“茅台酒”因“茅台镇”的地名而来,产生了相关性。
“一挑田”类变异搭配,是数量名的偏正结构,不是主谓宾的陈述结构,“挑”、“斤”等也不是“田”的某种属性,不会是命题认知模式;“挑”不是“田”的形状,“田”也不能装进“挑”里,不会是意象图式认知模式;“挑”、“斗”、“斤”等与田地之间也没有相似性,也不是隐喻认知模式;那就只能是转喻认知模式。田地与其产粮相关,粮食可以“挑”,可以用“斗”量,论“斤”称等,“田地”与“挑”、“斗”、“斤”等概念便产生了相关的关系。
(三)“一挑田”类转喻的特殊性
以上“一挑田”类量名的搭配有如下特点:
第一,那些量词与田地搭配,都不是常规用法,都是反理据的替代用法。因田地无法挑、背,无法用斗、升来量,更难以论斤称。这是“挑”、“斤”等非面积量词替代了与田地常规搭配的“亩”、“公顷”等面积量词。说是替代是因为,首先,在那些方言中“挑”、“斤”等量词的本身用法还是物质重量单位词,其次,在那些方言中仍有面积单位词,如上面例句(2)的文献中还有:
(11)七组刘家贵说:“在评产量的时候,刘绍武今年打的谷子是50挑,他只报40挑,……二保唐云华亦报告了国民党对九庄每户人的剥削帐:救国公债米10斤,自卫队弗米120斤,送兵弗米30斤,蒋介石祝寿费米60斤,航空卷米6斤,保甲长训练费米25斤,造业费米120斤……
(12)他谈起了他的家史:……连本带利算了一大堆,“当”字换成“卖”字,带搭上山林、耕牛、总算把帐还清了,可是刘明舟家也破产了。几亩薄土,怎么养活全家……
(13)马当田村农民在3月间就开始组织变工、犁田、翻土、上粪,……10天内就把全村二千多亩田和土全部犁完;
在那些方言中,不具体涉及产粮或田地较多时,往往还是用“亩”类面积单位词。
第二,有人从修辞角度研究名量结构的非常规搭配,可是这里的“一挑田”类非常规搭配从常规的修辞角度也难以解释。如,康家珑《量词的借用艺术》(1998),李艳《汉语移就范畴的认知阐释》(2010)中对量词移用的研究,都主要说是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形象;此外,如惠红军《汉语量词研究》(2011)对量词超常搭配动因的分析,说有的是为了表达说话者某种特殊的心理情感,或受会话暗示的影响,为了适应“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或是历时变化的现代残留。*量词历时变化的现代残留如:我们在万本芭蕉底下直像草根底下斗鸣的小虫。“本”,原指草木的根,引申作主干,“芭蕉”一棵一本(主干),所以早期“本”作“芭蕉”的量词是有理据的;而“挑”、“斗”、“斤”等在历史上也没有过用于“田”的量词,没有理据。“一挑田”类的非常规搭配,“挑”、“背筐”虽有形象,但不能表达“田地”的形象,“石(dan)”、“斤”更是抽象概念,没有具体形象;这些用法也都没有表达某种特殊的心理感情,“斤”与“亩”同样是没有感情的;也不是因为受会话暗示的影响,为了适应“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而形成的,应答协调,总要有人先那样说,第一个反常规说的,不存在与别人协调的问题;更不是历时变化的现代残留,这种情况是古时的常规用法,到现代用得少了,显得反常规,而“挑”、“斤”等词替代“亩”等词的用法,主要是方言和共同语言、标准语的差别。
有的认为汉语中存在一种“形式量词短语”,只有量词的形式,没有量词的实质,如盛林《语法手段·修辞方式·常规结构——试论量词短语在汉语言语中的演化》(2003)。*盛林(2003)所举形式量词短语如,“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形式上用了量词短语,但量词和所表事物不相对应,此处的量词“手”并不是“字”的计量单位; 量词短语并不提供事物数量方面的信息。而“挑”、“斤”等与“田地”组合是有量词实质的。
总的来说,根据以上的那些研究都无法解释“一挑田”类的转喻现象,可见这是一种特殊的转喻。对于特殊的转喻现象,应该从人们的认知思维模式方面考虑。
二、“一挑田”类的跨层次间接相关转喻性质
(一)目前人们研究到的转喻本体和喻体一般是直接相关的
关于一般研究到的转喻本体和喻体是直接相关的问题,在前面引言中提到过,这里再稍微展开来分析下具体的例子。如沈家煊《转指和转喻》(1999)有,现将一些主要的认知框架列举如下:
容器—内容、整体—组成部分、领有者—领有物、劳作者—工具、物体—性状、机构—所在地、当事—行为、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施事—动作—与事/目标一受事。[14]
以上沈家煊所列转喻的认知框架,也看作转喻的九个种类,这九类转喻本体和喻体都是直接相关的。如:“壶开了。”其中“壶”转喻代称“水”,水是直接装在壶里烧开的;“白宫没有表态。”其中“白宫”转喻代称“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存在于白宫之中,直接相关;“老张放书的”,其中“放书的”转喻代称(放书的)“箱子”等,也是直接相关。
吴为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2011)将转喻分为两大类: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概念转喻和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概念转喻,所显示的也都是直接相关。事物的整体和其组成部分直接相关,少了部分,整体也就不成立了;物体与其性状不可分离,少了某种性状,便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当然也是直接相关的;领有者与领有物,劳作者与工具, 具体的当事、施事、受事等与行为之间也都是直接相关的,如果分离开来,就不构成转喻,或不再是原来的转喻。[15]P150-159总之,以上所说转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都是不可分离的,分离了就不构成转喻。就这一点来说,也即沈家煊(1999)所说“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
(二)“一挑田”类转喻的间接相关性
所谓间接相关,即本体和喻体之间隔着一层关系。我们再来看前面的例(9):
“这里水田的面积单位,过去是以斤或以担计算的,一担为100斤。田面400斤约合一亩。一般来说,田面1,000斤,地主要收租500斤。”
地主从1,000斤中收租500斤,收的是稻子(粮食)500斤,不可能是“田面”500斤。这里说的“田面400斤、1,000斤”,指的是田面收到的稻子400斤、1,000斤;反过来说即能产“多少担”、“多少斤”稻子的田面(田地面积)。前面那些例子也都是这种结构关系:

“没收了封建土地3 656万多斤”→ 没收了产粮食3 656万多斤的封建土地
与扩展后的结构相比,例句的结构都省略了“产”类动词和“稻子的(粮食的)”定语,例句的结构为压缩结构。就量名结构来说,“挑”、“背筐”、“担”、“石(dàn)”、“斗”、“升”、“斤”等量词与“稻子”、“粮食”搭配在认知上都是合理据的,省略了“稻子”后与“田”搭配,就不合理据了。不合理据而又能被当地人接受、理解,那是因为在认知语境中,人们是按照未压缩的结构来理解的,理解时补充出了省略部分。在这种结构中,“挑”、“稻子”、“田”三者的关系是;
一挑→稻子的→田
“挑”与“稻子”是合理据的直接相关关系;“挑”与“田”是间接相关关系,词面上直接搭配,便不合理据,成了反常规的、变异的搭配结构。
彭媛《汉语常规物量词变异搭配实证研究》(2015)认为,人们在审美心理的作用下,刻意打破常规搭配,让常规物量词固有的语义特征渗透到另一语域名词上,从而使名词临时获得该物量词的某种语义特征,实现跨范畴的变异搭配,并提出“常规物量词变异搭配的转喻模式”:
把常规或者变异搭配构式中的名词、名词性成分相应地以“N1”、“N2”来代指,物量词则以“Q”来指代。以常规物量词Q去修饰与其惯常搭配对象N1存在相关关系的N2,从而形成变异搭配。N2与N1属于同一认知框架,N1在句中隐省。[16]如:
(14)缆车从山下擒下一厢笑N2,/扔上北洋的峰巅。
(丁芒《缆车穿空》)
(15)椰林深深院深深——一弯新月,一群欢笑N2,一坛酒……。
(王尔碑《梦苏轼归来》)
“一厢笑”、“一群欢笑”的“数+量+音响(N2)”的量名搭配是对“数+量+人(N1)”常规搭配的变异。音响(N2)与人(N1)处于同一认知框架,同一框架内视觉“人”隐省了。
按照彭媛的“常规物量词变异搭配的转喻模式”,在“产一千多挑稻子的田”结构中,“挑”为“Q”,“稻子”为N1,“田”为N2;在“一挑田”结构中,“稻子”N1隐省了。“稻子”隐省后即:一挑→ O →田
“一挑田”与“一箱笑”、“一群欢笑”也还是有差别的。“一箱笑”,突出了“笑”的融合、充满;“一群欢笑”突出了“笑”的多,只见欢笑不见人,大家笑在了一起,已分不出是谁的笑。这是“人们在审美心理的作用下”,做出的修辞行为。而“一挑田”类由隐省形成的变异搭配,并没有“审美心理”的作用,和“一亩田”比起来,也没有形成对“田”的突出表达。
(三)“一挑田”类转喻的错层式相关性
1.概念结构的不同层次
前面我们论述了“一挑田”类转喻的间接相关性。之所以间接相关,是因为“稻子”N1与“田”N2不在一个层次上,把理据上与乙层次概念搭配的量词拿来和甲层次的概念搭配,隐省了N1。
何爱晶《名-动转类的转喻理据与词汇学习》(2011)认为,转喻是通过相邻性将处于不同层级的两个概念进行暗含的联系,从而把二者在认识上视为同一,它的实质是把相关的对象加以分解与整合,用分解整合后的特征,尤其是用某些同相关语境联系的突出特征来理解对象,实现转喻义的涌现。概念的全部内涵、外延内容构成了该概念的概念域;根据语境对该概念域的选择构成对该概念的一个再现认知域。[17]P104-105
结构一般具有层次性。内涵结构可以具体理解为,一个概念的内涵包括多方面的属性,在结构上,属性是其下层。如:“车”这一概念: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其概念的内涵结构可以表示为下面图式(一):

图1 图式(一)
上面图式(一)表示,“车”运行主要靠“轮子”,“轮子”成了“车”的特征标志,即主要内涵属性。人们现在看到的车主要是汽车、自行车、板车,所以往往说“我两个轮子的跑不过你四个轮子的”,用“四个轮子”转喻“汽车”。“轮子”是“车”的下层概念。“扁圆”、“滚动”等又是“轮子”的下层属性概念,当然,“轮子”的内涵也可从另一角度分出“轮轴”、“轮圈”、“轮胎”等部分。正如“人类”这个概念分别属于“生命体”、“物理体”、“有意志的施事”等认知域,但是,“人类”与“生命体”、“物理体”、“有意志的施事”等概念之间是上下层关系。
一般的转喻都可用既不同,又相邻的层级来解释。如:壶开了:“壶中的水”与“壶”处于不同层级;大鼻子走了:“大鼻子”与“长着大鼻子的人”处于不同层级;他是个笔杆子:“笔杆子”与“耍笔杆子的人”处于不同层级。
关于转喻的一个争论是,过去一般认为隐喻涉及两个认知域,转喻只涉及一个认知域;现在又认为转喻也不限于一个认知域。用结构层次的概念,更能清晰的回答:转喻涉及的不同认知域,必然属于邻近的某同一上层认知域。转喻表现在言语上就是代称,替代式表达,只有涉及不同的认知域,才谈得上“替代”。转喻的替代与一个人几个名字的替代是不同的。
2.“一挑田”类转喻是错层式搭配的量名结构
在认知中,常规的量名搭配是讲理据的,不同层级的事物一般有不同的量词与其搭配。如,整体的鱼是上层概念,一般说“一条鱼”,切开后的部分是下层概念,一般说“一块鱼”;对某人可以称“一位先生”,但说到其受伤的部位时,只能说伤了“一条腿”或“一根手指”,而不能说“一位腿”或“一位手指”;可说“一辆车”,但不说“一辆轮子”。事物对量词的选择,是属性认知上的相关因素在起作用。如,“条”作为量词,一般与具有长而柔软属性的东西搭配,“鱼”有这种属性;“位”有尊称义,常与“先生”、“女士”搭配,“腿”、“手指”没有尊卑属性,所以不与“位”搭配。
“一挑田”类转喻的特殊性在于,“田”是上层概念,首先展现的是面积,常规搭配的是“亩”等面积单位量词;“稻子(粮食)”为“田”所产的东西,是与“田”相关的下层概念,常规搭配的是“挑”、“斤”等重量单位词。“一挑田”、“土地3656万多斤”类量名搭配,便是用下层概念“稻子(粮食)”的量词与其上层概念“田(土地)”变异搭配形成的,所以,其结构本身是反理据的。这可称之为“错层式搭配”。虽然错层,但仍是相关的。其层次关系如图式(二):

图式(二)
图式(二)是表明,“挑”、“斗”、“斤”类量词通过“粮食(稻子)”与“田地”产生了关系。说的时候隐省了“粮食”,便形成了下层“挑”等与上层“田”的错层搭配,也形成了间接相关的关系。“一群欢笑”也是错层搭配,差别是,与常规上层“人”搭配的“群”,错配了下层的“笑”,当然,“一群欢笑”是故意为之的“错”。
胡金梅《名量非常规搭配的认知解释》(2010)说,在表量结构中,量词与名词之间具有双向选择性。一个名词能否与某个量词搭配使用,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语义特征有无吻合之处。谈量名非常规搭配的主要方式中有“错位型量名搭配”,即专用性很强的量词用于修饰属于不同语义域的名词。如“一粒自豪”,“一缸眼泪”。这里要注意的是,“错位”不同于“错层”,“错位”不一定有上下层的关系。
三、错层式间接相关转喻的认知模型
模型,又称“模子”,模型概括指某种事体的定型样式。认知模型就是人们在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关于认知模型,不同学科的研究有不同的说法。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提出的有“符号系统认知模型”和“联接注意认知模型”;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模型”与“认知模式”等同。如,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的认知模式是“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18]P72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引用莱考夫(Lakoff)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包括四种认知模型:1)命题结构原则、 2)意象图式原则、3)隐喻映射原则、4)转喻映射原则。[19]P63-64对于转喻认知模型(模式),一般的说法是,在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的某种或多种模式基础上,用较易感知的部分来理解整体或者整体的另一部分。对于认知模型,这些说法还较简略,没有显示出具体的认知活动的阶段、过程。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1999)中提出了较具体的“转喻的认知模型”:
(1)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用概念A指称一个目标概念B;
(2)概念A指代B,A和B须同在一个认知框架内;
(3)在同一认知框架内,A和B密切相关,由于A的激活,B(一般只有B)会被附带激活;
(4)A要附带激活B,A在认知上的显著度必须高于B;
(5)转喻是A和B在某一认知框架内相关联的模型,这种关联可叫做从A到B的函数关系。
比较来看,沈家煊先生提出的“转喻的认知模型”更具体细化,具有了程序化、形式化的性质,注重转喻思维的步骤、过程。语义信息要进入计算机智能处理的话,是需要程序化、形式化的。认知研究的关键就是思维活动的过程、步骤。对于“一挑田”类错层式间接转喻,应该有不同的转喻认知模型,我们给出的“一挑田”类错层式间接转喻认知模型如下:
①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用概念C替代一个目标概念B;
②概念C替代概念B,B和C须在同一个上层认知框架A内;
③在同一上层认知框架A内,B和C都与A有关系,由于C的激活,A被附带激活的同时,B也被附带激活;
④C要附带激活A、B,并替代B,C在某语境中认知上的显著度必须高于B;
⑤这种转喻,C和B都属A的认知域,C替代B这种关联可叫做从C到A的函数关系。
以上模型可叫作“错层式间接转喻的认知模型”。此转喻认知模型中的C→B→A表示下、中、上的层次关系。
四、错层式间接相关转喻的认知模型产生的根源
语言认知与人类智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兴未艾的认知科学及人工智能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语言认知的研究。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从认知科学五个层级的理论看人机大战》说:根据人类心智进化的历程,人类心智从初级到高级可以分为五个层级: 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神经和心理认知是人和动物共有的,称为“低阶认知”,语言、思维和文化认知是人类所特有的,称为“高阶认知”。在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中,语言认知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其一,语言区分了人类认知和动物认知。其二,语言使思维成为可能。人类的语言能力表现在,它能产生和使用抽象概念,并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其三,语言和思维形成知识,知识积淀为文化。其四,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其五,语言建构社会现实。语言是人类心智的基础,语言决定思维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20]
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思维与文化成果便很难表达、传递,特别是较复杂的思维与文化成果。用语言把思维与文化成果表达出来,便是“语用”。如何表达和运用语言,其根源是“语境”。现在一般将语境分为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包容较广,与社会群体所生活的历史、民族、地域等有关,不同历史、民族、地域的社会群体形成不同的、各有特色的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以背景知识的状态存储人们的大脑,又可称之为“认知语境”。社会群体中一类语用现象的形成,主要和社会文化语境、认知语境有关。
从“一挑田”现象的文例看,用“挑”、“斤”类量词替代“亩”、“分”类量词计算土地的多少。这些地方的认知语境特点是,一般是山区,其土地整体上大块的少,边缘形状不规则,面积计算复杂,难度大,且过去那些地方有文化的人不多,更难以用“亩”、“分”、“平方英尺”等单位来计量。而山区农民的土地,主要是用于种粮食,以求不饿肚子。就函数关系说,土地产的粮食多,价值就大,直接用“挑”、“斤”等重量单位计算产粮多少方便得多。现在粮食多了用磅秤,过去农村少有磅秤,论“斤”计量也有不便,更简易的是“挑”、“背篓”等单位。因粮食收回家一般要“挑”或用“背篓”背回去的。地有坡地、平地的差别,能否浇灌的差别,肥沃与否的差别。“田”是能浇灌,种水稻的,较低平,水稻脱粒后用箩筐挑回,所以用“挑”与“田”搭配;“土”一般指坡地,种苞谷(玉米)等作物,上下山路窄而不平,只能用“背蒌(篓)”背,所以用“背蒌”与“土”搭配。“斗”、“升”是农村粮食进仓时专用的量具。这些不同搭配也是“因地制宜”的。在这些地方,“斗”、“升”、“斤”与“田”搭配,在计算价值上更准确一些。因为“挑”、“背篓”有大小的差别,“斗”、“升”、“斤”的量是较稳定标准的。但用“挑”、“背篓”计量更直接省事。
就以上农村语境看,以公顷、亩、分一类面积单位来计算土地的价值,反而不如用计算粮食多少的“挑”、“斗”、“斤”一类单位词直接简明。所以这类概念被激活。
此种情况正说明了,人们的一种认知方法不足用时,往往用另一种认知方法来补充。认知方法变了,说法也就变了,以至于变出独特的说法,一种说法用的人多了,便形成一类现象。这还能找到证明:
(16)我们家那时好象有十五、六挑水田吧,“挑”是老家乡下对稻田面积的一种丈量说法。好比通常说的亩,公顷,平方丈一样,只是一个单位。但具体和亩或者平方丈是什么换算关系,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我们这是梯田以前不好算亩数,以挑为单位,一挑田产量是大概80-150斤,……(《天涯社区网》,2013-8-8)
这种例证当前在正式的书面语不易找到,网络上还有,也说明目前有些人对“一挑田”类的量词变异搭配有疑问,感到不好理解,需要解释。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问题可归结为两点:第一,新明确转喻的一个类型;第二,给出其“错层式间接转喻的认知模型”,并且是具有具体过程步骤的。已有的转喻研究无论如何分类,都显示的是本体和喻体直接相关。本文所说“一挑田”类现象,是一种名量结构,可从名量结构非常规搭配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此角度研究也涉及转喻,而且一般名量结构也是本体和喻体直接相关。“一挑田”类现象,可看做“挑”等作为量词替代了与“田”常规搭配的“亩”等量词,“多少挑田”替代了“多少亩田”的说法,应看作转喻。但是,“田”却不能用“挑”来衡量,“挑”与“田”不能直接相关,也不能与“亩”直接相关。“一挑田”类转喻是一种特殊型的转喻。“一挑田”类量名的搭配的特点是,那些量词与田地搭配,都不是常规用法,都是反理据的替代用法。
“一挑田”类转喻具有间接相关性与错层式搭配性。所谓间接相关,即本体和喻体之间隔着一层关系。一个概念、认知域,是可以逐层划分的。在认知中,常规的量名搭配是讲理据的,不同层级的事物一般有不同的量词与其搭配。“一挑田”类转喻的特殊性在于,“田”是上层概念,首先展现的是面积,常规搭配的是“亩”等面积单位量词;“稻子(粮食)”为“田”所产的东西,是与“田”相关的下层概念,常规搭配的是“挑”、“斤”等重量单位词。“一挑田”、“土地多少万斤”类量名搭配,便是用下层概念“稻子(粮食)”的量词与其上层概念“田(土地)”变异搭配形成的,所以,其结构本身是反理据的,这可称之为“错层式搭配”。虽然错层,但仍是相关的,没有脱离转喻的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的转喻可以给出显示具体步骤的认知模型,所以我们也能给出了错层式间接相关的显示具体步骤的认知模型。
在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具体细致的认知模型应该是关键。当然,我们提出的“错层式间接转喻”及其“认知模型”,也只是一家之言,有无漏洞与偏误,希望学界同仁能给予批评指正。
[1]庄冬伟.转喻研究综述[J].科技信息2009,(3).
[2]陈香兰.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张辉,卢卫中. 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胡金梅.名量非常规搭配的认知阐释[J].湘南学院学报,2010,(4).
[5]三都水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三都水族自治县概况资料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12]赵铁.奠基:二野军大五分校一大队在息烽进行反封建斗争纪实[Z].内部资料,2012.
[7]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8]李良志,李隆基. 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9卷 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1941~194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李家鸿.外戚之祸[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
[10]刘晓农.井冈演义[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11]施隆庭.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 汉寿文史· 第十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13]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汇编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集成 第5辑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第105卷[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4]沈家煊.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
[15]吴为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6]彭媛.汉语常规物量词变异搭配实证研究[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7]何爱晶.名-动转类的转喻理据与词汇学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8]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9]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20]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从认知科学五个层级的理论看人机大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责任编辑:陈 刚
OnMismatchedIndirectMetonymyandCognitiveModels:ACaseStudyof“YiTiaoTian” (OneShoulder-carriageofField)
ZHAO Hong,HE Yingnan
Generally speaking, metonymy is about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enor and vehicle. In documents, however, such odd metonymies as “Yi Tiao Tian” (One Shoulder-carriage of Field) are found. It is argued that a mismatched metonymy exists in these examples, supported by relevant cognitive models and illustrated by peculiar cognitive contexts.
mismatched indirect metonymy; Yi Tiao Tian; cognitive model; cognitive context
H
A
1003-6644(2016)06-00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