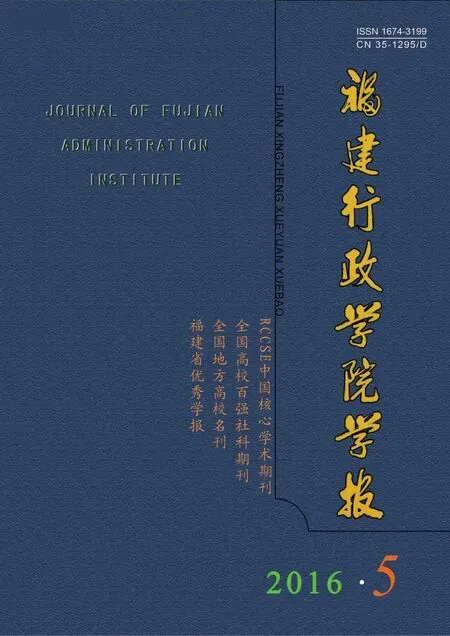“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及其兴衰
郭大为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 北京100091)
“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及其兴衰
郭大为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 北京100091)
人们所珍视的价值本质上是客观存在及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主观要求与反映。由于生产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不难发现许多相同的价值指标,而这些价值指标在整个价值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先性与重要性的不同与变化,就表现为文化的差异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同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些价值虽然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自身也正经历着危机、挑战乃至“衰败”。
价值;普遍价值;普世价值;道德金律;自然法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虽然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但由于国内价值论研究的学科体系不完善、理论储备不充分,相关的讨论存在着浮躁与混乱的现象①有关争论及评述可参见:李德顺. 怎样看“普世价值”?[J]. 哲学研究, 2011(1):3-11; 李德顺. 普世价值与中国故事[J].领导文萃,2014(14): 28-3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淆视听、搬弄是非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校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他还特别提到:“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就需要重点回答。”对于这样一个“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必须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总结和概括:第一,完整、准确地把握价值问题的内涵与复杂性,辨明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具体内容;第二,探究其理论依据;第三,认清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本质及其局限性,从而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价值与普遍价值
尽管西方思想史对于价值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但在现代知识体系中,价值理论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展开的,其中最早出现在古典经济学中。大卫·李嘉图所开启的劳动价值论改变并拓展了人们只从使用价值看待商品的朴素观点,由此引发的围绕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争论虽然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但持续至今的争论本身说明了价值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商品中凝结的一般劳动这一抽象的价值本质与使用价值的直观性及其实现形式的主观条件这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使价值问题的探讨突破了经济学研究的固有范畴,进入到哲学领域。哲学价值论(Axiology)的真正兴起是由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德国新康德主义推进的,它关注的焦点是伦理学、美学及文化问题。二战前后,伴随着社会学、心理学对于价值中立、社会转型、价值转换等问题研究的深入,价值理论才真正产生了具有说服力和操作性的实证性成果。
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是指“好的东西”(Güter, Goods)所具有的性质[1]11-12,即事物所具有的有用性或被人所渴望、珍视或赞赏的性质,或者说,某些事物或其属性、状态是人们需要、喜好和追求的对象或目标。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价值概括为“一种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统一状态”[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主体既可以指个体的人,也可以指群体性的人类实体(如民族、宗教团体);而这里所说的客体应当既包括自然的存在物(如生产、生活资料),也包括人的活动及其成果(如科学技术与文艺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价值定义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它以客体或事物的客观方面为基础,即使是作为理想目标的“价值物”(如完美的人格或大同世界)也只有在人类现实的存在与实践中才能获得确切的理解或意义充实;另一方面,价值所要求的“主客体统一状态”毕竟是“以人为本”的,即“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也就是说,在“价值物”所体现的主客关系中,主体或主观的方面是主动的、起主要或决定作用的,任何“客观价值”或“价值物”无不被打上了观念的烙印,只有在确定的价值观标准的衡量下才具有(或丧失)价值意义。从知识形态上来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人们可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但事物的存在、状况不会因人们的认识、需求或态度本身而发生丝毫改变,人们更无法改变事物所遵循的客观自然规律;与之相对照的是,人的需求偏好、愿望程度等主观取向和定位却是衡量客观事物是否对人具有价值以及具有怎样价值的关键。因此,观念形态的价值体系不但是主体或人(类)趋利避害、取舍好恶、判断客观事物是否有价值的直接根据,而且是人类主体分辨善恶美丑、确立行为目标、选择行为方式的标准。可见,脱离价值观来谈价值是无意义的*因而将价值共识与普遍价值完全割裂开来也是行不通的。参见: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J].哲学研究,2009(4):3-9.,而价值观念体系本身具有独立性,价值观研究是价值论研究中的核心内容。当然,价值论研究中的这些核心内容虽然表现为观念的形态,其实质却是客观存在及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主观反映。20世纪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为认识价值观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不但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议,也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研究的深化与系统化。战后颇具影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会学领域完成了开拓性的价值论研究。他在对社会所做的结构功能分析中,特别强调受到共有价值和规范性标准调节的主观取向的作用,从而把社会系统看作是“在文化价值和规范的控制之下,由行为有机体显示在行动中的基本能量的系统”[3]。由于价值取向是支配个体选择手段与目的、确定需求和目标的优先序列的规范性标准,因而成为考察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式变量”,对于规范性标准的考察也就成为价值论研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部分。
在对于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哲学家们虽然已经将各种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作为目的的价值与作为手段的价值、核心价值与衍生价值、个体性的价值与集体性的价值、普遍的价值与特殊的价值等不同的类型,并分析和推断它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与相互作用,但只有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让这些思辨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修改和丰富完善,这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施瓦茨价值总表(Schwartz Values Survey)。谢洛姆·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及其所领导的科研团队,经过20多年持续、大规模的调查分析发现,在40多个有着不同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中,至少有57个价值指标(如安全、财富、智慧、诚实、秩序)是被普遍珍视的,这些价值指标体现了个体的自我超越、自我提高、守成(Conservation)和对变化的开放态度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个体需要、社会整合的协调条件与群体生存与福利的要求,构成了普遍影响人们行为动机的十大价值类型(Universal Motivational Types of Values)。人们所熟知的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的满足存在着从生理需求渐次向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上升的过程,而每一种需求的满足程度是相对的,尤其是较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是有限度的,而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却有无限的可能性。在决定个人行为的因素中,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随着高层次的需要发展,低层次的需要虽然仍然存在,但对行为影响的程度不断减小。同样,施瓦茨所绘制的价值图表表明,虽然在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相同的57项价值指标,但这些价值指标的实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冲突,不同的文化及同一文化实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相关价值指标在整个价值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先性与重要性的不同与变化。*相关内容参见:Shalom H. Schwartz.Values: Cultural and Individual[M]//F. J. R. van de Vijver, A. Chasiotis,S. M. Breugelmans.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63-493;Shalom H. Schwartz.Basic Human Values: An Overview[EB/OL].(2005-01-20).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364051.
综上所述,价值理论研究表明,在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尽管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乃至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但人们不但对美好的、有价值的客观事物(比如财富、健康、适宜的自然环境)有着许多相同的偏好,而且对于人类生活实践及其成果有着相同或近似的价值诉求(比如公正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评价(比如智慧),并拥有相同或近似的用以决定行为方式和目标定向的原则和标准(比如诚信、友爱)。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些人类普遍珍视的价值物或价值尺度无不具有抽象的观念形态的烙印,但这种抽象性并不等同于抽象的人性论,因为对于人的普遍性类本质的抽象,不但是人的类本质力量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且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它是以人类共同具有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条件这些具体的现实存在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4]人们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利益”的观念,也是因为“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84
二、普遍规则与价值预设
关于某些基本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论证主要诉诸两种传统,即自然法传统与约定论传统,前者更多地用于政治法律领域,后者则更多地用于伦理规则,“黄金原则”或“道德金律”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论据。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与深化,各国人民的生产与生活突破了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界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进程中,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不但借国际资本的强大势力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地域性的道德与价值观念,而且也将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的冲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并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纷纷致力于探讨一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底线伦理,力图超越民族、宗教和地区差别而为人们提供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从而为建设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探索和努力以在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所确立的《世界伦理宣言》最为著名。这个宣言所宣称的世界伦理“指的是对于现存的具约束性的价值观、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个人基本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在著名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等人看来,这种基本共识早已为不同的文明所分享:“数千年以来,人类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黄金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我们看到,中国人所熟知的孔子的忠恕之道在几乎所有古代文明或宗教的典籍中都会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回声,西方人耳熟能详的表达式是《新约·马太福音》中如下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由于这些古老的箴言流传至今仍被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适合于一切人的”(霍布斯),构成了“一切社会德性的基础”(洛克)或“源泉”(莱布尼茨)的“金规则”,从而也被视为消弭冲突与危机的基础和增进交流与合作的通则。
然而历史经验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并不能充分证明“金规则”的普遍有效性,对于“道德金律”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批判至少可以上溯到康德。康德指出,所谓“道德金律”并不是一条普遍的道德法则,而是从道德原理中推导出来的行为规则。如果有人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与偏好,依照这样的规则行动,就会导致尴尬甚至是荒唐可笑的结论。比如: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帮助他人;而一个作奸犯科的被告也可以据此向法官提出撤诉的要求,因为他和法官一样不愿受到有罪的控告!尽管康德的批评有失偏颇,但他还是揭示出所谓“金规则”的局限性:在康德看来,这条规则并不包含对于自己或他人义务的根据,也不包含相互之间应有义务的根据,因为归根结蒂,“义务是出自对规律的敬重而产生的一种行为的必然性”。康德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他的绝对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7]然而,当康德把“人是目的”这一实质性的表达式加入到普遍立法的形式之中时,“他与新时代的整个哲学所共有的预设”[1]4是基于这样一个“理性的事实”:人的尊严根源于人的自由本质,自由是道德规律得以存在的根据。
正像孔汉思等人利用“金规则”要表达的是“全球伦理”的“基本要求”(即“每个人必须被当做人来对待”,亦称为“人道原则”)一样,学者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旧有的“金规则”只有在达成价值共识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即使可以通过逻辑手段改进“金规则”的表达式,从而消除许多实践应用上的技术性难题,但其命令的有效范围依然处在你—我—他这样的“对等性结构”之中,因而依然需要一种价值共识。[8]简言之,任何道德法则的普遍性都以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肯定与尊重这一价值预设为前提,单纯形式的、抽象的普遍道德法则是不存在的。
自然法传统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类似的自然法观念:内在于自然或宇宙中的规则或秩序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同等的约束和支配力量,它们被奉为“天道”乃至“神谕”,成为古代人用来规范个人行为、昭示尘世秩序、衡量善恶赏罚的根据和标准。到了近代,这种古老的自然法观念变成了人们借以摆脱旧世界的束缚、确立现代性原则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从格劳修斯、霍布斯、普芬道夫、洛克、卢梭直至康德和费希特,近代主流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借自然法之名来建构各自的政治或法学思想体系。人们甚至把罗尔斯为当代正义制度所作的有关“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论证设计看做是改进版的“新契约论”。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普遍认为,自然法不但是统御包括人世在内的宇宙秩序的永恒法则,而且是不证自明的理性的指令,因而是成文法或实定法颁定的依据。与古代自然法学说执著于初始来源、本然正当意义上的自然不同,近代自然法学说则通过把自然法等同于理性法,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凸显了人的理智力量。这样一来,个体的所谓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Ius Naturale)逐渐取代了古代观念中的自然法或自然的法则(lex Naturae/lex Naturalis)而在近代自然法思想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自然法或自然正当(φúσεúκαον, ius naturae, Naturrecht)概念在西方语言的历史演变中,因理解不同而表现出对它原本蕴含的对“法则”(Law)与“权利”或“正当”(Right)意义的不同侧重。参见: Joachim Ritter,Karlfried Gründer,Gottfried Gabriel.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d.6[M].Basel: Schwabe Verlag,2007:560.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时期,自然法远比从前成为了一种更具革命性的力量。这一事实乃是自然法学说本身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后果。”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自然权利就比之自然法更为根本,而且是自然法的基础。”[9]
黑格尔曾沿用自然法的名称来讲授他的法哲学思想,但他逐渐认识到这个名称很容易引起歧义,因为自然(Natur)既可以指事物的本质或概念,亦可指无意识的、外在的自然本身,从而误导人们把法和权利的来源归属于后者。而自然世界中所呈现的弱肉强食、强权有理的现象并不是黑格尔所继承的近代自然法理论所要宣扬的东西,因而他力图以自由的法来代替自然的法。黑格尔明确指出:“法权领域是精神的领域,即自由的领域。……自由依然是基础,自然只是作为非独立的东西出现的。”[10]质言之,为当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理论基础的近代自然法理论并不是因为具有自然规律一样的客观性而普遍有效的,而是因为确立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主体自由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归根结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政治法律制度,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它们所生长的土壤。因此,不论是源于约定论的“道德金律”,还是源于自然法传统的人权、民主、法治思想,它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与现代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5]142
三、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及其兴衰
尽管以赛亚·伯林坚持自己的价值多元论立场,但是,他的如下言论却被看做是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论的经典表达:“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普遍持有某些价值……普遍的价值即便不多,最低限度总是有的,没有它,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11]22伯林在此使用的是中性的“Universal”(通译为“普遍的”)而非具有基督教意味的“Ecumenical”(通译为“普世的”)一词,但他被视为“普世价值”论的代表却又实至名归。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伯林看来,人们在现实中把何种价值视为普遍的和基本的价值是一个“准经验的问题”[12],即它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这些历史的、经验的因素相关,并不存在固定、永恒的普遍价值,更不应为了某种终极价值而牺牲所有其他价值;另一方面,伯林不但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他所恪守的“根本性的”“长期地、广泛地得到人们承认”的“客观的、普遍的价值观”,实质上是指“希腊、犹太、基督教历史之下的习俗、传统”,是构成西方文明“道德基础”和“政治的基础”的 “普遍的伦理法则”[11]206-207。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当代西方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正式文献中,人们很少使用“普世的”(Ecumenical)一词,因为它烙有深深的基督教历史的痕迹,让人想起东罗马帝国的“普世牧首”和新教的“普世教会运动”,这些历史痕迹恰恰标志着一种地域性文明或价值观的特殊性,因而并未遍布全球、天下归心。然而,当西方中心论者将自己特有的这种价值体系称为“普遍的”(Universal),并力图不分青红皂白、对方愿意与否强行推广到世界各地时,这种“普遍性”与历史上基督教宣扬的“普世性”如出一辙,散发着浓浓的十字军东征的味道。以警示“文明冲突”而闻名的塞缪尔·亨廷顿对于个中玄机倒是毫不隐晦、直言不讳:他认为,尽管人类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人类在文化上也存在着日益趋同化的趋势,但是,这种“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说到底,西方推行的“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以美国为标准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13]55-56,45
应当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人权、民主、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曾经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同,并被正式写入了以《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诸多国内与国际政治和法律文献中。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14]。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普遍得到国际社会肯定的价值理念并不为西方文明所独有,这些理念本身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社会实践和制度设计中的落实与应用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历程,其普遍性并不是固有的和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西方观念史的发展来看,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所推崇的善的价值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别。古希腊人珍爱具有自然属性的“四主德”,比如在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中,如果统治者、保卫者与劳动者分别具有了“智慧”“勇敢”与“节制”这三种美德并恪尽职守,那么作为公共善的城邦“正义”就得以实现了。在基督教主宰精神世界的中世纪,人们把是否具有“三圣德”——即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救赎的“希望”与对基督的“爱”——看做是去往天堂或地狱的凭证。在当代,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被看做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民主并不天生就是一个褒义词,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君主统治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态。事实上,民主制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而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和采用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民主国家在人类史上相对罕见,在1776年前,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民主”[15]。
其次,在当今西方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和成熟起来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壮大,西方社会开始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的自由契约关系逐渐取代了农奴制的身份依附关系,家族血缘、特权等级、神权崇拜等传统秩序与观念让位给个人自由、民主平等、理性进步的新的时代精神。正是在此背景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分权制衡——这些构成当今西方政治制度理论基础的观念和学说纷纷应运而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可以说,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宽容、法治为内容的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成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它虽继承和融合了希腊文明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古代遗产,但它与古代西方文明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举例来说,世人公认,罗马法在西方法制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而针对19世纪历史学派的法学家们对于罗马法的迷恋与膜拜,黑格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罗马法就不可能对人下定义,因为奴隶并不包括在人之内,奴隶等级的存在实已破坏了人的概念。”[16]
再次,“普世价值”从理念、理想到社会实践和制度安排不但实现形式多样,而且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以美国的人权为例,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当时黑人和妇女并没有选举权,穷人与富人的选举权也是不平等的,纳税多的人可以拥有多张选票。差不多是在美国建国的百年之后,即1870年,黑人才争取到了选举权。而选举中的性别歧视则到了1920年才被禁止。差不多两百年之后,即1964年,选举权才不受纳税额限制。
最后,二战以后,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矛盾的变化,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和争执,这些分歧和争执通过政治派别间的竞争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的自我调整与变化,各种政治派别也主要根据对于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偏重程度不同而区分为左中右。[17]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社群主义抨击自由意志论者关于权利优先于美德的原则,认为抽象地谈论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不但在理论上无效,而且在实践中有害,只有纳入到共同善的生活情境中,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才是有意义的。这一争论的实质恰恰体现了当代西方的社会危机和价值的冲突。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已经宣告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但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福山承认,自诩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制度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并且“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18]443-445,458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也通过大量确凿的历史文献证实,西方社会的公平竞争只是个神话,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受到了威胁。
可见,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固有的、永恒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内容与配比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些价值虽然产生过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自身正在经历着危机、挑战乃至“衰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其表现和实现形式的多样性、特殊性是同时存在的,正如施瓦茨价值图表所揭示的那样,尽管有57项价值指标为不同民族与文化所共享,但不同文化与民族的差别表现为人们对某些价值的重视与偏爱程度不同,这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传统、现实环境与客观条件等因素造成的。亨廷顿在评论有关侧重群体的新加坡价值观与侧重个体的西方价值观的争论时也承认:“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这些价值观当做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13]370福山在新近的研究中发现:“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在三个组件之间拥有某种平衡。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所以说,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18]487这就是说,民主制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价值理念的分歧,而且还与实际发展的次序有关。总之,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各国人民必须独立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从而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文明模式。
[1]马克斯·舍勒.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上册[M]. 倪梁康,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4.
[2]李德顺. 怎样看“普世价值”?[J]. 哲学研究, 2011(1):4.
[3]D. P. 约翰逊. 社会学理论[M].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4:565.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95.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世界伦理宣言[EB/OL].[2016-06-20].http://119.90.25.49/www.weltethos.org/1-pdf/10-stiftung/declaration/declaration_chinese.pdf.
[7]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39.
[8]赵汀阳. 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3): 70-79.
[9]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彭刚,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178.
[10]G. W. F. Hegel. Vorlesungen:Ausgewä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Bd.1[M]. Hamburg: Felex Meiner Verlag ,1983:6.
[11]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M].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2]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50-51.
[1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8.
[15]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8.
[1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
[17]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册[M].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4-5.
[18]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郑继汤]
Univers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Values
GUO Da-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China)
Values what people cherish are by nature the subjective appeal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objective being and its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It is very easy to find that there are many common value term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ality of the ways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while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s an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ame culture originate from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the prior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se value terms in the whole value system. Although the alleged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west, which are product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layed a great worldwide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ty, they themselves are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crises or challenges and even decay.
values; universal values; ecumenical values; the moral golden rule, natural law
2016-07-23
中共中央党校2016年度校级委托项目(XJWT201603)
郭大为(1965-),男,黑龙江五常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B018
A
1674-3199(2016)05-00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