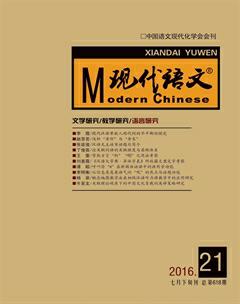试论吕新小说中的乡土文化理念
○宋赛赛
试论吕新小说中的乡土文化理念
○宋赛赛
摘 要:作为先锋文学的一脉,吕新小说创作中有其他先锋派作家所不具备的乡土文化色彩,在其文本之中,大量晋北山区形象的摄入,对农业社会的眷恋以及文本中流露出的乡土的人文价值取向都深刻地表明了,他是一个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深厚而坚实的乡土文化内涵的作家。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入手,分析其作家中所蕴藏的浓厚的乡土文化理念,从而对吕新有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吕新 乡土文化 童年经验
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正式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呈现出当代文学对现代性的不断追求,先锋文学在理论依据上多借鉴西方,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作为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舶来品,先锋文学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态势,它游离于中国本土文化之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而作为先锋文学的一员,吕新的小说创作却罕见地打破了这一局限。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他的先锋写作,不是浮在半空中的,而是将它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山西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以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将其滋养,从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先锋文学特质,又兼有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
首先,便是吕新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晋北山区形象。吕新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提到写作对于他来说,便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所谓“回到故乡”,便是在文本中回到那个苍凉萧瑟,但有着大片金黄灿烂葵花田的晋北故乡,在那里完成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吕新的先锋小说创作中,晋北山区往往是他小说中人物生活、故事发生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出生、成长、死去,经历着人世间的苦难。如小说《带有五个头像的夏天》、《农眼》、《太阳》等篇目都是以晋北山区为故事的空间载体。在吕新的笔下,那是个荒凉的所在,《农眼》中经常出现的大片荒凉贫瘠的灰褐色的土地,每年冬天呼啸而至的凛冽的西北风、长长的山路和连绵不绝的大山;那是个贫穷的所在,《瓦蓝》中为吃饱饭不惜去偷牛饲料,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被抓可以去公社吃顿饱饭;那又是个美丽的地方,《葵花》中那布满每一个角落的金光灿烂的向日葵、密集如云的庄稼、清澈见底的蓝色的河流和到处都橙黄碧绿,青翠欲滴的景象。出于内心对于故乡的深深眷恋,吕新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晋北山区的人物形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的是晋北山区那苍凉而辽阔的土地的血液,因而便成为山区的化身,吕新在小说中写他们的贫穷与受辱,无疑是在为故乡的不幸和凋敝痛心。这种对故乡的看重,正是乡土文化在吕新文学理念中的体现之一,他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使他的小说与晋北山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无法拆分的整体。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故乡情怀”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县等,故乡成为他们内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圣地,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作品风貌。在对故乡的回首中,他们获得了创作的强大动力及源源不断的素材,观察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悲惨命运,便振臂一呼,为自己的故乡发声。
其次,是吕新对于农业时代的眷恋。吕新对于农村的叙述,无意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而是在描述一种农业时代的巨幅的背景图,并通过人物与故事营构一个乡土的民间。在《消逝的农具》中,吕新这样叙述自己的创作活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眺望过农民与河流的关系,以及农具在四季里的形状和印象。描述农业岁月里的颜色和气候,是一次困难的空洞而悄无声息的活动。”[1]可以说,农业时代是他着力想要表现的重点,而农民与农具的出现,恰好使农业时代有了它存在的基础。在吕新的小说中,存在大量关于农村环境与农具的描写,如小说《消逝的农具》中,“五谷金黄。小麦和谷子的幽香轻轻飘散,土的颜色,阳光的颜色,牛的颜色不断在陈仓荒芜地视线里重复出现,寂静的窑洞仿佛山中的坟丘。”[2]大量的关于谷物、牲畜与土地的描写使文本具有浓烈的农业气息,是作者对于记忆中的晋北山区的一种情景的复现。而反复在吕新小说中出现的农具意象,则是农业时代的一个最有力的代表。作为人类生产力的标志,生产工具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农具则成为作者将文本带入到农业时代的一个有效介质。这些渗透了作者主体深厚情感的农具意象,如打谷场、石磨等,代表着那个淳朴而原始、恬淡自然的农业社会。而这个农业时代则成为结构松散、情节破碎的文本背后小说致力于强调的真正的主角,它是作者童年记忆中晋北山区的代表,同时也是乡土中国的化身。同沈从文不同,吕新不是在歌颂乡土的农业时代的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象,而是在试图把握农业社会中农村凋敝的迹象,物质欲望的无法满足以及精神家园的不断崩溃。如小说中饥饿的频繁出现,农村社会中男女关系的乱象等,这种愚昧和饥渴贯穿于他的许多小说文本中,代表一种古老农业文明的衰败。而执迷于描写农业时代的吕新,在叙述了种种乡村的式微和败落之后,仍旧眷恋地书写着这古老的乡土文明。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事物,如小说《一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但我们在文本中所见到的仍然是用石磨在磨豆腐,这种对农业生产方式的保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而且整个文本呈现出的也是农业时代的风貌,仿佛是与现代文明相剥离的一个存在。
最后,吕新乡土小说叙事中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诉求。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之中,乡土文明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和挑战,从而呈现出衰落的态势,传统乡村中的一些淳朴的民风正在消逝,许多美好的品德也被逐渐逐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吕新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对乡村日常及农民生活现状的关注之下对于这些乱象的批判,从中透露出的是他对乡土中国的深深的热爱。如《我理解的青苔》中,“我”来到绥中地区打探王老五的消息,遇见村长薛本仁,当我们俩在传说中的海边遇到一个与剧团走散的鼓师时,薛本仁对“我”说起村里已经好几年没看过戏了,而原因正是人们都在忙着挣钱、盖房子,很多风俗在物质欲望的挤压下都被忘记了。民间风俗的被忽略,代表民间乡土精神的被忽视,被压制,在现代文明强有力的攻势之下,传统的乡村文明被大家抛诸脑后,文本对这种现象的揭示,背后是作者对乡村文明衰败的无限担忧,它意图唤起人们在沉迷于物质欲望时同时保持对这种在历史中延续已久的乡土精神的热爱与坚守。凡此种种,使沉浸在乡土文明中的吕新担忧不已,而他自觉地在文本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描写当代农村的现状,揭露隐藏其中的问题,与传统现实主义“为人生”的宗旨不谋而合,他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故乡以及整个乡土中国的眷恋描写晋北山区,从而使他的小说在苍凉而萧瑟的山区背景之外,还具有了强烈的人文精神诉求,而这又使他的小说创作在先锋品质之外具备了传统的、乡土的文学品格。吕新从民间立场出发,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呈现民间乡村世界的精神堕落,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价值沉沦,从而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守护住这片乡土世界和传统文明。
总之,吕新的小说文本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他所深深地浸润的本土文化传统,使他的小说在先锋文学创作之中具有了独特性。而若我们要探究何以吕新的文学创作中会出现这许多的晋北山区形象以及他文本中弥漫的浓厚的乡村气息,我们不妨从他的童年经验中寻找答案。童年作为个人生命的起点和记忆中最初的地方,包含着最深厚、最真挚的人生体验,它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作者的创作视野,另一方面“作为先在意向结构”[3]对文本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吕新而言,童年在晋北山区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轻松地将他的记忆重现在文本之上,只是这种经验已不是原始的状态,而是经过了作家的文学加工和创作的被虚化了的文学形象。他在与林舟的对话中,称他的文学写作对象是留下了无数幼年记忆的晋北山区。而且,在他的眼中,“一个人的童年才是他真正的唯一的故乡”,童年的记忆成了吕新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成了他创作的归宿,他将熟悉的故乡的景物、人与事结构成篇,使他的小说中有了鲜明的晋北山区的印记,地理环境成为他小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童年经验会对他个人的思维方式与情感价值倾向产生异常深刻的影响,吕新曾说:“在家乡,有一带荒芜的山冈使我终身难以忘怀。” 生性孤僻而内敛的吕新在孤独感、压抑感折磨之下,将创作的目光聚焦于于他有着深厚情感的晋北故乡,因此,我们在吕新文本中见到的晋北农村,通常是荒凉而贫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困苦之中,遭受着生活给予的磨难,文本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的色彩,这与作家本身的审美倾向是密不可分的。童年的经验促使吕新将他文学创作的根深深地扎进了记忆中的晋北山区,使文本具有了浓厚的本土文化韵味,成为当代山西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1][2]吕新:《夜晚的顺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第223页。
[3]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宋赛赛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