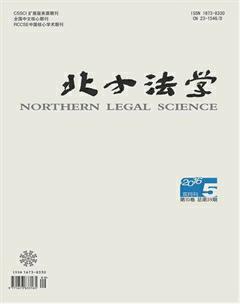女性与死刑:美国经验与本土探索
摘要: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女性犯罪人被判处或执行死刑的数量与比例要远低于男性犯罪人。死刑适用中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引发了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他们主要从司法制度与公众情感两方面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提出了“骑士精神”、“邪恶女性”等理论,并就性别歧视与平等保护的原则冲突与协调展开深入论述。这些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死刑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除了严重违背女性社会性别的罪行之外,我国应当严格限制对女性适用死刑。
关键词:死刑女性犯罪女权主义邪恶女性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5-0069-14
在当今社会,以欧盟诸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都已经在法律或事实上完全废除了死刑的适用。但美国仍然在立法与司法不断加以限制和完善的基础上,坚持保留与执行死刑。在美国长达50余年关于死刑存废与否的争论中,学者们针对死刑裁量的任意性、死刑罪名、死刑适用对象、犯罪受害人、证据标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讨。而犯罪人性别的差异与歧视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话题——“死刑制度的背后也是性别激烈交锋的战场”。①著名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死刑主要的适用对象是男性而非女性。从1930年至今,仅有32名女性被执行死刑,却有3827名男性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既然死刑看起来对两性均可适用,为何女性能享受到如此的优待就着实令人费解。”②难道死刑适用真的与性别有关吗?笔者以美国死刑制度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与理论探讨等方法,以期得出科学合理的答案与可资借鉴的结论。
一、实证数据分析
根据美国自殖民时期至今的死刑统计数据,我们不难看出男性与女性犯罪人适用死刑的比例存在天壤之别。在1608—2012年间,美国共处决了近20000名死刑犯,其中女性仅有571人,约占总人数的29%。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比例更是只有06%左右。截止到2014年10月1日,全美共有3035名死囚等待执行死刑,其中女性仅有57人,约占总人数的188%。③
以1972年的“福尔曼诉佐治亚州”案为界,美国死刑制度于1973年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1973—2012年间,平均每年因涉嫌谋杀罪而被逮捕的女性约占总被捕人数的10%。这些谋杀犯中共有8375人被判处死刑,但女性只有178人,仅约占总数的21%,远低于其在总被捕的谋杀罪犯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死刑犯中有3146人沦为死囚,而女性只有61人,约占总数的19%。至于实际被执行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仅为12人,约占总数的09%;而被执行死刑的男性则高达1308人,是女性人数的100余倍,相差十分悬殊。Victor Streib, Death Penalty for Female Offenders, January 1, 1973 through December 31, 2012, http:// wwwdeathpenaltyinfoorg/documents/FemDeathDec2012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15日。 在被判处死刑的男性罪犯中,最终被执行死刑的比例约为1596%;而女性则仅为67%。这一差距在美国的多数死刑州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从1976年到2011年3月10日,维吉尼亚州共处决了108名死刑犯,其中仅有1名女性于2010年被处决——而该州上一次对女性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12年;德克萨斯州共处决了466人,其中也仅有3名女性,约占总数的064%。数据来源于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executions-us-1608—2002-espy-file,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15日。
上述数据揭示出的美国死刑适用中的性别差异令人震惊,这难免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与男性相比,女性被判处或执行死刑的比例为何如此之低?是因为美国的死刑立法中规定了对女性犯罪人应当从轻处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美国立法中赤裸裸地表现出性别歧视的条款是难以想象的,关于死刑的立法自然也莫能例外,在形式上是完全“性别中立”的。那么,是由于应被判处死刑的女性犯罪人的数量极少吗?这一理由也无法成立,因为美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罪当处死的女性。从上文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美国男女谋杀犯的比例在9:1左右,即使考虑到女性犯罪的自身特征,被执行死刑的比例也难以扩大到惊人的110:1。为了探寻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诸多美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得出了一系列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侧重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为什么女性适用死刑的几率要比男性低得多?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部分女性罪犯成为被执行死刑的罕见例外?
二、死刑适用中性别歧视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美国在死刑适用中之所以存在性别歧视,主要有司法制度与公众情感两方面的原因。在死刑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女性犯罪人能够在立法设计、检察起诉、量刑情节的适用等多方面得到优待。而在公众情感方面,由于社会对女性犯罪人普遍具有同情、怜悯与宽容之情,这也导致陪审团与法官更倾向于不对女性判处死刑。下文将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一)从司法制度的角度
1死刑罪名的构造
基于死刑罪名的法定构造,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触犯这些罪名。以重罪谋杀这一在当前适用死刑比例最高的犯罪类型为例,根据维吉尼亚州的相关规定,在实施性犯罪、抢劫或绑架的过程中故意杀害被害人的,是重罪谋杀的三种典型表现,通常应被判处死刑。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实施上述严重暴力犯罪的几率显然要小得多——在所有的重罪谋杀者中,女性仅约占6%。Elizabeth Rapaport,Some Questions about Gender and the Death Penalty, Golden G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0, No3, 1990, p509此外,女性所实施的杀人犯罪多数系由家庭纠纷所产生的恐惧或愤怒所引发,并未经过预谋且社会危害较小,因此很难被指控为一级谋杀,更不用说可被判处死刑谋杀了。Elizabeth Rapaport,The Death Penalty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Law & Socy Rev, Vol25, 1991, pp370—371
2检察起诉环节的优待
据统计,在相同情况下,检察官更倾向于指控男性而非女性死刑。Michael JSonger and Isaac Unah, The Effect of Race, Gender, and Location on Prosecutorial Decisions to Seek the Death Penalty in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Law Review, Vol58, 2006, pp183—184而通过辩诉交易,女性被告人也往往能够得到指控罪名及量刑上的优待。以杰克逊(Vickie Dawn Jackson)一案为例,杰克逊女士被指控在其担任护士期间通过注射毒药的方式杀死了10名患者。她提出了不抗辩的请求,从而避免了陪审团的审理与可能对她不利的证人证言,所面临的最高刑罚也相应降低为终身监禁。她最终以这种手段逃脱了死刑的威胁,而被判处40年后方可假释的终身监禁。Nurse Receives Sentence of Life in Prison for Killing Multiple Elderly Patients,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archive//ldn/2006/oct/06101006,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12日。
3加重与减轻情节的影响
不少美国学者认为,在当前“性别中立”的司法制度中,应主要从女性犯罪可能具备的量刑情节出发来分析女性通常不会被判处死刑的主要原因。如果过于强调“女性”这一天然身份所产生的影响,则可能存在性别歧视之嫌。Carroll, Images of Women and Capital Sentencing Among Female Offenders, Texas Law Review, Vol75, 1997, pp1425—1427如有学者认为,在影响判处死刑的情节上,有关犯罪人本身的下列要素可以作为加重情节:(1)先前是否有暴力犯罪记录;(2)将来再犯严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3)犯罪前是否预谋并精心策划。Victor LStreib,Sentencing Women to Death, Criminal Justice Magazine, Vol16, No1, Spring, 2001, pp26—27与男性相比,妇女具有上述加重情节的几率要小得多。例如,女性具备严重犯罪前科的几率极低前引⑦, p372——事实上,在因涉嫌谋杀罪名而被逮捕的女性中,其是初犯的几率比其他任何罪名都要低。Glick and Neto,National Study of Womens Correctional Programs, in BPrice and NSokoloff (eds),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Women, 1982, p153通常而言,女性也很难被评价为能够对社会产生持续威胁的危险分子,且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情感与态度。法官与陪审团都倾向于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再犯的危险性较小,也更愿意改过迁善。Kopec,Avoiding a Death Sentence in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Capital Defense Journal, Vol15, 2003, pp356—357至于是否经过预谋或策划,则往往是最严重谋杀罪的必备要件。但根据调查数据,女性所实施的杀人案件多为临时起意,一时感情冲动而为之。Crites, Women Offenders, Myth vsReality, in LCrites (ed.), The Female Offender, 1976, p41甚至还有学者指出,既然女性杀人案件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事前精心策划、预谋的情形并不多见,这就导致在她们实施犯罪行为时,很难考虑到自己将会面临何种惩罚。因此,如果说死刑的目标之一是威慑潜在的犯罪人,使之不敢实施类似的罪行,那么其在典型的女性杀人案件中显然是无效的。Victor LStreib,Americas Aversion to Executing Women, Womens LJ, Vol1, 1997, p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一个以侵略性和武力为主导的刑法世界中,女性和男性的地位并不平等。”女性缺乏攻击性,力量上也有所欠缺,难以像男性那样在犯罪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不易起到主要的谋划作用和实施作用。Patricia MWald, Why Focus on Women Offenders? Criminal Justice Magazine, Vol16, No1, Spring, 2001, p12
与加重情节相反,和男性相比,女性犯罪人具备减轻情节的概率更高:如受强烈刺激而精神失控或神志不清、不堪忍受被害人的长期压迫或虐待、在某人的支配与控制下而实施犯罪、性格与环境因素、家庭背景等等。前引B11, p27法官与陪审团也更倾向于使用立法中的“兜底条款”,寻找或接受对女性被告人有利的“其他要素”。Victor LStreib, Gendering the Death Penalty: Countering Sex Bias in a Masculine Sanctuary, Ohio State Law Journal, Vol63, 2002, p445甚至在有的时候,不具备加重情节都可以被评价为具有减轻情节。
当然,也有学者对上述三种司法制度的原因提出质疑,认为法律并没有明确针对男女性别的差异而做出不同的规定。既然上述罪名、程序或情节对任何人都能够适用,又怎么能认为存在性别歧视呢?例如,如果死刑无法有效威慑女性不再实施严重犯罪,那么对男性也理应同样无效,而不应只作为对女性较少适用死刑的借口。至于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或长期虐待而实施杀人行为的女性之所以较少被判处死刑,根本原因也许并不在于其“女性”的特殊身份,而在于“受虐者”的角色;即使将被告换成男性,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死刑制度的设计中并不存在性别歧视,男女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实践中的巨大差别无非是由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相异的本质与特征所造成的。前引⑥, pp559—561但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男性与女性犯罪人所具备的特殊的加重与减轻情节完全相同,女性也会得到更轻的判决。”Victor LStreib, Death Penalty for Female Offenders, Cincinnati Law Review, Vol58, 1988, pp877—878“我并不认为这里面存在什么理性或客观的原因。”前引⑩, p1428诚然,法律上的各种规定均未明确地仅将犯罪人的性别作为死刑适用的考虑因素,但某些因素确实会在事实上导致即使是同一情节,在男女罪犯中所占的权重也并不相同——相较男性而言,同一情节对女性犯罪人起到的帮助会更大。如当被告人是女性、尤其是女孩时,辩护律师关于其性格与身世的举证就更能够触动陪审员内心温情的一面。前引B21, p877再如,人们普遍认为,失去母亲比失去父亲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更大。前引B14, p357如在吉尔伯特(Kristen Gilbert)一案中,被告人吉尔伯特的父亲与祖母恳求陪审团不要对其判处死刑——这将对她的两个年幼孩子产生致命的打击。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吉尔伯特被判处终身监禁。Nurse Sentenced for Killing Patients at VaHospital,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nation/2001—03—26-veterandeaths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4日。 因此,仅从司法制度与程序设计这个角度出发,尚无法为女性为何极少适用死刑提供充足的理由。
4对女性适用死刑违背宪法精神
美国《宪法第8修正案》规定:“不得施加残酷与非寻常之惩罚”。对于“残酷与非寻常”的解释,法院原本倾向于从立法原意中寻找答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最高法院开始认为“宪法第8修正案的本意无外乎强调人性尊严……应当从那些随着成熟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进化的文明标准中寻找其真谛”。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p1572—1573而陪审团的量刑裁决情况所反映出的人类理性情感与民意,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可靠的反映当代文明标准的客观指标。自美国殖民时期以来,对女性判决与执行死刑的案件数量就相对较少,400余年间仅有575名女性被执行了死刑。而随着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每年被执行死刑的女性人数在总体上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从1900年至今的100余年中,全美只有55名女性被执行死刑;其中,肯塔基、内华达与田纳西等3个死刑州在此前共处决过159名女性,但进入20世纪后却没有对任何一位女性执行过死刑。而从1973年至今,全美更是仅有16名女性被执行了死刑。数据来源于美国死刑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executions-united-states,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20日;前引B19, pp 439—440从中不难看出,伴随着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美国公众逐渐养成了限制对女性适用死刑的习惯。社会文明已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判处或执行死刑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过度的惩罚,有违社会的基本道德情感。那么,对“残酷与非寻常之惩罚”的解释自然也应当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大众的心声,将对女性适用死刑包括在内。毕竟,“一项刑罚虽曾经被我们的历史所认可,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当今亦应被认可”。Furman vGeorgia, 408 US238, 329 (1972).因此,对女性适用死刑违反美国《宪法第8修正案》的规定,应当加以废止。不过,该观点并未明确认定对男性适用死刑亦属违宪,如果司法实践将死刑适用对象默认为男性的话,恐怕又有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之嫌。
(二)从社会学及女权主义的角度
前文已述,虽然男女适用死刑的巨大差异具有司法制度层面的原因,但这些理由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之外,必然还存在着鲜活的、与人情世故密切相关的因素。女性与男性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质差别,才是这一现象的更深层次原因。从这一角度出发,美国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如下两种观点。
1.父权主义与骑士精神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的法律制度具有父权主义的悠久历史。在当今这个仍以父权主义为主宰的社会中,法律领域依然主要是男人的领地,女性被定型为被动、弱小、需要男性保护的对象,并一度被拒绝从政、从事法律职业甚至参加陪审团——这些工作对于她们这么纤弱的角色来说,显然是过于沉重的负担。Steven FShatzt and Naomi RShatz, Chivalry is not Dead: Murder, Gender, and the Death Penalty, Berkeley JGender L& Just, Vol27, 2012, pp5—6如美国最高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男性是,或者应当成为女性的保护者与守护神。”“女性最重要的命运与任务就是履行其作为贤妻良母的崇高而仁慈的职能。”Bradwell vIllinois, 83 US130, 141 (1872);Hoyt vFlorida, 368 US57, 62 (1961).而男性既然在社会上居于支配与主导地位,就应当像风度翩翩的骑士那样,主动承担起保护女性的责任与义务,即使她们是罪犯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公众并不情愿让女性面对死亡、甚至面临危险。例如当海难发生时,妇女总是被作为优先救援的对象;应征入伍的女兵也总是被安排远离战火纷飞的一线。前引B16, p6既然如此,我们也自然倾向于不对女性犯罪人施加残酷的刑罚,诸如死刑。长久以来,人们在心目中早已形成了固定印象:男性杀人犯是危险分子,女性杀人犯则是悲剧。当面对的是女性罪犯时,恐怕任何人心中报应的念头都会不自觉地减弱。因此,作为对严重破坏社会价值标准的犯罪行为的终极制裁,将死刑适用于女性是不人道、有损社会道德的。Andrea Shapiro, Unequal before The Law: Men, Women and The Death Penalty, Journal of Gender, Social Policy & The Law, Vol8, 2000, p454有学者认为,决定死刑判决的关键是罪犯的遭遇能否引起公众、也就是陪审团的共鸣。“死刑犯总是被人们视为恶魔,但女性在人们心中往往不具有这样的形象”。Thad Rueter,Why Women arent Executed: Gender Bias and the Death Penalty, Human Rights, 1996, Vol23, No4, p10在史宾尼莉(Eithel Spinelli)一案中,30位男性罪犯均自愿以抽签的形式代替史宾尼莉被执行死刑。在请愿书中,他们写道:“对史宾尼莉女士执行死刑将是令加州人民厌恶的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在心智正常的时候会实施类似的罪行。处决女性将会有损加州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法律和人民的意愿都反对对其执行死刑。此外,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史宾尼莉女士的这一特征也应当得到特殊的考虑。我们加州从未处决过任何女性这一令人骄傲的记录绝不允许被破坏!”前引⑥, p501史宾尼莉并不漂亮,甚至十分丑陋,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男囚的请愿,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就是其女性身份唤起了男人们内心深处的骑士精神。参见前引B29, p66
也有学者认为,在父权主义的视角下,从制度构建的角度出发,死刑并非是对最邪恶犯罪的制裁,而是参与某些权力等级的管理。与传统雪茄烟雾缭绕的男性俱乐部没什么两样,死刑制度也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各种犯罪行为而设计的,女性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只有那些具备男性化行为特征的女性才能加入。前引B19, p437不妨以美式足球这项男人的运动为例,在这里,男性们恣意对抗、冲撞,以把对手击倒在地为荣。但如果场上加入了一名女性,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应当像先前一样,对使她被抬出场外的男性给予最热烈的欢呼,还是仅因为她的性别而修改运动规则?与之类似,死刑制度也是一项属于男性的“运动”,目的是把最粗暴的男性对手驱逐出去,而不欢迎瘦弱的女孩介入其中。因此,处决女性就如同那些欺负女孩子的男人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懦弱表现。前引B11, p28
2.邪恶女性理论
既然在死刑适用上存在着如此显著的性别歧视,为何还有572名女性被执行了死刑?对于极少数的女性犯罪人而言,人们不吝于向其施加死刑这一在传统上只适用于男性的刑罚又是出于何种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邪恶女性”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严格区分人类的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认为前者与生俱来,反映出人的固有属性;后者则与行为人被社会赋予的角色、给予的评价息息相关,是可以变化的,Stephanie Covington, A Womans Journey Home: Challenges for Female Offender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From Prison to Home” Conference, January 30—31, 2002, p3并且反映出整个社会对男女在生活、婚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因此,在考虑性别因素时绝不能仅关注生理上的男女特征,还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进行综合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应重点关注女性实施犯罪时基于其社会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如妻子、母亲、护理人员或妓女等;认为抛除种族、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因素,她们是否实施了严重超越其社会性别的犯罪行为,将对其是否被判处死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那些严重违背了社会主流对女性形象的认知,实施与这一形象完全无关的犯罪行为的女性罪犯,才能被认为偏离或“越轨”了她们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从而被法律贴上“邪恶女性”的标签。前引⑥, p513;前引B21, pp878—879此时,她们违反了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首先,通过其所实施的严重罪行侵犯了公众的道德情操;其次,通过她们“非女性化”的行为暴露了其被自身性别所掩饰的本质,玷污了公众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与情感,违背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与信任。由于她们的恶行消弭了人们传统观念中两性之间的差异,因而丧失了女性身份给她们带来的庇护,反而被像男性一样对待,应当受到死刑的严惩。此时,她们被执行死刑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压力的驱动。Deborah WDenno, Gender, Crime, and the Criminal Law Defenses, JCrimL& Criminology, Vol85, No1, 1994, pp159—160死刑已不仅是一种普通的惩罚方式,更是摧毁她们社会角色与形象的一种公开手段。通过死刑判决,国家再度明确了被她们逾越的性别界限,并且向全体女性警告:老老实实地呆在线那边,否则你们将面临和她们一样的命运。前引⑩, p1437
不少学者认为,在1973年后被执行死刑的女性罪犯中,绝大多数都可以用邪恶女性理论加以解读。这些女性要么是恶毒杀害爱人的冷血杀手,要么是恶行程度不逊于其男性同伙的年轻杀手,要么是报复心极强的暴躁狂,抑或是在抢劫过程中像男人一样行凶的严重瘾君子。如在巴尔福德(Velma Barfield)一案中,被告人巴尔福德女士用砒霜毒死了自己的男友,并承认自己还先后毒死了前夫、母亲以及被她照顾的老人共5人。Velma Barfield,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lma_Barfield#Prison_and_Execution,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24日。 毫无疑问,巴尔福德严重违背了女友、妻子、女儿、照顾者等多个女性角色所赋予的义务,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特征在她身上荡然无存,明显超越了社会可以容忍的界限,最终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再如博诺阿诺(Judias Buenoano)一案中,被告人博诺阿诺女士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先后与多人交往,并通过毒杀自己的丈夫与男友获取了他们留下的高额保险金,最终在试图谋杀其现任未婚夫时被抓获。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博诺阿诺严重破坏了与丈夫、普通法的配偶与未婚夫所建立的密切关系,违背了他们的信任,这种纯粹为了经济利益而与无辜者结合的行为玷污了人们对照顾者、共同生活者这一角色的印象。作为邪恶女性的一员,博诺阿诺最终被执行了死刑。前引B14, pp359—360
与那些通常关注两性间性别差异的理论不同,邪恶女性理论主要反映出女性内部的歧视——对那些具备女性这一生理性别、却不符合女性社会性别的犯罪人的歧视。就女性罪犯而言,尽管同样被指控犯了谋杀罪,有的却更容易成为死囚——不是因为她们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实施了最为严重的罪行,而是由于没有合适地体现出作为“女性”的身份特征。Renee Heberle, Disciplining Gender; Or, Are Women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Chicago Journals, Vol24, No4, Summer, 1999, p1106通过对比不同女性在被判刑时的角色扮演,尽管法律的本意可能并非针对那些没有成为一个“好母亲”的犯罪人施加更为严厉的刑罚,但在死刑的适用中却的确有这样的歧视存在。Phillip Barr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USDeath Penalty System, 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 Vol3, No1, 2000, p95以鲁迪埃(Darlie Lynn Routier)与史密斯(Susan Smith)为例,二人均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并且都试图通过编造绑架案件的事实以转移调查的视线,但在庭审上的表现则大相径庭。鲁迪埃被认为是“冷酷无情地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严重背离了朋友所描述的、她曾经拥有的‘母亲形象”。通过杀害自己的孩子,她逾越了“母亲”这一性别角色的界限;通过强烈坚持自己无罪的冷血表现,她又逾越了“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界限。她之所以得到惩罚,不仅在于实施了杀人犯罪,还在于违背了社会所期待她扮演的性别角色。最终,鲁迪埃被判处死刑。而史密斯则不然,她杀害自己两个孩子的恶行虽然逾越了“母亲”这一角色的要求,但她啜泣的坦白与悔恨的表现却表明她尚未完全抗拒自己的性别角色,仍然符合人们心中的女性形象。因此,她被认为是“一个脆弱、胆小、无力面对生活与爱情中的失望,过于孩子气而不能胜任母亲这一角色的人”。正是由于其并未完全泯灭的“女性”身份,史密斯最终逃过了死刑的制裁。前引B45, pp91—92因此,虽然女性在美国的死刑判决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不可否认的是:性别内部的歧视或许是有些女性被判处死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除了着重关注女性之所以被判处死刑的原因外,邪恶女性理论同样可以回答女性整体在死刑适用上的歧视问题。根据这一理论,死刑适用的对象是男性与那些抛弃了生理性别所带来的优势、在社会性别上被视为男性的“邪恶女性”。这些女性与她们的罪行完全符合这一假设——美国的陪审团只倾向于对男性判处死刑;而公众也普遍认为死刑对女性而言是一种不合适的惩罚。前引B14, pp357—364通常而言,女性杀人犯的动机大多是基于孩子、妻子、母亲或保姆等角色所引发的家庭、婚姻内部的矛盾,因此,绝大多数女性犯罪人在社会性别上尚属于“真正的女性”,能够得到社会的容忍与宽恕,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死刑裁量上的性别差异。
三、性别歧视与平等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尽管美国的死刑立法与司法制度赋予男性与女性平等的地位,但在实际适用中却差别极大,这一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违反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原则的警觉与担忧。显然,“即使不是死刑支持者也会认为,既然能够对男性适用死刑,那么妇女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对待”。Victor LStreib, Executing Women, Juveniles, and the Mentally Retarded: Second Class Citizens in Capital Punishment, in Acker, Bohm, and Lainer (eds.), Americans Experiment with Capital Punishment, 2003, p322在美国,甚至还发生过被判处死刑的男性犯罪人怀特(White)以女性共犯未被判处死刑为由而上诉,认为在审理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的案例。他的上诉意见中写道:“对于相同的罪行,女性共犯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是否意味着对平等保护原则的否定?”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援引先前的判决,认为“法律上的平等保护意味着死刑可以被适用于所有条件完全相同的对象……但法律上的平等对待绝不能破坏量刑的个别化,因此,即使是实施同样罪行的犯罪人,获得不同的量刑结果也是完全合宪的”,最终驳回了上诉。前引B32, pp460—463但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并未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故学者们仍然就此进行着激烈的交锋。
有学者认为,对男女适用死刑的不平等严重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前引⑩, p1441该修正案明确指出,对于在美利坚合众国管辖下的任何人,均不得被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在刑事司法中,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比他人更轻或更重的惩罚,女性自然也不例外。自上世纪60年代起,女权运动在美国蓬勃开展,极大地推动了男女平等化的进程。尽管女权主义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抨击那种认为男人养家糊口、对家庭负有主要责任,而妇女注定只能在家生儿育女的陈旧观念,但也并不主张一味地抬高女性地位,从而人为地制造出新的性别歧视。即使是那些对女性有利的立法或措施,如果其出发点在于无条件地认为女性属于弱势群体而需要加以弥补的传统观念,势必将造成对男性的不公平,这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虽然在法律上的平等对待可能会废除这些对女性的额外优待措施,从而导致短时间内对女性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使女性最终在社会与经济领域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虽然死刑适用的现状明显对女性有利,但由于仍然属于一种积极的性别歧视,故这一做法依然值得商榷。
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平等对待并不意味着公平对待。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并不要求必须把某项条例平均适用于每个人,也不要求使一切实际上各不相同的事务在法律上得到相同的处理。既然男女之间存在差别,女性在现实中确实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更多的保护,故一视同仁地采取男性标准的话,毫无疑问将总是使女性成为输家,从而丧失更多的权利。因此,应当关注女性的特殊需求,在法律上对男女区别对待,才有可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发展机会和结果。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 on Life and Law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8—39;Chesney-Lind & Pollock-Byrne, Womens Prisons: Equality with a Vengeance, in Pollock-Byrne & AMerlo (Eds), Women, Law and Social Control,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5, pp155—175有学者甚至略带讽刺意味地指出,如果平等对待意味着平等被监禁的话,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认为如今男女之间非常平等——当前被监禁的女性人数可能要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参见 Stephanie Covington and Barbara Bloom, Gendered Justice: Wome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Barbara Bloom (ed.), Gendered Justice: Addressing Female Offenders,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3, pp3—4还有学者认为,根据女权主义理论,在女权运动初期追求的是形式的平等,即男女应当在法律上一视同仁,得到相同的对待与保护;但在中后期则追求实质的平等,奉行“差异主义”与“多样性原则”,认为男女之间,甚至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男女在法律上理应得到不同的对待,而不能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无差别。Yeemee Chan, Abolishing Capital Punishment, Nova Law Review, Vol31, 2007, pp341—345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的优待措施也并不总被认定为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如在“施莱辛格诉巴拉德”一案中,法院否定美国海军对女性给予更长的晋升时限存在性别歧视。理由就在于男女军官所处的境地不同,由于男性得到提拔的机会更多,故而延长女性的时限也是无可厚非的。Schlesinger vBallard, 419 US498 (1975).而在“密西西比女子大学诉霍根”一案中,最高法院也认为,为了补偿某一性别因为性别歧视而造成的不公平待遇,州政府完全可以出于补偿目的而给予其一种“歧视性的优待”。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Hogan, 458 US718 (1982).因此,基于女性的社会角色、人格特性与女性犯罪的本质特征,其较低的死刑适用率并不违反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尽管争论仍在持续,但双方都毫无争议地认为,决不能以平等保护为由提高女性适用死刑的比例——“我们不能认为,应当完全消除死刑适用中的这种性别歧视,只要男性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相同条件的女性也不应幸免。”Victor LStreib, Rare and Inconsistent: The Death Penalty for Women, Fordham UrbLJ, Vol33, 2006, p628在当今限制、废除死刑适用的浪潮下,无论如何都不应提高死刑的适用比例与数量,从而破坏在减少女性死刑适用上业已取得的成就——前进的车轮绝无退回过去的理由。相反,人们应当认为,判决中无法消除的性别歧视问题是死刑制度的一个固有缺陷,势必影响最终结果的公平与公正性,应当被作为废除死刑的一个有力理由。前引B32, p470既然在死刑适用中势必存在性别歧视,美国就应当像多数国家那样废除死刑。前引B53, p353
四、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美国学者关于该国死刑制度中性别歧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我国虽然尚保留死刑,但自从2006年“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正式提出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死刑案件的数量大幅减少。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废除了13个死刑罪名;2015年11月1日正式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废除了9个死刑罪名,这无疑彰显出我国减少、限制死刑适用的坚定决心。笔者认为,限制死刑可以从适用罪名、适用程序与适用对象等方面三管齐下。以往对死刑适用对象的研究,通常是从年龄或精神状态等方面入手的,但在今后,从男女性别差异的角度出发,融合社会学、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失为一条新颖、有效的探索途径。在这一背景下,下列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讨论:在限制死刑的进程中,女性这一性别特征能否作为特殊的考量因素?如何有效地限制对女性适用死刑?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在当前我国的死刑制度中,“女性”身份是否会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
(一)我国死刑适用中的性别差异及立法构想
与美国类似,我国在死刑的立法设计与司法操作中都对女性给予了特殊优待。例如,在适用罪名上,法定刑设置了死刑的强奸罪原则上只能由男性构成。在适用对象上,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被判处死刑。在各种加重与减轻情节的适用上,正如美国学者所讨论的那样,由于女性犯罪人大多没有前科,系初犯、偶犯,且更容易认罪伏法,故被判处死刑的概率也应当低于男性。参见莫洪宪、刘夏:《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的设想——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04—105页。 武汉大学莫洪宪教授曾收集了我国中部三个人口大省的绝大多数女性死刑案例,据统计,三省从2008年至2011年被判处死刑的女性罪犯共计66人,远低于被判处死刑的男性犯罪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女性罪犯更是仅有15人。虽然可能在数据收集上存在部分缺失,但不难在大体上推断出: 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被判处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女性犯罪数量也微乎其微。前引B59,第106页。 笔者认为,之所以实践中女性适用死刑较少,除了上述法律上的显性因素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发挥影响——这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性别因素对女性的天然同情。
在立法上,针对孕妇不能被判处死刑的根本原因,通说认为是为了保护胎儿:“考虑到虽然妇女犯有死罪,但胎儿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惩罚犯罪人株连无辜的胎儿”。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但是,如果仅为了保护胎儿,为什么不能像我国古代或是其他国家那样,等到产后一段时间再对孕妇执行死刑呢?例如,《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妇女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大清新刑律》亦规定:“凡孕妇受死刑之宣告者,产后经一百日非更受法部之命令不得执行。”埃及、泰国以及美国一些保留死刑的州虽然规定不能对孕妇执行死刑,但可以推迟到怀孕中止或分娩后执行。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与实践判例,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或是在羁押期间人工流产后脱逃,多年后才被抓获审判的,均应被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但是,此时胎儿并不存在,自然没有保护胎儿生命权的必要,为何也不能对孕妇适用死刑?理由只可能在于其具有“孕妇”这一特殊身份。只要妇女在审判时处于怀孕状态,就被绝对排除于死刑的适用,而不依赖于胎儿是否出生。由此可见,刑法的这一规定并非仅是为了保护胎儿,而是为了保护孕妇这类特殊女性,根本出发点在于罪犯的性别而非其他因素。立法者为了体现出对孕妇的特别关怀与优待,故对这类主体“废除”了死刑。
在具体的刑罚裁量时,虽然由于我国的死刑案件数量尚未公开,难以像美国那样通过数据分析判断性别因素是否会影响死刑适用,但笔者通过对网上公布的部分相关判决书进行研究,发现法官在量刑中也会有意无意地将“女性”作为不对行为人判处死刑,或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重要判断因素——事实上,“女性”(或“母亲”)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已经广泛体现于多种犯罪中。参见(2014)吉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2010)安刑终字第85号刑事判决书、(2014)杭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2013)杭刑初字第137号刑事判决书、(2011)黄刑初字第00018号刑事判决书等。 他们认为,如果对女性判处死刑,势必会对家庭、尤其是其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产生巨大影响,不利于维护家庭关系,保障社会稳定。例如,有的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由于被告人“有三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其最小的孩子案发时正处于哺乳期等情节”,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必立即执行;参见(2008)粤高法刑三终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 “鉴于被告人杨秀莲家中尚有三个未成年孩子,其所在村委会及本村22户村民联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以及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实际,可对杨秀莲酌情从轻处罚”;参见(2013)庆中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 “同时考虑到刘满足与被害人有三个未成年孩子、且三个孩子只有日渐年迈的肖某三监护的现实,为让刘满足尽早尽责尽孝,早日回归社会可让其未成年孩子早日得到母爱,使这个家庭能够延续生存,依法可较大幅度地从轻处罚”等等。参见(2014)赣刑一终字第126号刑事判决书。 其余类似表述的判决书还包括(2014)安刑初字第960号刑事判决书、(2014)大中刑初字第131号刑事判决书、(2015)鄂新洲刑初字第00077号刑事判决书、(2009)洪刑二终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2014)温乐刑初字第268号刑事判决书、(2015)贵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2015)达渠刑初字第183号刑事判决书、(2012)川刑初字第356号刑事判决书等。 即使在国际社会,主张废除女性死刑的首要理由也在于:“女性都是母亲,需要得到特殊的人道处遇”。参见《人权委员会第9届大会第202次会议摘要记录》,联合国CCPR/C/SR202文件。
但显而易见的是,父亲也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的特定而且严重的精神健康疾患可以归因于父母被判处死刑,参见《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E/2015/49文件。 而法官们却鲜有考虑到失去父亲对未成年孩子的消极影响。就这一因素而言,男性与女性的反差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我国的刑事判决书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基于男性被告人要抚养未成年子女,而不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之类的表述。甚至有的案件中,男性犯罪人的辩护律师以被告人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等情节提出从宽处罚的要求,法院也并未明确表示采纳,或是直接予以否认——“(被告人)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且有七十多岁的母亲属实,但这不属从轻处罚情节”;参见(2015)新刑二终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 “该上诉意见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参见(2014)海中法刑终字第181号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家庭情况及成员的生活状况不属于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等等。参见(2015)官刑一初字第561号刑事判决书。其余类似表述的判决书还包括(2013)云高刑终字第531号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书、(2015)长刑终字第109号刑事判决书等。此外,虽然极少数判决考虑到“孩子成长需要其父亲的事实”,也是基于夫妻离婚或丧妻后孩子由父亲抚养的事实,参见(2015)锡刑二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2014)温刑初字第00039号刑事判决书、(2014)温瓯刑初字第1544号刑事判决书等。 但如果将男性换成女性,类似表述就显得合情合理多了。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无法仅从孩子的角度来解释,根本原因还是女性性别所具有的天然优势。
由此不难看出,不管刑法有无明确规定,无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倾向于对女性罪犯适用死刑时“手下留情”,这已经成为了大家所默守的“潜规则”。虽然中西方的文化与国情不同,但我国社会大众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惜,与美国人所主张的“骑士精神”类似,对死刑适用产生了较大影响。事实上,这种现象可以一直溯源到我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将两性的活动空间和工作范围进行了重新规范,将社会与家庭的工作范围分为“公”“私”“内”“外”四个领域,而女性被封闭在“私”领域之内,对男性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参见杜房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基于“男尊女卑”的弱势地位,女性得以作为“幼弱”的代名词,在刑法中享受到恤刑原则的优待,在量刑与行刑中都远较男性为轻,如果不是犯十恶不赦的重罪,原则上都可以不被处死。因此,我国当今在死刑适用中对女性的特殊处遇,可谓是上述思想传承、延续数千年的结果。无论目前女性解放到了何种程度,与男性相比都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故不管主要目的是“怜悯”还是“尊重”,人们在考虑是否对女性判处死刑时都不禁会心头一软。
将这一现象对应到犯罪学与刑法学理论中,在本质上,社会公众对符合女性社会性别犯罪人的同情是一种非规范性的评价因素。所谓非规范性评价,主要是指生活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群体,根据一定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价值标准,对社会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做出善恶、正邪的道德评价,或对定罪量刑提出意见,以表明其褒贬态度的价值评判。其以社会需要、民众要求等法律的外在价值为基点,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民意,显露了理想化与普泛化的倾向,暗含了一种道德范围内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非规范性评价不但体现出犯罪对人们既有价值观念的破坏程度,也是人们心理上原有的价值平衡因受到犯罪的冲击而失衡的严重程度的外化,还反映出人们对犯罪的否定评价的严厉性程度,内含着人们要求处罚犯罪以求恢复价值的心理平衡的愿望的强度。参见于志刚:《犯罪的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第36页。 正基于此,非规范性评价对规范性的量刑环节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司法者需要考虑、并在判决书说理部分体现出来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由于法官也是普通人的一员,故在量刑时也难免会直接考量到非规范性的评价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不难理解社会性别为什么能够在实质上影响刑罚的轻重了。
基于上述预设,考虑我国公众对女性整体的认知与情感,并结合当前对女性罪犯判处死刑的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既然公众不太情愿对女性判处死刑,且死刑适用数量的不断减少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那么在今后尽可能减少、限制对女性适用死刑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做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期待立法者能够尽快全面地废除死刑,但这一想法在当前无疑并不现实,只能采取更容易为公众接受的折衷之策,呼吁进一步对女性限制、最终废止死刑的适用。理由主要在于:首先,“法律上的判刑与公众道德情感的关系就像缄封与热蜡的关系那样密不可分”。[美]H.CA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张志铭、方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由于法律是最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与载体,故公众感情对死刑立法与适用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和意义。远离大众观念、违背公众感情的死刑判决,只会导致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背道而驰,最终必然遭到社会的摒弃。而准确地认知和利用好公众对死刑的看法与态度,则可以为法官论证判决的正当性提供重要的社会心理依据。参见前引B73,第38页。 既然当前的社会道德情感对女性犯罪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希望女性面临残酷的刑罚与生命的危险,国家就应当顺应民意,尽可能少对女性犯罪人判处极刑,否则只会与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渐行渐远。其次,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故我们只能把其作为迫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适用于最需要判处死刑的案件。但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女性犯罪显然属于“宽”的一面,在刑事政策处理上应当侧重宽大、宽缓、宽容,具有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基础。最后,削减女性死刑案件的数量可以将宝贵的司法资源节省下来,以集中处理其他最为严重的犯罪,从而最大化地发挥死刑的惩治与威慑效果。
因此,与男性相比,我们可以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更为严格地限制女性的死刑适用,如类比刑法对老年人犯罪的规定,除了极端情节之外,原则上不能对女性适用死刑。这样一来,女性罪犯就不会因为贩卖毒品罪、贪污罪等非暴力性犯罪以及不具有加重情节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等暴力犯罪而被判处死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削减死刑适用数量的目的。此外,这一做法将导致对女性的死刑适用严格限制在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类型中,正契合当今死刑限制的潮流与趋势。
(二)社会性别与适用死刑的标准
在上一部分的论述中,笔者认为性别差异在我国的死刑适用中确实存在,并针对这一现象,围绕着限制、减少女性犯罪人的死刑适用提出了立法构想,希望女性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口。在当前,完全废除对所有女性罪犯适用死刑并不现实,但导致对女性适用死刑的“极端情节”究竟包括哪些因素,仍是一个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操作的共性标准,以较为明确地判断出究竟应当对哪些女性适用死刑。笔者认为,美国的“邪恶女性”理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除了关注女性生理特征意义上的性别之外,社会性别也是刑罚适用中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社会性别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强调文化在人的性别身份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性别是文化指定、文化分配与文化强加的,是被社会所建构的。社会要求每个人的行为与角色都应与其社会性别相符,并基于此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参见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例如,女性应当具有关怀、爱心、同情、服从、温柔等品格,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母亲,父母的好女儿。而一旦社会性别被赋予之后,社会秩序就将构建个体的社会性别规范和期待,并迫使个体遵循之。个体虽可以改变社会性别中的一些因素,但必须使自己符合社会认同的少数社会性别类别。前引B72,第32页。 正是通过个人的性别身份展示其自然属性与社会身份,才成为了个体的人。
而人们之所以同情、宽恕女性罪犯,不愿意对他们施加极刑,根本原因正在于她们的社会性别符合大家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即使行为人贩卖、运输了大量毒品,或是贪污了巨额公款,或是基于日常纠纷而杀害了邻居,但只要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相夫教子、赡养老人、操持家务这些传统意义上主要由女性完成的工作,就仍然符合人们对女性的社会期待,能够唤起道德与法律对这些“柔弱女子”的同情。而法律是人类社会互动下的产物,人类则是具有情感的理性动物,故法律机制的考虑与设计无法脱离人民生活所需的情感诉求。张丽卿:《台湾死刑制度现况与政策建议》,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680页。 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女性犯罪的特点与公众的道德情感,即使其罪行极其严重,也仍可以依法从宽处罚,不对她们适用死刑。但如果她们的恶行彻底颠覆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应扮演的“妻子”“母亲”“女儿”“照顾者”等角色时,后果则会大相径庭。例如,与他人通奸而杀死自己丈夫,为了报复丈夫而杀死继子,为了提早拿工资而杀死自己照顾的老人这类女性罪犯,与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女性形象严重背离,并不具有女性犯罪的明显特征。这些女性犯罪人犯罪动机之卑劣,犯罪手段之残忍,甚至远远超过男性犯罪人。此时,人们就不会再将这些犯罪人视为值得同情、怜悯、宽恕的女性,从而给予她们刑法上的任何优待。因此,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女性犯罪人,只有在严重背离其社会性别、损害公众对其扮演的社会角色认知时,才能考虑适用死刑。不满足这一条件的,原则上就不能判处死刑。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坚持这一标准会导致国家通过刑事制裁强制要求妇女必须符合“恪守妇道、中规中矩、贤妻良母”的社会期待,既人为制造了女性内部的歧视,也严重违背了刑法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笔者认为,死刑不仅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刑罚,同时也是社会自我保护的一种工具,意在惩罚严重侵害法益和破坏整个社会价值的行为。女性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违背自己社会性别的犯罪行为,与作为死刑裁量因素的“情节严重”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是判断“罪行极其严重”与否的重要参考指标。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死刑适用的实质标准不但要求行为的客观危害性达到了最高程度,还要求行为人的主观非难性也应达到最高程度。在不法侵害层面,“邪恶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更大,主要原因在于其违背了社会公众对其性别与角色的信任,在犯罪危害结果之外还增添了背信的因素。例如,“恐怖保姆”何天带残忍杀害自己照顾的老人的行为不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还严重破坏了社会普通公众对女性保姆这一代表着“善良体贴”角色的认知,对公众的心理冲击更大。“犯罪是伴随法益侵害的社会现象,多多少少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如同向社会这个水池投掷石块一样,如果石块越大,波纹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如果石块相同,那么,投掷力量越大、波纹越大,反之则越小”。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页。 由于该案,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聘请保姆时进行更慎重地思考与更全面调查,从而在生理与精神上增加额外的成本,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成本的提高。这种代表着普遍民意的非规范性评价,无疑会间接影响法官对该案的定罪量刑,乃至是否判处死刑。
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应在量刑中予以考虑,否则就会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多个司法解释或立案标准中都明确规定了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并切实反映在大量的司法判决之中。如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发布的“许红涛故意伤害案”,在“典型意义”中明确强调:“案发后,许红涛的近亲属及村民代表均要求严惩不务正业、打死生父、违背人伦道德的‘逆子”,因为其行为严重背离了尊老爱幼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5日第3版。 而严重脱逸了社会性别的故意杀人行为已经超出了故意杀人的常态,故将背信等构成要件之外的附随结果作为加重行为人刑罚的情节就不属于重复评价或间接处罚。
至于对主观非难性程度的判断,应当结合行为人的犯罪故意、犯罪目的、犯罪动机、责任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毫无疑问,“邪恶女性”通过逾越其性别界限的行为,践踏了社会大众对自身性别角色的构建与期待,在道德、法律和社会等多方面都体现出较强的人身危险性,标志着其主观上的反社会性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她们的犯罪行为严重冲击了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完全可以在客观违法“罪大”的基础上被评价为主观罪过的“恶极”。此时,适用死刑不但是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的报应,也是对社会伦理观念的维护。此外,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说,敢于逾越自己社会性别的女性的再犯可能性会更大。这是因为法律的实施在通常情况下都不是依赖法律强制的威慑,而是更多地依赖其他非正式规范。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会去杀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恐惧法律的制裁,而是因为这一行为从根本上就和他们的道德观念及其一般原则相冲突,在其内心就被断然否定;而对于那些真正的杀人犯,一旦观念冲破道德和一般原则构筑的藩篱,就很少会因为单纯恐惧制裁而中止实施犯罪。参见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3页。 那些从内心否定了社会对自身性别设定藩篱的女性杀人犯已经完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再次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显然要比普通的女性杀人犯大得多,故从预防刑的角度出发也理应重于后者。
综上所述,与未破坏其社会性别的女性罪犯相比,“邪恶女性”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主观恶性更大,应受谴责的程度也更高,故受到更严厉的惩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一做法体现出对不同主体的区别对待,非但没有歧视色彩,反而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笔者非常赞同美国学者的观点,即使性别因素可能导致死刑适用中的歧视,也是一种积极的、应当被允许的歧视——无论如何,这一做法有利于女性被告人,不失为削减死刑适用的有益尝试;如果对男女罪犯适用不同的死刑标准这一歧视终将不可避免,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彻底废除对所有人的死刑适用。
Abstract:In American judicial practice, female offenders who are judged and executed by death penalty are far less than male offenders. The serious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has aroused more and more concerns and fierce debates by American scholars, who seek the causations from two aspects of judicial system and public sensibilities. The “Chivalry Theory” and the “Evil Woman Theory” are proposed and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equal protection are deeply discussed. These researches can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n death penalty in China. The death penalty for female offenders should be strictly applied in China except for those crimes in serious violation of female social gender.
Key words:death penaltyfemale offencesfeminismevil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