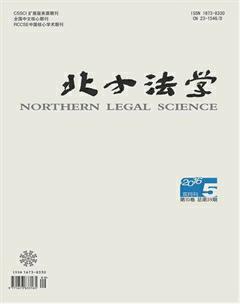法律的习俗正当性
唐丰鹤
摘要:对原始法、罗马法和普通法的考察表明,法律与习俗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长期流行的“发生学”解说和“法源论”解说不仅没有注意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习俗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意义。为此,需要在对西方习俗与法律关系历史传统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法律与习俗关系的正当性解说,即认为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若不符合习俗,法律便没有效力或减损其效力。习俗本身的正当性基础可以归结为习俗的两种内在品质:即习俗体现着人民同意与渐进理性。
关键词:实证法习俗罗马法法律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5-0025-13
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某个民族的过去相一致的律法,才能塑造这个民族的未来。①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习惯(usage),就其本质来说,不过是一些有规律的行为,或更准确地说,它指向的乃是一种行为的规律性。唯习惯有个体习惯和群体习惯之分,正是这后一种习惯构成了习俗(custom)的来源。因此,习俗乃是一种群体的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特质的习惯。正如康芒斯所说:“‘习惯,指的是个人的习惯……因为它只限于个人的经验、情感和预期;而习俗则是由那些集体地同样行动的其他人的经验、感觉和预期而来……习惯出于个人的重复,习俗则是出于团体的重复,虽则团体成员处于不停的变动中。”②
马克斯·韦伯正确地识别出习俗社会性的一面,他称它为一种“集体性的行动方式”。③在区分习惯与习俗时,他又区分了另外两个相关的概念:成规(convention)与法律(law)。④在韦伯看来,法具有一种正式的强制力,而成规却没有任何“物理的或心理的强制”,它简单的只是“构成该行动者所处环境的人们表示赞同与否这样的直接反应”。⑤但对于习俗与成规之间的分野,他却语焉不详,他直承,“习俗与成规的界线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前引③,第439页。 韦伯暗示,习俗只有经过成规,才能上升为法律(习俗法)。参见前引③。 所以,社会规则的连续体可以谱写成:
习惯(usage)—习俗(custom)—成规(convention)—法律(law)。参见林端:《法律人类学简介》,载[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修订译本), 原江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韦伯并没有揭示习俗是如何经由成规演化成法律的,他可能完全没有领会成规的规范性意义,他似乎完全是以一种社会学的外在视角来观察成规的,没有注意到成规具有一种内在的面向,即接受成规的群体成员对成规的一种主观态度。按照迈克尔·布拉特曼的“可共享的合作活动(shared cooperative activity)”理论对成规所做的说明,成规不仅有“共享合作的行动”,还有一种“共享意图”,即希望自己的行动与别人协同的意图。Michael E Bratman, Shared Cooperative Activit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01), 1992,pp331—336 也就是说,成规不是一种偶然的雷同,而是有意识的趋同,它必然具有一种内在态度,一旦有人违反,必定会招来群体的某种自察和随之而来的压力,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成规并不是没有任何强制,其可能诉诸群体舆论或态度冷淡,而法律则可能诉诸暴力机器。
成规与习俗间的关系确实不易厘清,更多的学者把成规理解为习俗的一种面相,“习俗与成规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涵指同一种社会实存。如果说两者存在差别的话,也只是程度的差别”。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如果把成规理解为习俗的一种面向,则这一面向无疑就是习俗具有某种约束力的一面。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则成规并不是习俗走向法律之路的一种跨越或飞跃,而应该说,习俗,本身就具有规则的气质,它与法律相去不远,“习俗对个人有一种强迫的效果” 。前引②。 所以,真正使得习惯向着法律转化的关键一步,并不是习俗到成规,而是习惯到习俗,因为正是习俗的社会性使得习俗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约束力。
到此为止的分析已经足以展示习俗与法律之间的微妙关系了,正是由于意识到此种微妙关系,学术界长期流行两种对于习俗与法律关系的解说,本文将它们称为“发生学”解说和“法源论”解说。
前者认为,法律是从习俗中分化出来的,人类社会的法律演变是一个从习俗到法律的过程。后者则着重考察法律内容的渊源,它发现,法律与习俗在内容上是高度重合的,习俗是法律的主要渊源,法律的主要内容均是习俗性的。
笔者认为,这些对于法律与习俗关系的解说虽然大致不谬,但却掩盖了法律与习俗关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隐藏在“发生学”解说和“法源论”解说内部的习俗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意涵完全被遮蔽了,而恰恰是这种正当性意涵才是对上述法律与习俗间微妙关系的最忠实而恰当的解读。另一方面,虽然绵延不断的自然法传统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然法与实证法的二元秩序图景,并且自然法作为一种“高级法”赋予了实证法正当性,但是,即使在自然法盛极一时的时代,都没有拒斥过习俗对于法律正当性的可能意义,实际上,在古代观念里,自然法、神的意志与习俗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法律正当性的基础。
基于这些考量,本文将宗旨落实在:经由对法律与习俗关系的历史考察,提出一种习俗与法律关系的正当性解说,并尝试提出法律的习俗正当性命题。
一、历史中的法律与习俗
(一)原始人的法律与习俗
原始人的法律与习俗被认为高度重合。对于这个问题,虽论说各异,但公允地说,要把原始人的习俗与法律相区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法律和习俗的界定。依马克思的说法,法律是国家和阶级出现后的事物,那么原始人就没有法律可言,如果认为法律的本质特征是高度组织化的暴力,那么原始人也差不多只有习俗。哈特兰德在1924年出版的《原始法》中断言:“原始法实际上是部落习俗的总体。”ESHartland, Primitive Law, London: Methuen, 1924, p5 他并不是说一切部落习俗都是原始法,而是说原始法差不多就是部落习俗,更准确地说,原始法是部落习俗中的规范性习俗。西格尔在《法律探索》一书中也主张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原始人生活在“习俗的无意识控制”之下。他认为,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和法庭,如果有法律和法庭,那就说明这不是原始社会。William Seagle, The Quest for Law,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1, pp33—69 另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看法,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对行为进行有序化的需要,也有解决纠纷的需要,而只要有这种需要,该社会总是会创造出某种产品来满足这些需要,这种产品在现代社会被称为法律。原始社会虽然诸事简陋,但是这种需要也存在,因而法律也存在。由此,他认为:“使用一个广泛且极富弹性的法律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无疑人们将会发现与在西北美拉尼西亚已发现的类型相同的新的法律现象。”前引⑧马林诺夫斯基书,第45页。 霍贝尔认为,“特殊的强力、官吏的权力和有规律性”构成了法律的必备要素,他对法律的定义是:法律规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规范,即如果我们对它不作理会或公然违反时,就会受到拥有社会承认的、有权这样行为的特权人物或集团,以物质力量相威胁或实际运用这种力量进行制裁。[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修订译本),严存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他考察了北极爱斯基摩人部落、北吕宋岛伊富高人部落、北美平原印第安人部落、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美拉尼西亚部落、西非黄金海岸阿散蒂部落等,指出即使在原始社会中,法律也是存在的。参见前引B15,第63—233页。 然而,抛开这些学者在法律与习俗的定义上的不同,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位原始法学者否认原始法律与习俗的高度重叠性。实际上,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是,即使原始法律是存在的,它也是从习俗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二)罗马法与习俗
罗马法与习俗的关系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分水岭是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的颁布。
首先,优士丁尼《国法大全》颁布之前。这段时期由于资料的匮乏,很难说清楚习俗法的地位。历史学家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声称,在罗马法的早期发展中,习俗是主要的法源,因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出现的《十二表法》,就被认为是对当时流行习俗的一种汇编和演绎。
但除了这一证据之外,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晚期和罗马帝国前期,习俗的地位都是不确定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也经历了几次翻转。他们一度认为习俗在法律发展中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但是后来又倾向于贬低习俗的地位,认为它至多不过是一种次要的法源,不过最近,他们又重新确认了习俗的主导性地位。David VanDrunen, Law and Custom: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mmon Law,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3, p16 扑朔迷离的情形即使到了罗马帝国后期,都没有变得明朗起来。彼得·斯坦因指出,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放松了对于罗马行省的控制,所以各省都采用了本地习俗; Peter Stein,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27 舒尔兹也认为,虽然帝国后期制定法增加,但是由于制定法在原理上对从前习俗的依赖,所以制定法的增加称不上是革命性的。 Fritz Schulz, History of Roman Legal Science, Clarendon Press, 1946, pp278—279 实际上,这段时期的许多立法其实都不过是对习俗的具体阐释,比如说,公元438年颁布的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收录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罗马帝国敕令和法律,就明确承认了习俗的法源地位。
范德吕嫩指出,在这一时期,无论习俗有没有在罗马法中取得超群的地位,由于这些原因,习俗必定会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一些杰出人士,比如西塞罗,就认为习俗是市民法的组成部分;其次,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学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罗马法学家一直认为习俗法和皇帝敕令都是罗马法的法源;再次,许多学者都认为,罗马法是保守的、理论化的、遵循传统的,其历史演进一直是平顺的、自生性的、有机的,这意味着对传统习俗的尊重;最后,一些罗马法学家认为,虽然皇帝的敕令是法,但是皇帝的权威却来自于人民,皇帝的权威并不是内在的,而是作为整体的人民外在地授予的,而习俗恰恰就代表人民的意愿,皇帝没有理由不遵守习俗。前引B17, pp16—17
其次,优士丁尼《国法大全》颁布之后。这段时期习俗的意义就很明显了。编纂《国法大全》的是一批熟悉历史的“编译者(compilers)”,这一称呼意指他们熟悉早期的规则、观念和习俗,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创造,毋宁说只是在汇编翻译已经存在的东西。实际上,编译者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古典时代的法律素材,然后将其收录进法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法大全》就是对从前材料的一系列征引。编译者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创作法律,而是拣选法律,他们要剔除原始素材中那些相互矛盾的地方,使得被拣选的材料尽可能地融贯。但是从结果来看,编译者的融贯性工作并没有做好,《国法大全》并不是一个非常融贯的法律体系。
《国法大全》明确承认了习俗的地位。《法学阶梯》有这样的说法:“所有由法律和习俗统治的人民” ,CJC, Inst, 121 这意味着在当时法律与习俗统治着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法学阶梯》是一部带有理论化色彩的讲义,当它说到“法律和习俗”时,它指的是成文法与习俗。其中法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分。成文法包括了法律、平民会议决议、元老院决议、元首的命令、长官的告示以及有学问者的解答。CJC, Inst, 123 不成文法则是对习俗的确认,“事实上,经使用者的同意确认的持久的习俗,扮演了法律的角色”。CJC, Inst, 129 所以,根据《法学阶梯》的解说,我们可以把罗马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律,它是成文法;一类是习俗,它是不成文法。而在《学说汇纂》中,习俗的重要性也被明确地承认,《学说汇纂》引用赫尔莫杰里安的话说:“完全由长期的习俗所认可并得到常年遵守的那个法作为公民的默示公约,也应该不亚于成文法一样被遵守。”CJC, Dig, 1335 接着又引用保罗的话说:“甚至,这种做法被认为具有极大的权威,因为它不需要写为成文法就被认可了。”CJC, Dig, 1336 也就是说,习俗如果不比成文法地位更高的话,起码也是分量相等的。结合《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国法大全》明确承认了习俗的地位。
(三)普通法与习俗
普通法在英国的产生是一个意外事件。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前,不列颠的法律发展与欧洲大陆基本同步,因为早期英格兰的统治者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实际上都是欧洲大陆人,但是诺曼征服在英格兰建立了中央集权,普通法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副产品得以产生和发展。参见高鸿钧:《英美法原论》(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7页。
普通法意味着一种为人熟知的东西,布莱克斯通沿用了传统的法律分类方法,他将英国市民法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前者他称为制定法,后者称为普通法。依布莱克斯通之见,不成文的普通法包括一般性习俗、特殊的习俗(只是用于个别地区)、某些以习俗为基础的特别法。Sir 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1:63—64
普通法是无法追忆的远古习俗,是“一堆古老的不成文的准则和习俗”,存在于民众的记忆中,它是一套“通过传统、使用和经验流传下来”的做法、态度、观念和思考模式。GJ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86, p5 1612年,爱尔兰总检察长约翰·戴维斯爵士说:“普通法不是别的,就是本王国的共通习俗。”JG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2 黑尔明确将普通法与王国的一般习俗相等同,称其为“习俗法”。Sir Matthew Hale, A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Printed For Henry Butterworth, Law Bookseller, 1713, pp3—4 布莱克斯通称呼普通法为“一般性的、古老的习俗”,称赞它构成了英国法的基石。Sir 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1∶73 公元871年—899年阿尔弗雷德国王在位期间,对当时的习俗法进行了汇编,公元1042年—1066年忏悔者爱德华在位时,又对阿尔弗雷德国王的法律进行了重新整理,奠定了后来普通法发展的基础。所以,正是这些英格兰古老而弥足珍贵的习俗,构成了普通法的实质性内容。前引B27,第48—49页。 而在诺曼征服之后,征服者首先进行的活动就是编纂和确认忏悔者的法律。前引B30, p43 梅特兰通过观察指出,他所处时代的许多习俗都已经成为了普通法的组成部分,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3, p184 波考克也说:“普通法一直被定义为不可追忆的习俗。在柯克和戴维斯之前的几百年中,借助于中世纪思想里常见的一个假设,人们就承认,英格兰法律是不成文法,法庭的功能是宣告本疆域内古老的习俗。”前引B30, p37 甚至是当代,迈登也指出无论是社会习俗还是行业习惯都在普通法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清晰可辨的角色。Stuart Madden, The Vital Common Law: Its Role in a Statutory Age, U ARK LITTLE ROCK LJ 18, 1996, pp573—574 即使是普通法的激烈批评者边沁,都承认普通法是不成文的习俗性法。前引B17, p11
但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习俗都是普通法,霍格和格伦登等人指出,法庭的引用成为决定习俗是否可以成为普通法的关键,参见 Hogue, A R, Origins of the Common Law, Liberty Press, 1985, pp192—200; MAGlendon, MWGordon & COsakwe,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West Publishing Co,1994,pp709—710 布莱克斯通认为是法官决定了习俗的有效性,能够被挑选出来作为普通法的习俗被认为应该是古老的、持续的、和平的、理性的、确定的和义务性的。Sir 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1∶76—79
二、基于习俗的法律正当性
通过对习俗与法律的历史进行梳理,不难看出法律与习俗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前文所述,
对法律与习俗的“发生学”解说与“法源论”解说其实都是关于法律与习俗关系的知识考古学,它们的论断可以凭借对古代社会的经验观察而获得证实或证伪。作为对法律与习俗关系的最为常见、最为盛行的解说,两者当然不乏合理之处,但是却可能会掩盖习俗与法律关系的其他面向,尤其是掩盖习俗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意义,为此,笔者提出一种关于习俗与法律关系的正当性解说。
其实,在传统的“发生学”解说和“法源论”解说里边,其实还包含着法律与习俗关系的另一面,即强调习俗对法律运作的支撑性作用。比如说,习俗被认为可以培养一种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习俗会限制和消解那些与社会生活相脱节的法律;习俗会弥补国家权力的不足,在一些国家权力覆盖不到的乡村和偏远地区,社会生活仰赖于习俗要多过法律。最重要的是习俗对法律正当性的赋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法律与习俗关系的正当性解说正是从法律与习俗的“发生学”解说和“法源论”解说中分化、发展而来的,或者说,是对两者言下之意的进一步发挥。
法律与习俗关系的正当性解说最基本的立场是承认习俗对法律的正当性意义,即法律正当性被认为出自于习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习俗为法律的权威提供着正当性基础,以习俗为基础的法律就是正当的。”胡平仁、鞠成伟:《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与习俗》,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美国著名法学家塔玛纳哈也指出,法律正当性除了自然法传统所提出的“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之外,还有一种“习俗/同意”的正当性,即实证法的正当性取决于它与“习俗/同意”相符合的程度。B Tamanaha, A General Jurisprudence of Law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 他总结道,实证法与习俗的关系有以下几个基本命题:(1)从历史上看,实证法最初是从主要由习俗和习惯控制的社会秩序中逐渐演化出来的;(2)实证法的内容来源于习俗与惯例;(3)那些违背习俗与惯例的实证法不会产生实效,或者不具有正当性;(4)习俗、习惯和惯例就是法律。前引B42, p5 显然,命题(1)属于“发生学”解说的范畴,命题(2)属于“法源论”解说的范畴,而命题(3)和(4)是正当性解说的范畴。
认为法律的正当性来自于习俗的看法是古已有之并一脉相承的一派观点。古希腊哲人虽认为法律的正当性来自于神意和自然,但是从来就没有忽视习俗的重要性。只不过,在早期希腊人那里,习俗也被认为来源于神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在强调习俗还是在强调自然或神意。比如“安提戈涅的故事”,安提戈涅的自然法是神的意志,因为它来自宙斯,所以它的“诞生不在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是不死的;没有人知道其在时间上的起源”;[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另请参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2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08页。 同时,这种自然法,即埋葬自己的亲人的律法,又毫无疑问地是当时的一种习俗。
在罗马人那里,习俗对于法律的重要性已经展露无遗,从《国法大全》的三个组成文件《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之具体论述来看,罗马法中的习俗主要发挥三个方面的功能:作为法律、废除法律,以及解释法律。首先,作为法律,《法学阶梯》说不成文法是对习俗的确认,事实上,经使用者的同意确认的持久的习俗,扮演了法律的角色。CJC, Inst, 129 《学说汇纂》也明确指出,“很有理由地,根深蒂固的习俗就像法律一样遵守,这就是被称为由习俗所组成的法。” CJC, Dig, 13321 习俗在什么时候被作为法律呢?一是当成文法欠缺时,被人民所“日用”的习俗应该被当作法律一样被遵守,《学说汇纂》引用尤里安的话说:“在不适用成文法的情况下,应该遵守由习俗和惯例确定的规范”;CJC, Dig, 1332pr 接下来又引用乌尔比安的话说:“在成文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长久的习惯通常代替法和法律而被遵守。”CJC, Dig, 1333 二是在成文法规定模糊时,对此,《学说汇纂》引用卡里斯特拉图的话说:“对于法律的模糊规定,习俗和长期以类似的方式做出的判决应该具有法的效力。”CJC, Dig, 1338 萨维尼在说到罗马习俗的法律效力时也指出,“如果制定法的表述不明确或模糊,或者一个法问题完全缺乏制定法的规定”,那么,习俗就可以被当作法律。[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其次,废除法律。《法学阶梯》指出,自然法是不可变易的,但是“各个城邦为自己制定的法,或因人民默示的同意,或因尔后制定了另外的法律,惯于经常发生变动”。CJC, Inst, 1211 在这里,“因人民默示的同意”就意指的是习俗。在《学说汇纂》中有这样的说法:“法律不仅通过立法者的表决而被废除,而且也可以通过全体默示同意的废弃而被废除。”CJC, Dig, 13321 即法律可以被习俗所废弃。虽然《法学阶梯》并没有说明法律要在符合什么条件时被废弃,但是毫无疑问,习俗的这种对于法律的废弃权是存在的,萨维尼举例证明说,罗马《十二表法》就通过裁判官告示被多次修正,而裁判官告示不过就是习俗;时效婚的有效性也被习俗所废除;询问之诉也同样如此。前引B50,第124—125页。
再次,解释法律。《学说汇纂》其引用保罗的话说:“如果对于一项法律的解释进行调查,首先应该考虑以前在同种情况下城邦适用的那个法:实际上习俗是法的很好的解释者。”CJC, Dig, 1337 在《法典》中,虽然习俗的角色显得比较隐晦,但是当它指出法律是习俗的模仿者(imitator)和维护者时(maintainer),CJC, Code, 852(53).3 它也暗示习俗发挥着某种解释法律的功能。
罗马人对习俗功能的看法代表了西方思想传统的一种态度,它被欧洲前期注释法学派代表伊尔内留斯所接受,后来又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了传承。托马斯·阿奎那写道:
“凡法律皆是出自于立法者的理性和意志……关于行动,人的理性和意志,是由言辞(speech)展现出来的,但是它也可以通过行动展现出来,比如说看一个人选择何为善并付诸实施。很明显的是,通过言辞,法律能够被改变和阐述明白,这表明了人类理性的内在活动和思想。通过行动,尤其是重复的行动——重复的行动构成了习俗,法律也能被改变和辨析清楚,有时甚至凭空确立了某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东西。通过重复的外在行动,意志的内在运动和理性的观念被有效地宣示了,因为当一件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它似乎只能被视为是理性慎思判断的结果。由此,习俗能够被当作法、废除法,以及解释法。ST, 1a2ae973
必须指出的是,托马斯·阿奎那在这里所说的法,是指他法体系中的人法(human law),而他所说的言辞(speech),其实指的是今天意义上的立法(legislation),人法能够被立法所改变和阐述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句废话,因为人法本就是人类凭着对自然法的领会和理解,并结合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所以,这段话真正令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阿奎那也赋予了习俗与言辞或立法差不多的地位,习俗被认为能够取代法、废除法,以及解释法。这番话也表明了阿奎那对于实证法(人法)与习俗的看法,这种看法与罗马人的观念基本一致。
首先,他认为,习俗能够被视作是法律,具有法的效力。阿奎那指出,不论是自由人还是服从立法者权威的人,都可以通过习俗来进行自我管理。阿奎那说:“产生习俗的人民有两种。如果人民是自由的,能够自己为自己立法,由习俗所表现的人民之同意,胜于官长的权威。实际上,官长之所以能制定法律,全因他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无权自己给自己立法,反而要屈服于主权者的权威,那么,盛行于人民中习俗,如果获得有权者的允许,便也取得法的效力。”ST, 1a2ae973 ad3 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习俗的法律效力,比如对于律师收费的额度问题,要根据具体业务、当事人情况,尤其是根据社会习俗来确定收费额;ST, 2a2ae714 再比如,对畅销产品的供应采取的措施要因时因地而异。但阿奎那指出,如果这些措施没有获得公共权威或习俗的支持的话,就是非法的。ST, 2a2ae772 ad2
其次,阿奎那认为,习俗能够废除法律。在特定的场合人们可以悖于法律而行动,这样的行动不能被视为是恶。当法律失效的情形屡次发生,根据习俗,就表明这样的法律不再是有效的。法律被习俗所废除,正如它当初被颁布一样自然。阿奎那说:“人为的法律有时不适当,因而有时候,即在法律不合适的时候,可以不按法律行事,这样的行为不能算是恶的。……这样的情形多了以后,则习俗证明那法律已经无用,这就等于正式颁布了相反之法律。” ST, 1a2ae973 ad2
再次,习俗可以解释法律。虽然阿奎那希望法律能够尽可能的清晰明确,但是他也明智地承认,法律解释有时是必需的。在他看来,立法只是对一般情形作出规定,碰上特殊情况,严格遵守法律的字面意义反而有害于公共利益,此时便要由官员做主,解释修正这条法律,ST, 1a2ae966 sed contra 而结合阿奎那论述的上下文来看,解释和修正法律的重要依据就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习俗。参见 ST, 1a2ae953; 1a2ae96 2; ST, 1a2ae973 ad2
阿奎那的法律与习俗观与罗马人具有非常明显的传承关系。笔者认为,这种法律与习俗观可以从法律正当性的角度来解释,当罗马人与阿奎那一致指出习俗对于法律的三大功能时,其实是在集中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习俗不仅具有效力,而且具有高于实证法的效力,习俗是实证法正当性的基础。当罗马人和阿奎那说习俗可以作为法律时,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习俗是有约束力的规范,这一点罗马人甚至比阿奎那表达得还要透彻,《学说汇纂》引用赫尔莫杰里安的话说:“完全由长期的习俗所认可并得到常年遵守的那个法作为公民的默示公约,也应该不亚于成文法一样被遵守。”CJC, Dig, 1335 接着又引用保罗的话说:“甚至,这种做法被认为具有极大的权威,因为它不需要写为成文法就被认可了。”CJC, Dig, 1336 习俗不仅是有约束力的规范,而且其约束力甚至要高于实证法所具有的约束力,由此,习俗构成了判断法与非法的标准。当罗马人和阿奎那说习俗可以废除法律时,他们着重指出的就是这一层意思。何谓废除法律?即当实证法的内容与习俗相悖时,实证法将不再有效,实证法将被剥夺法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这层意思不仅明确地表达在习俗可以废除法律的主张中,还隐晦地表达在习俗可以解释法律的主张中。因为对罗马人和阿奎那来说,解释法律其实特指的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官员如何结合个案实际来认定法律,这种对法律的认定不仅有澄清法律言辞和立法者原意之暧昧不明的地方,还有即使法律是清楚的,但是适用于个案会带来恶因而借助习俗废除法律的意思。
在此,我们不得不将习俗与自然法作对比。在自然法传统里,自然法同样被认为不仅具有效力,而且具有高于实证法的效力,自然法构成了判断实证法正当与否的标准,正是这样,才确立了自然法与实证法的二元秩序。同样,习俗具有高于实证法的约束力,习俗是判断实证法法与非法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说,习俗与法律构成了一种二元秩序,法律的正当性由习俗所赋予,这便是法律的习俗正当性命题。
法律若与习俗不一致,便要借机废除法律。这跟自然法传统的核心主张“恶法非法”何其相像!不同的无非是,当自然法传统说“恶法非法”时,它的判准是自然法或神意;而当习俗主义者说“恶法非法”时,它的判准换成了社会习俗。如果说自然法传统主张的“恶法非法”是一种神意或自然的正当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习俗主义者主张的“恶法非法”就是一种基于习俗的法律正当性: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若不符合习俗,法律便没有效力,不配称之为法。
这并不是一个牵强附会的结论,实际上,阿奎那就在罗马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明确指出了习俗的这种正当性判准的意涵。范德吕嫩指出,阿奎那赋予了习俗一种准宪法的角色:法律的效力存在于习俗所确立的边界里面,越界无效。前引B17, p41 作为一个自然法学家,阿奎那认为,法律应该符合美德、正义、接近自然、吻合习俗、因地制宜、必要、有用、表达清晰、服务于公共善。ST, 1a2ae953 obj1 对于实证法,阿奎那继承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看法,认为实证法必须与当前社会广泛流行的习俗保持一致,否则就会招致无效。在为伊西多尔辩护时,阿奎那说道:“法律应当与人类习俗保持一致,因为若不尊重他人的习俗,人就不能在社会上生存。”ST, 1a2ae953 实际上,在他看来,人法差不多就是习俗,人法就是习俗的一部分。
习俗对于法律来说,扮演着一个类似宪法的角色,违宪无效。这当然是一个颇为现代化的比喻,其实这里面表达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习俗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法律如果不是全部从习俗中取得全部的效力的话,也起码是部分从中获得了权威与效力,即获得了正当性。对于习俗的此种正当性意味,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一席话可与本文观点相互印证:一般的律法不会在它们被编纂的时候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中生出来那样全副武装地蹦出来……即便是新律法,也很少或从来就不是完全新创的,它们几乎总是要凭借并且以现有的习俗和公众意见为前提,后者或多或少与新律法相一致,人们的内心早已默默地准备接受它们了。世界上最专制的君主也无法强迫他的臣民接受一种绝对新式的律法,因为它可能违背了他们自然习性的整个倾向和趋势,触犯了他们世袭的观点和习惯,玷污了他们最珍视的一切情感与渴望。甚至表面看来最具革命性的立法活动,也总是有一些保守的成分来成功地确保某个共同体的普遍认可和遵守。前引①,第379—380页。
三、习俗正当性的基础
法律的习俗正当性认为法律的正当性源自于不可追忆的习俗,那么,我们难免好奇的是,习俗本身究竟有何魔力,能够提供这种正当性呢?或者说,习俗本身的正当性又得自何处呢?为此,我们必须进入西方思想传统中,对习俗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耙梳。
总体来说,西方思想传统对习俗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维柯对这一过程有很好的描述,他将诸民族的早期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的阶段、英雄的阶段和人的阶段。参见[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四卷“诸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第489页以下。 在神的阶段,人们通过共同生活培育出了习俗,这种习俗构成了当时的法律,这些习俗中很大一部分与神灵信仰直接相关,然而,即使是那些与神灵信仰无关的习俗,亦被认为出自于神。事实上,这个时代的一切制度与规范均被认为由神确立。所以,此一阶段,习俗当然是神圣的。第二个阶段是英雄时代,英雄在希腊神话中一直被认为是半神半人的物种,许多英雄,诸如阿基琉斯、赫拉克勒斯等都是神与人结合后的混血儿。这个时代的习俗同样被认为出自于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习俗依旧是神圣的。到了第三个阶段——人的阶段,情况发生了逆转。人具有了理性推理与反思的能力,他们的眼界也开阔了,通过战争或通商接触到了其他民族的神和习俗,在反对其他民族的神与习俗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民族的神与习俗。这个时代,随着智慧的增加,人们开始认为人性中有一种不变的自然(nature),与这种自然或本质相比,习俗显然是多变之物,是世俗之物,“今天和昨天,(自然律)在希腊和在波斯都是一样的……但是关于婚礼,或葬礼,则有数以百计的风俗。”[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由此也形成了这个时代自然与习俗的对立,自然成为高于习俗的范畴,后来到了苏格拉底时代,这种自然与习俗的对立慢慢演变成了知识与意见的对立。自然与习俗亦可称为自然与约定,参见[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3页;[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119页。
虽然习俗经历了一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其地位有所贬低。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习俗从来也没有下降到与立法等量齐观的地步,相反,主流的不言自明而又天经地义的观念一直要求立法吻合习俗,习俗被认为具有某些不同于立法的特质。实际上,由于下列两种理由,习俗被认为是自身正当的:(1)习俗被认为体现了人的自治与自由;(2)习俗被认为体现着理性。亦由于这种自身正当,它得以作为立法正当性的基础。
首先,习俗体现着人的自治或自由。要理解这一观念,首先需要了解西方思想史中被当作常识的另一个观念,即对西方思想传统来说,习俗意味着人民默示同意的东西,习俗是一种人民自己给自己的立法。习俗意味着人民默示的同意,这一观念在逻辑上并不难理解,因为习俗,不管是神灵启示的、英雄制定的、还是人民通过社会生活实践自然形成的,它既然为后来人所遵守,当然就可以视为是人民默示同意的。根据塔玛纳哈的考证,习俗意味着人民默示同意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习俗就是人们默示的同意;由于人们长期的使用,习俗深深地植根于社会”。Alan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Law,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4 《国法大全》中直接用“人民默示的同意”来指代习俗。罗马人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也被当作理所当然,成为当时社会习以为常的看法,“中世纪的法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习俗性规则对人们的约束作用归结为人们的默示同意”。W Ullmann, The Medieval Idea of Law, Barnes and Noble, 1969, p63 这种观念也被阿奎那所接受,甚至当作一种常识,所以他只是言简意赅地指出“自由人能够自己给自己立法,由习俗所表现的人民之同意,胜于官长的权威”。
习俗是人民默示同意的这一观念,后来又再次出现在普通法传统之中,普通法强调习俗是通过人们长期习用所形成的,也就意味着人民对于习俗的默示同意。布莱克斯通说:“在我们的法中,习俗的品性仰赖于它的长期被运用……在有记忆的时间内没有出现过悖反的情形。正是这让它有了分量和权威。”Sir 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1:67 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习俗的权威来自于它被人民的使用和接纳,也就是默示的同意。所以,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习俗意味着人民同意的观念已经是一种常识,正是因此,塔玛纳哈直截了当地宣告:习俗就意味着同意。前引B42, pp4—5
习俗意味着一种人民所默示同意或以行动来表示同意的东西,这种观念认为,习俗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期演化而生成的,习俗体现的不是或不只是神的意志,而是人的意愿。习俗,用一种更直白的话来讲,是人类通过长期试错、践行,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法律。既然如此,遵守习俗就是在遵守自己的话语,服从习俗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愿,所以,习俗反映的不是一种他律,而是一种自律。既然习俗是一种自律,所以遵守习俗或以习俗为基础的法律,就不是在限制自己的自由,而是在实现自己的自由。
所以,习俗体现着人的自治,就是说,习俗是人们自己为自己制定法律并运用这种法律来进行自我管理。阿奎那指出,两种人可能会发展出习俗:一种是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由人;第二种是服从立法者权威的不自由的人。对于第一种人而言,他们自己为自己所立之法正是习俗。对于第二种人而言,即便他们没有那么自由,他们必须服从主权者的权威,但是他们也仍然享有发展习俗来塑造社会的权利,“盛行于人民中的习俗,如果获得有权者的允许,便也取得法的效力”。ST, 1a2ae973 ad3 对第二种人来说,习俗同样是真切有效的,只不过相对于自由人而言,习俗是第二位的,他们必须优先服从主权者的立法,而对自由人来说,他们优先服从的是习俗。ST, 1a2ae973 ad3
通过这两种人的对比,习俗具有的自治、自由的意味更为明显。自由意味着服从习俗优先于服从立法,不自由意味着服从立法优先于服从习俗。这是因为,在阿奎那看来,立法体现的是主权者的意志,服从他人意志当然意味着自己的不自由;而习俗体现的是人民自己的意愿,所以,服从习俗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这意味着自治,意味着自由。
其次,习俗体现着理性。习俗是理性的体现,这一点同样可以见之于罗马人的思想。《学说汇纂》引用杰尔苏的话说:“一项规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出于错误被规定……它在类似的事情上没有效力。”CJC, Dig, 1339 萨维尼也解释说,“为了具有效力,习惯法必须是理性的。”前引B50,第126页。 阿奎那指出,习俗意味着重复的行动,而“通过重复的外在行动,意志的内在运动和理性的观念被有效地宣示了,因为当一件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它似乎只能被视为是理性慎思判断的结果”。ST, 1a2ae973 习俗,或者说不断重复的行为,为什么代表着一种理性的慎思判断呢?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必须对理性本身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毫不夸张地说,理性一词具有巨大的含混性,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只需要指出,习俗所体现的理性,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精英人物甚至是圣贤人物的个人理性或建构理性,而是意指社会或集体通过长时间实践、试错所积累起来的反映历代智识和集体智慧的渐进理性。对于这种理性要义,哈耶克有过集中的阐发,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一种人认为自己的理性是全知全能的,他们自认为可以知晓一切、计划一切、安排一切,他们对传统、历史和习俗持一种轻蔑的态度,认为凭着自己的理性,就可以重构社会,哈耶克称此为唯理主义的进路或建构理性的进路。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ules and Order (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9—10 持这种理性观念的人往往过于迷信自己的理性能力,他们所偏好的制度往往会是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计划、思想上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他认为,人类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够具备这样的理性能力,人类的知识和理性往往是极其有限的,“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必然的且无从救济的无知状态之中”。前引B81, p12 站在一种谦逊和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哈耶克指出,人类文明史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由大卫·休谟、马修·黑尔、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萨维尼、亨利·梅因、卡尔·门格尔、埃德蒙·伯克、熊彼特、卡尔·波普尔,当然也包括哈耶克本人等所开创和传承,前引B81, pp22—24 他们持一种渐进理性的观念,这种理性观认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个人的知识和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通过聚合众人的分散的知识和有限的理性能力,人类却可以获得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分散的知识和理性能力,甚至接近全知全能。渐进理性和知识虽不可能为任何个人所掌握,但是事情的奥妙在于,它可以体现在一些事物之中,比如说,市场就是众人知识的集合体,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商家可以知道所有消费者的需求,但是它总知道某些个别消费者的需求,当市场把所有商家掌握的需求信息集合在一起,市场就差不多等于知道了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相比于任何精英个人,才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者。再比如,习俗同样是历代人智慧、知识和理性的凝练,它比基于人为理性的制定法要知悉更多,也更能适合于该社会人民的真实需要。所以,渐进理性,就是历代人群体知识、智慧与理性的集合体,它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调研出来的,它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人通过真实的生活实践掌握并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理性。
渐进理性是一个历史传统,罗马人认为,习俗必须具有legitime praescripta或canonice praescripta,意即长时间持续时,它就隐含着这种渐进理性的观念;前引B50,第126—127页。 阿奎那说,重复行为反映了一种理性的慎思判断时,他指的就是习俗体现了渐进理性,重复行为,结合阿奎那对习俗社会性的论述,指的是社会中人民集体的重复和长时间的重复,这种重复行动,反映了群众集体的智慧、集体的理性。
当然,习俗体现着集体理性,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才表达得淋漓尽致。柯克认为,普通法与理性密切相关,“理性是法律的生命,而普通法不是别的,它本身就是理性”。Sir E Coke, Institutes1, sect21 如前所述,渐进理性与历史连续性、实践、群体智慧、合理性是紧密相连的,而普通法理论强调恰恰就是这些方面。在历史连续性方面,福蒂斯丘、柯克等人宣称,普通法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特洛伊王子登临不列颠,甚至自创世纪以来就存在,即是说作为普通法内容的习俗源远流长之意,它是历代智慧的结晶。参见前引B27,第45页。 言下之意是,这么多年代的持续运用(实践),说明这些习俗是合理的,是符合人民需要的。“在普通法思维中,历史连续性与合理性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经历时间考验的规则和实践表明了它的明智已经得到了民众亲身经历的证实。时间和许多个体的长期体验,确证了这些行为方式和价值的智慧和品性。”GJ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86, pp7—8 实际上,在普通法看来,只有长久连续地存在并被使用,才能证明该规则或习俗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参见前引B27,第56页。 这根本是因为,通过岁月积累下来的渐进理性,那些累积的岁月智慧,是任何一位精英的理性所可望而不可及的,马修·黑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与其冒险将自己的幸福和安宁托付给一个根据我自己的理论建立的王国,还不如选择根据某部法律而被幸福地治理了四百年或五百年的一个王国,虽然相比那部法,我更清楚我理论的合理之处。”前引B87, pp63—64 波斯特玛在评论时指出,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作为个体比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不要说任何个人,哪怕是整整一代人,其经验和智慧都不可能与经过无数世代累积起来并沉淀在法中的经验和智慧相提并论” 。前引B87, p64 所以,即使某个精英人物再聪明睿智都无济于事,戴维斯说,习俗是通过群体实践来型塑的,“一个已经做出的合理的行为被发现对人民来说是好的、有益的、符合他们的天性和取向(disposition)的,他们就会反复地运用它和践行它,通过这样的重复并扩散开去,它就会变成一个习俗” ,前引B30, p33 它反映了渐进理性,“就打造和维系一个国家而言,这样的习俗法是最完美、最卓越的,是无与伦比的”。前引B30, p33 柯克的这段话可谓是深得渐进理性的三味:
我们属于往昔,职是之故,我们需要前人的智慧。如果失去了先辈的启迪和赐予的知识,我们就会变得一无所知。我们在地上的时日只是往昔岁月和逝去时光的投影。在那里,法律借助于连续若干时代中最卓越之人的智慧,凭借着历时长久而持续不断的历练,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精炼而逐渐趋于完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的,要知道个体的生命如此短暂,即令将某一时代世间所有的智慧都装入某人的头脑,他也是力有未逮。因而可以这样说:optima regula,qua nulla est verior aut firmior in jure,neminem oportet esse sapientiorem legibu:任何人都不应当认为自己比法律更明智。前引B30, p35
习俗在时间长河中叠加众人智慧而形成,它接近于一种全知全能的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本来只能在上帝身上存在,渺小、有缺陷的、“朝生夕死”的人类,虽然不乏有人自命精英,却不可能达到或接近这种完全理性,实际上,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许多自命全能的人,其行为很快便显得无比乖张可笑,与理性毫不沾边,甚至背道而驰。渐进理性作为西方思想中的一个独特的传统,却在人性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接近完全理性的方法,这一观念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而习俗作为此种渐进理性的具体体现,无疑具有了内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结语
笔者在检视法律与习俗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法律的习俗正当性命题,认为法律的正当性来源于不可追忆的习俗。只有符合当时社会流行习俗的法律,才可能是有效的,一旦法律严重偏离了习俗的内容,习俗得以扮演一种准宪法的角色,宣告“恶法非法”,法律因而失去效力,也失却法律的身份。
法律的习俗正当性命题可以在罗马法与阿奎那关于习俗功能的看法中意会,因为当罗马法与阿奎那说习俗扮演了作为法律、废除法律和解释法律的功能时,他们的意思是习俗与法律相比,是一种仿佛可与自然法相比拟的“高级法”,实证法必须与这种“高级法”保持一致,它也正是从这种“高级法”中获得正当性的。
但是习俗毕竟不同于传统的自然法,自然法可以将自己的根基建立在永恒的理念和至善之上,也可以建立在上帝的意志或理性之中,自然法因此而具有了正当性。作为法律正当性之基础的习俗,它本身的正当性来自于何处呢?对此,笔者指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习俗,一直与两种观念联系在一起,即认为习俗体现了人的自治与自由、习俗体现着渐进理性。习俗正因为其自治性与合理性,而具有内在的正当性,并因此成为法律正当性的基础。
Abstract:Law and custom have close relations which have been proved by primitive law, Roman law and common law. However, popular interpretations of “generation theory” and “origin theory” have failed to notice and even concealed the justifiability of custom to law.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pecifically research on historic traditions of relations between custom and law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o propose justifiability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ustom and law, that is, the justifiability of law is based on custom, and the law should have no legal effect or the effect should be derogated in case of failing to conform to custom. The justifiability of custom itself can be concluded as two internal features of mass consensus and progressive rationality.
Key words:positive lawcustomRoman lawlegal justifi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