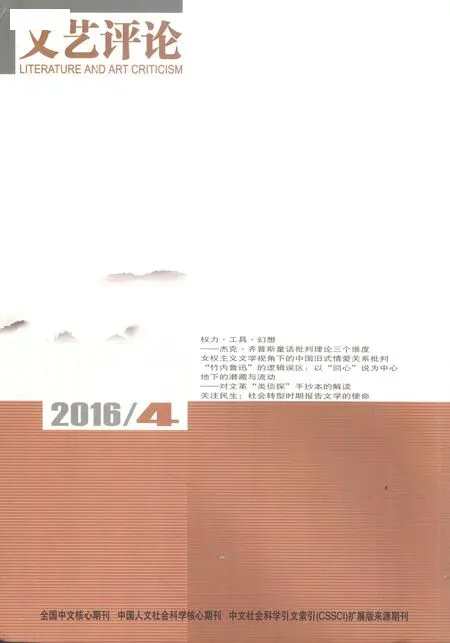形态与影响:论宋代山水田园诗
○于东新 张小侠
形态与影响:论宋代山水田园诗
○于东新张小侠
在山水田园诗——这一特别的诗体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与定型时期。宋代山水田园诗承袭了唐代李、杜、王、孟诸人,但它以独特的艺术形态,实现了山水田园诗艺术的发展与兴盛,并且这种艺术机制,从某种意义上,制式后代,规定了元明清山水田园文学的审美走向。
一、在情感主题的选择上,更贴近生活与政治
宋代的山水田园诗,最初继承的是唐人。宋初诗坛像王禹偁、梅尧臣、魏野、林逋等,其目标正像王禹偁所说的:“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他们所争的只是某些诗句的雕琢,如王禹偁的“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村行》)之所以被人称道,就是因为其接近杜诗。梅尧臣的《田家》《小村》等,也是如此。此后,王安石、苏轼等登上诗坛后,由于文人士大夫大多陷入“变法”“反变法”的争执中,演变到后来成为激烈的党争。这时的山水田园诗,围绕着农家的实际状况,有的夸耀岁丰人和,一片升平气象,而有的却诉说着农家破产的无限困苦。如王安石有《后元丰行》诗中说:“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苏轼的《吴中田妇叹》却道出丰年粮贱伤农的境况:“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秕。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这正如陈师道《田家》所云:“人言田家乐,尓苦人得知!”可见,北宋的田园诗不论写“农家苦”还是“农家乐”,均带着政争——政治的浓厚色彩。不带政治色彩的反而是一些纯写山水风景的诗,像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江上》,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惠崇春江晓景》《题西林壁》等,刻画自然景色生动形象,有的蕴含哲理。除此类小诗外,苏轼还有《百步洪二首》这样的诗章,气势宏大,颇具李白山水诗的气象。其它的,如孔平仲的《禾熟》:“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张舜民的《村居》:“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徐俯的《春游湖》:“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等等,这些山水诗,一般都不长,小巧玲珑而又自然有趣,与过去只将景色作为烘托出现的写法判然有别,这为后来杨万里、范成大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的山水田园诗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形态。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最为代表。杨万里从江西诗派的脱胎法、换骨法里走出来,不再一味地从古人诗句中去“点铁成金”,而是提倡“活法”,即如钱钟书先生所看到的:“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①这就使他的山水田园诗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生活,在一幅幅自然或生活画面里,让人感到亲切自然,又可欣赏到一种天然美,如《晓出净慈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时他的山水田园诗在不事雕琢中,时时流露出一种风趣与幽默。如他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桑茶坑道中》:“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以及《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在这些诗中,诗人把自己的山水田园体验与天真的童趣糅合在一起,机智而又风趣。他还写过农村民俗的诗,像《观小儿戏打春牛》《观迎神小儿社》《观社》《蜑户》等。杨万里还有一部分诗也写了“农家乐”,如《田家乐》《安乐坊牧童》《至后入城道中杂兴十首》《江山道中蚕熟三首》等,但他并不是闭眼不看现实的诗人,所以也有《悯农》《农家叹》以及《插秧歌》等反映农民疾苦与劳苦的诗,这两者并存的主题成了宋代山水田园诗共同的现象。可以说,杨万里的山水田园诗也如其它诗歌一样,形成宋诗乃至中国古代诗歌转变的重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活泼的写法,史称“诚斋体”。
范成大是宋代山水田园诗的集大成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指《诗经·豳风·七月》)、《怀古田舍》(陶渊明诗)、《田家词》(元稹诗)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②范成大的山水田园诗不仅仅是《四时田园杂兴》,另外尚有《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催租行》《后催租行》等反映了当时农民痛苦的诗章,但以《四时田园杂兴》最突出。不妨举几首《四时田园杂兴》为例: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其一)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蜒蛱蝶飞。
(其二)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其九)
(其十九)
《四时田园杂兴》透过作者独特的视角,把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和艰苦生活细腻地描绘出来,而且每首诗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用笔轻巧自然,使人如临现实生活的天地里。可以说,山水田园诗自范成大开始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与高峰。
杨万里、范成大之外,成就较大的诗人当属陆游。陆游为越州山阴人,他一生写诗主要抒发他的爱国情怀。但与此同时,由于仕途不顺,他前后几次回乡闲居,晚年又生活在乡村故里,这使他对乡村生活有深切的体验。终其一生他写了近千首山水田园诗,成为宋代山水田园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其山水田园诗自成一格,以再现农村真实的生活情景与当时农村的风土习俗为主要特色,如《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再如他的《散步至三家村》:
人情简朴古风存,暮过三家水际村。见说终年常闭户,仍闻累世自通婚。罾船归处鱼餐美,社瓮香时黍酒浑。记取放翁扶杖处,渚蒲烟草湿黄昏。
同类的诗还有《赛神曲》,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风民俗。陆游也有《农家叹》《记老农语》《秋获歌》等,可以见出他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和同情。他的山水田园诗贴近生活,形同生活的现实记录,诗风朴实生动而饱含生命的张力。因此,宋代的山水田园诗不同于唐人,具有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并且这种主题倾向成了后世山水田园诗的主要形态。
二、在体裁的处理上,更开放自由
宋代山水田园诗的艺术形态,不仅在情感主题上形成了特有的机制,其在体裁的选取上也有新的突破,它更开放更自由,大胆使用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即:首先大量使用词体形式来表现山水田园,打破了传统的山水田园诗的诗体范畴。像柳永的《望海潮》,以长篇慢词,赞美自古繁华的钱塘,描写杭州景色“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并且那里有“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且,柳永词开辟了把山水和地域以及都会结合起来以描绘山水田园题材的先例。柳永之后,苏轼的《浣溪纱》(山下兰芽短浸溪)、《浣溪纱》(簌簌衣巾落枣花)等,则运用短词小令,以轻松的笔触描绘山水田园,更让人耳目全新: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迨至辛弃疾,他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平乐·村居》等作品,则用词体来表现优美恬静的南方山水和谐趣横生的田园景象: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村居》
宋人这种以词体形式来描绘山水田园的作法,得到元人的继承并有新的发展,即开始以散曲的形式来拓展山水田园诗的领地,像贯云石的【双调·折桂令】(田家):
绿阴茅屋两三间,院后溪流门外山,山桃野杏开无限。怕春光虚过眼,得浮生半日闲,邀邻翁为伴,使家僮过盏,直吃的老瓦盆干。
此外,像乔吉的【双调·折桂令】(荆溪即奉)也写了江南水光山色。至于写农民劳苦的,也偶有所作,并且此种主题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像明人冯惟敏的【胡十八】(刈麦有感)、清人吴锡麟【南仙吕·掉角儿序】(吴兴道中观插秧)等,只是数量不多了。而用传统诗体来写山水田园的,相对于词、曲来说,因为缺少新鲜感,有退化、萎缩的趋势。不过从金代开始,后世也有值得一读的作品,像金赵秉文的《长白山行》《游华山寄元裕之》,元好问的《游黄华山》《泛舟大明湖》;元人白珽的《余杭四月》、宋无的《旱乡田父言》、方夔的《田家杂兴》、戴表元的《耕桑》、杨维桢的《庐山瀑布谣》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元人从宋人那里承继了山水田园诗歌艺术之后,随着蒙元帝国版图的扩大,在题材上他们逐渐突破了中原地域的局限,“嵌入了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经验”③,像耶律楚材写的诗有“阴山”(今之天山),如《阴山》《过阴山和人韵》《再用前韵》,如此详尽描绘天山的景色,前所未见。元朝建立后,许多文人如袁桷、萨都剌等人所描写的上都与塞外风光,也为中国古代山水诗增添了新的特色。这些显然是与宋代山水田园诗迥然不同的。
其次,宋人还开创了用组曲联章形式来表现山水田园的先河。如欧阳修的《采桑子》共13首,今举其中两首: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春深雨过西湖好,百卉争妍,蝶乱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兰桡画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间,水阔风高扬管弦。
这13首词,用同一词牌,每首的头一句都带有“西湖好”以突出诗人对颍州西湖的眷恋之情。这种联章体式与宋代流行的“大曲”有关,这种大曲在演奏歌唱时,前有“致语”,常常采用四六句式。除了这种联章体,还有在歌咏同一山水景色的主题时,从一个个侧面,写成一组,或四首、八首、十首不等(通常是八首)的写法。这起于宋代画家宋迪,他画有《潇湘八景》。沈括在《梦溪笔谈·书画》中说:“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④这八景画的是湖南潇湘一带即湘江流域八处名胜之地。宋迪的《潇湘八景》问世之后颇受当时文坛的欢迎,著名书画家、诗人米芾为之作序,并为每一幅画题写一首诗,诗僧惠洪也写过题咏《潇湘八景》的诗。翻检一下,后世诗人以“潇湘八景”为题的作品颇多,并且体裁上除诗以外,也有大量的词与曲。如元李齐贤的《巫山一段云·平沙落雁》就是词体,而元代曲体“潇湘八景”则更多,像马致远的【双调·寿阳曲】:
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四周山一竿残照里,锦屏风又添辅翠。
(山市晴岚)
夕阳下,酒旆闲。两三航未曾着岸。落花水香茅舍晚,断桥头卖鱼人散。
(远浦归帆)
南传信,北寄书,半栖近岸花汀树。似鸳鸯失群迷伴侣,两三行海门斜去。
(平沙落雁)
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
(潇湘夜雨)
寒烟细,古寺清,远黄昏礼佛人静。顺西风晚钟三四声,怎生教老僧禅定?
(烟寺晚钟)
鸣榔罢,闪暮光,绿杨堤数声渔唱。挂柴门几家闲晒网,都撮在捕鱼图上。
(渔村夕照)
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半飘柳絮。江上晚来堪画处,钓鱼人一蓑归去。
(江天暮雪)
芦花谢,客乍别,泛蟾光小舟一叶。豫章城故人来也,结束了洞庭秋月。
(洞庭秋月)
除了马致远的【双调·寿阳曲】外,鲜于必仁【中吕·普天乐】也用同一曲牌联章八首来咏潇湘八景,而同时代的沈和更是用套曲【仙吕·赏花时北】来咏歌潇湘八景。这种或用诗,或用词,或用曲的形式来歌咏潇湘八景的特殊山水文学创作,由宋人首倡,经元代一直到清朝,几乎代代有作,像明宣宗朱瞻基的《潇湘八景》是诗体,而康海的【南仙吕·二犯月儿高】(潇湘八景)却是套曲形式;清人王夫之作《潇湘小八景词》《潇湘大八景词》与《潇湘十景词》,则是词体。不仅如此,受宋人“潇湘八景”启发,从元代开始,描写各地名胜而用八景、十景名目的诗歌,简直到了层出不穷的程度,如元冯子振有散曲《燕南八景》、鲜于必仁有《燕山八景》,以致诸如西湖十景、金陵八景、姑苏十二景、金台八景、长沙八景、淮阴十咏、浦阳十咏、冶源十大景等等,越写越多。并且,值得玩味的是,明清时期,民歌俗曲中也开始歌咏山水名胜,像见于清人华广生《白雪遗音》中就有《济南八景》《西湖十景》以及春景、夏景、秋景、冬景之类的俗曲。最稀见当属一首歌咏蒙古地区风物的《蒙古》:
吐鲁番儿济木萨,不养蚕桑不种豆麻。春雨过山头,恰似嫩雪纷纷下。刮起风,飞飞砂如豆打的行人怕。春无芳草,夏有冰花。惨凄凄,奇巧的佳人拧辫双垂挂。冬雪天,如掌的鹅毛压倒了松树杈。
元明清诗坛还有写“十二月”、四季(春夏秋冬)以及专门写“渔樵耕牧”之类的诗,有的还与山水田园有关。此外,士大夫中还有归隐田园的,他们写了美化田园的淡泊宁静的诗,山水田园诗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品类众多,形式多样,与宋以前的单纯文人的山水田园诗已迥然不同,这也足以看出宋代山水田园文学的不凡贡献和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①②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5页,第312页。
③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④沈括《梦溪笔谈》[M],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卷。
[基金项目:内蒙古民族大学国家基金培育项目(编号:NMDGP1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