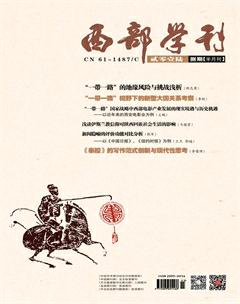康熙朝“理学名臣”对“道统论”的发扬
摘要:在清初政权儒学化的过程中,“理学名臣”注重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论”学说。围绕这一学说,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推崇程朱理学、编纂书籍、发展文教事业,重塑社会风气等。“理学名臣”对“道统论”的发扬,不仅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也进一步促使了清政权的儒学化。但同时理学名臣的活动也触及到皇权。
关键词:“理学名臣”;“真假理学”;道统;治统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清初有这样一类官僚群体,史籍称之为“理学名臣”,他们既是学界的一方领袖,又是深居庙堂的国之重臣,在清初学术与政治重建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前人对“理学名臣”的研究成绩斐然。①但这些研究多为个案研究,还缺乏有深度、综合性的研究,忽略了“理学名臣”身份的双重性,割裂了政治与理学之间的联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②围绕“道统论”学说的重新发扬,通过考察“理学名臣”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探讨他们在发扬儒家“道统论”学说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一、“理学名臣”
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始自秦汉。即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同时也是为帝国服务的官僚。[1]3明末清初政坛,涌现出这样一批官僚,史籍称之为“理学名臣”。“理学名臣”之名较早见于明代典籍。李贽所撰《续藏书》,其中有“理学名臣”之目,“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2]702其后又有不少以“理学名臣”为题名的著作出现,如杨亷撰有《理学名臣言行录》二卷。孟化鲤撰有《理学名臣言行录》。[3]268
清初“理学名臣”一词也屡见于史籍和清人笔记。清代范鄗鼎撰《理学备考》,“列有明一代讲学诸儒”,“卷一至卷六掇取辛全《理学名臣录》”。[2]877《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述及汤斌所做《汤子遗书》时说:“斌与陆陇其俱号醇儒,陇其笃守程朱,于陆王攻击甚力。斌则根柢姚江,而亦能持新安、金溪之平。故二人异趣同归。其生平得力具见语录中,其他著述亦皆有体有用通达治体。洵不愧国家理学名臣之目也。”[4]394《榆巢杂识》有“理学名臣”条:“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之端(鹏翮)、魏敏果(象枢)、熊文端(赐履)、汤文正(斌)、张清恪(伯行)、李文贞(光地),皆崇理学,践履笃实。”[5]14“理学名臣”在明代以及清初的学术史编纂过程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一类。但如何界定“理学名臣”这一概念,并不清晰,基本凭借编纂者的个人评判。从清人的描述中,“理学名臣”应该概括为信奉理学,在学术上具备一定的地位,同时承担着重要政府职务的官员。康熙朝“理学名臣”主要包括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张鹏翮、陆陇其等人。③
康熙希望通过树立“理学官员”为榜样,来拯救清初的人心、风俗。他说:“朕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主。”[6]552统治权力的归属与人心密切相关,理学正好可以统一民众的人心,束缚百姓的思想。康熙皇帝尊崇朱熹,笃信程朱理学,“非《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6]309正因为统治者的需求,一大批“理学名臣”登上历史舞台。针对“理学名臣”的历史地位,邓之诚认为他们多利用学术,以此谋求高官厚禄,并不能挽救日渐衰败的人心。他说:“康熙时所谓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稍有本末。余皆以此致身持禄而已。虽亦尊闽洛,而与其时名儒之在野者,不甚相涉。欲恃此数人转移风气难矣。”[7]104邓之诚之说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应看到康熙朝理学名臣在拯救道德人心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尤其注重恢复与发扬儒家之“道统”学说。
二、“理学名臣”对“道统”的恢复与发扬
“道统”学说,起于孟轲,经韩愈发扬,最终完善于朱熹。韩愈、朱熹皆认为上古有所谓“道统”,这个“道统”是被历代的士人加以传承的。“道统论”的本质是指谁继承了上古圣王的思想,谁对上古所传承的文化就有解释权。 “道统论”的问题,不单纯是学术问题,更关乎“治统”。杨维祯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8]487钱穆说:“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刃锯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9]357
正因为“道统”有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康熙帝非常重视“道统”,他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10]185康熙元年(1662),康熙帝“御制”黄帝陵文中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道、道统,昭垂奕世。”[11]387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率领礼部前往国子监举行临雍大典,宣布以“圣人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他说:“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莫能外也。”[12]康熙认为只有“兴道”才能“致治”,提倡“道统”是手段,维护“治统”是目的。康熙十六年(1678),康熙说:“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彰,讲明斯道。”[10]185康熙认为历代贤明之君应表彰《四书》,因为无论是“道统”还是“治统”都包含其中。康熙帝刊刻《日讲四书解义》自然属于贤明之君的范围,当然也有资格继承“道统”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御制”黄帝陵文中再次说:“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11]390历来学界把清初程朱理学的兴起归结为清初中央政权的推崇,其实程朱理学之兴起,正是因为康熙帝主张宣扬“道统”学说。“道统”说复兴在前,程朱理学之复兴在后。
“理学名臣”对“道统”的衰落痛心疾首,他们把这其中的原因归之于佛道二教。熊赐履说:“文教之日衰也……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13]220魏裔介《圣学知统续录序》:“自孟轲氏既殁,圣学晦蚀,火于秦,杂霸于汉,佛老于六朝,诗赋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继起,伊洛渊源灿烂可睹。其后,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14]117熊赐履、魏裔介认为朱熹之后,儒家地位衰落,佛、道二教盛行,最终导致“道统”不知所闻。
陆陇其认为明代阳明学对“道统”的失传起到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嘉隆以后“异端纷出,持身者,流入于魏晋;讲学者,迷溺于佛老”。[15]241因此要想发扬儒家的“道统”,首先要尊朱子,发扬朱子之学。陆陇其说:“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武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16]657又说:“道统之辨,遡其源则本之于洙泗”,“非周、程、张、邵、朱六子者崛起于宋室,则道统或几乎息”。又认为:“今之世当尊朱子”,“朱子者……孔子之道所自传也”。[15]242李光地也说:“朱子叙道统渊源。”[17]355理学名臣”提出要尊朱子,就要如焚书坑儒一般禁绝其他学派。陆陇其说:“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5]242魏裔介说:“欲定万世相传之道统,当绝异端相似之议。”[18]908
其次,发挥学校的教化功能,在学校中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康熙六年,熊赐履上奏:“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将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19]这里的正学即程朱理学。陆陇其说:“凡《太极图》、《通书》、《东西铭》、《皇极经世》诸书,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学宫,俾学者肄而习之。而又选敦厚有道术者,为之师表,使之不惟诵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则天下晓然。”[15]242
第三,“理学名臣”围绕“道统”,还编纂了一系列著作。熊赐履著《学统》、《宋道录》。魏裔介著《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表彰程朱理学。魏象枢,治学宗程朱,著有《儒宗录》、《知言录》。汤斌编《洛学编》,阐述中原儒学。张伯行以程朱为宗,著《道学源流》、《道统录》、《伊洛渊源录续录》等书,推崇程朱理学。李光地、熊赐履主持编纂《御纂朱子全书》,编篡次序即以“道统”为序,卷五十二至五十七,分为“道统一:圣贤诸儒总论、孔子、颜曾孟思、孔门弟子、周子;道统二:程子、张子、邵子;道统三:程子门人、杨氏门人、罗氏门人、胡氏门人;道统四:自论为学功夫、论自著书;道统五:自著书序跋;道统六:训门人。”[20]1
第四,“理学名臣”鼓吹康熙接续“道统”,并且把“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④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熊赐履向康熙进言,强调“道统”为用人行政的根本。他说:“俯仰上下,只是一理……人主……用人行政,原无穷尽。先将道理讲明,根本立定,不惑于他歧,不迁于异物,一以二帝三王为法,而后用人行政,次第将就施行,务期允当,不患不登斯世于上理也。”[21]118陆陇其也说:“天下之盛衰,自道统之明晦”,“居今之世而不明道统之所自,在上者何以为临民出政之本”。[15]241理学名臣认为道统即明,政治即明。人君治理天下,明道统是首要任务。
“理学名臣”极力宣扬康熙帝继承了“道统”,合“道统”、“治统”于一身。魏裔介说:“《御制序文》有云:‘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大哉!言乎道统、治统,我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18]688李光地也说:“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17]257又说:“皇上躬膺千载之道统,黙契列圣之心传。”[17]148
第五,“理学名臣”为道统、治统合一寻求理论根据。李光地结合河图、洛书来论证康熙帝合“道统”与“治统”为一的合理性。他说:
河图所蕴乃阳奇阴偶,二气流行之序,而其中数则太极也。洛书所具乃参天两地,方圆相包之形,而其中数则皇极也。太极者,周子所谓无极之真是也。皇极者,周子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立人极者是也。此羲、禹画卦、叙范所以为天启文明之运,而万世道统、治统之宗也。[17]171
李光地以经学中之河图、洛书为论证依据,他认为河图之中数为太极,洛书之中数为皇极。道统与治统分别对应着太极与皇极。河图、洛书是上古圣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因此,圣王要治国就要合道统与治统。
总之,“道统”论是康熙朝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康熙朝的“道统”说,是依靠“理学名臣”建立起来的。道统、治统最早由“理学名臣”提出,最终由“理学名臣”完善。他们引导康熙帝发扬道统,推崇程朱理学。康熙朝意识形态的完善与“理学名臣”密不可分。
三、“真假理学”之争
“理学名臣”对“道统论”的发扬,不仅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也进一步促使了清政权的儒学化。但同时理学名臣的活动也一定程度地触及到了皇权,威胁到康熙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因此,康熙依靠“真假理学”之争,打击“理学名臣”的话语权,把“道统”的解释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二十四日,康熙与张玉书、汤斌论真假理学。汤斌说:“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要躬行。”康熙则云:“朕见言行不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21]1089在这段对话中,康熙谈到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躬行实践乃理学之核心。康熙指出理学不单纯是学术上的争论,更重要是言行一致,这才是“真理学”,其他都是“假理学”。康熙所讲“真理学”应“言行一致”,强调“躬行”一面,他认为“凡读书人,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21]2222因此,康熙批评汤斌“在君前作一语,退后又作一等语”,[21]1758说熊赐履“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21]2222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21]2222康熙皇帝其实是指“理学名臣”为“假理学”。
理学核心在“道统”。“理学名臣”是“假理学”也就无权解释“道统”。康熙提“真假理学”的真意在于争“道统”。他提出只有言行一致才是“真理学”,实际是说“道统”与“治统”要合一。虽然“理学名臣”为重建和恢复“道统”、鼓吹康熙帝继承“道统”,出力颇多。但“理学名臣”利用对“道统”的解释权,掌握学术和政治上的权力是非常明显的。“士人一直在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解释权对治统实施批评和一定程度的干预。”[22]相比较而言,士人有德无位,而“理学名臣”有德有位,他们借助对“道统”的话语权,成为朝中掌握学术、思想的官僚群体。尤其是“理学名臣”这个称号,也意味着身兼“道统”和“治统”的双重身份。康熙帝也说:“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21]2222可见康熙帝对于理学名臣掌握道统是有所警惕的,由此,他才发起了“真假理学”之争,打击“理学名臣”的学术地位,“争夺对文化合法性垄断权”。[23]144
在康熙皇帝向“理学名臣”发难不久,其他官员也群起而攻之。康熙二十六年(1678),“大学士明珠即举出翰林院侍读学士德格勒即假借道学之号以欺世盗名”。[24]康熙三十三年(1694),李光地母亲去世,李光地任顺天府学政,没有去官丁忧,康熙皇帝下旨“李光地特行简用,著在守制”。[25]708这引来了清议沸腾,给事中彭鹏上书弹劾说:“光地敏罹母丧,……忽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弗请守制,清议沸腾。有绝不赴弔者,以谈理讲道如光地,为珪为璋,……倐忽瓦裂。”“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25]709彭鹏认为李光地作为讲道学之人,母亲去世,理应辞官去职,这体现了儒家的“孝道”。李光地没有这么做,证明了他就是个假道学,只是在嘴上言忠言孝而已。皇帝应该严惩李光地,把他作为“假道学”的典型。丁忧守制本为所有官员应遵守之制度,而彭鹏尤其强调李光地为讲道学之人,似乎暗示讲道学之人为宵小之徒。
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皇帝再次与朝中诸臣论及“理学名臣”之道德人品,康熙皇帝说:
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亦系讲道学之人。……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后十八年地震时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朕曰:“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道学之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又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汤斌)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熊赐履所著《道统》一书,王鸿绪奏请刊刻颁行学宫。高士奇亦为作序,乞将此书刊布。朕览此书内过当处甚多。凡书果好,虽不刻自然流布,否则虽刻何益。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今将此等处,不过谕尔等闻知。朕惟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之于心。[6]758
康熙指出熊赐履、魏象枢、李光地、德格勒、汤斌等人虽假托理学名臣之名,其实都行小人之实。背后攻击政敌,互相援引,口是心非,沽名钓誉。康熙尤其指出熊赐履《道统》一书,“过当处甚多”。熊赐履希望《道统》一书颁于学宫,热衷虚名而无其实。魏象枢与索额图意见不合就“挟仇怀恨”,希望杀之而后快。李光地与德格勒互相援引,成为政治上的攻守同盟。汤斌当面一语,背后一语。康熙皇帝把“理学名臣”的真面目都揭露了出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存治理天下之心的“真道学”,“朕惟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之于心”。康熙认为“治理天下国家之道”才是真的道学,康熙试图重新解释“道统”,认为“道统”的地位要低于“治统”。道学不应仅仅强调“知”,更应强调“行”,要重视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通过“真假理学”之争,“理学名臣”被逐一打击,失去了对“道统”的解释权。康熙皇帝针对的不仅仅为个人,而是“理学名臣”这个官僚群体。
“理学明臣”因特定的原因而登上政治、历史的舞台,一方面他们为扭转康熙朝之社会风气而奔走,一方面又大力鼓吹“道统论”。他们著书立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完善了儒家的的“道统”学说。他们尤其认为“道统”说与“治统”合一,为“道统”说的推行附以相应的政治依据。“道统论”的发扬,进一步促使清初政权的儒学化,并使得程朱理学得到较大的发展。程朱理学之传承就是围绕着道统建立的,因此得以获得大发展。“理学名臣”对康熙朝意识形态有话语权,又在政治上多有建树。这让康熙帝已经意识到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威胁。康熙帝毫不犹疑地对“理学名臣”加以限制和打击。康熙皇帝指出,“真道学”者应心怀治理“天下国家之道”,其他皆为“假道学”。“真假理学”之争的本质是“道统”之争。康熙朝的官僚,已经失去传统士大夫的高贵身份,只能屈从于皇帝对于理学观点的解决。康熙皇帝不仅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同时也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地位。关于清初“道统论”发扬的这段历史,渗透着皇帝与知识分子之间关于思想上的冲突,并最终以皇帝的胜利终结。
注 释:
①程分队的《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余龙生,张文革的《清初理学 名臣陆陇其的治政思想评述》,《朱子学刊》2004年。常越男的《试析清初理学名臣魏象 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潘振刚的《康熙朝理学名臣 理学思想与政治事功初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
②参见高翔:《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王钟翰:《康熙与 理学》,《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史革新:《略论清朝前期理学的复兴、作用和影响》,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朱昌荣:《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 重建》,《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③“理学名臣”与“理学官僚”有区别也有联系。“理学名臣”主要指为信奉理学,在学术 上具备一定的地位,同时承担着重要政府职务的官员。朱昌荣认为“理学官僚”是指信奉 理学基本教义、思想并能够积极将之用以指导政治实践的官僚群体。理学名臣范围比较狭 窄,特指清初固定的官僚,可以说是高级官僚和著名学者的结合体。理学官僚范围比较宽 泛,他们不一定是著名学者。(参见朱昌荣:《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历史研 究》,2014年第3期。)
④理学名臣鼓吹道统、治统合一,从顺治皇帝就开始了。熊赐履为顺治皇帝所写碑文中说: “我皇考以道统为治统,以心法为治法。禀天纵之资,加日新之学,宜其直接乎帝王之传 而允跻于三五之隆也。”(熊赐履:《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经义斋集》卷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集部230册,1997年,242页。)
参考文献:
[1]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97.
[3]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皇朝文献通考[M].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5]赵慎畛.榆巢杂识[M].中华书局,2001.
[6]圣祖仁皇帝实录[M].中华书局,1985.
[7]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M].中华书局,1983.
[8]鳳凰出版社.全元文[M].凤凰出版社,2005.
[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0]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11]李学勤.炎黄汇典[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12]章梫.康熙政要[M].华文书局,1969.
[13]熊赐履.经义斋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魏裔介.圣学知统录[M].齐鲁书社,1996.
[15]陆陇其.三鱼堂文集[M].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16]陆陇其.松阳钞存[M].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17]李光地.榕村全集[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18]魏裔介.兼济堂文集[M].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19]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6.
[20]李光地.御纂朱子全书[M].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M].中华书局,1984.
[22]罗厚立.道统与治统之间[J].读书,1998(7).
[23](美)斯沃茨(Swartz, D).文化与权力[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4]王钟翰.康熙与理学[J].历史研究,1994(3).
[25]王钟翰.清史列传[M].中华书局,1987.
作者简介:王寅,男,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ZD20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