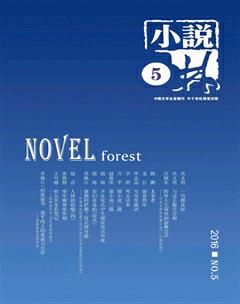奉军辅帅张作相
一
张作相、张作霖,一字之差,两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出自东北军的将领,张作相始终在张作霖的手下,好多人便认为他们是兄弟,至少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其实不然,张作相与张作霖名字差一个字纯属巧合,两人根本就不是宗亲。说他们是兄弟也有一定原因,张学良始终称张作相为老叔,因为张作相和张作霖拜过把子,是盟兄弟,张作相的发迹靠的就是东北王张作霖。
在旧军阀之中,张作相的名气不算很大,他没有独立山头,没有自己的地盘和队伍,始终傍着大哥,在张作霖的羽翼下发展,既没有罪恶昭彰的劣迹,也没有彪炳史册的战功,属于二三流的军人。先有老帅张作霖,后有少帅张学良在那儿罩着,张作相虽然在奉军中地位极高,极富声望,但一直是一个辅帅,第二号人物,相对次要的角色。
张作相人称辅帅,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一直担任副手,辅佐大帅东挡西杀,功勋卓著,后来又辅助少帅稳固霸位,令人尊敬;二是他字辅臣,一作辅忱,以字相称,倒也符合他的身份。
张作相1881年生于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比张作霖小六岁。他的祖辈是河北省深县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先辈逃难闯关东流落到了锦州义县。
张作相的父亲靠种田难以为生,养活不了家人,业余时间干起了“吹鼓手”,遇到乡邻有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给人家吹吹打打,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张作相兄弟二人,他居长,自小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家里也没有读书的环境和条件,到了九岁他还没有读过一天书,更没有个学名,父母觉得指望孩子读书致仕走科举的路根本行不通,但无论如何得让他识几个字,也许能借此改换门庭,不用天天再和土坷垃打交道。夫妻二人省吃俭用请来本村学馆的私塾先生要给儿子起个学名,以便让孩子读两天书。私塾先生得人钱财,也是顺情说好话,随口说道,官大莫过于宰相,这孩子就叫“作相”吧!没想到,真应了先生的话,后来张作相虽然没有做到相位,但是在军阀割据的东北,其地位也不在相位之下,除了张作霖父子,他也在万人之上,身居辅帅之位。后来张作相发达了,想起小时候的这段经历,作为回报,举荐当初那位私塾先生当了一个小官。
张作相限于家庭条件,没读过太多的书,私塾只上了三年,勉强识点字便辍学在家。年少,家贫,无事可做,他在村里除了帮助父亲下地干活外,还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泥瓦匠,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一半时间给别人打下手,生活勉强能够维持。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相的家乡遭受战乱。为谋生计,他到一位族叔家里帮工,和堂兄张作正的关系很好,两个人脾气相投,亲密无间。东北民风彪悍,械斗成风,当地乡里常有少年打架滋事,很可能他们小哥俩也不是什么老实孩子。他的堂兄有一次事牵斗殴,被仇家诬告进了大狱,后来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了,在回家的路上,被仇家堵上一顿暴打,性命垂危。堂兄临死的时候,嘱咐十六岁的张作相一定要为他报仇,这句话,张作相牢牢地记在心里。
张作相为了防止仇家杀人灭口,离家出走,流落到了奉天(沈阳),那时的他生活无着落,靠打短工、当瓦工勉强糊口,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饱尝辛酸,走投无路。有一回他剪了头,因为差了几文钱交不上,让人扣住一顿数落,多亏遇到一位好心人替他补交了钱,这才得以走脱。又有一回,碰上娶亲的大花轿,他凑上去看热闹,竟被当成叫花子给赶走。可见,那时的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整个一个沦落街头的盲流,受尽了人间屈辱。张作相最难忘的是,有一年的冬天,他往沈阳故宫跟前去看一种叫“大十面”的经咒石幢。因为没有钱买帽子,他就用一件单衣裹在头上防寒。在故宫外边巡逻的清兵看见他穿得破破烂烂,不容分说,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撵走。青少年时代受尽屈辱,遍尝冷暖,让张作相痛恨世道,发誓要反叛社会,走铤而走险、出人头地的险路。
张作相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心里却一直没忘记替堂兄报仇这件事。四年之后,二十岁的他潜回老家,在一天夜里联络好了几个兄弟乘着夜色闯入仇人家里,把当年打死他堂哥的凶手杀死,然后几个人出逃,落草为寇,拉杆子当起了土匪。张作相他们人少势微,自觉成不了大气候,一年以后他带着二十多人到新民府(今台安县)八角台村投奔了同样落草的张作霖。几支人马加在一起发展到了二百多人,名为“保险队”,其实就是为地主绅商保驾护航的“保镖”。张作霖这股土匪的势力日渐强大,不仅遭到周边其他匪股的忌恨,也成为官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打算将他们剿灭。
1902年,官府采取“化私团为公团”“以贼攻贼”“化盗为良”的政策,开始收编这些散匪。张作相从此随张作霖一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民府游击马队张作霖手下的哨官(连长),从此走上仕途。
1907年,满清盛京(沈阳)将军赵尔巽,将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张作相为骑兵一营管带(营长)。同年,与张作霖为伍的八个入伙头领按年龄为序结拜为盟兄弟,张作相排行最末。从此,他紧随在大哥身后,亦步亦趋,忠心耿耿,拼拼杀杀。
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相为二十七师步兵旅长。张作霖秉政之初,因重用才子王永江,引起绿林老伙伴盟兄弟汤玉麟的不满,两人反目。汤玉麟曾联合张景惠、孙烈臣、张作相等人带着枪觐见张作霖,要求罢免王永江,并以全体辞职相要挟。起初,张作相站在汤玉麟一边。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当发现汤玉麟由反王永江转向反对张作霖时,他马上调转枪口,站到张作霖一边,共同对付汤玉麟,直至汤被免职。张作相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很让张作霖感动,从此,张作相被张作霖视为忠心耿耿最可信任之人。
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任命张作相为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后改为巡阅使署总参议兼任二十七师师长和卫队旅旅长。翌年2月,张作霖为壮大军事力量,将原来东三省讲武堂改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特派张作相兼任堂长,同时还让他兼任奉天的警备司令,充分体现了张作霖对他的极度信任。也是在此时,张作相开始精心培养、照顾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并举荐他代替自己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一职。endprint
张学良在奉军的迅速崛起,暗地里得益于有他老爸在背后撑腰,明着在台前唱戏的却是张作相。在这一点上张作相深刻领会到领导的意图,摸透了大哥的心思,哪有当爹的不惦记儿子的,张作霖有好处自然时时处处想着儿子张学良,但是碍于情面,做事必须掌握好分寸才好服众。张作相从旁人的角度提携张学良,马屁拍得恰到好处。他在盟兄弟中排行第八,张学良称其为老叔,张作相为侄子说话也不失身份。晚年张学良说过,他在东北军能够短时间就做到那么高的位置,不是因为他爸爸特意的关照,全仗着老叔张作相的帮忙。当然,说到底,张作相之所以帮忙,看的还是他老爸的面子,张作霖想说的话,想办的事,都由张作相想了、办了,他这么做一举两得,父子两人心里都会感激他。
在张作霖的几个盟兄弟中,论资历、能力,张作相都不是最出色的,他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成为奉军的辅帅,第二号人物,关键在于他的为人。出身绿林,张作霖的几个盟兄弟都没有什么学问可言,也不需要学问,张作相超出常人的地方除了对张作霖的忠心不二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野心,甘愿在鞍前马后效力,无怨无悔,这种人最让领导放心,最能得到领导信任。对权对位,他不贪不占,总能保持头脑清醒。也许少年时经受的磨难让他满足现状、珍惜现状,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更高的志向,绝对忠诚主公。不与人争反而为他挣下了更多的人品,捞取了更多的好处。
二
在张作相从政的生涯中,至少有三次主动辞却职位的升迁,在东北军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19年8月张作相任第27师师长后,张作霖感到张作相离开自己身边,工作起来有许多不便。不久,就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副使。张作相以位高权重为由坚辞不就,于是改任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和奉天督军署两署总参议。
1921年初,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转任吉林省督军,张作霖让张作相去当黑龙江省督军,当即被他婉言辞却,张作相还建议让第29师师长吴俊升出任。他说:“论资历我不如兴权(吴俊升字),论年龄他也比我大。为表示待人公正,不徇私情,请让兴权先升。这对我们的前途和事业有好处。”
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特任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并将原热河都统姜桂题撤职,由奉系派员充任都统。张作霖拟派张作相继任,但张作相仍执意不肯,并极力推荐28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
张作相在官场最得意的时期是单独主政吉林七年之久,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出任吉林督军也是事出有因。
1924年4月,原吉林督军孙烈臣在奉天病故,这个位置一直被人视做一块肥肉紧盯不放,许多老派人物梦想着能得到这个肥缺。有的人跃跃欲试,暗中活动,但呼声最高的却是张作相。张作霖左思右想,交给别人不放心,推举张作相又怕他再谦让,于是特派儿子张学良去面见张作相,好言相劝,晓以利害,告诉他这一次必须当仁不让,否则别人乘机染指,后果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为了顾全大局才答应就任,前往吉林省任督军兼省长,同时兼任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一职。
放着高官不做,主动让给别人,张作相这一品质就是放在今天也相当难能可贵。他不过分看重职位的高低,顾大体,识大局,不计得失,对自己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张作相的所作所为,不仅得到了张氏父子的敬重,也得到了周围同僚们的好评,虽然他在张作霖的盟兄弟中排行最小,却后来居上,逐渐积累起很高的人望。
张作相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几次在关键时刻救张学良于水火之中。
1925年11月,奉军年轻将领、一向被张学良敬重信赖的郭松龄在滦州率十万奉军倒戈,通电驱逐奉军参谋长杨宇霆,请张作霖下野,拥护张学良主政东北。部队沿京奉路向奉天推进,当时奉天空虚,仅有张作相的第十五师驻守在锦、绥一带,双方展开激战。郭松龄部队是奉军的精锐,张作相的部队难以抵挡,节节后退,形势非常严峻。张作相整顿部队,死守锦州。在巨流河决战前夕,他召集师、旅、团长听取汇报情况时,对于前些日子在连山的败退,引咎自责,没有责罚任何一个失职的军官。谈到天冷衣薄,士兵出现冻伤时,他流下眼泪,使在场的官兵深受感动。
张作相的部下曾这样评价说:“从连山败退下来的军队,能再获全胜,官兵对张作相感戴心情是起着一定作用的。”经过这场激战,张作相部先占领新民车站,后又占领新民县城,郭松龄的总司令部由刘占武营接收。郭军除郭松龄夫妇外,参谋长以下人员及一、二、三军军长都当了俘虏。张作相马上命人前去妥为安抚,并亲自来到郭军总司令部对郭松龄部下的军官讲话:“在战斗中死去的袍泽已无法挽救,活着的官兵由我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明天张军团长(张学良)即刻到来,你们要听他的话。我去奉天向老将(张作霖)请求宽恕。有我一息尚存,就不会再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请大家相信我,听我的佳音。”
12月29日晚,张作霖在大帅府召集讨郭的善后会议。吴俊升、张作相、张景惠、杨宇霆等奉系重要将领出席。当时郭氏夫妇已被就地枪杀,部下均已被捕。主持会议的张作霖开口便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处理郭逆叛乱的善后问题。现在郭逆已经伏法,这也是大家齐心努力的结果……”
接着,张作霖向与会各位将领询问对叛军的处置办法,与他一起出道拜过把子的老派人物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等因平素仇恨郭松龄等新派分子,要求将郭的部属一网打尽,以除后患。郭的死对头杨宇霆坚决主张“根除首要分子”。而平叛功劳最大的张作相却力排众议,郑重提出:“郭松龄既已伏法,其他人员都是我们桑梓子弟,多年袍泽,应该让他们戴罪立功,一律免究,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宽大,以安郭军部下之心。”
张作相的意见,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他在会上竭力辩论达两个小时之久,大家还是杀声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张作霖对此也不置可否。张作相见形势十分严峻,竟在会场上当众失声痛哭:“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相杀了吧,我可不愿看见不幸的惨剧再次发生。”会场里的紧张气氛慢慢缓和下来,最后大家不得不默许张作相的建议,纷纷替他讲话,张作霖心里其实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诛杀叛将势必引起内讧,削弱奉军实力,这种结果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意见。张作相的意见应该说正中下怀,也说动了一些老派将领,于是张作霖决定对郭的部属“一律免究”。但是对儿子张学良纵容的叛逆行为,张作霖还是怒火中烧,气愤难平:“这次兵变,郭鬼子闹得我痛心极了,小六子信任郭鬼子比信任他老子还胜,闹到这步田地,几乎把我闹得身败名裂。当时我要抓着他,我一定把他处理啦,妈拉巴子,可把我害苦了,非毙了他不可!”老派人物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大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是张作相接着说:“汉卿年轻,受了郭鬼子的骗,罪魁祸首是郭鬼子。再说,倒戈部队垮得这么快,多亏汉卿在里面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才控制了郭的主力部队,他见了我痛哭流涕,不敢来见您老,他表示一定接受教训。至于其他将领多是胁从,咱们东北军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我看汉卿他心中有数,让他酌情处理吧!”最后,张作霖总算点了头:“那就让学良去看着办吧。”张作相见状,恐怕事后有变,立即叫通电话,请父子直接通话,这才避免了奉军内部一场自我残杀的悲剧,保存了一批骨干将领,稳定了奉军的大局。张学良知道会议情况后,对张作相非常感激,此后也就更加敬重他了。endprint
张作相的哭谏是为张作霖的霸业着想,忠心可鉴。他的忠厚宽大,为他在奉军上上下下赢得了更高的声望。
三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大帅府密不发丧。当时张学良人在北京,十三天后,才从关内化装回到奉天。这期间东北军群龙无首,奉军“老派”将领希望张作相上台,“新派”将领希望张学良上台。两人由谁主政,势均力敌,张学良的部队皆部署在山海关一带,黑吉两省不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他的优势是大帅之子,得到少壮派的拥护,而张作相素有“辅帅”之称,其资历、声望和人脉更为元老派倚重。
在张学良尚未回到奉天时,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并刻制印信,由奉天省议会议长亲自到张作相的公馆递交公推书和印信。张作相不为所动,坚辞不受,要求等张学良回到奉天以后再作决定。
6月17日,张学良化装返回奉天,除了着手办理父亲的丧事之外,立即召集东北元老们开会,研究推举东北新主的问题。张学良很理智,认为自己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不但不争权,反而三顾茅庐,极力恭请老前辈张作相出任东北保安司令,统辖东北的军政大权。
张学良先后三次派人将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公推书、印信等送到张公馆,张作相面对众人的信任和抬举,深受感动,热泪盈眶。但他没有被眼前的名利所迷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知道,自己只读过几年私塾,没什么文化,难于应付各种局面。而东北是人家老帅张作霖的天下,奉军是人家的张家军,自己有了今天的地位都是老帅的恩惠,这时候乘人之危独揽大权,太不仗义。张作霖死了由儿子继位,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况且少帅是他看着长大的,对自己一向敬重。于是他决定:坚辞不受,让贤张学良。并且表示要竭尽全力辅佐少帅,保境安民,稳定东北大局。张作相对劝他的人说:“老帅在世时,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可以说,张作相对张作霖一直忠心耿耿,始终认为东北是张作霖家的天下,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而且他也认为自己无力应付当时的复杂局面,张学良年少有为,新派势力雄厚,一定能够拯救危局,保持东北的稳定。
他当着大家的面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你不好好地干,我会在没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老辈中最有分量的人物,张作相的这一番话,等于一锤定音,解决了张学良的继承权问题。
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再次召开大会,张作相再次力推张学良。最后,大会决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宣誓就职,取得了东北的最高军政权力,开始了奉系军阀史上的少帅时代。张作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张学良心领神会且刻骨铭心。
事后,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张作相幽默地对人说:“不是我让贤,看我这名字就坐不了第一把交椅,是当老二的命,作相吗!只可做相,不能当王啊!”
张作相深明大义,从此,以辅帅身份继续辅佐张学良。
张作相没什么文化,心机也不是很重,如果不是他做出这种明智的选择,不管由谁继位,奉军内部必有一场大乱。
没想到张学良却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三年之后就将老爸打下的天下丢失殆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落敌手,当时的张作相正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沈阳的军政交由参谋总长荣臻代理。事发突然,张作相一夜之间成了光杆司令,他苦心经营的吉林也被参谋长熙洽出卖给了日本人。张作相虽派人到宾县另组了一个吉林省临时政府,但是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在吉林的家属子女以及在沈阳的子侄,经锦州撤离到天津。他的许多财产未及带出,张作相初到天津后,生活相对困难。张学良赠予生活费约十五万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933年张作相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华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兵团总指挥,于热河参加长城抗战。热河失守,张作相退兵古北口。张学良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张作相也随之宣布辞职,从此退出军政界,举家迁往天津,一直在英租界隐居,在家养花种草消磨时光。
以后,他的盟兄弟张景惠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当了汉奸,张景惠曾几次派人来找张作相,强行要他出山任职,帮助日本关东军干事,张作相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动摇,每一次都严加拒绝。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西安召开东三省讲武堂同学会,住在天津的原东北军旅长赵绍武要去西安开会。已下野赋闲的张作相把他找到家里,让他到西安后代他向汉卿问候,并嘱其告诉汉卿,当前形势复杂,以保存实力为上策,将来也好打回东北去。赵绍武到西安后,张学良接见了他,先问候张作相的身体如何?有困难没有?赵转达了张作相对他的嘱咐。张学良点头称是,告之:“一切请辅帅放心。”回津后,赵绍武向张作相汇报了西安见闻。张作相思考了一会儿说:“据我从军多年的经验,西安可能要出大乱子。”此话说过没几天,西安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从此,张学良被禁,张作相为营救他曾四处奔走。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利用张作相的声誉和威望,多次请他出来到东北任职,他都婉拒不受。十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北平宴请北方高级军政大员,张作相应邀参加。蒋介石将张作相安排在主宾座位上,并恭维他说:“抗战八年,你一个人在沦陷区,日本人多次引诱你,你没给日本人干事,这一点就十分可贵呀!”然而,无论蒋介石如何允诺,张作相仍是不愿与囚禁少帅的人合作,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任职邀请。1948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夕,曾派人催请张作相去台湾,几次送来飞机票,并为其家属准备了半条船的空位,张作相心念旧主,毫不动心。
1948年9月锦州解放,张作相在锦州家中处理财产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误俘。当解放军知道他就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要人张作相时,马上向他道歉,派人一直把他送到天津芦台火车站。张作相回家后,蒋介石派机派人催他到台湾去,张作相不为所动。1949年4月19日,张作相在天津解放三个月后因脑溢血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张作相没有张氏父子的野心和魄力,他一直主张以实力偏安关外一隅,无需入关争雄。他在主政吉林时期打出的口号就是:“固守关外,将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实际上他一直是这种思想,拥重兵固守关外,不参与内战,训练士兵,扩充实力,做稳东北王,然后再坐以待变。张作相的想法是很务实的,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和谋略,但是以稳重踏实著称,如果按他的思路经营东北,张氏的天下也许会相对持久。
张作相除原配夫人赵静宣外,还有六位姨太太。生有九个儿子和十一个女儿,在天津他有多处房产,最著名的是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上的故居,东抵湖北路,南临重庆道,西临澳门路,北抵郑州道。占地面积一千六百一十九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三百七十平方米,为砖混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建筑设计考究,墙面凹凸多变,镶有西式雕花,楼顶高低错落,屋顶平坡结合,风格别致。主楼两侧设有青条石台阶,内装修豪华,设有精致的壁炉,为一座西洋古典式建筑。
作者简介:张映勤,笔名梦石。1962年7月生于天津,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某文学杂志执行主编。
出版有《寺院·宫观·神佛》《中国社会问题透视》《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佛道文化通览》《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事》等十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
另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报告文学、学术文章等数百篇500余万字散见于内地及香港几十家报刊。发表及编辑的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