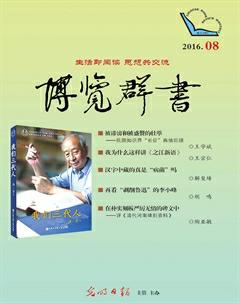再看“剥削鲁迅”的李小峰
胡鸣
·壹·
李小峰,北新书局的老板,如今知道他是出版家的人越来越少了,偶有提到李小峰的时候也都是因为他和鲁迅的版税之争。也正是因为他曾经克扣鲁迅版税一事,掩盖了人们对他作为一个出版家应有的客观评价。1925年3月北新书局正式创办,到1929年前后达到顶峰,这期间也是李小峰个人事业和声誉的黄金时期,而这与鲁迅的支持甚至“偏私”(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是分不开的。此后,鲁迅因北新书局长期拖欠版税与李小峰发生纠纷,后经郁达夫调解得到解决。虽然版税风波后鲁迅依旧将自己的书稿交北新出版,但无奈大势已去,在北新历经三次封门劫难之后,凭鲁迅一己之力已难以让北新重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公私合营,北新书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55年李小峰成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但他却从此被扣上了“剥削鲁迅”的政治高帽,终其一生都在不断的反省和检查中度过,直至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在出版界的功绩再无人提及。可以说,李小峰一生的荣辱都与鲁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鲁迅感激但也不无委屈,而这一切都要从一本叫《语丝》的杂志讲起。
“五四”运动后,孙伏园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当时北方的一些进步青年都把它当作发表作品的园地。鲁迅先生受孙伏园邀约也经常在副刊上发表一些短评杂感,其中著名的《阿Q正传》便是那个时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然而,孙伏园因为鲁迅的《我的失恋》三段打油诗被抽出之事与代总编辑刘勉己发生争执,终于闹到非要辞职不可的地步。事后,孙伏园想自己创办一种刊物,与晨报副刊抗衡,便跑到鲁迅那里寻求支持。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末》中说道:“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 “而我们这几个人总是要动动笔写写文章的,就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于是,《语丝》便诞生了。而李小峰当时不过是一个刚从北大毕业的“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末》)。“当时没有职业,恃译书为生,就多出些劳力”(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语丝》第一期印了2000份,出乎意料,几天内就销售一空,后来又再版七次,共印了15000份。渐渐的,收支相抵,再后来,略有盈余,于是李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孙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掰住了多睒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盈余来,每月请一回客。1925年3月,李小峰以《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为出版基础,在北京创立了北新书局(即北大新潮社的缩写,表示它和新潮社的传承),他负责组稿、编辑和出版,《语丝》也由北新负责出版。当时鲁迅为表示对北新的支持,将译稿《苦闷的象征》交给李小峰,作为北新书局开张时出版的第一种新书。
李小峰(1897—1971),字荣弟,笔名林兰,江苏江阴人。1918年入北大哲学系,其间参加新潮社,在《新潮》月刊中担任校对和记录。孙伏园去《晨报副刊》后,新潮社由他负责编印。1923年4月15日晚孙伏园带着孩子与李小峰一起去八道湾拜访鲁迅,这是李小峰第一次出现在鲁迅的寓所(《鲁迅日记》),从此拉开了与鲁迅一生交往的序幕。而两人现今可查的第一次通信却是三年后的11月13日,这封信篇幅很短,内容仅限《语丝》出版事宜,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期间两人交往很少。据《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亲自或派人访鲁迅123次,鲁迅则访李小峰80次,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两人见面频繁,关于编辑出版的诸多事宜都当面交涉,从而免去了通信的烦琐和不便。据李小峰的亲友描述,李小峰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很节俭,也很少交游,他不善交际,不像旧时代上海的出版商那样征逐酒肉,搞拉关系的应酬,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何满子,《记李小峰》)。也正是这点可爱之处让鲁迅对北新一直“偏私”,对小峰一贯关照。鲁迅致张廷谦的信中这样描述李小峰:“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字里行间流露出鲁迅对一个晚辈的关爱,其对小峰的认可也可见一斑。
在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支持下,北新书局迅速成长起来,出版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其中鲁迅的著作或译著共24种(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而鲁迅创作的初版权几乎全部归北新书局所有,这种殊荣一直持续到1934年。鲁迅自己也深知其中的意义,他说:“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为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绝不将创作給与别人。”而李小峰对鲁迅在出版方面给予的建议也都一一照办,诸如实价售书、开架售书、版面留天留地等。同时,李小峰给鲁迅25%的版税在当时也是最高的,而因为鲁迅对毛边书的偏好,北新书局还出版了许多毛边书。
·贰·
然而世事难料,就在北新书局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27年4月,当时入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查封北新书局并要逮捕李小峰。李小峰幸得苏联大使馆的庇护逃过一劫,而当时担任北京北新书局的账房李丹臣(李小峰的堂兄)却成了替罪羊。从此,北新书局的重心转移到上海。“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鲁迅,《我和〈语丝〉的始末》)这样,鲁迅承担了《语丝》的编辑工作。“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末》)终于在1928年,鲁迅将《语丝》的编辑工作交给柔石,而柔石主编了半年后也辞掉了这项工作,编辑工作又交给了李小峰。没有了昔日灵魂与光芒的《语丝》在1930年3月10日出满五卷后自动停刊了。鲁迅对《语丝》的废刊充满了惋惜却也无可奈何,其实早在北新转战上海后不久鲁迅就有此担忧,他在写给张廷谦的信中这样说道:“《语丝》若停,实在可惜,但有什么法子呢。北新内部已经鱼烂,如徐志摩陈什么(忘其名)之侵入,如小峰春台之争,都是塌台之征。”此时的北新已不是先生当初所认识的那个北新了,其主要原因是北京北新书局遭查禁后,李小峰本就心有余悸,而南京政府的文网又日见其密,这样,李小峰做事难免顾虑增多。加之1928年,他二哥突然去世,使李小峰不得不担下二哥的工作,终日忙碌在经营事务当中,没有精力再从事编辑工作,很多原本应由其亲自办理的事都交由其夫人蔡漱六和店员打理,且小峰本性木讷,不善言辞,时间一久,很多疏忽便埋下了祸根。而鲁迅因与北新关系最为密切,所受影响也最大。据荆有麟回忆:“先生曾言:北新书局欠他版费,已有八十万余元,可惜此款,多为北新老板李小峰之兄,拿去嫖女人,讨姨太太去了。”( 荆有麟,《鲁迅的生活和工作》)对于北新拖欠版税一事鲁迅一忍再忍,而李小峰长期拖欠鲁迅和郁达夫为北新编辑的《奔流》杂志的稿费最终成为此次版税风波的导火索。1929年8月11日,鲁迅致李小峰的信中辞去《奔流》的编辑工作,并于8月12日一早立即找张友松和党家斌同访杨铿律师,准备控告北新书局。在8月17日致张廷谦的信中说:“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也许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难说。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此事后来虽经郁达夫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但从此鲁迅与北新便有了隔膜。
其实,鲁迅对北新办事人对他的怠慢和小峰的糊涂积怨已久。1926年10月29日鲁迅致璇卿的信中写道:“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鲁迅做事认真,对自己编辑的杂志不想敷衍,自然对北新办事人员的马虎颇为恼火,而这种恼火在北新转移上海后越发加重。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了对北新的不满。1927年8月7日鲁迅致韦丛芜信:“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北新现在对我说穷,我是不相信的,听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1927年12月26日致张廷谦:“……但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即如《桃色的云》的第一版卖完后,只给我一部分,说因为当时没钱,后来补给,然而从此不提了,我也不提。”可见北新拖欠鲁迅之版税由来已久,但先生“不提”,我想除了对北新一贯的“偏私”外,小峰的“傻气”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份情谊让先生一再忍让,而小峰似乎并没有完全体会先生的忍让,依旧糊涂,依旧怠慢。这种情况在1928年年底至1929年年初达到了顶峰,以鲁迅这段时间给张廷谦的信为例:
1928年9月19日:“北新校对,是极不可靠的……凡对小峰所说,常无效,即如《游仙窟》,我曾问过两回,至今不送校。……北新办事,似愈加没有头绪了……夫岂有对于本刊负责记者,而不给其看新出之报者乎。”
1928年10月18日:“小峰似颇忙,不知何故。”
1928年11月7日:“小峰不知是忙是窘,颇憔悴,我亦不好意思逼之。”
1929年1月6日:“小峰老板事忙易忘,所以不以见示……北新近来殊胡里胡涂,虽大扩张,而刊物上之错字愈多矣。”
1929年3月15日:“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我因听见郑公振铎等,亦在排印,乃力催小峰,而仍无大效。”
1929年6月25日:“小峰久不见面,去信亦很少答复,所以我是竭力在不写信给他。……北新经济似甚窘,有人说,将钱都抽出去开纱厂去了,不知确否。倘确,则两面均必倒灶也。”
1929年7月21日:“北新书局自云穷极,我的版税,本月一文不送,写信去问,亦不答,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自己弄得遍身痱子,而为他人作嫁,去做官开厂,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矣。”
终于,8月11日鲁迅给小峰下了最后通牒,“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那么,鲁迅的这个“玩笑”为何不早不晚非要这时开呢?
·叁·
1927年10月抵上海后鲁迅开始了专职写作的生活。所谓专职写作就是说他的身份是自由的,而这之前无论是在北平教育部供职还是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书,鲁迅都是有单位、有组织的人,所谓写作其实是兼职,而单位不仅提供工作更发给薪水。辞去职务意味着没有了固定收入,身份自由的同时经济来源也不稳定了。如果说之前先生靠每月薪水可以勉强支撑日常生活的话,现在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常生活的每一笔开销都要自己去“挣回来”。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稿费和版税就成了关乎基本生存保障的问题。于是,北新书局拖欠稿费和版税的事情便不能“不提了”,在“开了一点玩笑”之后,北新答应按月摊还积欠的19122.334元,此款于1931年4月15日最终还清,新欠的则每月送四百元。可以说,经济原因是导致此次版税纠纷的根本原因,对于鲁迅自身来说,他也从不回避这个现实问题。
人先得活着,这是鲁迅思想的根本点。活着就离不开穿衣吃饭,继而就需要有收入来维持这穿衣吃饭,这就不难理解当稿费和版税成为鲁迅唯一收入来源时他与北新的版税纠纷之必然性了。鲁迅的这个根本思想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以《伤逝》最为典型。“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独立的经济、独立的精神才是爱情最坚实的基础。同样,经济生活也是其他一切生活的前提,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人先得活着”这句话的深意早在鲁迅幼年便因家庭的衰败而早早根植于他幼小的心里,而作为家中的长子,这种对家庭的担当和责任始终成为其行事、作文的准则,“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情感等,都受‘支配于经济”( 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面对穿衣吃饭等现实问题,洒脱终究是说说而已。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伴随鲁迅一生,他歌颂革命却不赞成无畏的牺牲,他辞掉了所有正式的工作却“计较”稿费和版税。一种“人得要生活”的单纯的生物学信念深深根植在鲁迅的思想里。面对生活,他“常抗战而亦自卫”。
除上述经济原因外很多其他因素也推动了此次纠纷的产生。北新书局虽是新文学重镇但毕竟是商业机构,李小峰虽有“傻气”但终究是老板。在北新书局南迁上海后,语丝同人各奔东西,维持书局生存的巨大压力使得小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于是,北新书局将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而为了赚钱,广告内容开始杂乱,甚至在《语丝》中出现了性病的广告。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末》中这样写道:“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 ,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末》)鲁迅对北新出版在思想上的日渐庸俗,在经历了惋惜、无奈后终于走向了愤怒,虽然风波最终平静落幕,鲁迅也依旧将他的著作交与北新出版,两人的通信较之以前反而频繁了,但通信的内容大抵只有谈钱和出版两件事,再无他事,可见彼此关系由亲到疏。而面对这种局面,李小峰也是无可奈何,与其说他背叛了与鲁迅在出版事业上达成的一致思想,不如说现实的商场规则战胜了他出版事业的高尚理想。此后,北新又遭两次打击,情况更令人担忧,鲁迅将自己的《两地书》《伪自由书》《鲁迅杂感选集》先后交由北新出版,助其渡过难关。无奈大势已去,“北新以社会情形和内部关系之故,自当渐不如前,但此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如何,而况我亦年渐衰迈,体力已不如前哉?区区一二本书,恐无甚效,而北新又需选择,我的作品又很不平稳,如何是好。”(鲁迅致李小峰信)鲁迅委婉地道出了他的无奈和苦衷,正所谓“花开花落两由之”。
1936年鲁迅逝世,此后李小峰一直在支付版税,直到抗战爆发。李小峰作为北新书局的老板,在新文学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北新书局与鲁迅也创造了一个出版机构与作家之间合作与纠葛的经典案例,见证了那个年代民间资本创造文化经典的奇迹。“文革”开始后,李小峰背负着“剥削鲁迅”的骂名含冤而死。但他在出版界的功绩从未被人们忽视和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