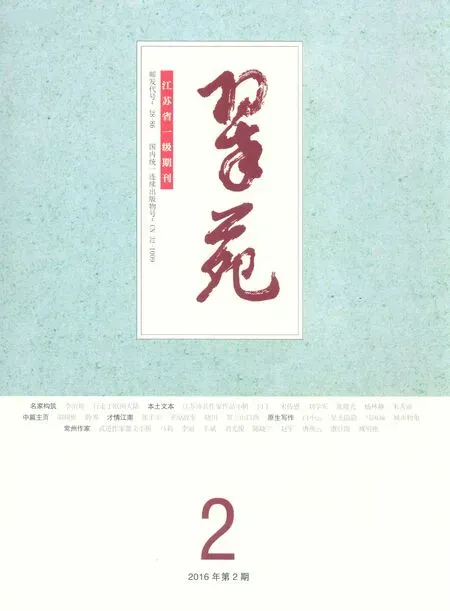年年有鱼
■虞红霞
年年有鱼
■虞红霞

虞红霞 ,1974年生于武进,从事教师职业。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武进区作家协会理事。在《翠苑》《常州晚报》《常州日报》《江海晚报》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曾获第二届武进文学奖。
年年有鱼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鱼,积自然之灵气,美味也。江南,鱼米之乡,佳丽之地。池塘一个接一个。“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优美隽永的意境,勾勒了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荷叶,莲叶下是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鱼,乃水中舞者。时而独自玩耍,时而三五成群,时而水草间吐泡,时而腾跃水面,自在潇洒!
我很喜欢吃鱼。小时候,父亲经常捉鱼给我吃,他有好几张渔网。有时,他赶到几里地之外的野河撒网捕鱼。野河东西约1000多米,沿河芦苇、茅草丛生,一般人都无法捕鱼。父亲却拨开青青茅草,选择一方圆池开始撒网捕鱼。只见他把大网抛向空中,网缓缓地飘落水面,稳稳地沉入水中。他和叔叔慢慢移动大网,待到池边时,再缓缓拉升大网。此时,大网波光粼粼,大鱼、小鱼尽在网中跳跃。父亲把大鱼拣出,抛入水桶,小鱼依旧放入河里。
黄梅时节天天雨。河水突涨,河里的鱼儿四处游逃,水田里、沟渠里,只要有水流处就有鱼。父亲穿着雨衣,赤着脚,奔走在泥泞中捕鱼。他把网安置在堤坝处,两眼紧盯着急速流动的水势。只要网里稍有动静,他就快速提起小网兜,白晃晃的鱼儿正欢蹦乱跳呢,他笑眯眯地把鱼儿放进水桶里,全然不顾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滴。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渔歌子》唐·张志和)老家的池塘一个连一个,池塘的鱼儿肥硕得很,夏日里,我们整日在乡野消磨,揪草摸鱼。
午后,阳光白晃晃地照射着河面,河面闪着耀眼的金光。我们 “噗通噗通”跳入河中,河岸上一溜的鞋子,五彩的衣裤和木桶、竹竿子。河面被我们搅得水花四溅,一浪推一浪波及岸边,不时有大小鱼儿跃出水面,稍大的孩子俨然捕鱼高手,拉锯式拉开大网,小不点只敢在岸边徘徊,摸得小鱼小虾,机灵的小鱼儿从手里滑脱逃溜,我们就开怀大笑。
红霞满天,我们满桶满盆而归。其实我们摸的鱼总是小个儿的,所谓的“猫鱼”。但大人们会用几条小鱼炖上咸菜,做又鲜又热辣的汤,羊奶一样白,就着白米饭,吃起来有滋有味。
父亲烧的红烧鱼特别诱人。他把铁锅烧得很烫,倒进菜油,放入生姜、大蒜等,待油烟起,他把洗净的鱼儿放入锅中,顿时油花四溅,贴着锅底的鱼皮顿时焦黄,再翻身煎炸,另一面也油汪汪、黄灿灿时,便倒入料酒,旺火烧至熟,开锅再放些许红糖,然后盖好用微火煨笃一刻钟,直至鱼汁浓稠翻滚,撒一大把早已准备好的蒜末等香菜,星星点点的绿漂浮着,煞是好看,屋子里鱼香飘溢。
一盆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鱼上桌了。我们兄妹紧紧盯着盘子里色泽鲜润的鱼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父亲一声令下,都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夹起早已看中的鱼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父亲则用一碟花生米下酒,母亲早已盛上一碗饭,就着青菜、萝卜汤吃了。鱼肉的味道实在鲜美无比,不一会工夫,一条大鱼的鱼身就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鱼头和鱼尾在盘中遥遥相望,中间是残破的鱼骨架。
鱼汤也是美味,母亲是舍不得倒的。拌饭吃,特别香。特别是冬天,放在碗橱里冻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成了鱼冻冻,我喜欢把鱼冻冻放在热气腾腾的粥里,看它慢慢融化,那鱼冻冻越来越小,融化的鱼汁四处流溢,在碗里开成褐色的花朵来,渗进碗底深处,直把一碗热腾腾的米粥吃成冷冰冰的。“好好的一碗粥,吃得清汤寡水的!”母亲就把我的粥倒进狗盆里,又给我盛上半碗米粥来。父亲吃鱼冻冻是大快朵颐的,他喝一口粥碗里就浅一层,大块的鱼冻冻一口就没了,看着都爽。那时,我就喜欢看着别人吃,这是我的小秘密,可乐着呢!
丰饶的水土养育了鱼米之乡,世代居此的乡民,靠着地广物富、天地之灵气,过着踏实、安静的日子。家宴上,他们必上的一道菜就是鱼,家常的有红烧鱼、猫鱼杂烩、鱼头笃豆腐等等,吃着鱼肉,欢颜道:“天天有鱼,年年有鱼!再上一盘鱼来!”
陋巷
穿过青砖黛瓦的围墙,走进青石板铺就的陋巷,心头漾起与世隔绝的恬淡。规则不一、随意摆放的青石板向每一位过往的行人诉说她深藏的故事。走在陋巷,耳边不时传来小伙伴“咯咯咯”的笑声,院子里“擦擦”的洗衣声,还有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青石板磨得圆润的棱角,是那般亲切温馨、宁静安详。
这是一条百米陋巷。这里虽比不上热闹的街市,却是小孩子喜欢的去处。
陋巷朝南的人家,沿粉墙砌上小型花坛。花坛里种上一些常见的鸡冠花、夜来香、茉莉等,淡雅素净的茉莉优雅地站立着,散发着阵阵淡淡的清香。鸡冠花,大红冠子,活如一只只骄傲的公鸡。三爷爷家的那几株夜来香长势葱郁,繁茂得很。暮色时分,它们绽放粉色、白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醇香飘逸,整条陋巷都浸在香海中了。
沿着灰白的院墙,丝瓜与葫芦藤蔓姿态婀娜地攀爬着,满墙的绿叶,星星点缀着黄花,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水粉画。小曼家的一枝梨树斜伸出院墙来,几只鸟雀也飞来了,它们悠闲地在陋巷上空盘旋,悠闲地栖息在葡萄架上,葡萄架下缀满了青色的葡萄,满是祥瑞丰收的景象。
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巷子里跳格子、跳绳、弹珠子……玩得不亦乐乎。大人把小桌子、小凳子搬到门口,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巷风缓缓地吹,夜来香的幽香弥漫整条小巷,空气里满是花香的甜味儿。
陋巷的东边有家早餐店,早餐店里供应大、小馄饨,面条,还有各式小吃:油条、麻花和铜鼓饼等。餐点是梁大妈开的,梁大妈黑黝黝的皮肤、大鼻梁,说起话来清清脆脆的。每天凌晨3点钟,她就摸索着起床了,做馅包馄饨,烧水磨粉搓面团,忙得不亦乐乎。东方显白,有零星顾客上门来吃早点了。有的一碗面条加一个煎鸡蛋,有的一碗大馄饨。每当面条上桌时,大妈就吆喝一声,那吆喝声还有调子,就如山里的姑娘唱山歌一般好听。碰到老顾客,大妈还会给她端上一小碟子花生米或炒得油汪汪的萝卜干。
下午时分,大妈就做些麻花卖,麻花吃起来“咯喯咯喯”的,特别的香甜。哪天能吃上一根小麻花,我就心满意足了。铜鼓饼是现炸的。小孩子嘴馋,没事就往梁大妈店里跑,有零钱就花上几个子买一个铜鼓饼,站在街角和好伙伴分着吃,你一口我一口,外脆里软,吃得十分地欢。口袋里没子儿时,就看大妈炸铜鼓饼。只见她用一个铜鼓状勺子舀一勺糊糊,放入油锅中,顿时油花“哧哧”地翻滚,眨眼间,糊糊就凝成了一块饼。有时,我们也帮大妈洗碗递水,大妈也会奖励一个铜鼓饼我们吃呢。
陋巷里有一位红鼻子爷爷,他家正在陋巷的拐角处,他开了一家杂货铺,以卖萝卜干为主。每天清晨,他早早地起床了,拆下一块一块木板门,放一张长桌子,然后摆上一袋袋各式的萝卜干,腌制的萝卜干品种很多,有红萝卜干、白萝卜干、干萝卜丝、五香萝卜干,还有各种品味的腐乳。旁边的架子上还有花生米、大米、油盐酱醋糖,架子下面是一坛子一坛子的酒,有黄酒、白酒。我经常跑去为父亲买些花生米和酒,偶尔买一根棒棒糖。
红鼻子爷爷在门口放置几张小板凳,吃过晚饭,门口便坐满了人。他们边喝茶边闲聊,从长矛造反聊到崇祯上吊,从秦始皇聊到末代皇帝,我特别喜欢听爷爷讲《三国演义》的故事,他给我们讲民间流传的《桃园三结义》,据说当初关羽和张飞瞧不起刘备,搬一张凳子在陷阱上,让刘备坐,刘备却安然无恙。张飞偷窥,瞧见井里居然有一条龙顶着刘备,吓得他俩连忙磕拜真龙天子。这一段精彩的故事我记忆犹新。
陋巷里还有一位钟表修理工,满脸络腮胡子。他戴着一副眼镜,就着日光灯把很小很小的螺丝装进盒子里。穿着脏衣服的修鞋师傅,一天到晚套着一件脏兮兮的褂子,整天拿着一只破旧的鞋子在缝补。买多味瓜子的大妈脸灰灰的,头发上总有瓜子壳,一双手很粗糙。只有理发店的黄师傅,整天把头发梳得发亮,我们小孩子笑道 “苍蝇都要掉下来了!”
如今,老巷斑斑驳驳,显得芜杂、陋旧、灰暗、潮湿。一些老屋翻新改造过,但在新楼耸立群里,更显得老屋的破败。陋巷,不仅衰老了,陋旧了,它沉默着,隐在这繁华喧嚣的尘世后面,反而显得清幽宁静了。
现今住在陋巷里的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爱上了陋巷,甘心在这儿住一辈子的老居民;另一种则是漂泊者,他们暂时蜗居着,并时时期待着飞出去的一天。
夜深人静,巷里的人家大都已熄灯就寝,看不清老巷的模样,那株栽了十几年的夜来香,却依旧浓郁,晚风拂过,花气袭人,让人倍感亲切。花开花谢几十年,她的香,她的魂,早已和陋巷融为一体了。
萝卜的滋味
母亲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平安”、“多吃萝卜,不劳医生开药方。”小时候,她就经常煮萝卜汤给我们吃。
儿时,我家屋后有一块菜地。母亲总要种上几垅萝卜,有红萝卜,也有大个白萝卜。稻子成熟季节,萝卜也差不多长成了。一个个鲜红的萝卜从泥土中羞涩地露出来,惹人爱。小孩子嘴馋,看着鲜艳的萝卜直咽口水,拔下一根来,摘去兔耳朵似的叶子,来不及洗净,剥下带泥巴的红皮,露出一段雪白。咬一口嚼嚼,凉丝丝、甜蜜蜜的。“秋后萝卜赛人参。”我们吃了一个又一个,母亲总是笑眯眯地说:“洗干净了吃呀!”我们便嘻嘻哈哈地跑开了。母亲的那份慈爱、暖意,总在心头荡漾。
稻子收割完毕,垅上的萝卜个个长得水灵、红鲜、饱满。这时,母亲便开始收萝卜了。她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拔、轻轻地放,就如侍弄孩子似的谨慎。一顿饭的工夫,垅上便铺满了红艳艳的萝卜,甚是喜人。我一边哼着儿歌一边把萝卜一个一个装进箩筐。母亲把两大箩筐的萝卜挑回家,铺放在院子里,她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急急上班去了。
母亲忙里忙外,既要耕种,还要上三班制,那份艰辛,我懂得。下班间隙,她一篮子一篮子把萝卜担去河边洗。蹲在码头上一洗就是一下午,腿麻了站起来跺跺脚,双手因长时间浸泡在水里,皮儿起疙瘩了。母亲洗萝卜时,我便也在一旁帮着洗。每逢人来便夸我能干,母亲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心里是喜的,她的眼睛、眉毛一直在笑,于是我也是喜的了。母亲将白萝卜洗干净,切成小手指宽窄的长条,置于大竹匾里,放在暴晒通风的地方晾晒,这样晒上几个日程,即可做成自制的萝卜干。
母亲腌制萝卜干的方法简单易学,跟平常人家没什么区别,只是她在腌制的时候,喜欢撒一些黑芝麻在上,她说这样腌制的萝卜干更加香甜。
冬日的早晨,母亲煮了一锅粘稠稠的香米粥,又从瓮中摸出一大把腌制的萝卜干。她把萝卜干切成细末,放油锅里翻炒,再撒上些许调料。这样,香甜脆嫩的萝卜就出锅了,喝粥时辅佐萝卜干,甚觉享受。那些清淡的日子是一去不返了。
我最喜欢母亲为我们包的萝卜丝团子了。萝卜去皮,擦成细丝。将白萝卜擦丝,肉绞成肉末,先将萝卜丝加盐腌制一会,过一小时后萝卜丝会出水,将水分挤干,然后加入肉末、姜末、蚝油、盐、鸡精拌匀,拌好馅备用这个是关键:猪油哦!萝卜丝团子好不好吃,放猪油就是关键了啊!一是香,二是包起来容易,汁水都凝固了,这样煮出来的团子么也水水的好吃。将糯米粉加适量开水揉匀,搓成长条,摘成一个个挤子,然后将馅包入、揉圆,就成了。舀一个萝卜丝团子,纯白如玉,用筷子夹一下,香糯细滑、清香袭人。咬一口,那股糯香沁入肌肤。真是人间美味。
长大后,菜市场里新颖别致的菜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的饮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没味没油性的萝卜便被人们所冷落了。偶尔也吃萝卜,但总觉得不是味儿。
可每次回家的日子总是喜悦的。入冬以来,母亲经常烧一锅骨头煮白萝卜汤,她把整块的肉洗净,放置锅灶里,和着大白萝卜一起煮。先后木柴猛火煮,约煮了一个多小时,空气中就弥漫着肉香。锅盖打开,热气蒸腾,清爽的萝卜味弥漫开。母亲把洗净的葱切成细末,撒在奶白色的汤面上,星星点点绿,让人垂涎三尺。经过一上午的煲汤,骨头酥松,油儿渗出,骨头上的肉酥软而不油腻,渗出的油星子浸透大萝卜,软松松的大萝卜便有了肉味儿。我夹一块大萝卜,抿嘴一咬,不油不腻,肉的精华便和萝卜融合一起了。这样的萝卜,在今天看来,虽然平淡,但我们吃着,永远有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人间有味是清欢。”那清欢永远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