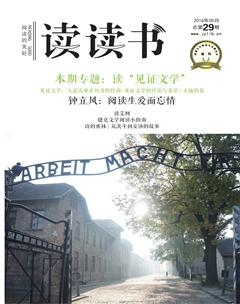“我一直认为一本好书比它的作者更具智慧”



《巴黎评论》
《巴黎评论》:是什么令您根据历史事件去写小说?
艾柯:与其说历史题材小说,还不如说真实事件的小说化更能真正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的历史。我也喜欢将教育小说的元素结合到历史题材小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总会有一个年轻的人物在成长,在学习,以及历经一系列的磨难。
《巴黎评论》:为什么直到48岁您才开始写小说?
艾柯并非像大家所想的那样这是一个大飞跃,因为甚至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在我的理论形成过程中,我已经在创作故事。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大多数哲学书籍的核心是在讲述他们调查研究的故事,正如科学家们解释他们如何获得重要的发现。所以我感觉一路以来我都在讲故事,只不过风格稍有不同而已。
《巴黎评论》:但是什么促使您感觉您必须要写一部小说?
艾柯:1978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想监督出版一系列由业余作家写作的短篇侦探小说。我说我不可能写侦探故事的,但如果写,它将会是一部以中世纪修道士为人物的500页的长篇。那天回到家,我着手列出了一张虚构的中世纪修道士名单。随后一个遭毒害的修道士形象突然浮现在我心头。所有的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从那个人物形象开始,它成了无法抗拒的推动力。
《巴黎评论》:您的很多小说似乎都依靠了富有智慧的思想。这对您而言,是否是一种自然的手法来沟通理论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差异呢?您曾说“对于那些不可以理论表达的,我们必须讲故事。”
艾柯:这是来自维特根斯坦(W-ffgenstein)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事实上关于符号学我写了无数的论文,但我认为与这些论文比较,在《傅科摆》中我反而能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你的某个想法也许不是独创的——亚里士多德总会早在你之前已经想到。但基于那个想法创作出小说,你能令其成为独创。男人爱女人,这不是什么创见。但如果你围绕这一思想终究创作出精彩的小说,那么借由文学的巧手,这个想法便完全成为一种新奇的见解了。我完全相信,在最终故事总是更为丰富多彩——在故事里,想法在事件中再现、由人物传达、并在精心雕琢的语言中擦出火花。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一种想法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个体时,它便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事物,很可能变得更为传神。
另一方面,矛盾可以是小说的核心。杀害老妇人是能引起人兴趣的。持着这个想法的伦理学论文会被判为不及格。在小说里它却变成《罪与罚》,这散文力作中的人物不能辨别杀害老妇人是好是坏,他的这种正反感情——正是我们在说的矛盾——成为了富有诗意的和引起挑战兴趣的事物。
《巴黎评论》:您说过写作一部小说之前您必先创造一个世界,随后“千言万语便会自然涌现。”您是说一部小说的风格总是由主题来决定的吗?
艾柯:是的,对我来说主要就是着手构造一个世界——住着受毒害修道士的十四世纪的修道院、在墓地吹喇叭的青年和受困于君士坦丁堡的骗子。而接下来的写作研究就是在为这些世界设定具体的条件限定:螺旋梯有多少层台阶?洗衣单上有多少衣物?一个任务要几个人执行?语句则会围绕这些限定展开。在文学领域,我感觉我们经常错误地认为风格只与语法和词汇有关。其实叙述风格也属于风格的一种,它影响着文段堆砌和情境创建的方式。以倒叙为例,它就是写作风格内的一种结构元素,而与语言没有丝毫关联。所以风格远比单纯的写作复杂得多。对我而言,风格之于创作,就如蒙太奇之于电影。
《巴黎评论》:您是如何努力去做以获得恰如其分的写作口吻?艾柯:一页文字我要重写几十次。有时候我喜欢高声读出一段文章。我对文字的口气有着惊人的敏感。
《巴黎评论》:您会像福楼拜那样,发觉只是创造一个好句子就已经很痛苦吗?
艾柯:不会,对我而言那不痛苦。我的确会反复改写一个句子,但现在有了电脑,我的文字处理方法改变了。以前,我手写完成《玫瑰之名》后,我的秘书再用打字机将它打印出来。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句子重写十遍之后,再拿去重新打印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碳式打印机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用到剪刀和胶水来处理。但是有了电脑之后,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某页文字检查十遍、二十遍,进行修改或重写。我想我们天生就难以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但如今修改完善是那么的容易,也许是太过容易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变得更为苛求。
《巴黎评论》:您的学术著作数量惊人,五部小说篇幅也不短。您这样多产有什么秘诀吗?
艾柯:我总是说我能利用时间的空隙。原子与原子,电子与电子之间存在大量空隙,如果我们通过消除这些空隙来缩小宇宙的物质,那么整个宇宙会被压缩成一个球。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空隙。比如今天早上你按了门铃,然后得等电梯,再过数秒才能到门口。在等你的这几十秒里,我就在思考自己正在写的新作品。我在厕所里,在火车上都可以工作。游泳时,特别是在大海里游泳时我创作了很多东西。洗澡时我创作的东西要少些,不过还是有的。
《巴黎评论》:您现在最大的乐事是什么?
艾柯:在晚上读小说。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不再信奉天主教,我脑中可能就不会有一个清晰柔和的声音向我低语:白天读小说是过于享受了。因此我白天通常都是写论文,努力工作。
《巴黎评论》:您一直因您在作品中展现的知识受到批评。一个评论家甚至曾说对于一个普通读者而言,您的著作的主要吸引力就是让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换句话说就是天真地敬佩您的炫耀。
艾柯:我是个施虐狂吗?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暴露狂吗?也许是。我是开玩笑的。当然不是。我一生这么努力,当然不是为了把知识摆在我的读者面前。我的知识确实影响了我的小说的复杂构成,但是最后是由我的读者来探索这些小说是什么。
《巴黎评论》:您认为作为一名小说家,您广为人知的成就改变了您对读者的看法吗?艾柯:作了这么久的学者,对我而言,写小说就像是一个戏剧评论家突然问登上了舞台,你以前的同事——那些评论家——盯着你。刚开始时这让我茫然不知所措。
《巴黎评论》:写了小说之后,您对一位作者能对读者产生多大影响的看法改变了吗7
艾柯:我一直认为一本好书比它的作者更具智慧。书能讲述作者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巴黎评论》:您现在是最畅销的小说家,您认为在全球这是否贬低了您作为一位严肃的思想家的名誉?
艾柯:自从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我收到了来自全球35所大学的荣誉学位。根据这个事实,我给你的回答是不会。在大学里,教授们对叙事和理论问的变化很感兴趣。他们经常会发现我的作品在这两个方面的联系,甚至比我自己认为的还要多。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向你展示一堵墙,上面都是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我的文章。
而且,我没有放弃撰写理论论文。我还是像一个在周末写小说的教授一样生活,而不是像一个在大学教学的作家那样生活。我参加科研讨论的次数多于参加国际笔会的次数。事实上,有人会反着说:也许是我的学术工作扰乱了我在大众媒体眼中的作家形象。
《巴黎评论》:纳博科夫(Nab0k0v)曾说:“我把文学分为两类,我希望是我写的书和我写的书。”
艾柯:那样的话我会把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Yonnegut)、堂一德里罗(Don DeLillo)、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保罗一奥斯特(PaulAuster)的作品归为前一类。不过总的来讲,我喜欢美国当代作家胜于法国当代作家,虽然由于地理原因我接受的主要是法国文化。我出生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处附近,法语是我学习的第一门语言。我甚至更了解法国文学而非意大利文学。
《巴黎评论》:那如果必须让你说,你觉得谁对你有影响?艾柯:通常我会回答乔伊斯(Joyce)和博尔赫斯(Borges)来让采访者无话可说,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有影响。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当然对我有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翰一洛克(John Locke)等等你能说出的学者都对我有影响。
《巴黎评论》:你在米兰这里的图书馆简直就是个传奇。你喜欢收藏什么样的书籍呢?
艾柯:我一共拥有大约五万册书籍。但是作为一个珍藏本收藏者,人类对离经叛道思想的偏爱让我着迷。所以我收集那些关于我不相信的主题的书籍,比如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kabbalah)、炼金术、魔法、虚构的语言。我喜欢那些说谎的书籍,虽然它们并不是故意说谎。我有托勒密的书,但没有伽利略的,因为伽利略所说的是真理。我更喜欢疯人的科学。
《巴黎评论》:在你的人生中,知识和文化给了你何种益处?艾柯:假设一个文盲在我这个年纪去世了,他的人生是单一的,而我还有拿破仑、凯撒、达达尼昂(d。Artagnan)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阅读,因为那是一种使人博闻强记,发展多样性格的理想方式。如果你多读书,那在你的人生结束之时,你就拥有数不尽的人生经历,这可是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极好特权。
《巴黎评论》:但是博闻强记也可以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就像你最喜欢的博尔赫斯的人物之一,《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 orious)里的富内斯那样。
艾柯:我很喜欢“固执克已,绝不好奇”这一观念。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将自己限制在某些知识领域里。你不能太过贪婪。你必须强迫自己不要学习所有事物,否则你将一无所获。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关于懂得如何忘记,不然,你确实会变得像富内斯那样记得三十年前见到的一棵树上的所有叶子。从认知角度上讲,找出你想要学习并铭记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巴黎评论》:对于那现场宣称小说已死、书籍已死、阅读已死的人,你怎么看?
艾柯:相信事物的终结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时代开始,我们就坚信我们的祖先优于我们。这项由大众媒体参与的日益激烈的闹剧总是使我心情愉悦、兴趣盎然。在美国不论春夏秋冬,总会有一篇关于小说之死、文学之死和读写能力之死的文章。人们再也不阅读了!青少年们只是沉迷于电子游戏!而事实是,世界各地都遍布着满是书本和青年人的书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书店、这么多去书店买书的青年。
《巴黎评论》:你想对那些散布恐慌的人说些什么吗?艾柯:一直以来,文化总会适应新的环境。或许会出现一种不同的文化,但是文化是不会消失的。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几百年是深刻变革的时代,充斥着语言、政治、宗教、文化的变革。如今这些变化的速度之快更是以十倍计算。但是激动人心的文化新形式会层出不穷,文学也不会灭亡。本文转载自“译言网”(译者为独眼一点五);本文转载过程中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