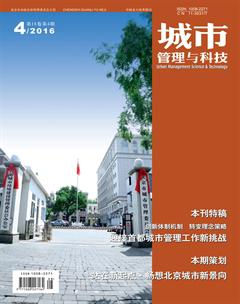城市:“人是人的最大乐趣”
张洪兴
“人是人的最大乐趣”,这句话来自一首留传千年的古冰岛诗。
当初,笔者并不理解这句话,直到后来开始研究城市形象,观察在城市中人们的活动规律和注意力规律。
什么是城市?有一种解释是,城市就是很多的人相聚的地方。想想也是。乡村田园是什么?是小桥流水人家,是田野森林庄稼,很难想像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城市,则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景象。因此,一般意义上,人们通常都是到乡村看景,到城市品人。
人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通常是人。所以,这就注定了人的一生最大的兴趣和乐趣就是人。人长有五官,通过眼、耳、鼻、舌、身感知外面的世界。而人这一生,对外界最大兴趣的感知,就是人,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需要观察别人,同时,也希望被别人观察。而在城市,则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深层需求。
笔者的家乡天津武清,沿运河边,政府近年来投资开发了一个郊野公园——“北运河休闲驿站”,每到周末,人流如织。这里有树有草,有河有船;有明媚的阳光,有徐徐的微风,有鸟语花香,更有人们的欢声笑语,确实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开发了一处专供人们露天烧烤的地方,水泥石桌古凳。但需要付费使用,笔者问了一下价格,每小时50元,但见那个区域已经没有空位了。还有人拉着一车烧烤器具在门口被保安拦住,悻悻而回。笔者估算了一下,人们呼朋引伴,租用一个桌子最少要用4-5个小时,光租金就要200多元,这要到稍远处的河滩去烤,也没问题,200多元还能多买几斤羊肉呢!可是,人们不。人们宁愿多花钱也要扎堆儿在一起。是挤在一起吃起来香?仔细想想,还真不是。
人们在休闲的时候,其实五官并没有休闲;人们在品着美味的时候,更需要感觉到旁人艳羡的目光。同时,人们也在无意识中,观察着更多周围人的举动:别人用的是什么炉子?什么炭?羊肉是不是煨过?他们在喝什么?谁差不多喝高了?是一家人还是几个朋友?彼此是什么关系?他们在聊些什么?他们烤的羊肉为什么闻起来那么香?那个美女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人吃独食的时候所能体验到的。所以,与其说人们是在花钱租一个烤位,不如说,是在“购买”与人相处时带来的种种乐趣。
以上仅是一例。推而广之,对于一个城市,最大的魅力其实是这个城市里的人。川流不息的人流,是城市流动的血脉,是城市富有生命力的象征。城市一旦失去人,就是一座死城,一片废墟。人们进了一个临街的餐馆,一般会选择什么位置坐下?通常会选择靠窗的位置。其原因大多是靠窗的地方明亮通透,窗外人来人往,人们点菜吃饭,间或朝窗外望上一眼,看一看世井百态,满足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作家贾平凹说过,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看人。“在地铁入口,在立交桥头,人的脑袋如开水锅冒出的水泡,咕噜咕噜地全涌上来,平视着街面,各式各样的鞋脚在起落……在街头看人的风景,实在是百看不厌。”城市的最大吸引力,其实就是人。
不可否认,当人们漫步在街头,关注的焦点无疑是那些衣着合适、妆容自然,给人以亲切、靓丽、自然的美丽女子。人们不需要知道她的名字,也无需了解她的个性,更不必考验她的智慧,只从第一眼上看,就享受了视觉上的美感。当然,还有大街上时尚帅气的轮滑小伙儿,婴儿车里甜睡中的宝宝,夕阳下相互搀扶的老人……这一切,构成了一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所在。
遗憾的是,人们在城市的建设中却忽略了这些本真的规律。尤其是在近代,很多城市的规划、建设部门,都把“车是人的最大乐趣”作为最根本的设计原点。于是,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车站,大商场,大剧院,大公园,大饭店……什么都在追求大。
正因为“人是人的最大乐趣”,城市就应以人的移动作为思考的原点。
人类在上百万年的进化中演变为直立行走,缓慢行走和用脚行走。当人们步行时(约5公里/小时),可以有时间观察人脸和身体的细部。而当开车时(约40公里/小时以上),就会失去观察细节的机会,其结果是无趣而乏味的。人与人之间,安全而温暖的接触发生在近距离、小范围内。而这正是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成都的小巷能够留给人强烈的城市记忆、人文情怀和市井味道的真正原因。但实际中,国内一些城镇化建设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一个区区几万人的小镇,非要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的市民广场,徒留下阳光下的空旷在嘲笑人们的无知。
正因为“人是人的最大乐趣”,人就是城市最突出的风景。我们应该为这样的风景搭建展示的舞台。
城市空间的打造既要有利于人们举行大规模的政治性仪式,更应有利于人们开展日常活动与交流。城市要通过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引导人们更多地采用步行、骑行交通。行走中的城市是有魅力的城市。行走中,人们可以随时停下来,彼此交谈几句;可以随时坐下来歇一歇脚,欣赏周边的美景。国外很多城市会在沿街两侧安放很多桌椅,供行走的人们稍息,喝一杯咖啡。人们在这里喝着咖啡,看着眼前晃动的人流。而街上的人流也在看着坐着的人们。这几乎成为很多宜居宜游的城市的共同画面。而我们的很多城市,满大街只会见到停车线,看不到公共座椅。一个装在“车轮上的城市”,真的谈不上什么宜居。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不仅“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还要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围绕《意见》中“拆除小区围墙”的要求,赞同者有之,质疑的声音亦有之。有人疑问:没有围墙,物业怎么管?陌生人随意进出怎么办?还有人冷嘲热讽,认为中央推广的街区制无助于疏解城市交通拥堵。而笔者认为,中央此举正是针对治理“城市病”的一剂良药。随着大宗用地开发越来越普遍,宽马路、大广场、超大型封闭社区,迫使人们不得不开车出行,而却拥堵在路上。“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不仅造成了街区宜居性不高,社区活力缺乏,而且也令不少人的城市生活并不快乐。没有围墙的街区制可以使封闭小区内的其他资源公共化,例如绿地、停车场、服务设施等,带来更多的商业活动,带来更多的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接触的机会。这些神经末梢被激活,整个城市的经济就会更有活力。
中国一些城市的老城区,例如南方一些城市的骑楼,就是典型的街区制。这里,居民们往来密切,邻里关系融洽。而在一些大城市“高大上”的封闭式小区里,小区居民互不相识,甚至一个楼层的邻居都从不打交道。推广街区制带来的更多公共空间,将使更多的城市居民告别冷漠的围墙,给社区带来生活气息,逐步建立起熟人社会。这岂不会给居民带来更大的安全感?人流是小区最安全的围墙,人眼才是“全天候”的监控。
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需要在他们的城市里相互交流。而外地游客进入一个城市,在“吃住行游购娱”的活动中,也在品评着当地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风习俗。旅游的目的,既是观景,也是看人:直爽的东北人,好客的山东人,精明的上海人,会吃的广东人……需要人们真的要到当地亲身体验一番。
笔者曾到内蒙古各地旅游多次,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草原、蓝天和白云,也没有看到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更多的是当地人为你敬酒唱歌献哈达时,目光的纯净、无邪和友好。那里有首歌唱道:“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目光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我的心底……”的确,草原不只是草的地方,草原更是人们相聚、相知、相交、相爱的地方。
旅游者到一个地方,说是看景,其实往往还是体验不同的生活观和世界观。比如民宿,卖给大家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杨丽萍的太阳宫现在成了网红,一共十个房间,最便宜的价格每晚也要几千,而且还很难订到,原因就在于,人们冲的是杨丽萍这个人去的,太阳宫卖的实际上是杨丽萍的生活品味。
当然,人是城市的亮丽风景,也是要有条件的,那就是社会的和谐,生活的富庶,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
笔者曾到温州考察,印象最深的不是商市楼宇,而是一个“红日亭”的地方以及亭下忙碌的人们:一棵大榕树,一座红日亭——温州民间慈善的地标,40年的善举,风雨无阻施粥每天80多斤大米,煮18锅粥;茶水每天供应1-2吨,喝茶水的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清洁工、生活清贫者、孤寡老人等。最初,只是红日亭等少数几个伏茶点老人们的零星善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温州已有大大小小300多个伏茶点,乐善好施的义务烧茶人更是不计其数。笔者在现场看到,服务者都是社区义工,其中的一位已九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动作灵活,真是爱心常在,青春常在!这位老人,就是温州的一道最美的风景!
一个宜居宜游的城市,应该是步行者多于骑行者,骑行者大于驾驶者;车行道让于人行道,供人们休憩的座椅多于停车位;笑脸多于指示灯,相互间的问候声多于汽车的喇叭声。
山美,水美,城美,乡美,人——其实更美!
(责任编辑: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