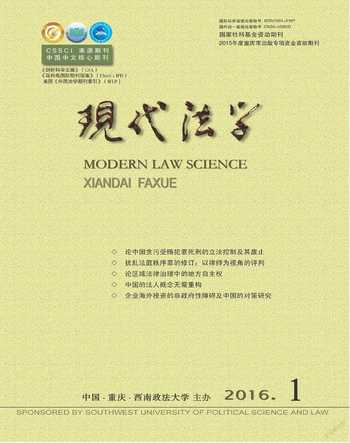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强制性发展
胡绪雨
摘要: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强制性演进,是随着托运人与承运人间谈判势力持续对比变化而发展的,其统一与变革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目的与法律价值。航海过失免责的存废,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航海技术状况所决定的,集中反映了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变化。加重承运人的强制性责任,折中于各国际公约的完全过失责任是社会化班轮运输业的发展趋向,是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求。《鹿特丹规则》所确立的承运人责任基础趋向严格化和规范化,顺应了国际航运发展实际,通过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变革和举证责任再分配或重新安排,以达到新的利益公平与平衡,对于促进航运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国际航运市场秩序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责任基础;国际公约;严格责任;过失责任;批量合同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14
引言
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强制性发展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承运人与货方之间风险与利益的分配,贯穿于国际国内立法始终,而“承运人责任体系的统一是海商法国际统一的基本动因”[1]。随着海上货物运输技术与运输方式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与航运市场形态的改变,当前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所确立的、偏袒于承运人的不完全过失责任渐受质疑。这种理念是否反映了当今航运实践本质,需要研究目前出现的航运经济与技术的新因素与价值变化对立法的影响。《汉堡规则》就船货双方责任重新进行分配,在价值判断上已有更新趋势,体现了海商法公平性思潮的发展。《汉堡规则》制定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注国际公约的统一与协调,制定并于2008年12月11日通过了《鹿特丹规则》。《鹿特丹规则》历经多年讨论,于立法模式上,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汲取《汉堡规则》的成分而成为混合立法,承运人责任采取完全过失责任,废除航海过失免责,将适航能力注意义务扩及整个航程,但求偿人举证责任大幅加重,对国际班轮市场将产生重要影响。在起草《鹿特丹规则》的过程中,承运人责任基础是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争议中许多观点都未获得强有力支持,其能否跨出《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立法思维的目的,将主要取决于国际公约批准加入国的数量及其所代表利益的衡量。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涉及国与国的海权竞争、法系与法系间的竞合、国际贸易与航运秩序维持,以及国内产业保护和政治经济大国的影响,并非单纯法律议题。因而国际公约所揭示者,也并非必然是船货双方利益平衡或公正性的最适方案,往往都是谈判、妥协与折中的结果。
在当今国际航运秩序中,承运人责任基础是否应该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强制性责任分配能否有效控制货损的发生,并使得当事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需要从立法论对强制性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强制性规则是在何种航运经济与贸易环境下制定的,当时受到航运经济与技术发展制约的因素,评价干预所确立的重新分配责任效果等根本性问题。需要探讨在当下航运秩序中,合同自由原则是否应服从于国家基于航运秩序中公平性的强制性干预,是否允许对双方达成一致且富于成效的合意直接用强制性责任规则予以替换。这种揭示与研究能导致对承运人强制性责任基础立法模式的批判,引起国际航运秩序的重构,也可以使立法者
摈弃“与经济目的过分不相容”的承运人强制性责任规则,减少干预所产生的风险。
一、承运人担保责任原则时代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强制性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严格责任、不完全过失责任与完全过失责任。19世纪初,货物灭失或毁损,除有特约免除或例外规定,承运人须负严格责任。在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的时代,强调运输的安全性是海商立法的重心,因此承运人需要对运输的货物受损承担责任,即使其无过失。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强调社会个人自由行动和自主决定,海上货物承运人过失责任原则得以发展,责任成了过失的必然结果,而不再不加区别地归因于所有造成货物损害的行为。在契约自由原则之下,承运人开始于提单中加入免责条款,从而脱离严格责任之拘束,产生了严格责任的缓和。
(一)普通法中公共承运人的严格责任制度
传统上,商人与船东之间的关系是共同冒险,海上风险威胁着双方利益,共同承担风险造成的损失或应由双方平均承担被认为是较为合理的[2]29。公元6世纪,罗马法律将海上承运人本质上视为所承运货物的保险人,应该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责任,所负责任为“担保责任”,仅凭受领事实即须负绝对担保责任,托运人受到保护而承运人必须承担广泛的货损责任[3]。因为当时保险未发达,货物交付承运人之后,托运人无法监督又须支付运费,承运人最能够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损害的发生。在中世纪,英国商船队在全球航运界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习惯法中有所谓公共承运人责任,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交的义务,如同负有保险人一样的责任。承运人严格责任于1671年“Morse v. Slue 案”中提出,于1703 年“Coggs v. Bernard案”中确立[2]29 。至此,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确立了承运人的严格责任,承运人对货物安全,除能证明系归因于不可抗力、公敌行为、货物固有瑕疵与共同海损牺牲,以及托运人行为与公权力行使外,应负严格责任。依照运输契约,请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如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无须证明承运人有无故意或过失,只要能够证明本身系有权索赔之人和货物灭失或毁损发生之情况且无免责事由,承运人就须承担货损责任。1767年英国海事判决免责条款,仅以海上危险、天灾、公敌行为为限,1776 年提单上仅载有“除海上之危险外”而已[4]。在严格责任基础下,要求承运人对货物承担注意义务是较为苛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贸易不发达,航海贸易多数仍是船货一体,受到了航海、造船技术落后和社会经济状况制约,为了货物安全与贸易发展需要,承担严格责任是必要的。
(二)承运人严格责任的缓和
19世纪各国竞相发展海运,与陆上运输相比,海运危险性较大,非经保护不足以鼓励。为提高海运市场竞争力,各国航运政策开始向承运人倾斜。英国立于船东国地位,主张契约自由原则,以缓和严格责任拘束,成为海运市场的主流。“为避免被作为类似货物损害保险人的角色,为减少或免除在运输过程中的责任,19世纪末承运人开始使用提单中的免责条款。”[2]29为了避免公共承运人的严格责任,需要把所有货物损失以及迟延风险转移给货主[5]。此时海上承运人责任仍属严格责任,仅藉免责条款及其限制达到缓和的地步,并非提出了过失责任立法。然而在这些条款得到法院判决认可后,承运人所处地位几乎截然不同于普通海商法中的公共承运人。于是,只要在谈判中具有竞争优势,尽可签订享有免责且无须虑及承担疏忽责任的合同[6]190。从契约约因理论和同意原则的本质角度看,契约内容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免责条款才能成为契约的一部分并发生效力,倘未经托运人同意,对其自不生拘束力。然在航运垄断、承运人处于强势地位以及格式条款广泛使用的形势下,托运人的同意成为一种“拟制”。
契约自由原则打破了普通法中公共承运人承担的严格责任,但基于船货利益平衡立场的差异,英美两国关于
承运人责任基础的问题出现了分歧。英国适用普通法时,虽然认为承运人责任应采用严格责任,但事实上法院支持承运人运用契约自由免除其本身过错行为所产生的几乎所有责任。当时英国皇家航运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按照从1800年以来逐渐流行的一种做法,英国承运人习惯性地在提单中用合同来免除在普通法上很大程度的责任。”[7]提单中免责约款急速增加,到1880年趋于高峰,绝大多数定期航线提单几乎均插入与处理货物有关的一切过失、船员恶行以及不适航等免责约款,从而使海上承运人达到无责可负的程度,以致“承运人仅有收取运费的权利,而不负任何责任”[8]。英国船东在提单上滥用免责条款,大幅降低了承运人的注意义务,损害得以藉免责条款转嫁给托运人,破坏了船货双方的平衡地位,使美国货主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为了保护本国货主的利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公共利益或政策为由,将滥用免责条款的合同条款认定为无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58年在“The Niagara v. Cordes案”中对承运人采用严格责任并认为:“海上承运人在没有任何立法对其设立不同规则时,通常来说他也是一个保险人,对于一切损失都应当负责,除非是由于天灾、公敌行为,或者某些其他原因,承运人对任何过错和疏忽承担责任,且不得在提单中加以排除。”[9]
契约自由是私法的基本原则,核心在于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在具有平等地位的契约当事人之间,订定契约时可经由自由调节以达到某一均衡点,双方当事人都能平等维护各自的合理利益以达成自愿协议。契约自由原则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平等谈判地位的丧失。在航运实践中,班轮承运人处于垄断地位,而班轮公会组织的存在,导致在运输条款谈判中,承运人相对托运人而言具有更强的优势地位[10]。因此,船货双方平等协商地位在当时许多情形中是不可能成立的,单纯依赖私法自治及契约自由原则来调整航运经济制度下所发生的矛盾与弊端、调和船货双方利益已渐不可能,也就无法避免国际社会对国际航运秩序的强制性干预。
二、承运人不完全过失责任立法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领域的自由化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免责条款泛滥,使承托双方风险和责任分配不均衡,有失公正性;二是提单信用下降,其作为物权凭证的流通性受到限制,危害到了交易安全,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合同自由需要受到限制,以便对承运人免责事由作出必要的立法限制,体现公共利益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影响。因此,实现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统一,调整与平衡船货双方利益,成为20世纪初期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主流。1924年国际社会延续美国《哈特法》的精神,通过了《海牙规则》,其效果是契约自由不得不接受明确的限制[5]。然而,基于社会经济、航运发展及船货双方利益平衡等原因,《海牙规则》中的承运人责任体系未公平反映风险与责任分配要求,《海牙—维斯比规则》顺应时代发展而作出改变,但仍未脱离不完全过失责任立法。
(一)《哈特法》:船货利益的平衡
19世纪末,美国航运业并不发达,其海上运输相当程度上须依赖外国船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89 年“Liverpool and Great Western Steam Co. v. Phenix Ins. Co.案”中宣布过失免责条款无效,但该判决于英国法院无法执行,而在英国法院诉讼的案件,美国托运人又常败诉于英国承运人。为避免冲突与平衡船货双方利益,美国国会于1893年制定了《哈特法》,开创了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进行强制性规制的先例,规定承运人应承担最低强制性责任,确立了承运人不完全过失责任,且在适用上不论契约履行地或诉讼地,船舶出入美国即要适用。至此,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逐渐脱离“绝对责任”,跨入“相对责任”立法阶段。《哈特法》在货主和承运人之间达成了利益的折中,承运人放弃了通过合同条款免除在开航当时没有提供适航船舶责任的自由,或者作为公共承运人对于没有适当管理货物而引用航海过失以及其他海上风险免责的自由[11]5,第一次提出了承运人应谨慎处理使船舶具有适航能力并延伸适航能力注意义务,承运人对船舶不适航要承担责任。但是,《哈特法》是“谨慎处理”标准,而不是先前绝对适航义务[12]。明定了承运人对其船长、船员等海上履行辅助人于航海技术及管理船舶过失得以法定免责的规定,“航海过失免责事由,破坏了雇佣人应就其履行人行为负责的法律基本原则,系美国《哈特法》创设,对于承运人颇为有利”[13]。因为违反公共政策,法案视任何寻求减轻承运人在“适当的装卸、记载、保管、照料以及适当的交付”货物方面的疏忽责任,以及任何减少承运人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义务的提单条款视为无效。在本质上,《哈特法》是平衡的结果,以保护美国的货物利益免受强大的欧洲承运人提单中泛滥性免责条款的损害[14]。其对当时各国有关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制定具有深远影响,许多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法以《哈特法》为蓝本,对提单免责条款进行限制,从司法实务提升至立法层次,但因各国海运立法分歧,造成托运人与承运人的责任分配不定,而有1924年《海牙规则》的通过与生效。
(二)《海牙规则》的不完全过失责任
《哈特法》制定之后,许多国家仿效该法而制定国内法,以强制性规则解决运输责任问题,以资保护国内货主[15]。国家级立法试图遏制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无限制的合同自由,但并不是十分有效,国际社会认识到需要共同修正这种合同的不公平性[16]。《海牙规则》被认为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统一立法的最大成就之一,是第一个对承托双方权利与义务进行调整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符合当时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实际上为船货双方的利益平衡找到了一个法律支点,合理分担风险和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
目前仍然为大多数国家所奉行。其最大效果是统一了提单中承托双方的权利与责任,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强制性立法的改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较高层面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17]。由于海上运输的特有风险,承运人对货物受损承担严格责任,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抵御海上风险能力有限的小型航运企业由于一次性巨额赔偿而破产。取消承运人的无限责任风险与经济负担,扶植了海运业的发展,促进了航运资本的增长。
《海牙规则》规定了适航能力与货物运输应尽必要注意义务,产生了承运人不完全过失责任,其享有航海过失免责与火灾免责。承运人适航义务从普通法中严格责任性质的义务变为“合理谨慎”的义务,即从绝对的适航义务改为相对的适航义务。只要船东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尽了谨慎处理义务,即使船舶存在不能发现的潜在缺陷,仍然认为船东已经履行了适航义务,不需要承担不适航的责任。在尽到适航义务的前提下,如属航行中驾驶和管理船舶过失导致货物受损,承运人享有法定免责权,但航海过失免责并不包含承运人自身的过失,如属于承运人本身的过失,则承运人不能免责
承运人为法人时,对于董事会、董事长、经理人等有管理权限之人,均应认为其系承运人,其过失无本条免责款之适用。。就航海过失和火灾免责而言,一定程度上减损了过失责任的整体效果与功能发挥。
随着1924年《海牙规则》的产生,承运人牺牲契约自由换取了“航海过失的免责”,提单条款转而由强制性法律规则调整,控制了日益失控的不公平合同条款,修复性地对货物利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一些海商契约的强制性法律在世界范围内推出。1968年通过的《海牙—维斯比规则》对《海牙规则》所确立的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架构并无重大改变,未触及承运人责任基础这一核心问题,仍旧维持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规定,仅针对不足部分加以补充。总体上,《海牙规则》有利于防止承运人借合同绝对自由而损害货方的利益[18],通过移除特定主体的优势地位以维护航运市场中的自由与公平秩序。“19世纪承运人滥用谈判优势地位,《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的目标是保护货主免受承运人广泛的免除责任的侵害,对货主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19]虽然《海牙规则》在各利益方之间并未达成公平,但多年来,该规则以强制性保护潜在的弱势货主方利益,提供一种基于承运人和托运人利益平衡的理念,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价值[20]。无疑,平衡取得了某些改进与进步,但这一结论只是基于历史上的“公平”观念。
三、承运人完全过失责任的构建
航海过失与火灾法定免责的承运人不完全过失责任对船方利益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保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鉴于科技和航海技术的局限,这种强制性责任基础被认为是合理的和现实的。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40年航海科技与航运市场经济的发展,集装箱运输方式出现,以及受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海上货物运输法已不足因应世界航运经济新秩序之需要,当时技术与经济背景发生变化而不复存在,遂产生重新调整海运政策及其法制的需要[21]。《海牙规则》中的航海过失免责规定遭受了抨击:“《海牙—维斯比规则》规定的赔偿责任与限制是过时的和难以应用的,是帆船时代的产物,未能反映现代航运的现实,亦未适当分配承运人和托运人间的风险,为什么驾驶船舶和管理船舶的疏忽风险应当分配给托运人。”[22]“航海过失抗辩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给海上承运人提供了一种任何其他运输公约都没有的保护。”[23]11“公约充斥着技术缺陷和过时的政策。只有通过货主和承运人之间完全新的风险分配,才能消除《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根本缺陷。”[23]566
(一)《汉堡规则》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强制性发展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海牙规则》所规定的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体系予以强烈指责,认为其系保护航运发达国家利益之妥协产物,严重妨害了货主国经济发展而主张予以修正[2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78年通过并于1992年生效的《汉堡规则》对承运人责任基础作出了重大变革,变更了承运人的责任基础,采过失责任主义,重新调整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承运人责任基础的体系可概括为:(1)对海上货物运输不采取所谓严格责任,而维持过失责任原则;(2)修改和废除船舶航行上过失和船舶管理上过失免责,强化过失责任并采推定过失;(3)对于免责事由采抽象概括式规定,摒弃了《海牙规则》中免责事由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承运人提供适航船舶义务的时间应理解为“开航前、开航时和航行途中”,而且适航义务不再是“恪尽职责”的义务,只要船舶不适航,便推定承运人有过错,由承运人进行举证。“《汉堡规则》代表了货主国的觉醒,代表了海运市场新秩序的调整及建立,这是势所必然的。”[25]“《汉堡规则》起草工作组(UNCITRAL)的目标是消除《海牙规则》中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条款,建立一个承运人与货主利益之间公平的风险和责任分配体制。”[26]
《汉堡规则》以完全过失责任原则作为责任基础,并采推定过失原则,使过失责任趋于严格化,承运人责任加重。其核心是通过法律将行为人与某个特定的损害结果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赔偿责任的基础,可以理解为使负有责任的行为人成为潜在损失承担者的一种归责机制。因为在许多情形下,货损事故的发生难以区分是不可抗力还是人为过失因素造成的。采取推定过失原则,要求掌握或有条件取得灭失或损坏发生证据的承运人证明其本身对灭失或损坏的发生没有过错,此方案可以被认为是公平且合乎逻辑的妥协。在不完全过失责任原则以及举证责任条件下,无法得到赔偿的部分,在《汉堡规则》中得到了保障,风险转移给了船方。航海过失免责的废除,打破了沿用已久的承运人在运输成本、费率订定、保险支出、船舶碰撞、共同海损、船舶侵权责任等方面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和分摊责任所涉及的责任成本,更容易快速地确定赔偿责任,是对《海牙规则》及《海牙-维斯比规则》中船方利益减损、货方利益增加的一种新的船货利益平衡。“《汉堡规则》增加了承运人责任,适度平衡了托运人与承运人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现象。”[27]其制定的最主要目的是在货物毁损灭失的责任分配方面,谋求国际贸易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实现了法律框架的重大改革”[11]280—281,维护了货主与承运人间风险分配的公平,形成了新的利益均衡,对传统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强制性责任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失责任”已转化为承运人的“准严格责任”,承运人责任之重,几乎可与担保责任主义时代相同[28]。废除航海过失免责给海法秩序带来了重大的变革[29]。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对船舶航行过失免责作了批判,即与现代船舶技术革新相对照,此种免责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承运人在实践中运用该抗辩,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有价值了”[30]。 所以,须调整国际海运货物责任法律以跟上发展的步伐。
《汉堡规则》是一个代表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虽已制定多年,但对国际海运业现实上仍没有什么大影响[31]680。《海牙规则》在船货双方利益之间的分配明显偏袒于船方,这与经历70年之后明显偏袒货方权利的《汉堡规则》发生直接冲突。《汉堡规则》的制定,试图从正义的形式中演变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全部内容,并且推导出有效性,其“目的是在承运人和货方利益间创造一个公正性的平衡”[32]。虽然公约确立的承运人完全过失责任在法律层面上更加趋于公正,然并未得到各国的广泛接受,为承运人抗拒而无法实践,在国际海上运输领域的影响较小。《汉堡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从航运实践出发,脱离了客观现实,因而不可能对国际海商事法律制度的效力根据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汉堡规则》虽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效果不理想,但其对制定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理论创新价值是极其重要的:“该规则并没有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但推动国内立法并入了其部分条款。”[31]19
(二)《鹿特丹规则》:完全过失责任新构建
《汉堡规则》生效以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不统一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国际航运界普遍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责任体制,反映现代商业实践和需要,以代替《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33]“《海牙规则》时代给予船舶所有人特殊保护、豁免和特权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交通部2009年度科研项目:《联合国统一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研究(研究报告—分报告二:中国政府代表团“建议案”及重要立场、观点说明),课题负责人:司玉琢,承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和科学征服了海洋,而承运人也被给予或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责任。”[34]为建立现代统一的运输法律体系,促进国际航运与贸易发展,《鹿特丹规则》于2008年通过。《鹿特丹规则》有关承运人责任基础的规定,兼容了《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合理部分。承运人责任架构沿袭了责任事由与免责事由列举式立法模式,平衡分配了承运人与求偿人间的举证责任。在承运人的免责事项中,取消了“承运人的航海过失免责”,承运人责任基础采取完全过失责任制,承运人须谨慎并注意地履行货物收受、装载、搬移、堆存、运输、保管、看守、卸载与交付义务,扩展适航义务的连续性,这将对承托双方间的责任分配产生重大影响。承运人适航义务从“开航前和开航当时”扩展到“整个航程”,是承运人责任基础采取“完全过失责任制”的必然结果,是取消航海过失免责的必要补充[35],并与现行《国际安全管理规则》(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相一致, 因为自1998 年7月起该规则
已陆续适用于各类船舶。根据《国际安全管理规则》,公司得确保及保持该船只在整个海上航程适航,此项规定可以有效淘汰次级船舶,对航行安全与海洋保护具有积极意义。《国际安全管理规则
》和1978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以下简称《STCW公约》)已经加大了对承运人的监管力度,从公法角度对承运人欲援引航海过失免责提高了标准,与承运人完全过失责任形成互动作用,并同时影响了公法和私法
《国际安全管理规则》(ISM)适用于国际航行中大多数种类的货船,1998年7月1日开始生效,2002年7月19日起适用于所有其他货船,如海上钻井平台。《国际安全管理规则》是一个公法影响私人当事方权利和义务的典型范例,因为它确立了适用于操作和管理所有船舶和预防海洋污染的国际标准和程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航运发达国家并没有一致反对公约草案取消航海过失免责与火灾免责,此种局面的出现乃是由国际立法形势的敦促所致,也是因为海上安全及环境的长久保护已成为全球航运国家的共同利益。但对于废除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也提出必须认识到海上航行环境与陆地不同,船长很难作出决定,决定不仅要考虑船舶和船员安全,而且还有货主方的商业利益,这两者是相冲突的[36]。需要考虑保留或取消航海过失抗辩在不同货物责任制度中产生何种实践上的不同,以确定谁实际上承担这些费用及其优势所在。
货主能否实现其货物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仅与归责原则有关,还与举证责任分配密切相关。《鹿特丹规则》中的举证责任由船货双方共同分担,构建了“三个推定”立法框架,此三种推定分别针对“管货义务”、“免责条款”和“适航义务”。在涉及管货义务方面,对承运人实行过错推定,举证责任由承运人承担;对于免责事项,对承运人实行无过错推定,举证责任由索赔方承担;对于适航义务,对承运人实行有过错推定,但需要索赔方完成初步举证,然后才要求承运人对“谨慎处理”和不适航与货损间无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种举证责任安排是为了平衡承运人与货方间的利益,防止航海过失免责取消后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变得过重[37]。“为了平衡船货双方利益和风险,作为对承运人义务与责任增加的平衡,在举证责任上作了更为有利于承运人的倾斜。”[38]实行承运人的完全过失责任,无疑增加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其运营成本也将提高,打破了长期以来承托双方的风险责任分配状态。选择一种体制或另一种体制产生的结果仅是风险或相关费用在承运人和货主之间,更可能是在保险人之间的再分配
研究发现,欧洲大多数托运人(75%-80%)都购买货物保险,货物保险费用仅占货值的很小一部分(通常低于1%),反映了比较低的货损事故率,而大多数承运人对约占海运船舶总量的90%-92%进行了保赔保险。。因此,船货双方利益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在短期内对国际航运市场的稳定带来一定影响。《鹿特丹规则》试图改变承托双方责任分配不均衡的状况和建立新的责任体系,考虑到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从而形成一个比《海牙—维斯比规则》体系要求更严格,而比《汉堡规则》要求略宽松的承运人责任体系[39]。对船货双方的举证责任重新调整、配置,体现了新的立法理念和对船货双方利益的再调整。
四、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发展:“契约自由”原则的立法选择
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其体现必然是具有强制性效力的承运人责任基础。在立法选择中,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否进一步受强制性立法约束,已沿不同的路径发展。《鹿特丹规则》中的批量合同以契约自由为原则,将塑造承运人责任新秩序,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理论发展和对制度的需求,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合同自由和不受强制性干涉将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或在向这个时期转变。在合同法一般性原则的规制下,谈判势力对等的船货双方自我协商平衡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责任,这将是一种新的方法。
(一)长期的协同性合同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发展
传统班轮运输合同类型在双方之间维持一种单项交易,并不对未来交易提供承诺,每一次运输都是临时性处理的,决定性因素是价格,双方都不会对以后的货运量和船舶运力负责,这种关系类型能够使托运人和承运人的风险最小化。在任何一方都缺乏优势的情况下,托运人和承运人重视与交易相关的风险责任和回报,倾向于交换剩余的平均分配。现代航运经济依赖于大规模的资本投资,随着航运规模的不断扩大及航运经济中交易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承运人需要长期稳定的货源,以便此种交易模式灵活应对持续变化的航运市场形势,其结果是强调长期合作性的合同占据了班轮运输合同交易的主导地位
这项服务的价格基本上是以托运人对最小数量的保证为基础,这种关系类型目前在班轮运输行业较为普遍。贸发会议指出,“文书草案中所谓的服务合同或‘远洋班轮运输服务协议’有相当大的意义”,因为据报80%-90%的班轮运输采用这种类型的合同。另据统计,目前中美航线根据海运服务协议运输的货物达到80%左右,在中欧航线也达到了60%-70%。随着班轮运输业日益集中以及全球货运代理行业发展和各种结盟的出现,使用这种类型的合同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班轮运输的趋势。(参见:Comments from the UNCTAD Secretariat on Freedom of Contract, UN Doc A/CN.9/WGIII/WP. 46, para .2.) ,进而影响到当事人间的信赖合作和责任关系,突破了传统班轮运输个别性合同的承运人责任基础模式。
为了保持公约内容的延续性和连贯性,《鹿特丹规则》在制定之初也旨在承继对承托双方都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但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会议中提出,将其在对外贸易中广泛采用的海运服务协议纳入公约,公约应该对协议条款的内容作出非强制性规定,允许突破公约的强制性规定
运输法:拟定[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二届会议(A/CN.9/WG.III/WP.42),2003年10月6-17日,维也纳。。《鹿特丹规则》最终基本上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并以“批量合同”概念加以定义和特别规定,允许承运人和托运人自由协商确定承运人的责任,可以协商一个更高的运费率以换取更高的赔偿责任,作为同意对货物损失减低责任甚至零责任的回报,托运人将受益于运费的降低。根据《鹿特丹规则》第80条的规定,“一个合同可以排除航海过失责任的选择,精明的托运人和承运人可能签订长期的运输协议,协议中可以免除责任或减低责任限制并相应地降低费率”[40]。赞成批量合同的观点认为,现行的承运人强制性责任基础是在一种与目前已不再相关的商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不能满足当今商业需求,作为一个新的公约应有前瞻性,必须能够应对行业的变化需要,应有从事贸易和商业所需的灵活性[41]。事实上,作为对简单合意模式的反对,批量合同中承运人与货主之间建立了信赖关系,注重结果性价值、忠诚度和长期合作。从理论上讲,没有强制性责任,承运人依然会有动机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货损的发生[42]。承运人并不是随时都想把合同履行中的风险尽可能地推卸给托运人,因为在海上运输中,对运输质量的需求在增加,且市场还存在潜在增长的趋势,随着合作期限延长,承托双方所具有的谈判力量不平衡会减弱,货主受到承运人滥用权利侵害的可能性会降低。如果承运人为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而对假定具有团结信念的托运人施加较大的损害,那么团结的信念就不复存在。虽然有许多因素可能使交换偏离公平,但多数合同是相对公平的,因为承托双方都希望交换能够实现
公平与互利,存在达致公平的压力,否则批量合同关系就不会产生。
《鹿特丹规则》中的批量合同作为一种试图超越或取代传统班轮运输合同的新型契约理论模式,在引起人们关注的同时,受到批评和质疑也在所难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批量合同规则是否会促进国际航运秩序的发展,是否会损害托运人的利益。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强制性责任将会被批量合同制度所稀释,结果托运人会被拉回到《海牙规则》制定前的混乱时代[43]。然而,美国的提案反映了一个更一般的评估:“近 20 年的经验显示,海运服务协议中承运人或托运人对于基本运输条件与责任谈判方面,没有那一方处于不利谈判地位。”[43]批量合同是符合经济合理性要求的交易形态,是一种现代航运实践中全新的契约法模式,其价值在于对协同关系的保证和商业上的合理性,是关于“未来计划”的原理,开创了契约自由与长期合作的新方向。
(二)承运人责任基础中的契约自由
关于批量合同对强制性规范是否可以完全或部分删减适用,公约强制性规定到何种程度,是否有必要提供最低级别的强制性限制,一直是《鹿特丹规则》制定会议上各国代表争论的焦点。起草者们都清楚,合同自由不是唯一的社会价值,法律必须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其他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恢复契约自由有利于提高商业效率、鼓励自由竞争,使班轮运输服务流向“高价值”的使用,因此,非强制性承运人责任基础的解决方案立法获得优先考虑。“为了避免承运人通过没有限制的缔约自由,订立单边条款损害那些缺少对等谈判能力的小型托运人,《鹿特丹规则》设立了严格的标准,旨在确定托运人和收货人没有受到批量合同滥用的损害。”[44]《鹿特丹规则》第80条第2款规定了背离公约强制性规定的条件,防止谈判势力较强的一方滥用合同自由,中小货主有权选择是按该公约的强制性规定与承运人订约,还是签订批量合同,中小型托运人并没有失去公约的保护。而且,为了减损对于托运人产生的效力,托运人必须有机会对合同条款进行磋商。如果托运人决定缔结批量合同,应在合同中明确表明同意背离《鹿特丹规则》中的有关条款。
批量合同虽然可以背离强制性体制的大部分内容,但仍有若干“超级强制条款”不允许当事人背离,自由依然是有限制的,强制性体制仍在最低程度上发挥着调整规制的作用。《鹿特丹规则》第80条第4款规定了不允许以合同形式减损、背离的强制性义务与责任,包括托运人提供信息、指示和文件的义务,托运危险货物时承担的告知、标识义务与责任;承运人的适航义务,以及《鹿特丹规则》第61条规定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权的丧失。适航义务一直以来就是承运人在货物运输合同中应当承担的一项重要义务。“违反船东基本义务造成的损失,一般的免责条款不能适用于他的赔偿责任”这一原则将仍然有效[6]189 。这几项义务除了第61条的规定之外都与航运安全有关,对海上货物运输具有重要意义。《鹿特丹规则》第14条规定的前两项适航义务是强制性的,但第3项义务(船舶适货义务)是非强制性的。前两项义务直接关系到海上航行安全,而船舶适货义务相对而言并不一定影响航行安全,因为其在大多情况下只是危及货物安全,可能造成货损;禁止批量合同背离第61条的规定,是因为当事人之间约定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不可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而违反公共政策。如果合同债务人本人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失,将不再适用免责条款。托运人的强制义务与责任主要是为了让承运人和收货人及时了解货物的必要信息,合理操作和运输货物及采取预防措施,遵守有关运输法令,防止不必要的货损和违法情形,保证航运安全并维护公共利益。
《鹿特丹规则》的制定反映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船货双方力量在当今世界新的发展与平衡,将实现法律与商业现实的协调。虽然我们不应当低估《鹿特丹规则》下批量合同的外在缺陷,但私人交易制度似乎比强制性干预的责任分配规则更为有效,实行强制性的损失责任分配,实际上把控制目的简化为单一的损失补偿,而且承托双方享有更多的自治,可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批量合同制度在谈判能力均衡的当事人之间赋予当事人一定的契约自由,同时又为潜在或可能的实力较弱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强制性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其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程度合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在私人优先权的价值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和适度。
结论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立法应就新技术带来的运输革命作出预见性规定,或者至少是同步规定,以保护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当下进行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统一立法运动中,承运人责任基础强制性立法是否仍有必要得到维持或扩展,还不存在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在强制性责任体制之下,虽然对确定船货双方之间的风险与责任分配,以托运人利益抑或以承运人利益优先或两者利益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强制性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强制固定交易条件会妨碍当事人实现成本效益。承运人责任基础是否取消强制性主要取决于承托双方谈判力量的对比变化,目前,一些托运人具备了与承运人相当的谈判能力,能够自由地商谈运输条件与责任,从而不再需要强制性承运人责任体制为其提供保护;而且,作为一个纯粹的海商经济事务,在合同风险责任通常通过保险公司加以分散时,货主的一种倾向是对现实客观存在收益的关注超过了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法律需要尊重此种合同行为的自由选择或决定。
参考文献:
[1] 傅廷中,杨俊杰.国际海运立法中分化与协调的百年变奏——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为视角[J].法律科学,2007(5):99-108.
[2] Samuel Robert Mandelbaum. Creating Uniform Worldwide Liability Standards for Sea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the Hague, COGSA, Visby and Hamburg Conventions[J].Transporatation Law Journal, 1996(21).
[3] Chester D. Hooper. Carriage of Goods and Charter Parties[J].Tulane Law Review,1998-1999,73:1698.
[4] Thomas Gilbert Carver.Carver’s Carriage by Sea[M].13th ed.Stevens & Sons, 1982.
[5] Jan Ramberg.Freedom of Contract in Maritime Law[J].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1993(2).
[6] G·吉尔摩,C·L·布莱克.海商法[M].杨召南,毛俊纯,王君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7] 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20.
[8] L. F. H. Stanton.The Law and Practice of Sea Transport[M]. revised ed. Glasgow:Brown, Son & Ferguson, Ltd., 1970.
[9] Nicholas J. Healy, David J. Sharp & David B. Sharp.Cases and Materials on Admiralty[M].42nd ed. West Publishing,2006: 314.
[10] Jose Angelo, Estrella Faria.Uniform Law for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at UNCITRAL: New Times, New Players, and New Rules[J].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9(4): 280-281.
[11] David Michael Collins.Admiralty-international Uniformity and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J].Tulane Law Review, 1985,60.
[12]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Bill of Lading)[R].CFCG-Service Issue No.6-2,1995: 294.
[13] 梁宇贤.海商法精义[M].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131.
[14] Michael F. 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J]. JMLC, 1991(2):13-14.
[15] 林群弼.船舶适航能力的研究[J].法学论丛,2000,46.
[16] Simon Baughen.Shipping Law[M] . 4th ed.Routledge-Cavendish, 2009: 103 .
[17] Synopsis of Responses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R].CMI Yearbook,1999: 451.
[18] 李志文,尉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适用范围的新发展:合同自由与限制[G]//李志文.国际货物运输法律热点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
[19] John F Wilson.Carriage of Goods by Sea[M].4th ed.Harlow, Pearson Education,2001: 176.
[20] Stewart C. Body, Andrew S.Burrows & David Foxton .SCRUTTON租船合同与提单[M].郭国汀,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13.
[21] 柯泽东.最新海商法——货物运输责任篇[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1:18.
[22] Thomas J. Schoenbaum.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M].4th ed. West, and Thomson Business, 2004: 566.
[23] Leslie Tomasello Weitz.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The Nautical Fault Debate (the Hamburg Rules, the U.S. COGSA 95, the STCW 95, and the ISM Code)[J].Tulane Maritube Kaw Journal, 1998(22).
[24] 柯宝秀.海上件杂货运输损害赔偿问题研究[G]//林咏荣.商事法论文选集(下).台北:五南出版社,1984:937.
[25] 王肖卿.载货证券[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134.
[26]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egislatio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s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J].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1988(19).
[27] 程家瑞.中国经贸法比较研究论文集[M].台北: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 177.
[28] 杨仁寿.汉堡规则[M].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0: 234.
[29] 樱井玲二.汉堡规则的成立及其条款的解释[M].张既义,李首春,王义源,陈薇薇,译校.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 291.
[30] 雅恩·拉姆伯格.国际贸易运输经营人法律与实务[M].杨运涛,丁丁,王宁,译.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20.
[31] 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2] Hannu Honka.New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The Nordic Approach Including Comparisons with Some Other Jurisdictions[M].Abo Akademi University, 1997:6.
[33] Diary of Future CMI and Other Maritime Events[J].CMI News Letter,1999(4).
[34] 威廉·泰特雷.国际海商法[M].张永坚,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94.
[35] Talal Aladwani.The Supply of Containers and “Seaworthiness”:The Rotterdam Rules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2011,42: 10.
[36] Synopsis of Responses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R].CMI Yearbook, 1999: 450.
[37] 司玉琢.承运人责任基础的新构建——评《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责任基础条款[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3):1-8.
[38] 杨运涛,翟娟.《鹿特丹规则》对航运物流业务的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156-157.
[39] Gertjan Van Der Ziel.Chapter 10 of the Rotterdam Rules: Control of Goods in Transit[J].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9,44(3): 375.
[40] Andrew Tettenborn.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Rotterdam Rules : Framework for Negotiation or One-size-fits All?[G]//Rhidian Thomas.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e under the Rotterdam Rules. Informa Law, 2010 .
[41] Proshanto K. Mukherjee & Abhinayan Basu Bal.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Volume Contract Concept under the Rotterdam Rules: Selected Issues i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2009,40(4).
[42] David S. Peck.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llocation of Liability for Cargo Damage: The Case for the Carrier , Or Is It?[J].Transportation Law Journal, 1998,26(1).
[43] Honka Hannu.Scope of Application, Freedom of Contract[R].CMI Yearbook, 2009: 257- 258.
[44] Theodora Nikaki.A New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Contemporary, Certain, Inclusive and Efficient, or Just Another one for the Shelves?[J].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