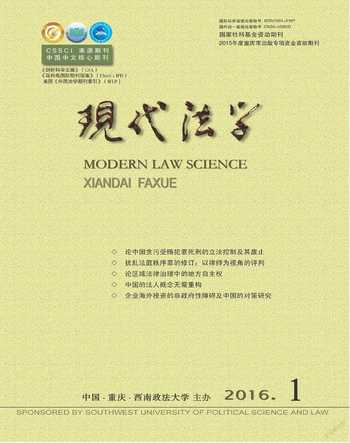现行犯:一个亟待解释的法律概念
吴宏耀
摘要:
现行犯(flagrant delict)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个法定用语。但是,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像西方国家那样给予现行犯一个明确的界定,而是将其规定为刑事拘留条件之一,致使现行犯概念一直没有引起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足够重视。然而,现行犯观念的缺失,不仅为刑事拘留制度的异化洞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严重影响了对现行犯紧急应对机制的研究。故此,需要以传统刑事诉讼法学中的现行犯理论为基础,对“现行犯”这一法学概念进行学理解读,并结合大陆法系国家现行犯的立法体例,对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犯规定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期可以推动我国现行犯紧急应对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现行犯;准现行犯;刑事拘留;扭送
中图分类号:
DF61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11
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Ignoratis terminis [artis] ignoratur et ars.)
——拉丁谚语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含义。于是各自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鲁迅:《扁》(1928年)
一、被遗忘的“现行犯”
现行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个法定用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在我国现有立法中,除《刑事诉讼法》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0条)也使用了“现行犯”这一术语。但从条文内容来看,这两条规定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法规范。。在新中国立法史上,该条规定始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后经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而定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方面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另一方面,修正逮捕、拘留条件以适应追究犯罪的需要,将原属收容审查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和‘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纳入拘留的对象,并将后一种人的拘留时间延长至一个月,而对前一种人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参见:修改刑事诉讼法概述——代序言[M]//陈光中,严端.刑事诉讼法释义与应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8.)。
我国立法尽管采用了“现行犯”这一术语,却并没有像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典那样对其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定。在比较法上,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在规定现行犯制度时,往往都会以立法的方式首先明确“现行犯”一词的具体含义和外延范围。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卷第二编第一章在“现行的重罪与轻罪”标题下,具体规定了现行犯的相关制度。其中,作为整个现行犯制度的基础,该法典第53条规定第一款首先明确了现行犯与准现行犯的含义。又如,《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212条在“现行犯、准现行犯”标题下,规定了现行犯、准现行犯的含义。同样,《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382条、《韩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11条也就本国立法中“现行犯”一词的外延做出了明确规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国立法均采用了“现行犯”这一法律概念,在现行犯的外延范围上,则因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价值取舍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制度设计上,西方刑事诉讼制度一般先明确现行犯的概念,进而以现行犯这一特殊犯罪现象设置必要的紧急处置措施。其内在逻辑是,基于现行犯这一紧急情形,立法设置特别紧急处分具有充足的正当性。然而,在我国,相关的立法规定并没有刻意强调“现行犯”这一紧急状态的法律意义,相反,“现行犯”一词只是作为拘留对象的指称捎带性地规定在了拘留制度之中。受此影响,在我国一贯喜好“下定义”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中,关于现行犯的论述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根本没有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学概念。在立法规定中,“现行犯”一词最早出现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根据该条规定,当时的教材将拘留条件概括为两项:一是罪该逮捕;二是情况紧急。至于何谓该条文规定的“现行犯”,甚至连只言片语的说明都没有。[1]1996年《刑事诉讼法》删除了原刑事诉讼法关于“罪该逮捕”的限定。受此影响,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一般将拘留的条件重新概括为:其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其二,具有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其中,就拘留的对象,新版教材进一步解释说,“现行犯是指正在进行犯罪的人;重大嫌疑人分子是指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2]由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触及拘留的条件,在新版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中,关于现行犯的解释一仍其旧,只有不足一行的文字[3]。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理论研究层面,有关现行犯的研究成果同样门可罗雀。迄止2015年6月,在“中国知网”,以“现行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能检索到6篇学术论文这6篇学术文章依次是:耿连海.关于对现行犯适用先行拘留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4(6);谢小剑.现行犯诉讼程序论[J].河北法学,2009(7);冯露,马静华.比较与实证:现行犯速决程序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5);周其国.论我国现行犯速决程序的构建[D].合肥:安徽大学,2011;周长军.现行犯案件的初查措施:反思性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117条对传唤、据传的修改为切入[J].法学论坛,2012(3);姜琪,卢娴.试论我国现行犯速决程序的构建[J].法制博览,2013(8).。
现行犯观念的缺失,为拘留制度的异化洞开了方便之门。就拘留制度而言,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直接源于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第6条。在条文表述上,与《逮捕拘留条例》相比,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只做了两处小的改动:一是删除了原条文(“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于情况紧急,可以先行拘留”)中“由于情况紧急”的解释性文字;二是将第七项中的“打、砸、抢、抄”简化为“打砸抢”。但是,在拘留制度和实践层面,1979年《刑事诉讼法》却发生了两点重大变化:第一,无论是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还是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均不要求拘留必须有拘留证。这一点与两部条例均要求逮捕“必须持有逮捕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则明确要求,“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第二,无论是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还是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均强调拘留是一种基于“情况紧急”(1979年的表述)而“采取的紧急措施”(1954年的表述)。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因删除了“由于情况紧急”的解释性文字,客观上强化了“罪该逮捕”与“先行拘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拘留开始从一种基于紧急情况而设置的临时性处置措施逐渐蜕变为逮捕前的常规性替代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上述两点变化又是互为表里的:一方面,由于将拘留视为一种因来不及办理逮捕手续而不得已“先行剥夺人身自由的替代性手段”,因此,从保障个体人身自由的角度出发,要求拘留“必须出示拘留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另一方面,在程序上,要求拘留“必须持有拘留证”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在采取拘留措施之前,必须已经做出刑事立案的决定,而且,已经完成了科层审查、批准的内部流程。在此意义上,拘留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侦查人员有权现场做出决定的“紧急处置措施”。而且,值得注意是,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年代,由于人口流动性不大、警务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坐班式”的回应性执法等社会原因,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一年也难得碰到几回需要必须立即做出现场处置的紧急情形。因此,迄止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拘留作为逮捕“先行措施”的角色已经基本固化成习;与此相应,拘留与现行犯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变得日益淡薄。有鉴于此,在1996年修法中,立法者才会在决定取消收容审查的时候,将“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这两种根本不属于“情况紧急”的实践情形大胆地塞进拘留制度之中。换句话说,1996年修法之后,拘留制度已经彻底远离现行犯的正当性基础,而成为一种因不能逮捕而采取的先行羁押替代措施。
然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国的拘留制度,那么,该项制度的正当性何在呢?值得注意的是,前后两部《逮捕拘留条例》尽管时隔25年,但是,条例的第1条均明确引述相关宪法的规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作为整个条例的宪法基础。然而,从宪法角度看,既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那么,为什么又在《条例》中进一步规定拘留措施呢?研读《逮捕拘留条例》的条文,我们可以发现,该条例事实上规定了三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手段:逮捕、拘留与扭送。而且,从条文的顺序和表述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拘留与扭送是作为逮捕这一宪法保障制度的特别例外而存在的,其正当性均源于其适用情形的“紧迫性”。换句话说,拘留是立法赋予执法人员在面对法定“紧急情形”时的一种紧急处置措施,而扭送则是公民个人在面对法定“紧急情形”时享有的紧急处置权。在此意义上,我们只有通过重建现行犯与拘留制度之间的内在法律逻辑,才能洞见我国拘留制度已经积重难返的病灶病因。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厘定现行犯概念入手,重新审视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鉴于我国现行犯制度是近代法律移植的产物,本文认为,在比较法层面,只有将其重新置于法律移植的制度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国相关规定的立法本意。故此,在资料取舍上,本文主要立足于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历程具有明显传承关系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及其研究成果,而不过多涉及英美法系的相关制度。
二、“现行犯”的学理解读
“刑事诉讼法上所规定的现行犯,……其概念原系由实体刑法转换而来,就其要件规定而言,仍有多处涉及刑法中之概念,谓其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两种性质,似不为过。职故,如何在此二性质间寻绎其应有之含义,遂为建立现行犯理论架构之际,相当重要之问题。”[4]
有学者考据认为,现行犯原系刑事实体法上的一种犯罪划分,旨在对现行犯处于较普通犯罪更重的刑罚制裁
例如,在古罗马时代,《十二表法》将盗窃分为现行盗窃与非现行盗窃。其中,对于现行盗窃的制裁要比非现行盗窃严厉得多。《十二表法》第八表第14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现行窃盗被捕,处笞刑后交被窃者处理;如为奴隶,处笞刑后投塔尔佩欧岩下摔死。如为未适婚人,由长官酌处笞刑,并责令赔偿损失。”“对非现行盗窃提起的诉讼,仅得处盗窃者两倍于赃物的罚金。”也即,对于“现行盗窃犯,如果他原来是一个奴隶,十二铜表法判处他死刑;如果他是一个自由人,十二铜表法判处他为财产所有人的奴隶……在该雅士时代,十二铜表法对‘显然的盗窃’的过于严酷大大减轻了,但是,法律仍维持旧的原则,处以四倍于盗窃价值的罚金。”(参见: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14.)对此,梅因认为,这是立法者以“被害人可能要采取报复的程度”为刑罚依据的例证之一。“古代立法者无疑地认为,如果让被害人的财产所有人自己处理,则他在盛怒之下所拟加的刑罚必将和盗窃在一个相当时期后发觉时,他所能满意的刑罚,完全不同;法律刑罚的等级就是根据这个考虑而调整的。”;后来,随着有关现行犯的实体法内容逐渐自成制度(如正当防卫、抗拒抓捕将构成更重的罪名等),现行犯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较为纯粹的诉讼法概念[4]。
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下,现行犯之成立,与犯罪性质、犯罪形态等实体法问题无关,而仅取决于发现犯罪的方式。“现行犯与非现行犯之区别,……究非属于犯罪性质上之问题,纯于手续上有实益,即不论何种犯罪,倘在现行中,无论何人不用拘票可以径行逮捕而已。究未可与犯罪本质上之分类混为一谈也。”[5]换句话说,“现行犯与非现行犯,乃非犯罪性质之区别,而系犯罪发觉状态之区别”[6]。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现行犯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犯罪行为人的确定性。现行犯着眼于“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因此,在概念上,应当区别于“现行犯罪”、“现行犯罪案件”等偏重犯罪事实、犯罪行为的概念。也即,“现行犯以发觉犯人为必要者,……犯人未臻于明了,即无所谓发觉,亦即无所谓现行犯。” [5]有学者认为,在概念上,现行犯有“主观的意义与客观的意义之别”。其中,“主观的现行犯云者,即于犯罪实行中或实施后即时发觉,而犯人究为何人已臻明了之谓。客观的现行犯云者,即犯罪实施虽已发觉,而犯人究为何人尚未明了之谓。”[5]很显然,这里所谓的“客观的现行犯”,实乃“客观的现行犯罪”,而非“现行犯罪人”。
在诉讼法上,区分现行犯与非现行犯的意义在于:对于现行犯,任何人均有权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实施人身控制
为制止正在实施犯罪的现行犯,如果抓捕人对相对人造成了不适当的肢体伤害,则引发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问题。但就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则只能以现行犯逮捕作为其正当化依据。。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下,现行犯与紧急逮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在事实层面上,如果“发觉犯罪之人”没有及时实施紧急逮捕措施,那么,随着时空链条的拉伸,也就不存在诉讼法意义上的现行犯了;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上,只有在实施紧急逮捕措施之后,才会基于正当化的需要,对被逮捕人是否构成现行犯做出法律上的评价。因此,有学者结合现行犯的诉讼法效果,将现行犯定义为:“所谓现行犯,就其文意而言,乃现在正在实施或实施甫终了之犯罪,其犯行明确昭彰,不易发生误认情事,为求保全证据并防止损害继续扩大,刑事诉讼法上特别规定不问何人,而且不依任何司法官宪签发之令状即可立予逮捕。”[4]然而,究其实质,对现行犯可以采取何种法律措施,必须以构成现行犯为前提。故此,将诉讼法律效果纳入现行犯之概念显然有违背逻辑之嫌。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认为,所谓现行犯是指因正在实施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根据当时的情形足以确认他就是犯罪人的自然人。
具体而言,在概念上,现行犯重在强调“人”而非犯罪结果。但是,由于“犯罪人”并非个体的自然属性,而必须借助特定的犯罪行为、犯罪事实才能得以确定,因此,现行犯的讨论又必须以“现行犯罪活动”为基础。换句话说,“现行犯概念之最大特色在于犯罪之‘现行性’,而犯罪现行性则反映于‘犯罪与犯人之明白性’,以及‘时间之密切性’二者之上。”[4]故此,现行犯的认定必须具备三项基本内容:行为人的确定性、犯罪行为的明了性以及时空上的密切性。
申言之,现行犯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就行为人而言,现行犯必须具有人身的确定性。如前所述,现行犯的特别之处在于,犯罪的行为人具有确定性。如果个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断裂,即便犯罪行为刚刚发生,依然不能成立现行犯的问题。
此外,在主体范围上,现行犯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单位。这是由现行犯制度的立法定位决定的。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现行犯制度的讨论旨在保证紧急剥夺个体人身自由的正当性。因此,作为与人身自由权利紧密相连的法律制度,现行犯只能及于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单位等拟制的法律主体。
第二,就行为而言,现行犯必须以犯罪行为的明了性为基本特征。具体而言,现行犯的认定,不是基于人的相貌、种族、前科等人身特征,而是基于其行为具有显而易见的犯罪属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行犯是一种认知结果,而非事实状态。就事实状态而言,任何正在实施犯罪的人都是“现行犯”。但是,如果这种事实状态不为人知(没有“被发觉”)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果。因此,所谓“正在实施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事实上意味着这是第三人(即“发觉之人”)当时做出的一种主观判断,至于事后该行为是否真的构成犯罪、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正当化事由、是否具备诉讼条件
民国以降,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对于告乃论之罪的现行犯,即便未经合法告诉,依然应当适用现行犯的规定,得径行逮捕之。对此,夏勤解释说,因现行犯之逮捕,“系为防止犯人逃亡保全证据而设也。至于逮捕后有无告诉权人告诉,及能否起诉,系另一问题。”(参见:夏勤.刑事诉讼法释疑[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69.)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3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则在所不问。
在此,之所以强调“正在实施犯罪”其实只是“发觉之人”个人的主观判断,具有两方面的实践价值:一方面,基于保卫社会安宁的考虑,关于“犯罪属性”的判断,应当立足于保护“发觉之人”的立场,做适度从宽的解释,而不宜严格以刑法上的罪与非罪为判断标准。在我国“违法-犯罪”二元结构之下,尤其应当如此。换句话说,只要相对人的行为具有“构成犯罪的现实可能性”,即便事实上“尚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亦不能认定为错误。事实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对于扒窃人、小偷小摸的扭送,理应成为一种受到鼓励的社会善行,而不是在罪与非罪问题上提出苛求。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个体人身自由造成不适当的侵犯,在事实基础方面,则必须立足于保护相对人(即“违法犯罪人”)的立场,要求“发觉之人”在做出判断时,必须具有客观的事实基础,而且,这一事实基础的犯罪属性必须是“显而易见”。也即,尽管“在社会危害性上,是否足以构成犯罪”可以存在较为弹性的解释,但是,在行为的“违法犯罪属性”上,则必须坚持“不证自明的明了性”。换句话说,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如果某行为的违法犯罪属性并不具有一目了然的确定性,则不能以惩罚犯罪为由,径行做出不利于行为人的解读。
第三,在时空关系上,现行犯必须具有时空上的衔接性。
从立法例看,现行犯主要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正在实施犯罪而被发觉的;另一种是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就前者而言,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行为是特定人的行为、人是实施特定行为的人。此时,即便行为的性质可能存在争议,行为人的人身确定性却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后者,由于系“犯罪实施后发觉”,此时,犯罪行为已经结束、行为与行为人已经相对分离,因此,立法上特别强调必须“即时发觉”方可。一般而言,所谓“即时”者,是指“距离之时间不远,犯罪痕迹未消散之谓也。”[7]然而,在个案中,“犯罪实施后至如何之时点为止,始克认定为现行犯,故亦较属困难。”[4]因此,在理论上,尽管现行犯的核心含义几乎不存在任何异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成立现行犯,却存在相当程度的灰色地带并出现见仁见智的歧见。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后,虽然犯罪行为与犯罪人已经发生分离,但是,透过特定的活动(如追呼、追捕)、行为人的某些异常特征(如浑身血迹、手持凶器),依然可以将某人与特定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一般而言,以犯罪行为的时、地为基点,距离犯罪行为的时空关系越近,由此建立的现行犯特征也会越明显。因此,在立法例上,除规定典型意义上的现行犯外,还有将足以建立现行犯特征的特定情形,亦按照现行犯对待的规定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11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3款。。理论上,将这些依法视为现行犯的法定情形,称之为准现行犯。一般而言,法律之所以规定准现行犯制度,“仅在于准现行犯对时间密切性之要求略为放宽而已”[4]。
换句话说,在“犯罪后被发觉”的时空链条上,准现行犯距离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地距离比较接近,而且,如果具备立法规定的法定情形,也足以担保该人与犯罪行为具有显而易见的关联。
此外,关于现行犯的应用,还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在共同犯罪中,未实际参与犯罪活动的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等,均不构成现行犯[8]。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发觉犯罪之人”在发觉犯罪后并没有立即采取紧急处置措施,那么,等犯罪人逃离后,将不再构成现行犯。故此,有论者认为,“盖现行犯与准现行犯发觉之事实的本身,纵自发觉以后经过若干之时间,亦不致即归消灭。故即使不为何等手续,而从实质上观察亦不妨称之为现行犯。然在刑诉法上,关于此实质上的观察之现行犯,倘使法定机关未尽一定之手续,即失却为诉讼上现行犯之性质,不许仍认为现行犯而实施特别处置。” [5]
三、立法例中的“现行犯”
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现行犯制度必须平衡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基于保卫社会的需要,必须允许社会公众对现行犯立即采取紧急抓捕措施;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对个体的行动自由与人身自由造成不适当的侵害。显而易见,将现行犯的范围规定得大一些,可以更好地保卫社会,但是,却会因时空链条的拉长,增加误认的风险。反之,如果将现行犯的范围规定得小一些,尽管可以更好地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却需要付出放任部分犯罪人的代价。因此,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选择,直接影响着一国关于现行犯范围的规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以是否规定准现行犯为标准,有关现行犯的立法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德国模式,即只规定狭义的现行犯;法国模式,即在狭义现行犯之外,还规定了准现行犯的内容。“即德国法上对于现行犯限制甚严,排斥准现行犯而不设规定;法国治罪法则定明性质上本非现行犯亦视为现行犯,即于现行犯之外,复认准现行犯之观念,而使二者受同样之处置。” [5]
(一)法国模式:“现行犯与准现行犯”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刑事诉讼法最早确立了现行犯制度,并开创了区分狭义现行犯与准现行犯的制度先河在法国,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还曾经规定一种特别拟制的现行犯。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任何在屋内实施的重罪或轻罪,即便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情况,只要屋主要求共和国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官查证认定的,应视为现行重罪或轻罪。”与准现行犯的立法例相比,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拟制的现行犯呈现以下鲜明特点:不要求有明确的犯罪行为人;不要求与犯罪行为存在时空上的紧密性;其立法目的不是为了实施紧急抓捕,而是为了赋予司法警察特别的侦查权限。因此,该项规定不仅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准现行犯”,而且,严重背离了现行犯概念的本意。在法国,根据1999年6月23日法律,“这种情形已经被立法者排除。”(参见: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26.)。现行犯制度“在诉讼法上之发展,最早见于法国法制。法国自一八一〇年开始施行之旧刑事诉讼法中已有现行犯之规定,一九五九年开始施行之新刑事诉讼法,有关现行犯之规定,亦大体沿袭旧制。在法国法上,现行犯概念分为两个大类:一为固有之现行犯,亦即现在正在实施或实施甫终了(qui se commet actuellement, ou qui vient de se commettre)之犯罪;二为准现行犯,亦即密接于行为之后而被公众追呼为犯罪嫌疑人之犯罪,以及持有足以显示其犯罪之物品或显露犯罪痕迹之犯罪。”[4]
法国法关于现行犯的分类,不仅对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还通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刑事诉讼立法,间接影响了我国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现行犯立法
参见: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第202条、第203条。。
在日本,现行犯的范围不仅包括狭义的现行犯,同时还包括依法“视为现行犯”的准现行犯。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2条在“现行犯、准现行犯”标题下规定,“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刚实施完毕犯罪的,是现行犯。”“符合下列各项情形之一的,而可以明显地认定是实施犯罪终了后间隔不久的,视为现行犯:一、被追呼为犯罪人时;二、持有赃物或者持有可以明显地认为是曾经供犯罪使用的凶器或其他物品时;三、身体或者衣服有犯罪的显著痕迹时;四、受盘问而准备逃跑时。”显然,日本立法以犯罪是否完成为节点,将对犯罪人的认知划分为两段。其中,对于犯罪后发觉的犯罪人,必须有法定的情形予以担保,足以将该人与特定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才得以成立准现行犯。
在日本,“现行犯逮捕是宪法确立的证件主义的例外。”[9]因此,基于日本《宪法》第33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2条关于准现行犯的规定,“相当程度扩大了不适用令状主义的例外情形,有其问题。……此等规定是否逾越宪法第三十三条的现行犯规定所预想的事态,不无疑问。多数学说认为,籍由此条文的严格解释,得承认其合宪性,但亦有主张其有强烈违宪之疑者。”[10]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准现行犯的人身确定性,日本立法要求,在时空条件上,“视为现行犯”的法定情形必须是“可以明显地认定是实施犯罪终了后间隔不久”。至于“是否‘不久’,只得根据具体案件判断”[11]。而且,日本判例“亦甚重视场所之因素,认为犯行现场与逮捕现场愈为接近,则犯行愈逮捕之时间亦愈为密接。” [4]
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基于宪法的要求,对于准现行犯,“在时间间隔上不能有太大的缓和。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应该限定在1、2小时间隔的幅度内。”而且,该学者结合日本实务进一步阐释说:“(1)准现行犯拘留的情况下,结束后为时不久的‘犯罪’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特定的。实际上,司法警察职员通常是通过受害通报和无线通报,知晓发生了犯罪。(2)如果多种事由同时存在,那么,犯人的明确性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下,对时间衔接要件可以适当放宽。最高法院平成8年(公元1996年)1月29日的决定认为,对具备第2款至第4款要件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1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40分钟以后,在离开事发现场40公里以内,进行准现行犯拘留是合法的。”[12]
也有学者建议,应当以警察接获报案后急赴现场通常所需之时间作为认定标准者[4]。
(二)德国模式:狭义的现行犯
德国立法虽然接受了现行犯的观念,但是,在立法例上,德国法关于现行犯的规定仅限于狭义的现行犯。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27条在“暂时逮捕”标题下规定,“某人现行时被发觉或者被追捕,如果他有逃跑嫌疑或者身份不能立即确定时,任何人都有权即时无法官的命令也将他暂时逮捕。”据此,在德国,现行犯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基础要件,即在犯罪实施中被发觉或犯罪实施后被发觉而受到追缉的;二是紧急情形,即身份不能立即确定或有逃跑之虞的[13]。其中,就基础要件而言,除正在实施犯罪的情形外,德国法对“犯罪后被发觉的现行犯”,要求必须有实际的追缉行为作为担保,可以最大限度地担保“犯罪行为人的确定性”。
(三)现行犯概念重述
通过对上述立法例的扼要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作为诉讼法上的概念,何谓现行犯,取决于立法者对事实状态的裁剪。具体而言,在事实层面上,从“正在实施犯罪”到“犯罪后间隔不久”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事实状态;在这一时空链条中,立法者将“现行犯”的节点置于何处,则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立场与取舍。至于准现行犯,“则是在适当缓和时间上的接近性、稍微偏离犯人的确定性的角度上进行把握的”[12]。
在现行犯概念中,“行为人的明确性”是最核心的要求。其中,对于“正在实施犯罪”的情形,由于犯罪行为与行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行为人的明确性”只是一个“看”的问题:只需亲眼看见,行为人的明确性也就一目了然了。然而,在犯罪实施终了之后,人与犯罪行为开始发生分离,因此,随着人与犯罪行为时空距离的拉长,“行为人的明确性”也在逐渐变得模糊。因此,必须借助额外的证据信息,才能够建立特定的个人与犯罪活动的联系。
在此意义上,所谓现行犯与准现行犯的划分,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如果根据犯罪活动的整体性,可以一目了然地确定谁是犯罪行为人,无疑应当将其归属于现行犯之列。比如,尽管杀人活动已经实施终了,但是犯罪行为人正在清理现场或清洗身上的血迹。此时,尽管属于“犯罪后被发觉”,但是,基于犯罪活动时空的整体性,无需额外的证据信息,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地“明白”谁是犯罪行为人。与上述认识方式不同,对于准现行犯,由于犯罪活动的整体性已经瓦解,谁是犯罪行为人已经不可能通过直观观察来获得,因此,只能通过综合各种信息(如与犯罪活动的时空距离、其他特别异常的证据信息)才能做出推理和判断。
四、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现行犯”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拘留与扭送的立法规定事实上蕴含了现行犯的内容。具体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82条的规定,在我国立法上,狭义的现行犯是指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犯罪人。至于准现行犯,则主要是指以下三种情形: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在身边或者在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的
由于立法并没有对“现行犯”的含义做出相应的规定,加之,关于现行犯的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第80条的理解缺乏最基本的共识。其中,除第一项属于狭义现行犯的规定毫无争议外,在该条其他各项法定情形中,究竟哪些属于准现行犯的内容,则看法不一、难成定论。例如,有学者认为第二、三、四、五项都属于准现行犯的规定。(参见:耿连海.关于对现行犯适用先行拘留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4(6).)有学者则认为,只有第二、三、四才属于准现行犯的规定。(参见:周长军.现行犯案件的初查措施:反思性研究[J].法学论坛,2012(3).)。
“现行犯之主要问题,在于‘认定’。承认现行犯之逮捕,无论就承认人民于国家不及保护时之自力救济权利,或者终结正在发生之犯罪并保全被告便利追诉而言,虽然有其必要,但是,若现行犯之认定过于宽松,可能过度侵害被逮捕人的人身自由权利。”[14]故此,本文以下结合我国立法规定,就现行犯的内涵与外延予以进一步的讨论。
(一)狭义的现行犯
关于狭义的现行犯,立法例上一般只规定“正在实施犯罪”,而不具体规定包括犯罪过程的哪些具体形态。但是,我国民国以降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一般认为,所谓“正在实施犯罪”,事实上包含了犯罪过程的各种阶段。例如,京师大学堂笔记关于“正在实施犯罪”的解释是,“所谓实施,含一切犯罪行为,不区分实行、着手、预备及阴谋也。”[15]根据民国时期“司法院”关于“实施”一语的解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亦认为,所谓实施,“范围较实行为广,即实行外,尚包含阴谋、预备以及着手(实行之开始)各阶段在内。” [4]因此,在刑法规定处罚预备犯罪的前提下
关于预备犯罪是否具有可罚性,是“两个刑法原则——最后手段性与有效法益保护——的拉锯战。”(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7.)因此,是否处罚预备犯罪,各国立法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关于犯罪预备的刑事责任,西方刑法大都采取‘犯罪预备原则上不受处罚,但例外情况下也要受处罚’的政策。……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据此,可以认为这是采取‘原则上要处罚,但可以从轻处罚或减免的政策。’”(参见: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344.),正在预备犯罪也可以成立现行犯应无异议。
与外国立法例不同,关于狭义现行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一项明确列举了犯罪过程的两个阶段:“正在预备犯罪”与“[正在]实行犯罪”。因此,结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预备、未遂、即遂的规定,所谓“正在预备犯罪”,是指为了犯罪,正在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所谓“正在实行犯罪”,则是特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至于“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其重点在于对“即时”二字的理解。对此,民国时期的“司法院”曾经解释说,“……所称之即时,系指犯罪事实中或犯罪实施后之当时而言。”参见:民国“司法院”1947年院解字第3395号。也即, “即时”等于“当时”。推敲文意,上述解释的核心含义在于强调“发觉犯罪”与“犯罪终了”之间的“同步性”。如果将犯罪活动看成是一个特定时空之下持续发展的三维事实,那么,所谓“即时”,事实上是通过一个时间概念,指称一种包含了时间、空间、行为人的三维事实状态。例如,正在犯罪现场毁尸灭迹;正在准备携带赃物逃离现场。在上述情形下,即时发觉的是一个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事实状态:此时,尽管犯罪行为已经终了,但是,根据所见所闻的事实状态,可以一目了然地得出特定人行为性质的直观判断。因此,我们认为,立法上关于“即时”的规定,旨在通过强调时间上的即时性,要求“即时发觉的事实”必须是一种足以建立特定人与特定犯罪行为之间明确联系的事实状态。或者说,在发觉犯罪之时,犯罪人与犯罪活动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据此旁观者可以一目了然地形成“刚刚发生了犯罪、是他实施的”的明确认识。基于此,我们认为,关于“即时”的判断,应当包括三个方面要求:“时间上的临近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空间上的一致性”以及“行为人举止含义具有一目了然的明确性”。也即,综合时地人三方面的因素,必须足以得出“谁、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的明确结论。
(二)准现行犯
与现行犯概念不同,准现行犯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故此,在适用范围上,准现行犯只能以立法上明确规定“以现行犯论”的法定情形为限。恰如京师大学堂笔记所言,“按准现行犯,与现行犯不同,在法律上有列举之规定,当勾引、逮捕时,可准用现行犯之办法。如法律无明文者,不得作为准现行犯办理,因其性质本非现行犯故也。”[15]简言之,尽管各国关于现行犯的规定大同小异,但是,就准现行犯而言,立法例上则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于有的国家(如德国)根本不承认准现行犯之规定。
在立法上,准现行犯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拟制。所谓法律拟制,又称法定拟制,是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来处理。作为一种立法技术,法律拟制旨在通过“以A为B”的立法规定,赋予A与B完全等同的法律效果。因此,一方面,就本质而言,准现行犯所列情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行犯;而另一方面,作为现行犯概念的扩张,有关准现行犯的理解,“其性质仍不得与固有现行犯相去过远。”具体而言,有学者概括两点:
“首先,就犯罪与犯人之明白性言,此乃固有现行犯概念所强调者,在于准现行犯方面,亦不容忽视此一特质。……其次,就时间之密接性而言,现行犯之本质既为正在实施或实施甫终了犯罪,以现行犯为由而为逮捕者,在时间上自不得间隔过久,此不仅为固有现行犯所要求者,即使准现行犯方面,法、日法制亦同为此种限制。所不同者,仅在于准现行犯对时间密接性之要求略为放宽而已。” [4]
在此,有必要澄清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像现行犯一样,仅仅凭借存在立法规定的准现行犯情形,就可以控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事实上,准现行犯所列情形仅仅是一些具有高度犯罪嫌疑的异常特征。因此,一旦脱离特定的时空链条或事实语境,这据此只能说某人存在较大的犯罪嫌疑,而不足以断定其犯罪人身份。在此意义上,对于准现行犯,尽管立法有“以现行犯论”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应用中,则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时空链条之下,才能够较大限度地担保“犯罪人的明确性”。对此,日本学者曾解释说,“与上述本来意义上的现行犯情况相反,准现行犯则是在适当缓和时间上的接近性、稍微偏离犯人的确定性的角度上进行把握的。当对象为‘被追赶的犯人’;持有‘赃物以及明显用做犯罪的凶器以及其他物品’;‘身体和衣服上有明显的犯罪痕迹’;以及‘受到喝问,欲行逃走’的场合,只要可以明确认定该人‘刚刚犯罪后不久’,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定其为犯罪嫌疑人。”[1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第195条、第196条曾经明确规定,对于现行犯,无论是作为公权力的径行拘提还是作为私权利的紧急逮捕,都必须以“现行犯仍在犯所者”为前提要件。显然,在概念上,狭义的现行犯原本就包含了在场的要求。因此,立法关于“仍在犯所”的规定,其实就是针对准现行犯所做的限定。迄至民国,早期的现行犯立法也有“于犯罪发觉后最近期间内”之类的规定。可惜的是,1935年《刑事诉讼法》删去了准现行犯条文中关于时间方面的限定。不过,我国台湾学者一般认为,相关立法应当予以检讨,并在理论上强调,“……准现行犯,应解释为须具备时间上之限制。亦即,唯有犯罪行为发生于不久(不超过数小时)之前,始得认定为准现行犯并径予逮捕。” [14]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采用“准现行犯”这一法律用语。但是,基于现行犯的一般理论以及我国近代现行犯立法的历史考察,我们认为,《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紧急情形,应当属于准现行犯内容。
其中,关于“指认犯罪”,应当明确以下三点:第一,作为一种现场行为,这里的“指认”重在即时性。因此,与作为侦查手段的“辨认”不同,不宜对指认程序做过多要求。例如,即便现场只有被指认人一个人,也可以进行。第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的“指认”,不仅应当有明确的被指认对象,而且还必须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换句话说,在这里,指认的功能旨在填补犯罪人与犯罪活动之间的时空断裂,从而将特定的人与已经发生的犯罪活动重新联系起来。因此,指认人应当立足于刚刚发生的犯罪活动并能够当场做出明确的指认。第三,在法律上,根据指认人不同,该项指认可能构成(被害人)控告或(第三人)举报。作为立案材料来源之一,根据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的指认,如果可以一旦构成刑事案件,则应当尽快组织指认人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目击辨认,以便及时固定证据并形成适格的证据材料。
至于“在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追溯法源,可以参照民国立法的规定进行解释。即,该项规定,可以解释为,“于犯罪发觉后最近期间内,持有凶器赃物或其他物件,可疑为该罪之犯人,或于身体、衣服等处显露犯该罪之痕迹者。”在此,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该条的“犯罪证据”必须指向已知的特定犯罪。比如,根据“110报警”,侦查人员知悉刚有抢劫案发生,犯罪人背一瑞士双肩包。据此,如果在犯罪现场附近发现一人背一瑞士双肩包,则可以根据双肩包这一事实,将该人与刚刚发生的抢劫案件联系起来。显然,如果脱离了“110报警”的犯罪信息,瑞士双肩包也就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则应当以犯罪人犯罪后尚未离开犯罪现场为要件
。如果已经远离现场,则属于“犯罪后……在逃”。对此,虽应采取紧急措施,却不得以现行犯作为其正当化理由。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立法关于准现行犯的规定,还可以增加两种紧急情形:一是被追呼为犯罪的。在立法例上,“被追呼为犯罪”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准现行犯情形。而且,在我国传统封建立法中,为了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打击犯罪,甚至明确要求附近的人必须给予追呼者协助。例如,《唐律·捕亡律》规定,“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救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16]考虑到我国立法允许私人扭送现行犯的范围非常狭小,而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又肩负着“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法定职责,在被害人或其他公众“追呼犯罪”之时,执法警察理所当然负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的责任。二是讯问其身份而逃跑的。这是现代巡警制度的必然要求。在警察执行巡逻任务时,对于形迹可疑的人,有权查问其身份,以发挥预防犯罪的积极作用。此时,如果相对人掉头逃跑,显然不应听任其一跑了事。因此,在制度上,理应赋予巡警据此采取紧急处分的权力。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124.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03.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34.
[4]吴景芳.现行犯研究[J].刑事法杂志, 1983,27(2).
[5]方劲益.现行犯研究[J].警高月刊, 1935,3(1,2).
[6]陈瑾昆.刑事诉讼法通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6.
[7]冈田朝太郎.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76.
[8]夏勤.刑事诉讼法释疑[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69.
[9]田口守一.逮捕后的人身羁押[M]//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东京:成文堂,1997:313.
[10]阿部照哉,等.宪法(下)[M].周宗惠,译.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1:261.
[11]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1.
[12]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3.
[13]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2.
[14]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351.
[15]冈田朝太郎.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2:110.
[16]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