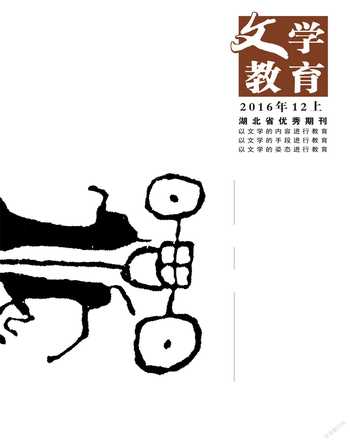《牡丹亭》与《聊斋志异》中的婚恋故事比较
内容摘要:本文将一部戏曲和一部小说放在一起比较,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形式上有相同的内容。《牡丹亭》和《聊斋志异》中的婚恋故事有极大的相似性。恋情的发展都是在非现实的情况下,前者是通过梦以及人鬼来实现,而后者多是人与狐鬼精魅。两部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欲”和“色”进行了肯定和描写。并且,对女性的刻画笔墨尤其多,《牡丹亭》里杜丽娘一枝独秀,《聊斋志异》中众多女性色彩纷呈,她们的共同点是会主动寻求情感和欲望。通过挖掘这些共性,可以窥探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风潮,引起人们对婚姻,对人性,对女性更多的思考。
关键词:梦幻 情 欲 女性
明末清初的许多作品无疑都呈现这样一个特点:将梦境搬上了现实的舞台,将内心的隐秘欲求一层层剥开袒露其外。男男女女对情对欲的渴望不再停留在羞耻的代名词上,而表现得更为大胆甚至疯狂。晚明时期的《牡丹亭》是这样,清初的《聊斋志异》亦是如此。在笔者看来,尽管汤显祖和蒲松龄用不同的形式来阐述“情”,但在本质的表达上如出一辙。现象总是反映本质的,当然,不同的现象也可以反映同样的本质。通过对《牡丹亭》和《聊斋志异》中恋情的分析,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极大的相似性。梦幻的情节,超越生死的执着及对欲的露骨的展现,对女性主体的“偏爱”。透过这些相似性,回顾晚明到清初的相关作品,无疑有一股无形的浪潮在翻腾,只是是什么让潮水决堤,决堤的潮水又涌向了谁?
一.梦幻的情节
“晚明的作品中有一个新的重点,即‘缘情生幻’”。[1]《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游春而梦云雨,因梦而病,死后魂追柳生,共续梦中之缘。柳生因梦梅树下的美人而改名梦梅,机缘之下来到葬下丽娘的梅花庵,拾到美人自画像,整日对画痴唤美人,终于盼来佳人。整部剧由梦贯穿起来,因情而梦,因梦而病,因病而死,死而复生。相比《牡丹亭》,《聊斋志异》中婚恋篇章大多偏向于扑朔迷离的梦幻,除了人鬼恋、人狐恋外,还有人与其他异类的婚恋。其中情节与《牡丹亭》最相似的篇章要数《鲁公女》了,张生见鲁公女丰姿娟秀极意钦想,后女子暴卒,张生朝必香,食必祭,每酹而祝曰:“睹卿半面,长系梦魂……然生有约束,死无禁忌;九泉有灵,当姗姗而来,慰我倾慕。”[2]而后果如生想,鲁公女遇夜而来,与其欢好5年,投胎而去,相约15年后再续姻缘,再生后,女因张生面貌不符年纪泣涕而死,托梦张生询问缘由,后死而复生,相伴而终。可见,二者都是通过这种超现实的幻境来实现情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一篇,很多篇故事里,恋情的女主人公都是“幻”的化身,突然而来,缥缈而去,恋情不免带着神异的色彩。《莲香》中只要反复玩弄绣履,鬼女李氏就会现身。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3],人们有所希望,不能在现实中实现,故而寄托于梦境。杜丽娘的梦,张生与鬼女鲁公女的欢好都是源于内心的欲望,对情的渴求,更强烈的对欲的渴求。正如张生的剖白,生有约束死无禁忌。在超现实的梦幻里,他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本我”,不用顾忌现实里的“自我”。梦是内心世界真实地再现,礼仪廉耻的规范,风俗的教化抑制不住主观意志的投射。非现实的世界是内心欲望实现的所在,抛开所有的束缚,隐秘的意识得以显现,潜藏的东西浮出水面。所以整个晚明到清初的一些作品里才存在那么多“梦”式的情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是最典型的代表,其中以《牡丹亭》为最。《画中人》中的郑琼枝和母亲共赏春色,春心动离魂赴爱约;《梦花酣》中的谢倩桃因画思春,想生梦生。在当时流传的这些人鬼恋情戏不在少数,那么观众作为受众对它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他们在心理层面建立起了一种“共鸣”的关系。当然不仅仅是在戏曲界,小说界也在这种影响下有了自己的创作,《聊斋志异》是当之无愧的代表,鲁迅称其“用传奇之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形,出于幻域,顿入人间”[4]。笔者甚至以为蒲松龄是《牡丹亭》的忠实粉丝,在其影响下激发了其创作灵感。
二.对情的执着还是对欲的渴望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5]在这样一场梦幻的戏曲里,“情”之一字似乎感人至深,《牡丹亭》的题词让很多人感慨杜与柳的情深,用《诗经》的语言来形容就是“死生挈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戏文在演唱的过程中必然掺杂了演员对戏文的感知,在传达给观众的时候,观众接收到的已经不是戏本里的《牡丹亭》了,而是舞台上的《牡丹亭》。演出毕竟与文字不一样,演出所要达到的效果便是观众的喝彩,一部爱情戏,没有比深情更能打动人了。也就是在舞台效应下,受众对情的感知超越了一切。然而在文本细读过程中,找不到情的发展,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少女的怀春,寻春。舞台演出在最大胆的地方必然有所保留,更不用说官府在这方面的把控极其严格。明末清初,朝廷多次下令禁毁“淫秽”的小说戏曲,康熙二年、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都曾下令禁毁。换言之,在表演过程中对于“欲”的表现必然是隐含的,因为这是在现实世界演出。在笔者看来,二人的情感是存在很大漏洞的,杜丽娘因为一个梦而恋上柳梦梅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柳梦梅因为一幅画像而爱上杜丽娘显然也不靠谱。当然文学创作有夸张和浪漫的色彩在里面,有意的着色渲染作者想要突出的部分也是理所当然。但透过文本看到的并不是“情不知所起”,这显然是有缘由的。在第十出《惊梦》中杜丽娘发出感慨“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以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隙耳。”这个姑娘想嫁人了,但没有对象。
【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传?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身子困乏了,且自隐几而眠。[6]
从她做梦前的这番怀想,以及对《关雎》的另一番解读,可见这位少女对情的深深渴望。渴望到做梦也想着这事儿。但是梦里,她与柳生没有诗词唱和,没有人生观价值观的交汇,而是直奔主题“小姐,咱爱杀你哩”,然后杜丽娘就跟这书生走了。而且是在明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下自愿,或者说欲拒还迎的走的。看第十出《惊梦》在《山桃红》这支曲子里对二人的具体描述。
【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旦低问〕那边去?〔生〕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低问〕秀才,去怎的?〔生低答〕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生强抱旦下〕
【山桃红】〔生、旦携手上〕〔生〕这一霎天留人便,草借花眠。小姐可好?〔旦低头介〕〔生〕则把云鬟点,红松翠偏。小姐休忘了啊,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
这就完全是露骨的描写了。也无怪乎《才子牡丹亭》对其进行“情色”般的解读,还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对于上文所引《山坡羊》,书里做如此点评“‘没乱里’以下共十四句,只是贤文禁杀之注,又即天壤王郎一句。独于古今往来之中,写出聪明男女急色实情。”[7]一句“急色”点出了杜与柳的情感源泉,二人与其说是因梦结缘倒不如说因欲结合。在第三十九出《如杭》中提到“色身无坏”,标榜“人欲”的不可磨灭与天经地义,绝非礼教可以禁杀。“因色生情,因情见色”是明末清初诸多戏曲小说描绘的情感套路。整个“杜柳恋”完全是在“欲”的引导下才发展为情,才有了杜丽娘的死而复生。当然,从男主人公柳梦梅的角度来看,就不单单是“欲”了,“色”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拾到画后,柳生对画中女子痴迷不已,第二十六出《玩真》将他的情态表露无遗,自此每日把玩对画呼喊“美人!美人!姐姐!姐姐!”
这种状态跟《聊斋》中大多男子如出一辙。连圣人都承认“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在婚恋故事长达三分之一的篇幅里,“急色”可以说是100%,几乎每一个婚恋故事里,都饱含着对色对欲的追求。《鲁公女》中,张生“归忆容华,极意钦想”,见到女子的美貌后,念念不忘不能自已。鲁公女就夜来相奔,遂共欢好。情感的发展非常迅速,以鬼的身份,抛却一切礼俗,就朝着最终的目的进发。《画壁》更是将这种渴求描绘到极致,男子看到画中女子就臆想万千,进入画中与女子欢好。《婴宁》中的王子服则到了一种痴病的地步。《聊斋》中几乎所有的婚恋故事都有这样的特点:女子十分美貌,男子等不及就要欢好。只有少量的两三篇如《青梅》不是如此。在《胡四姐》中,尚生在夜里独居“遐想”,忽然一女子就来了。这样的开头是《聊斋》婚恋故事的普遍概括了。这种开场,与杜丽娘游园惊梦没有实质的分别。差别只是怀想的主人公性别不一样。人欲的追求并无性别之分。在《聊斋》中,更多的是美色与欲望的联系,而不是情与欲的联系。“美色为诱发人内心产生吸引感觉的要素,因此她将‘色’与‘情’联结起来。而这种吸引的感觉又会反过来加深对美色的欣赏。”[8]笔者认为从《牡丹亭》到《聊斋志异》反映的是明末清初这一时代对“欲”的肯定与大胆的追求,对“美”的欣赏与渴望,这是天性的释放,是追求本真的自我。
三.女性的主动
女性成为绝对的主角,异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男女之大防,女子主动的思慕异性,是《牡丹亭》与《聊斋》的最大特色。在这些婚恋故事里,作者把女性从一贯的幕后推到了幕前。《牡丹亭》中对柳生的笔墨并不多,连容貌与性格都不分明,没有字句描绘。恋情的主导者归于杜丽娘,因为她春心动,才有了春梦,春病,才有了人鬼恋的可能。她是“欲”和“情”的发起者和承载者。《聊斋》虽然也写了男子的欲,但是对女子的刻画更为细致突出。她们是“美”的化身,尽管她们大多非人,但是“美”的吸引足够抵挡住对异类的恐惧。鲁公女“丰姿娟秀”,娇娜“娇波流惠”,婴宁拈梅花,容华绝代,聂小倩“妖艳尤绝”,胡四姐“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媚丽欲绝”。《牡丹亭》突出的是女性对美的自我欣赏,杜丽娘对镜自照,画自画像,游园时对花草无人欣赏的哀怨,映射出她内心世界对自我的欣赏,同时也要求得到别人的欣赏,尤其是异性的欣赏。相比而言,《聊斋》更多的是从男性的角度来发现女性的美。但是在情的主动性方面,女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杜丽娘是最具有突破性的代表。她主动去寻找,但是她的寻找是隐形的,是不具备现实性的,所以这种突破也只不过是内心的遐想。杜丽娘想嫁人了,并未对父母言说,只敢在梦中肆意。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她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不允许她做出这种“有辱门风,不知廉耻”的事情来,这是有伤风化的。更不要提她还有个把人束缚得紧的爹,连自家园子都没让女儿逛过,整日将其关在闺房里。此种情况下,杜丽娘没有勇气诉说,更没有勇气决裂。她处在一个父权和夫权的社会,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只是作为依附者存在着,一旦脱离依附,生命将会终结。所以当恢复了人的身份之后,她需要回到现实世界,认回父母,婚姻必须被社会被家庭承认。《聊斋》则彻底抛却了这种现实性的根基,女性多是狐鬼或者精怪,她们的出现是在男子独居的时候突然降临,然后与男子过一段很随意的同居生活,不需要被承认,也不需要天长地久,合适就缠绵,不合适就分手,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更多的是处于强势地位,她们的态度决定着关系的持久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婚恋关系同样适用。花妖狐鬼通常具备超人的能力,不依附人生存,甚至大多数穷书生得依靠她们过活。在《聊斋》里,女性大多具备经营能力,掌管家庭生活。像素秋身怀绝技,阿纤十分勤劳,绩女善织布。故而,具备占有主动性的地位和可能。
当然明末清初,现实世界里,女子是否有这种觉醒的意识和争取自我的斗争,还并没有非常确切的根据。就拿主动性这一点来讲,从《牡丹亭》和《聊斋》来看,是不存在的。因为主动性必须是真实地自我的主动,且不说创作这些女性的是男性,赋予她们主动性的也是男性,在男性赋予的女性角色里,也就是在社会氛围下的男性观点中,女性在现实中依然不可能突破界限,所以他们在创作中幻想女性在不真实的世界里拥有主动性。
四.结语
《牡丹亭》和《聊斋》带给了读者关于那一时代很独特新奇的感受,两者之间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排开形式,它的的确确反映着明末清初的时代风潮。对人的肯定,对情对欲的真实追求。这两部作品揭示了当时的一个流行的创作模式:恋情的载体是梦幻,恋情的根源是色欲,恋情的主体是女性。那么整个时代好像是朦胧的掩映在雾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的场景。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观点,文学界做出了相应的反应,狂潮自然而然就兴起了。时代总是一步步发展着的,现实的变化总会引起思想的变化。明末出现了一批思想革新者,像“异端之尤”李贽就提出“士贵为己,务自适”的个性解放之观,他还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不仅仅是他,王守仁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也肯定人欲肯定个性的释放,而汤显祖的师傅罗汝芳恰恰是泰州学派的人。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他的作品自然带有反对礼教束缚,解放个性,肯定人欲的色彩。只是这种影响在男性身上有很明显的痕迹,女性却不尽然。
参考文献
[1]李惠仪,蔡碧野译.晚明时刻[M].徐永明,陈靝沅.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择.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31页
[2]蒲松龄.《聊斋志异》[M].山东:齐鲁书社,2009年4月.第115-117页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孙名之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年
[4]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5][6]汤显祖著,王思任评[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页、26-27页
[7]汤显祖撰,吴震生、程琼评[M]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社,2004年4月,第121页
[8]华玮.《牡丹》能有多危险[M]//徐永明,陈靝沅.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择.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1-233页
本文为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
(作者介绍:夏二姣,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