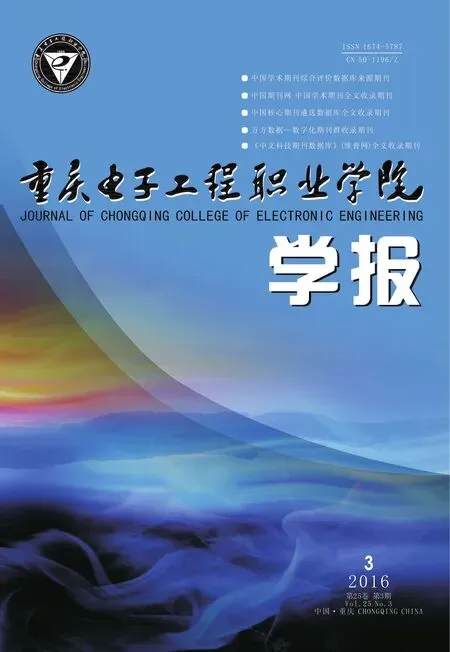“臭”的形义衍变考论
——兼释“三嗅而作”
李志文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
“臭”的形义衍变考论
——兼释“三嗅而作”
李志文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
“臭”在古代作动词表示“用鼻子闻”,作名词表示“气味、味道、香气、恶臭”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臭”的词义衍变做全面的考察,同时窥探词义变化与字形变化的关系。再基于“臭”词义衍变考辩的结论,对《论语·乡党》中“三嗅而作”之本义进行辨析,进而为形体与词义衍变关系提供实际例证。
臭;词义衍变;字形变化;三嗅而作
0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用鼻子辨别气味”多用“嗅”和“闻”,其中以“闻”为主导,而“臭”主要作名词表示“臭气”。通过对“臭”和“嗅”的语料进行历时梳理后发现,“臭”从先秦到西汉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作动词表示“嗅觉义”,即“闻”;作名词表示“气味、味道、香气、恶臭”等意义,且用法成熟。西汉以后,“臭”的动词用法逐渐被“闻”替换,“臭”作名词用法不变,“嗅”作动词的用法一直保留发展至今。汉字是表意文字,它是汉语词义的外部表现形式,词义又是汉语形体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因此,为满足人们表达的需求,词义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汉字字形的变化。
1 “臭”的词义衍变
1.1战国前
(1)贞御臭于母庚。(前五·四七·四)释为:疑为人名[2]。(《甲骨文字诂林》)
东汉许慎《说文·犬部》:“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3]和甲骨文所示的本义一致。
1.2战国末期至西汉以前
“臭”的词性和词义开始分化,主要用作名词。其义为“气味总称、味道、香气、恶臭之气”等。如:
(1)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
(2)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文王》)
(3)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语·晋语》)
(4)夫人之情,目欲其色,耳欲其声,口欲其味,鼻欲其臭,心欲其佚。(《荀子·王霸》)
“臭”作动词表示“闻”,“臭”单独作动词的用法不多。随着用法逐步成熟,词义也开始增多,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还用同一个形体,难免带来理解障碍。此时为交际需要和表意更加清楚准确,后世在“臭”的基础上增附类母“口”转形而作“嗅”,由会意字变成会意兼形声字,且“嗅”只能用作动词。在作动词这一词性上,“臭”与“嗅”音义相同,形体不同,“嗅”成为“臭”的异体字,因此,作动词两者可通用。例如:
(1)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庄子·天地》)
(2)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韩非子·十过》)
(3)彼臭之而无嗛于鼻。(《荀子·荣辱》)
(4)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庄子·人世间》
(5)主府笑而曰:“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韩非子·外储》
(6)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于颤。(《列子·杨朱》
“臭”作名词可以用作主语也可以作宾语,“嗅”与“臭”作动词主要充当谓语。“嗅”与“臭”的用法在这时期几部主要文献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1 (例数/总数):
可以清晰地看到,“臭”与“嗅”在这一时期共存,“臭”的用例较多,“嗅”的用例虽少,但它作动词的用法初现端倪。
1.3两汉时期
“臭”作名词的用法更加成熟。并在“臭”的基础上再增加相应的类母造字,如增附类母“歹”转形而作“殠”,《说文·歺部》:“腐气也。从歺臭聲”,段玉裁注:“腐臭也。按臭者氣也。兼芳殠言之。今字专用臭而殠废矣。”[4]《说文·歺部》:“歺,骨之殘也。”[3]则“殠”表示与肉相关的事物腐烂、坏烂之臭,作名词。例如:
(1)其味苦,其味臭。(《礼记·月令》)
(2)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秦始皇本纪》
(3)焦,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礼记注·月令》
(4)傅太后棺臭闻数里。(《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十一》)
(5)以芬香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为乱耳。(《盐铁论》)
(6)发棺时臭憧于天。(《论衡·死伪》)
(7)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前汉书》)
“臭”作动词的用例,在以上文献中,我们尚且发现《论衡》中有一例。但是这个动词不是“用鼻子闻”的这个动作,而是表示“发臭、变臭、变味”的意思。其词义又进一步扩大。
(8)醢暴酸者易臭。(《论衡·状留篇》)
“嗅”作动词的用法在以上文献中尚未发现用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未收录“嗅”,但该字在先秦文献中有用例,并且都是用在主要文献典籍中,我们认为当属许慎漏收。但他收录了“齅”,后人更换类母“口”为“鼻”转形作“齅”,改换为“鼻”,更加突出“用鼻子闻”这一义项。《说文·鼻部》“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声,读若畜牲之畜”[3],即“用鼻子闻”,作动词。正好与“臭”和“嗅”作动词的词义一样,则“臭”和“嗅”、“齅“构成异体关系。该时期文献中目前只发现一例,即:
(1)不絓圣人之罔,不齅骄君之饵。(《汉书·叙传上》)
“嗅”与“臭”的用法在两汉时期几部主要文献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2 (例数/总数)
“臭”的用例不多,并且在这些例子中以名词性用法为主,与先秦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作动词更是微乎其微。“嗅”作动词的用例我们目前也尚未发现。但诸多文献中不可能没有“用鼻子闻”这一意义的词。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嗅”和“臭”表示“用鼻子闻”的意义可能被另一个词代替。
洪成玉先生在《释“闻”》中指出,“闻”在古书中最常用的用法是表示听觉,即耳闻[5]。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闻之言分也;谓声音气臭之分布;有接于人之耳鼻也。声通于耳谓之闻;臭触于鼻亦谓之闻。”“闻”其义包含了声、臭两方面。常媛媛《“闻”与“嗅”的历史替换研究》中认为:“在战国末期开始用‘闻’来表示‘用鼻子闻’这一动作,但是‘闻’还是以听到占主导,同时表示‘用鼻子闻’这一动作以‘臭’为主。西汉以后‘闻’表示‘用鼻子闻’的用法在这一时期替换了‘臭’和‘嗅’。”[6]徐时仪先生在《“闻”的词义衍变迁嬗考论》进一步指出进入魏晋“闻”替换“嗅”和“臭”的用法趋于完善,并一直沿用到今天的现代汉语中。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嗅”和“臭”表示“用鼻子闻”这一动作在西汉以后逐渐被“闻”替换以至两者的用法极少。在《论衡》中,“闻”总计出现472次,“用鼻子闻”这一动作用例6次。而“嗅、臭、齅”则无用例。考察同期的文献,情况也大致如此。
1.4魏晋至今
魏晋之后,“嗅”与“臭”无论是在口语性强如小说、语录、话本、杂剧、笔记、宗教翻译类文献等,或者传统的文言文性质的文献中,两者作动词表示“用鼻子闻”这一动作用例仍不及“闻”的用例多,“闻”还是占绝对的优势。“嗅”仍然保留作动词的用法,一直延续至今,还可以和语素“觉、闻、神经”固定成词。例如:
(1)不为时用,嗅禄利诚为天下无益之物,何如?(《抱朴子·外篇》)
(2)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散嗅馨香泣。(《杜工部集》)
(3)无罪者,嗅而不食。(《太平广记》)
(4)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点绛唇》)
(5)数其影约十余,以巨杯挹酒洒之,皆俯嗅其气。(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6)可是,人的嗅觉毕竟不能和猎犬相比。(李先定《峨嵋深情》)
“臭”作动词的用法进一步弱化,主要用作名词,且作名词表“气味总称、味道、臭味、香气、腐败”等义缩小到只有“臭气、气味”,发展至今,其词性有所扩大,出现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用法,后面可以接动词,也可以加名词。例如:
(1)对他们的想法,最好是臭骂一顿。(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2)他修表技术四城有名,可车工手艺却臭得厉害。(张征《天时》)
(3)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叶永烈《谁的脚印》)
这时期关于“齅”的用法更少,只是在古代少量的文献中有依稀用例。
2 “三嗅而作”本义辨析
基于前文从词义变化和字形变化的角度对“臭”和“嗅”词义的衍变的探讨,我们就《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中“三嗅而作”进行本义辨析。杨伯峻《论语译注》云:“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很满意的解释,很多人疑它有脱误。”[7]其实要理解本节文意,正确解读其中的“嗅”是一个关键。
“三嗅而作”之“嗅”历来争议较大,有的版本作“嗅”、“齅”、“臭”等。《论语注疏》谓:“‘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8]阮校:“按《说文》止有‘齅’字,‘嗅’乃‘齅’之俗字。”《论语集释》:“《五经文字》:《说文》‘齅’字,经典相承作‘嗅’,《论语》借‘臭’为之。”[9]《玉篇》“齅”下引作“三齅而作”。“嗅、齅、臭”在先秦作动词其义都表示“用鼻子闻”。“臭”最早产生,嗅与齅都是在“臭”的基础上分别增附类母“口”转形而作“嗅”,增附类母“鼻”转形而作“齅”。此三者形体不同,音义相同,构成异体关系,是同一个形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嬗变的面貌。此处无论是用哪一个形体,其义都是表示“用鼻子闻”。
前文孔子与子路于山梁见“雌雉”,孔子感叹它们得其时,于是“子路共之”,即向它们拱拱手。钱穆《论语新解》:“共作拱,竦手上拱,作敬意也。”[10]以感叹“雌雉”得其时,而己不缝时,拱手以示敬意。与前文“色斯举矣”相对,鸟见子路拱手,乃惊也。若后文“三嗅而作”释为“闻了闻就飞走”,亦不合文义。
杨伯峻《论语译注》:“‘嗅’当作‘狊’,jǜ,张两翅之貌。”钱穆《论语新解》:“‘嗅’本作‘臭’,当是‘狊’字,从目从犬,乃犬视貌,借作鸟之惊视,雉见子路拱其手,疑将篡己,遂三嗅而起飞。”[7]《说文·犬部》:“狊,犬视儿,从犬目。”[3]将“目”放在上面,以突出犬见状而目睁大,同时犬的上半嘴会伸展开来,如同鸟张开翅膀一样,以喻鸟张翅之貌。《尔雅·释兽》:“鸟曰狊”,郭璞注:“张两翅。”[11]《字汇·犬部》:“狊,鸟张两翅曰狊。”[12]《说文》同时收录“臭”、“狊”,两者形体相似,仅有一笔之别。此处当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误将“狊”作“臭”,而“臭”又和后来产生的“嗅”与“齅”音义相同,形体有别而造成误用。于是“狊”与“嗅、齅”相去甚远,这是古人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普遍存在的讹误现象。我们认为杨伯峻与钱穆得其本。因此,“三嗅而作”之“嗅”当作“狊”,释为“雌雉振一振翅膀飞走了”,才有前文总结性的“翔而后集”,同时与前一句“子路共之”之语义相协。
3 结语
总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臭”随着词义的不断变化,其字形也会有所变化。如:嗅、齅。这两者作动词和“臭”作动词一脉相承,他们形体虽异,但音义相同,构成异体关系的字组。因此,对词义的衍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文献的校订,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行词义的替换演变的探讨。宋永培先生认为:“汉字是形体和意义有着紧密关系的文字,远古先民创制某一特定的文字是为了表达某一特定的事物与现象,是具体而象形的,直接而切实的。词义的引申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开来。”[13]因此,对于词义的分析我们在了解它的源头的同时还要对它的历时发展和共时变化作出分析。词义的变化往往伴随着词字形的变化,词义的分析在描写词义的变化的同时还应兼顾字形变化。
[1]李圃.古文字诂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598.
[2]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5,85,74,204.
[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43.
[5]洪成玉.释“闻”[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5.
[6]常媛媛.“闻”与“嗅”的历史替换研究[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08.
[8]邢昺.论语注疏[A].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1980:95.
[9]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730.
[10]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5:126.
[11][晋]郭撲,[宋]邢昺.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20.
[12]梅膺祚.字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13]宋永培.中国训诂学[M].广东:广东教育文出版社,2000:320.
责任编辑 闫桂萍
Study on the Shape and Meaning Change of“Xiu”——And Explain the Meaning of“San Xiu Er Zuo”
LI Zhiwen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 Sichuan 610041,China)
“Xiu”used as a verb refers to the meaning of“smell with the nose”;used as a noun means “smell,taste,aroma,stench”in ancient times.This paper will show the study of its meaning change from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ngle,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form and meaning change,trying to explai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San Xiu Eer Zuo”in“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Village”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aning change of“Xiu”and further to provide the actual example.
Xiu;development of the word meaning;font change;San Xiu Er Zuo
H139
A
1674-5787(2016)03-0115-04
10.13887/j.cnki.jccee.2016(3).31
2016-04-10
李志文(1988—),男,贵州贵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