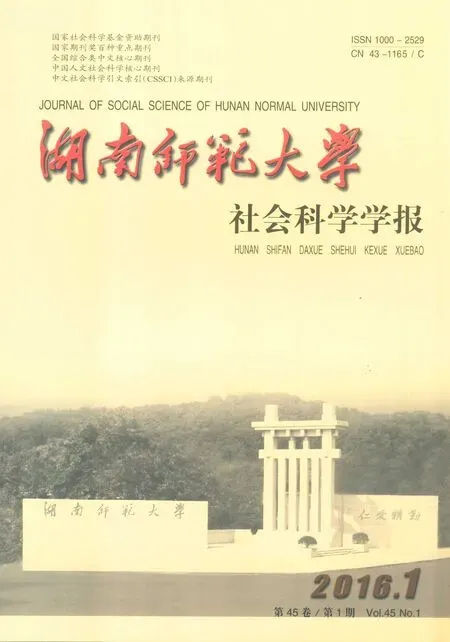胡适关于新文学与国语建设的三种价值维度
文贵良
胡适关于新文学与国语建设的三种价值维度
文贵良
“死”与“活”作为一对不太清晰的价值区分概念,其实用主义的倾向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哲学基础。“文言”与“白话”的语体区分,其进化论色彩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历史基础。而文学革命以及文字改革的主力都在小老百姓的动力来源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平民主义态度。当然,实用主义、进化论、平民主义弥漫在胡适关于文学与国语的所有论述中。“文学”与“国语”的结盟,即以“国语的文学”造“文学国语”,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本体论部分。
新文学;国语;实用主义;进化论;平民主义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写道:“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①。“归功于胡适”并非把开创白话文时代的所有功绩都归于胡适,而是强调胡适对于开创白话文时代的“头功”。胡适自己曾认为如果没有他们一辈人的有意提倡,白话文时代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到来,但不过至少要迟二三十年。穿过近百年文学上的历史烟云回看胡适当年的文学主张,我不得不承认,胡适以白话取代文言、以活文字取代死文字、以活文学取代死文学、以国语的文学建设文学的国语的观点,睿智地为推动文学的现代转型找到了最为恰当的杠杆支点,从而催生了强大的力量。
一、“死”与“活”:实用主义
1915年8月26日,胡适记载作一英文论“如何可使中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该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以“死”“活”来区分文字。他写道:
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②
这里“汉文”一词的指向并不太明确,大致指书面的文言,与被称为“活文字”的“吾国之白话”相对。1916年7月6日的日记把这种意思明确化了:“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③。“死文字”可指语言,如拉丁语;可指文章,如拉丁语文;也可指文字,如拉丁语字词。其核心意义是不再被人们使用。“半死文字”介于“活文字”与“死文字”之间,即介于“日用语言之文字”与“陈死”文字之间。“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意思指汉语书面语中有些汉字属于已“死”文字。可见,“死”、“半死”与“活”三者之间的区分在于“日用”与否,但是“日用”与否却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法区隔,“日用”与使用频率有关,其间切分有无限多的方式。“死”与“活”这是一对区分不太清晰的价值概念。
胡适在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的辩难中,不断提升“死”与“活”这对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任叔永《泛湖即事诗》中有一段借用古代描写大江风浪的词语来写湖水,胡适毫不留情地批判为“小题大做”④,并指出作者“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任诗中所用的“言”字、“载”字都为“死字”;“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中前一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后一句为“三千年之死句”⑤。他的观点遭到另一朋友梅光迪的坚决反对。梅光迪反对胡适以“活字”入文学的文学革命,认为“文学革新”“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⑥,并且认为胡适所谓“廿世纪之活字”也是古人所创。只有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俗语白话只有经过美术家之锻炼方可用。胡适从梅光迪的观点中敏锐捕捉到与自己观点趋同的东西:“我正欲叩头作揖求文学家、美术家,采取俗语俗字而加以锻炼耳”⑦。胡适“死”与“活”的区分把思想与文字结合起来:“思想与文字同无古今,而有死活”⑧。因此他更坚定地相信文字有死活:“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⑨。胡适那么强烈地祛除文字的“古今”之分,而高扬文字的“死活”之别,目的只有一个:突出文字是否可以为今人所使用,是否可以进入今人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言说之中。胡适也尝试着用“死”与“活”来区分古代的书面语言,比如他举《尚书》的例子:“惠迪吉,从逆凶”。从作文的角度看前一句是死语,后一句是活语。从听的角度看,后一句也是半活之语⑩。这样一种思路是他撰写《白话文学史》与《国语文学史》的起点,古代文学中的“活语”奠定了古代白话文学作为活文学的基础。
胡适把文字的“死”与“活”带到了五四时期。到底如何理解文字的“死”与“活”?一个人因为哮喘停止呼吸,几分钟后人即“死”。就这个人来说,构成人身体的物质并没有改变。原因在于氧气无法进入体内,因为人自身已经丧失吸入氧气的能力,无法维持身体的正常需求。人无法维持自身基本需求的状态即谓之“死”。文字不被人们使用,意味着它已经丧失进入新的言说的能力,谓之“死文字”。其中情形比较复杂,因为文字不像人非死即活。有些汉字,人们已经很长时间不用,或许永远不会再使用,比如梅光迪列举的关于马的汉字:“言文学革命第一要事,即在增加字数,字数增而思想亦随之,而后言之有物”。他举的例子有:二岁马曰驹,三岁或四岁马曰马兆,八岁马曰马臼,白额马曰马勺,马饱食曰马必,二马并驾曰骈。梅光迪主张效法法国雨果的文学革命,revive多数古字,“将一切好古字皆为之起死为生”⑪。还有一种情形,一个汉字有多种意义,某种意义已经不再使用,从不再使用这种意义的角度看,这个汉字就是死文字。其实从语言的历史角度看,所谓“死文字”都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随时可能因被召唤而苏醒。五四时期,为了应对印欧语系的形容词词尾的变化,不再做助词的“底”被唤醒而作为表述所属格的助词,如“海底梦”。近年来网络媒介每年会产生一些热门词汇,其中“囧”于2008年成为网络热门词语之一,就是一个从沉睡的状态中被唤醒过来的字。“囧”的本义是“光明”,而网络用语中被赋予新的意义,表示“抑郁、悲伤、无奈”等意思。
“死”与“活”是一对灵活的概念,胡适同时把它们用于文学。胡适1916年在美国读书时就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活文学”的样式。他列举的“活文学”样本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以及元代以来的杂剧与章回小说。不过他举的例子中有南唐李后主的词,宋代苏东坡、黄庭坚、辛稼轩、吕本中、柳耆卿、向镐的词,曲有《琵琶记·描容》、《孽海记·思凡》、《孽海记·哭皇天》、弹词《长生殿·九转货郎儿》,其中尤为欣赏《孽海记·哭皇天》的末一段,称赞其“文妙,思想亦妙”。“文妙”在于其语言“畅快淋漓,自由如意”;“思想亦妙”表现为思想上的“革命文字”,攻击僧尼制度的不近人情之处,可为中国之问题戏剧(problem plays),堪与卜朗吟(布朗宁)的Fra Lippo Lippi相比⑫。可见“活文学”不仅文字语言属于活文字,而且思想上也有其革命之处。
胡适在五四时期通过“死”与“活”这对概念把文字与文学联系起来: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⑬
胡适的意思非常清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活文学必须用白话(活文字)来做文学的工具,但是仅仅是活文字还不能产生活文学。“活文学”不等同于白话文学。胡适的主张简单说就是用白话造活文学,但是仅仅用白话还不能造活文学。因为在胡适看来,白话只是工具,白话与思想是二分的。
对于胡适的“死文学”与“活文学”的区分,一直有人质疑。同是新文学阵营里的周作人就提出不同看法。1927年他在《死文学与活文学》中写道:
不见得古文都是死,也有活的;不见得白话文都是活的,也有死的。⑭
国语古文的区别,不是好不好死不死的问题,乃是便不便的问题。⑮
死文学活文学的区别,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方便不方便,和能否使人发生感应去判定他。⑯
周作人讲的“方便不方便”的问题从字面上看,比“死/活”这对词语更感性,更不可捉摸,而“能否使人发生感应”这种对读者的重视,还与胡适的观点不完全一致。要做到使人发生感应,首先作者要做到自己能对时代感应。胡适关于“死文字”造“死文学”、“活文字”造“活文学”的众多论述,总归一句话就是:只有当代的“活文字”才能造当代的“活文学”,这种“活文字”就是当代的白话;同理,“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⑰。可见,“死”/“活”的价值区分突出文字的实用性。
二、白话与文言:进化论
尽管“死文字”常常与“文言”配对,“活文字”往往与“白话”结盟,但是“死文字”不等同于“文言”,“活文字”也不等同于“白话”。按照胡适的观点,“文言”乃是“半死的文字”,但是胡适从来没有彻底否定过文言,他彻底否定的是“死文字”。他留学美国时期,就反对那种诋毁汉文、采用字母的主张,而认为“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以其为仅有之各省交通之媒介物也,以其为仅有之教育教授之具也”⑱。汉文不能普及的根源不在汉文自身,而在教育方法的不完善。
文言与白话的区分,建筑了五四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两大阵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抓手,而且白话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有两大问题需要辨析,第一是文言与白话的区分到底在哪里?第二,如何评价文言与白话?
胡适1916年7月6日的日记列出九条进行白话与文言之优劣的比较,提出了五四至1930年代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主要问题。胡适主张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作小说,理由如下: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实用。凡言语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如“赵老头回过头来,爬在街上,扑通扑通的磕了三个头。”生动有趣,如译作文言则趣味顿失⑲。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
(3)文法由繁趋简。
(4)文言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⑳。
(七)白话可生第一流的文学。如白话的诗词,白话的语录,白话的小说,白话的戏剧㉑。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小说,戏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㉒。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㉓。
第六条谈白话为文言的进化问题,实际指向是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属性。其余八条指向文言与白话的价值评判。第六条把文言与白话的区分落实在语言这块基石上,因为无论文言与白话在语体、文体上如何不同,两者都是语言问题。胡适的区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词语方面,文言单音词多,白话复音词多;语法上,文言不自然,白话自然;文言繁杂,白话简单。张世禄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言和白话的区分,可以看作对胡适的观点的补充和发展。张氏从四个方面区分文言和白话:第一,因为音读演变的原因,相同意思或相类的语词,文言和白话会用不同的语词表示,如第二人称代词,文言中多用“尔”“汝”“若”“而”“乃”等词,而白话中用“你”。第二,因为语义演变的原因,往往同一个词,在文言和白话中表示不同的意义,因而其用法也不相同。第三,因为语词组织的变异关系,文言多单词,白话往往改用复词。第四,因为语句组织的变异关系,文言的语句次序与白话的语句次序有很多不同㉔。很明显,张氏着重理性的学术探讨,而胡适因急于提升白话的价值,即使从语法角度区分文言和白话,都是倾向白话的。
文言与白话的价值区分,主要表现在文言是半死的文字,可读而不可听,不能造就活文学;白话是活的语言,可读,可听,能实现人们表情达意的目的,优美实用;白话已经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是造新文学的唯一利器。胡适写道:“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事实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㉕
造新文学,唯一的利器是白话。但是否可以绝对排斥文言?胡适的认识有过变化,原来他曾经肯定过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在创造《尝试》集的时候并不排斥文言中的某些词汇㉖。与此问题相关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应用文是否全用白话,艺术文是否白话文言并用?五四时期的蔡元培肯定白话以及白话文最终将会胜利:“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一定占优胜的”㉗。不过他也没有彻底否定文言:“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还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㉘。
三、文字改革的主力是老百姓:平民主义
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提出研究语言文字时发现的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还有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㉙。小百姓所做的汉字形体上的“惊人的革新事业”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胡适列举的汉字有:“萬”改作“万”,“劉”改作“刘”,“龜”改作“龟”,“亂”改作“乱”,“竈”改作“灶”,“蘆”改作“芦”,“聽”改作“听”,“聲”改作“声”,“與”改作“与”,“靈”改作“灵”,“齊”改作“齐”,“齋”改作“斋”,“還”改作“还”㉚。
胡适读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大赞“马眉叔用功之勤”㉛,《马氏文通》术语完备,条理清楚,方法精密,建立了中国文法学。但胡适批评马建忠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认为马建忠把“文法定律历千古不变或者很少变化”。马建忠看到的是中国语法稳定的一方面,胡适更关注中国语法变动的一方面。胡适认为语法变化主要在民间语言中发生:“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文言文中否定句里做止词(宾语)的代名词要放到动词前面,如“莫我知”、“不汝贷”、“莫之闻、莫之见”的文言结构,“鹦鹉文人”不敢改动,可是一般老百姓不怕得罪古人,不知不觉地改成“没人知道我”、“不饶你”、“没人听过他,也没人见过他”。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中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与文人、文法学者没有关系㉜。
胡适1921年指出,当时所讲的国语还只是一种“候补国语”,已经具备做中国国语的资格,但还不是正式的国语。所谓国语是“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㉝。胡适坚信国语是进化的观点,他反驳了某君在《评新旧文学之争》中提出的所谓文言“虽未甚进化,亦未大退化”而白话却退化了的观点,也反对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提出的“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的观点。胡适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给出一个评价进化退化的标准: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应用的,应用的能力增加,便是进步,应用的能力减少,便是退步㉞。从古代文言变为近代的白话,语言的变化表现在:第一,改变繁的都变繁了;第二,改变简的都变简了。变繁的例子:(1)单音字变为复音字;(2)字数增加。变简的例子:(1)文言里一切无用的区别在白话中废除了。(2)繁杂不整齐的文法变化多演变为简单画一的变化了。(3)许多不必有的句法变格,都变成容易的正格㉟。胡适称之为“中国国语的进化小史”,其功绩要归之于“乡曲愚夫,闾巷妇稚”,这是那些文学专门名家不能做又不敢做的革新事业㊱。
有学者认为胡适的语言文字观过多地依赖于进化论,并不恰切。胡适的语言文字观确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但胡适的语言文字观还有其他思想的影响㊲。文字改革的主力是老百姓这种平民主义观点,其深层的思想原因源于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把中国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解释为“三W的不朽主义”(worth、work、words)㊳,继而发展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观念。其核心意思是,任何小我对于社会、人类或者大自在的那个所谓大我,总会留下某些痕迹㊴。19世纪西方思想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美国作家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认为“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或是通过其中的一种禀赋得以体现;你必须观察整个社会,才能获得对完整的人的印象”㊵。美国思想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认为“我们全都归属于社会”㊶,有学者这样解释梭罗的“社会”一词:社会“既是近在眼前的那个帮我们盖房子的人,又是遥远的先祖留下的遗迹,还有古代哲学家们的那些文本”㊷。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㊸。“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㊹斯宾塞认为理解人的认识,是对社会认识的第一步㊺。他提出的“第一原理”即作为正确的社会关系的法则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其内涵是“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㊻。
这些学者对人的理解都是把人放在社会中理解,虽然他们各自对社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这点对中国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为把人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与封建皇权伦理中解放出来打开了一扇窗口。胡适1919年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把《左传》的“三不朽”说改造为“社会的不朽论”㊼。胡适从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关系考察个体生命的永恒性。个体生命就是“我”,就是“小我”,而社会、历史就是那个“大我”。个体/“小我”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社会/“大我”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个体/“小我”只是社会/“大我”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细胞。胡适的社会不朽说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小我”看似短暂,但与社会的未来密切相关,无数的小我构成大我,以此种方式通向未来㊽。其次,社会不朽的要素“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㊾。
四、文学与国语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学革命的目的“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㊿。无论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国语的角度,胡适的十个大字都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上高高飘扬的大纛。这其中凝聚着晚清以来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因国家命运起伏跌宕而变革的诸多伤痛,同时也内藏了以建设“新中华”为价值取向的变革路向。这一观点在此不展开论述,在此要关注的是胡适理解文学与国语之间互生关系的理路。
第一,什么是胡适所说的“国语”?

第二,胡适为什么会把文学与国语结合起来作为自己文学革命的新旗帜?当胡适在美国与朋友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国语运动在国内早就已经开展。国语运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清简字拼音方案的制作。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教育部成为“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求“书同文”,同时从普及教育和开通民智的角度要求“话同音”。《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刊载了《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以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写道:




我们所提倡的国语的中坚分子:“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也是《水浒传》《西游记》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白话。”

其实,这种“文不文,白不白”、“南不南,北不北”的“南腔北调的国语”表明国语建设的坚实基础。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改成“四条”主张: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八不主义”中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被取消了,代之以“四条主张”中“说话”中心论。这就打通了“白话”与“国语”的连接。
第四,如何理解以“国语的文学”造“文学的国语”?这是人们常常纠缠不清的地方:没有文学的国语,何以造国语的文学?简言之,没有国语,如何造文学?其实不妨这样理解:“国语的文学”中的“国语”是“现有的国语”,“文学的国语”中的“国语”是“理想的国语”,那么胡适的宗旨就可以表述为:“国语的文学”以“现有的国语”来创造文学,通过文学而不断锤炼“现有的国语”,使得“现有的国语”在文学的不断进化中而发展,从而走向“理想的国语”,达到“文学的国语”。



胡适谈论文字、语言和文章往往紧紧依靠着文学而谈,要想从他的言论中剥离出纯粹谈文字语言的内容非常困难,在此就没有分论胡适的语言文字观和文学观,而是结合着一起阐释。“死”与“活”作为一对不太清晰的价值区分概念,其实用主义的倾向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哲学基础。“文言”与“白话”的语体区分,其进化论色彩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历史基础。而文学革命以及文字改革的主力都在小老百姓的动力来源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平民主义态度。当然,实用主义、进化论、平民主义弥漫在胡适关于文学与国语的所有论述中。“文学”与“国语”的结盟,即以“国语的文学”造“文学国语”,成为胡适文学与国语观的本体论部分。
注释:
①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⑥⑦⑧《梅光迪复胡适》(1917年7月17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2页,第1203页,第1202页。
⑪《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8月8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8页。
⑬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⑭⑮⑯周作人:《死文学与活文学》,《大公报》1927年4月15日,引自钟叔和编《周作人文类编3》,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第103页,第103页。
⑰㊿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
㉔张世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社会科学》1939年第3号。
㉕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㉖胡适以“文言”/“白话”的区隔切入对文学的区分,遭遇到古代白话诗与现代白话诗之间区分的阻碍,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参看李丹《论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㉗㉘蔡元培:《国文的将来》,朱麟公编辑:《国语问题讨论集》,中国书局,1921年,第44页,第45页。
㉙㉚胡适:《〈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3年。
㉛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㉜胡适:《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㊲周晓平:《从黄遵宪到胡适:“五四”新文学何以可能》,《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㊳㊴㊾胡适:《我的信仰》(1931),《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第19页,第19页。
㊵(美)爱默生:《美国学者》,《爱默生集》(上),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63页。
㊶(美)梭罗:《瓦尔登湖》,潘庆舲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㊷(美)斯蒂芬·哈恩:《梭罗》,王艳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页。
㊸㊹(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第18页。
㊺㊻(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页,第52页。
㊼㊽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原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引自《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9页,第479页。









(责任编校:文建)
On Hu Shi’s Three Valuble Dimensions about New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Language
WEN Guiliang
In Hu Shi’s theory of new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language,the pragmatism about the different valuble concept about“death”and“life”is the philosophical base;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s of“classcial Chinese”and“vernacular”is the hostorical base;the populism that main forces of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reform of writing systom are the common people is the subject base.Of course,pragatism、evolution and populism pervade all over discussions of Hu Shi’s theory of new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language.
New Literature;National Language;vernacular;pragmatism;evolutionism;populism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