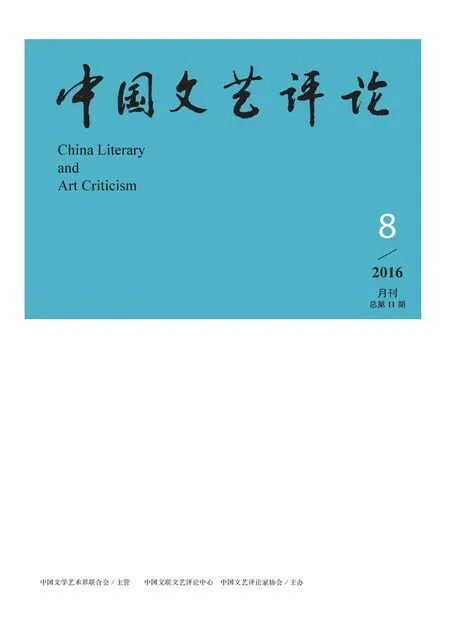经典的跨文化传播与解读
—谈“二度西潮”期间的契诃夫戏剧演出
吴小钧
经典的跨文化传播与解读
—谈“二度西潮”期间的契诃夫戏剧演出
吴小钧
编者按:时代呼唤经典,经典需要阐释。重读经典,为的是从前贤那里汲取智慧和勇气,更好地回应当下的问题。而对经典的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思想火花和艺术体验,这也是经典永恒的魅力所在。

契诃夫
一
“重读契诃夫”,是契诃夫戏剧研究的一个专有名词,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最早出现“重读”的是在西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50年代的初期,代表人物是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马丁·艾斯林,他发现契诃夫戏剧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出现在贝克特、品特等现代派剧作家的作品中。而明确提出“重读契诃夫”的则是在1960年的前苏联,当时正是处于为期十年的“解冻文学”时期,爱伦堡在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时发问:难道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契诃夫是为了了解19世纪的俄国的阶级斗争?我们读契诃夫,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永恒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大陆,则又晚了三四十年;“重读”一说是在世纪之交提出的,而真正对契诃夫戏剧成功“重读”的则是在“二度西潮”[1]。
1998年4月,林兆华的《三姊妹·等待戈多》在北京首演,算得上是当年的一起文化事件,笔者没有看过那一次的演出,不过后来《南方周末》的报道给我的印象很深,据称此剧受到冷遇,演出过程中观众纷纷退场,能够坚持到闭幕的观众似乎只有一二百人。如果说那一次是因为演出在当时比较先锋的话,那么时隔十年之后的另一次契诃夫戏剧的演出则更能说明问题。
2007年10月,被称之为“欧洲戏剧界宠儿”的俄罗斯圣彼得堡青年艺术剧院携带《三姊妹》应邀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是历史上第一家登上上海戏剧舞台的俄罗斯专业话剧院团。它也是自2004年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契诃夫忌辰100周年“永远的契诃夫”戏剧节演出《樱桃园》之后,第二个来华演出的俄罗斯戏剧专业院团。这一版本的《三姊妹》首演于2005年,执导该剧的是被誉为“涅瓦河上最有才华、最具魔力的导演”谢苗·斯彼瓦克。演出既忠实于契诃夫戏剧的精髓,又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此剧是在拥有千人座的上戏剧院演出,只有两场,笔者全都观看,开场近乎满座,由于每一幕的幕间都有休息,于是每一次的休息都有人退场,剧终大约只有一半不到的观众,俄方演职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据笔者了解,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观众对于文本不甚了解,有的甚至都没有阅读过。
但是,在“二度西潮”期间,这一现象大为改观。2013年6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万尼亚舅舅》首演,首轮16场,平均上座率93.4%。现在该剧已经成为剧院保留剧目,而且上座率稳中有升:2014年演出10场,上座率98%;2015年也是10场,上座率98.6%。此外还曾经去宁波巡演,上座率不俗。此剧首演之前,沪上媒体只是一般性地发了消息,未有深入报道。但是我在观看演出的同时,特意留意了观众席的反应,结果发现观剧氛围很好,凡是应该出效果之处都有反响。
二
为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剧场效果?原因可作如下分析:
(一)“二度西潮”时期的契诃夫戏剧与此前的契诃夫戏剧演出的比较与衔接。
契诃夫戏剧最早的中译本(目前所知是1921年郑振铎的《海鸥》),至今已有95年;契诃夫戏剧第一次登上中国舞台(1930年辛酉剧社的《文舅舅》)至今已经85年。[2]从那时至今,契诃夫戏剧在中国大陆的演出的大致阶段是:
1. 1949年之前,仅只演出三部契诃夫的剧作,分别是,1930年《文舅舅》,上海辛酉剧社;1936年《三姊妹》,上海女声社;1939年《樱桃园》,苏联侨民俱乐部。而且都是集中在30年代的上海。
2. 1949年至1966年,所谓的“十七年”,也是三部,集中在1954年至1960年的六年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万尼亚舅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三姊妹》;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的《樱桃园》。
3. 1960年代至1980年代,整整30年间,契诃夫戏剧演出几乎一片空白。只有在80年代,中央戏剧学院演出过一台《海鸥》。
4. 1990年代,十年期间一共上演七部契诃夫戏剧:1990年,上海戏剧学院的《海鸥》;199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海鸥》;1992年,北京电影学院的《三姊妹》;1993年,上海戏剧学院的《万尼亚舅舅》;1994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樱桃园》;1997年,上海戏剧学院的《海鸥》;1998年,林兆华工作室的《三姊妹·等待戈多》。其数量是1930年至1980年代的60年间数量之和。虽然只局限于京沪两地,而且一半以上是艺术院校的教学剧目(57%);但是出现了大陆“重读”的先声,即林兆华改编并执导的《三姊妹·等待戈多》,尽管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契诃夫戏剧。
5. 新世纪的前十年(2001年至2010年),这一时期,契诃夫戏剧的演出与此前相比出现崭新的现象。就其演出剧目的数量而言,总共有16台(其中有两部剧目是二度演出,林兆华的《樱桃园》和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安魂曲》),超过了前70年的14台的总量;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以契诃夫戏剧为名的国际戏剧节:2004年“永远的契诃夫”,演出的剧目不再仅仅是契诃夫戏剧,还包括根据契诃夫短篇小说改编的《安魂曲》《契诃夫短篇》等,也有反映当代人与契诃夫戏剧关系的《我是海鸥》;演出的样式愈加丰富,譬如中国戏曲学院移植的《樱桃园》首次将契诃夫戏剧搬上京剧舞台,譬如林兆华的《樱桃园》更加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此外,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来自契诃夫故乡的专业院团以及以色列、加拿大、匈牙利等外国院团的参演。但是,如果进一步考量的话,以上种种现象还是表面的,仍然存在着短板:譬如仅就受众面一项而言,还是相当狭窄,所有的演出局限于京沪两座城市,如果除去“永远的契诃夫”国际戏剧节集中在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六台剧目和五台艺术院校的教学剧目,那么在这十年中更多的时间里能够让观众看到的契诃夫戏剧实在是微乎其微了。所以契诃夫戏剧于国人而言仍然是陌生的、神秘的。这也就是我为何在当时撰文批评林兆华的《樱桃园》的缘故,因为“中国观众对契诃夫的《樱桃园》的熟悉程度远远不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外国名剧,更不要说与曹禺的《雷雨》等我国的名剧相比了。在相当多的中国观众对《樱桃园》这样一部极为复杂的剧作还很不熟悉、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实验、革新,甚至颠覆,是否合乎时宜?在没有比照的情况下,它是否会使观众以为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契诃夫的《樱桃园》就是这样的?”[1]当然必须承认,之所以批评林版《樱桃园》也包含着对于该剧人物形象以及形象体系的把握、剧作结构与情节处理的意见。
6. 2011至2015年,即所谓“二度西潮”时期,契诃夫戏剧演出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质的提升阶段。一是演出的数量,五年27台剧目,平均每年5.4台剧目,是新世纪前十年年均1.6台的3.4倍;更是上一世纪70年间演出总量的近两倍(1.93)。二是演出的地域,终于从京沪两地走向天津、沈阳、南京、西安、长沙、合肥、宁波、青岛等十余座城市。三是演出形态多元多姿多彩,譬如演出的院团既有正宗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了《樱桃园》),也有以幽默而充满节奏感的形体表演风格和对契诃夫作品的解构方式获得世界剧坛关注的美国运动集市剧团(演出了《站台3》和《安东尼的舅舅们》);既有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国家一线院团,也有像北京的蓬嵩剧场民营社团(演出了《三姐妹.7z》)、个人与民营文化公司的合力制作形式(演出了《海鸥》),以及包括像赖声川的戏剧工作坊、林兆华的工作室、中央戏剧学院的“行动艺术讲习所”等演出单位,当然更有一直以来在此领域从不缺席的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公演;此外还聘请了俄罗斯著名导演来华执导契诃夫戏剧,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万尼亚舅舅》和中央戏剧学院中青年教师演出的《樱桃园》。在上述琳琅满目的演出中,主流还是契诃夫戏剧的演出,有18台(次);改写或解构的有五台,与契诃夫生平有关的有四台(次)。四是契诃夫戏剧的演出趋向常态化,有三分之一的演出是其二轮甚至是三轮的演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万尼亚舅舅》,作为保留剧目,自2013年首演至今,连续三年上演,并去宁波巡演。此外还有林兆华的《樱桃园》和赖声川的《海鸥》等剧目。[2]
以上现象充分说明当下的中国观众能够接受并欣赏契诃夫戏剧了。笔者在一次研讨会上,曾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万尼亚舅舅》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为例,说明观众的审美情趣是可以引导的,观众的审美层次也是可以培养并提高的。
2012年10月,中国大学生戏剧节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期间,莫斯科艺术剧院附属高等戏剧学校带来了根据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我们都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作家最为复杂的一部作品。该剧的演出场地是只有288个座位的上海戏剧学院端钧剧场,仅只一场,未料剧场并没有坐满,演出过程中有人退席,散场时笔者遇见一位资深教师,她坦言自己没有看懂。期间,有学生事先阅读原著,结果凡是阅读过原著的学生都非常喜欢这台演出,而没有阅读原著的学生就像那位教师那样一头雾水。这也说明,对于经典剧目的演出与接受,无论对于院团,还是导演和演员,或是观众,都是需要积累和准备的,也就是所谓的“质变来自于量变”的过程。
(二)契诃夫的戏剧描述与中国当下现实有呼应——契诃夫戏剧演出的社会语境。
所谓“重读契诃夫”的核心,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寻找蕴藏着的当代性并与之“永恒的精神对话”,这种能够穿越时空的力量,正是契诃夫戏剧的魅力所在。就像日本的著名作家井上厦在评论《樱桃园》时感悟的那样:《樱桃园》初次上演是在1904年,但契诃夫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契诃夫就像是释加牟尼一样,就是现在,有时也觉得是在他们的手心上工作似的。[1]遗憾的是,中国的戏剧人和戏剧观众对契诃夫戏剧的这一感悟来得晚了。君不见:“一度西潮”的上世纪80年代,戏剧界之活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从戏剧观的大讨论到对舞台语汇的探索,涉及戏剧的本质、特征、功能、形态、技法等诸方面,大量引进国外的各种观点、剧作,先后举行莎士比亚、奥尼尔、布莱希特等戏剧节。但恰恰契诃夫戏剧却是缺席的,十年期间,只有中央戏剧学院排演过一台《海鸥》。
世纪之交,从林兆华在1998年推出的《三姊妹·等待戈多》到2004年“永远的契诃夫”国际戏剧节的举行,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演出活动,倒是大陆的文化界对此的敏感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戏剧界本身,《读书》杂志专门出面举办座谈会,并以“永远的契诃夫——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为题在当年最后一期的《读书》首要位置刊发专栏。因此,那时的“重读契诃夫”犹如空谷足音。
但是不管怎么样,真正意义上的“重读契诃夫”毕竟还是在“二度西潮”期间来到我们中间。在这一期间,除了前面提及的近30台剧目之外,还有两件事应该记入“重读契诃夫”的名下:一是,上海戏剧学院在2011年5月9日至6 月11日举办自2009年创办以来的第三期国际导演大师班,全部是由来自俄罗斯的著名戏剧导演授课,在他们各自主持的工作坊中,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契诃夫戏剧为教学剧目,譬如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首席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的《海鸥》;全俄儿童与青年人戏剧联盟主席阿朵夫·沙皮罗的《三姊妹》;圣彼得堡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拉丽莎·格拉切娃的《万尼亚舅舅》。期间,还特邀两位俄罗斯著名戏剧评论家:号称当代俄罗斯“别林斯基”的《戏剧》杂志主编玛丽娜·达维多娃和圣彼堡戏剧学院副院长尼古拉·索钦可斯基教授做关于俄罗斯戏剧的昨天与今天的专题讲座,他们的理论讲授常常是言必称契诃夫。二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4年为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全四册,囊括契诃夫所有戏剧作品,在国内出版界首次将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以“精品全集”的方式呈现,填补了外国文学出版中的一项空白。出版一个月内首印即告售罄,至当年年底已达三刷,总印数逾三万套。译文出版社在2014年12月于北京举办的“流动的舞台,永远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全集》首发分享会”,邀请了近二十位来自戏剧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吸引了五百多位读者报名参与。此后又在2015年1月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举办《契诃夫戏剧全集》与读者的分享会。
记得也是在2014年,《深圳晚报》的记者曾经就《契诃夫戏剧全集》的出版采访我,曾有一问: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国内将契诃夫戏剧搬上舞台的多了,看契诃夫戏剧的人也多了。我认为:契诃夫戏剧中的描述与中国当下现实有呼应——这是契诃夫戏剧演出的社会语境。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是处于沙皇俄国末期,他戏剧中的人物全都面临着时代的交替,以及这一交替而产生的变革、分化与组合,因此告别与憧憬、困惑与失望,构成契诃夫戏剧的情绪基调。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评价“面对社会生活中严酷的进程进行重新评价的时代,往往都是对契诃夫最感兴趣的时代。”(波洛茨卡娅)也就是先对改革充满希望,后又充满失望的时代。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二度西潮”期间,契诃夫戏剧中被搬上舞台次数最多的作品是《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都是六次上演(包括复排演出),而《三姊妹》和《海鸥》则是四次,《伊凡诺夫》两次。还有一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万尼亚舅舅》自1930年至今共有九次搬上舞台,其中的六次是在“二度西潮”期间;《樱桃园》自1939年至今共有14次搬上舞台,其中六次是在“二度西潮”期间;而《海鸥》和《三姊妹》虽然先后都是十次搬上舞台,则有四次在“二度西潮”期间。无独有偶,北京人艺最近公布的剧院2016年的全年演出计划,也是契诃夫的这两部剧作,6月为李六乙新排的《樱桃园》和12月为复排的《万尼亚舅舅》。
契诃夫戏剧的主题都是多声部的,从《海鸥》至《樱桃园》一直贯穿着“美”的主题。譬如在《樱桃园》,“美”的意象是这座俄罗斯最美的但只有观赏价值而无经济价值的樱桃园,其无可挽回的出售以及被砍伐,让我们看到了“美”的消逝与告别;而在《万尼亚舅舅》中,则是所谓的“美”的被占有与摧残。这一“美”包含三个层面:万尼亚舅舅、索尼娅、阿斯特罗夫医生、奶妈等人的劳动所带来的心灵之美;叶莲娜的外貌之美;庄园以及周边乡村的自然之美。当然,之所以在“二度西潮”中导演们更加钟情于这两部作品,更为主要的恐怕还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契诃夫戏剧展现了在时代交替,社会变革中人们不得不做出改变,重新面对生活。体现在《万尼亚舅舅》中,就是万尼亚舅舅们对于自造的虚妄偶像——高高在上的教授的依赖以及醒悟时必然的反叛;体现在《樱桃园》中,是通过庄园的主仆们在面临着与美的告别的两难抉择,展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类精神困惑与痛苦。对信仰的怀疑和对改革的困惑,是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契诃夫戏剧并不是正面去表现变革的时代及其事件,他只是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甚至是平庸的生活,他一直在跟庸俗进行斗争,这不仅表现在貌似高贵的教授身上,同样也根植在万尼亚舅舅们的身上,正是庸俗使得人不再自由,使得人有了奴性,因此万尼亚舅舅们才会重新坐回到桌子旁边工作。同样,庸俗与奴性使得樱桃园的上上下下都是一群“不成器”的人们。所以契诃夫的戏剧有一个指导思想,他认为最有戏剧性的就是人将奴性从自己身上一滴一滴挤出去的过程。难怪萧伯纳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契诃夫比易卜生来的柔和,他也比易卜生更加毒辣。这也就是为什么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3年,仅莫斯科一地就有六家剧院在排演《万尼亚舅舅》。
三
新世纪初,由权威的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撰出版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是这样评价契诃夫的:“契诃夫对于当时美学与道德探索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戏剧方面。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导演不曾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寻找创作的支撑。现在,他日益增长的声誉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
彼得·布鲁克曾长期在世界各地轮演的两个戏:一部是《哈姆雷特》,另一部是《樱桃园》。对此王晓鹰认为:“这给导演们一种昭示,当你成熟到一定的时候,你必须跟这两位大师对话”。他同时认为“即使不是大师,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你也能跟莎士比亚对话,你可能不敢碰《哈姆雷特》,但可以碰《第十二夜》。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信心,你是不可能跟契诃夫对话的”。
因此,能否与契诃夫对话,在“二度西潮”时期似乎成了一个导演是否成熟的试金石和标志。但是,契诃夫戏剧的“原生态”对于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图像文化”的一代确实又不那么好看。于是如何使得契诃夫的戏能够好看起来,如何在好看的同时,还要看座,这无形之中就成了导演的首要任务。
于是乎,我们看到在巨大的海报上有这样的广告语:某某导演“全新阐释俄国大文豪契诃夫巅峰之作,探索‘喜剧谜团’,让戏剧从不可预知的方向出现”;或者某某导演“与契诃夫跨越百年的灵魂对话”,等等。就在这样的旗帜下面,请来有着票房号召力的影视明星领衔演出,也确实有许多观众是冲着看明星而去剧场;明明是适合于小剧场演出的先锋戏剧被请上了上千人的镜框式舞台(譬如立陶宛OKT剧团的《哈姆莱特》);正是在“对话”的名义之下,一个著名导演声称“在这个戏中,思想和性格相比,我认为主要是表现思想。我不要性格的细节”。于是最为传神的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被舍弃了,人物形象由圆形变成了扁形,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体系被弱化为三种类型的文明人;另一个来自海峡对岸的著名导演事后悉知前者的舞台处理,痛心疾首得“一贯平静的语气都颠覆了”,[2]为了“纠正被误读的契诃夫”,据说自认为与“契诃夫是灵魂的知音”[3]的这位导演干脆一俗到底,将剧情本土化,改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上海周边的水乡,于是在观演过程中确实笑声不断,有人笑是外行看热闹:因为身着旗袍、长衫的人物在台上扭动腰肢、在躺椅上裸露大腿等,展现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大惊小怪、装腔作势的声调;有人笑是内行看门道:因为“1896年俄罗斯乡村各式人等的台词原汁原味地原封不动地从1930年代上海附近一个乡下的各式人等嘴里说出来”。[1]于是也有人痛心疾首地说:观众笑了,契诃夫哭了。这样一种所谓的“灵魂”也罢、“精神”也罢的对话的背后,是否存在着“票房”的推手?其实,这是否也是在潜意识中流露出一种对契诃夫戏剧在舞台驾驭的不自信?
这一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万尼亚舅舅》身上,这是一部自2013 年6月首演以来无论在业内还是在观众中广受好评的作品。该剧是由俄罗斯著名导演阿道夫·沙皮罗执导,演出是在忠实于文本的前提下,根据当下的观演特点,在形式上进行了改动,譬如通过舞美设计强化视觉元素:舞台背景写意,前景为实,舞台两侧一前一后各有一挂秋千,其中右侧突前的那挂秋千用于人物抒情,会荡向观众席的上空,到了第四幕,舞台上方又降下无数秋千,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又譬如加强人物的外部行动作为内心行动的外化,但是对于有的处理笔者不是很认同,也是在第四幕,万尼亚舅舅与医生阿斯特罗夫有一场在钢琴边的争论,阿斯特罗夫最后爬上钢琴,用脚踩琴键。记得笔者在观看首轮演出时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舞台上的老年演员与中青年演员在表演风格上不太一致,前者还是我们以往所熟悉的那种表演风格,如扯着嗓子说话;而中青年演员则是尽量以“生活化”方式展开行动,明显感觉到在控制着自己,不敢太“放”出来。2014年,再次观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万尼亚舅舅》,我感觉舞台上老中青三代演员的表演风格相互之间开始靠拢了。2015年,第三次观看,舞台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尤其在首轮演出时曾经以其质朴风格演出的青年演员也完全放开了,声嘶力竭,剧中叶莲娜也一反矜持躺倒在地。这些年里,让契诃夫戏剧中的女性形象躺地打滚或撒泼似乎已成时尚,如林兆华版本的《樱桃园》中蒋雯丽扮演的朗涅夫斯卡娅在第三幕在证实樱桃园已被拍卖之后,在地上哭喊翻滚。我曾在剧评中调侃:“看着蒋雯丽在台上声嘶力竭,这哪里是一个曾在巴黎生活过的贵族,分明是电影《立春》中一心想要进入京城成为歌唱家,未果之后寻死觅活的县城教师王彩玲的形象”。去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毕业公演《万尼亚舅舅》,也出现了让叶莲娜和索菲娅都在地上翻滚的一幕。
既然是“重读契诃夫”,当然应该允许艺术上的探索,但是我们同样也应该而且必须对契诃夫戏剧怀有敬畏之心和真诚的态度,换言之,探索不能背离契诃夫戏剧精神,就像一位学者早在2004年在一次关于契诃夫戏剧的座谈会上所言:不要由于过多照顾了剧场效果,而使得契诃夫戏剧的品位掉了下来。[2]
“重读契诃夫”,我们还在路上。
吴小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