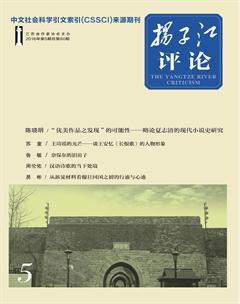错指的“乱象”之因与被遮蔽的沉潜写作
一
谈到所谓当代诗坛的乱象,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一个稍稍留意文学、甚至只是留意热闹新闻的人,就可能听说过口水诗、梨花体、写诗官员砸电脑、鲁奖诗歌评选风波等八卦新闻。笔者近日偶与本省几位诗人相会,就听他们不断感叹现在的诗歌活动实在太多,有时甚至一天要跑两三个场子。据说一位德高望重的诗论家前辈都感叹,诗歌疯了。面对此种情景,有人出来撰文疾呼《中国新诗何日走出乱象?》,甚至还有什么屈原的后人都站出来“怒批诗坛乱象”。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停留于看热闹的层面,而是稍加认真观察的话,则会发现在所谓的诗歌乱象与声讨和拯救之间,有一种颇为奇怪的错位。前面所列举的那些诗歌乱象,或是非诗性的口水写作,或是小吏的飞扬跋扈,或是诗歌评奖的腐败,或是诗歌活动太过频繁。但是某些声讨者,则指责新诗的写作者们沉迷于个人性、炫技性的写作,使得他们的作品难以读懂、脱离广大读者,不仅如此,这些批评者还进一步将问题归罪于整个新诗片面学习西方的传统。在他们看来:
“中国现代诗学所发展出的语义学和修辞策略,只有在极个别诗人和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之间,才存在精微的审美感应和理解互动,因而是不折不扣的象牙之塔……从白话文、口语开始,突破文人化的藩篱,面向社会历史,拥抱生命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启蒙现代思想……最终,致力于解放体制(打破音韵、格律)面向大众的现代新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为极点,再度发展成了一种读不懂的白话!在近百年的探索期中,仍不知“自由体”的“自由”谓何,“体”又何在”。a总之,“中国的新诗已经走得离诗歌的本源太远了,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应该是诗歌如何回归传统的问题,如何回归诗歌基本元素的问题”b。
关于如何评价新诗传统的问题实在太大,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存而不论,我想追问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出现将混乱的诗歌现象都归罪于新诗向西方学习、脱离读者、脱离古典传统的情况呢?第二,当代诗歌真的只是混乱、自闭、自我炫技吗?
二
批判新诗食洋不化、脱离广大读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且不去提上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观点与运动了,也不用说“大跃进”时期那场由领袖所发动的全民倒新诗的“新民歌运动”,就是近三十年来的诗坛,主张重归传统、重归汉语诗学本体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就连一些当代诗坛著名的先锋诗人们,都越来越多地加入其间。
这当然不只是诗歌界发生的孤立现象,而是时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否定启蒙运动、否定新文学新文化运动风潮的一部分。这一风潮至少早在26年前的那场巨大的风波之后,就正式粉墨登场并不断强化,发展到今日,其大有成为思想文化界共识之势;这也不是所谓反思启蒙、恢复儒学、复兴传统之保守主义思潮的自然发展,其与权力和体制的关系清晰可辨,九十年代初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文化立场的突变就是如此。
1990年北京大学的张颐武先生接连在《文艺争鸣》《读书》 《上海文学》等六家刊报上发表文章,热情推荐作为“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主张“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深刻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寻找人类文化成长与发展的新的契机”c。
1993年《文艺研究》第1期特辟“拓展理论思维,促进理论繁荣”专栏,邀请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以后殖民、后现代话语为主导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化现状;《读书》杂志第9期也集中发表了4篇与后殖民批评有关的文章;同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虽然相关学者的观点并非一致,但从总体趋势来看,以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话语则被系统性地颠覆。
在新的解讀框架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文化传统,不再被视为由启蒙知识分子所开拓的伟大而艰难的传统,而成了全球化时代下的以西方文化霸权为主导、为中心的中/西二元对立话语逻辑的中国展开。这样,五四新文学就成了自绝于中国古典传统的“急躁”的不成熟的产物,白话替代文言则是对西方逻格斯语音中心论的臣服d;而鲁迅以降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成了西方学术话语的代言人,以傲慢的态度去对”人民,行使“牧师的权力”,屏蔽、推延、扭曲、抹擦了“人民记忆”。只是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当商品化大潮涌来之时,新的历史才开始了,“人民的记忆”才得以在《渴望》等通俗文学的叙事中苏醒、恢复。虽然它们显得“世俗”、“琐碎”,但却“朴素”、“温和”,不再是“‘单一性的、直白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一种新型的人民“神话”。它既“与商品化的语言/生存状态相联系”,同时又可以将中国人引领向物质丰裕、“人伦关系”和谐的现代社会。从而既解决了国人“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也最终想象性地解决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e。
这一“新视野”的出现,虽然有着西方后现代观念的启发,但总体而言并无现代文学界内部思想反思的前兆,而是那个燥热的夏季突然中断后的突转f。
否定启蒙文学的后学思潮出现的稍后,儒学复兴、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时至今日,它们早已发展成了自上而下的普遍社会观念。民族主义思潮从“逆向民族主义”的声讨开始,经过“中国可以说不”再到“大国崛起”、抗日神剧映遍神州等一波波的现象,已经稳固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场域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而作为其姊妹现象的儒学复兴、传统复兴,更是早已脱离了其最初的“学术”样态。现今各种各样的与儒学或传统话题相关的会议层出不穷;孔子学院开遍世界;越来越多的原本拥护自由理性学理的学者加入到了新儒学的阵营;祭奠炎黄、孔孟等的活动也在各地举行;在其他民间性的社会组织或活动日益被收紧的同时,各种读经会却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背诵《论语》 《三字经》乃至于《弟子规》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的“必修之课”;越来越多的地方不仅搞什么汉服活动,甚至下跪也被堂而皇之地引进学校、展示于公共庆典活动之中;拜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力才直立不久的国人的双膝,又在国家的未来那里弯曲了下来……
三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问题——当下诗坛真的如其表面所表现的那样混乱不堪吗,那样个人炫技吗?表面上看去,似乎的确如此,但实际这只是被所谓“后时代”的喧哗、犬儒的表演、保守主义的张扬、权力的抑制之共谋所造就的虚假的表相,且不说整个百年中国新诗,就是当代诗歌,也绝对不像某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除了昌耀、北岛之外都不堪入目。我们不妨结合实例,从启蒙诗学的坚守、现实的直面与超越、“绝对之诗”的探寻三个方面来稍加论证。
启蒙诗学的坚守 启蒙诗学是贯穿当代诗歌历史的内在主线。所谓“启蒙诗学”在精神、价值、立场层面上,表现为抵抗、追求自由的诗与思,坚持个体独立的写作姿态,并且骨子里充溢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愫;在形式层面上,也同样努力追求打破常规的表达方法,追求既富于个人特质又具有时代穿透性的艺术形式。因此启蒙诗学的写作,往往的确表现出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亲缘性,表现出较强的先锋性特质,但是真正的启蒙诗学的写作,决不会追求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而且也不拒绝与读者、与时代的精神对话,他们往往在巨大的压力下,默默地抵抗、坚守,以个体之肩担负艺术、民族与时代的重压,所谓炫技性的象牙塔写作,既不是他们的存在状态,更不是他们的艺术追求。
例如哑默这位当代诗歌最早的启蒙诗学的开启者之一,有一首长诗《飘散的土地》(1976~1986),一方面其暗哑中的独立的写作状态,使得它的批判、坚守、追求,显得焦灼、幽暗、狞厉,但是另一方面,它在诗歌结构上又改造性地继承了《凤凰涅槃》的毁灭再生的现代民族史诗的结构,并在诗体上与艾青雄浑的象征、浪漫气质相接,而且其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更是直通千年前的屈原。所以它之不被主流批评界所提及,不為大多数读者所知,并非是因为故弄玄虚、远离读者,也非什么片面地摈弃传统。启蒙诗学所批判、所摈弃的是束缚人们精神与灵魂的旧物,而非对民族、对国家、对传统的弃之如敝履。
启蒙诗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借助于思想解放的契机,曾以“朦胧诗”的名义短暂进入诗坛前场,此后一直挫折不断,尤其是那场巨大的震惊之后,启蒙诗学似乎远遁海外,与我们再无关系。其实并非如此。至少那场巨大的震惊,淬炼了一批中国新诗史上最精湛的诗篇,其精神的抵抗、隐喻的独特精湛与穿透,直抵现实、艺术、存在之深处。它们现在以单篇的形式,散布于诗坛g,但它们曾以“红色写作”的名义,汇聚于《非非》1992年复刊号上,在诗歌的地层中,固执地放射着幽暗的凛冽之光。
行文至此我再次想起“哑默”,以此命名的那个人及其同伴的突破与坚守,使这两个字宿命般地具有了历史的象征性,象征着当代启蒙诗学的写作者们,执拗地坚守着暗哑的“摇滚喧哗”h。
现实的直面与超越 从大的社会环境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当代诗歌的确表现出越来越小众化的趋势,所以坊间有写诗者多于读诗者之说,但是当代诗歌并未放弃直面现实并诗性地超越的努力。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使得诗歌加强了“与现实之间的深层‘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时代与人生的中心”i。不过笔者感觉,一些评论尤其是“重要期刊”的“权威评论”,往往重视那些可谈论的社会重大事件的写作,而忽略或回避那些所谓的“敏感事件”的写作,沈苇的《安魂曲》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安魂曲》写于2009年的9月,它既是那场突如其来的“7·5惨剧”的震惊记忆,又是那个被延长了的“09褥暑”的“编日”“编月”“编年”。我们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刚刚经受狂乱屠戮的惊愕与愤怒:
被唤醒的魑魅魍魉,走街串巷,小试狰狞/恐惧,将城市变成它乐意居住的绿洲//
暴徒们作鸟兽散,化整为零/在更隐蔽的洞穴里,打鼾/梦见火光和烤全羊//
擒魔直升机轰响着飞过/盘旋,搅拌似血的残阳
从下面这些关于九月的描写中,也不难体味那个漫长的“09褥暑”的动荡、不安、愤怒与煎熬:
十万民众的愤怒/是一个人又一个人的愤怒/据通讯社报道,有十万种之多//它不是别的/是加法的愤怒,乘法的愤怒/然后混淆为加、减、乘、除的愤怒//沙漠中,十万颗沙子诞生了大海/旗帜下,十万底层的岩浆在涌动/从街道、地底和内心/喷涌出来的愤怒/注定了新闻和算术的失败
但是诗人,没有停留于现场的记录,更没有执著于个体或族群的痛感与愤怒,诗人拒绝选边站队,拒绝以族群的名义将愤怒摔向另一个族群的面庞。尽管“安魂曲”这一题名,传达出某种上帝或安拉的口吻,但诗人知道自己不是上帝,也不是安拉,他只是在本分地尽一个诗人所应尽的“保姆”的职责,“保卫基本的人道和人性。受伤的人道和人性,在这个夏秋的乌鲁木齐变成了哭泣的瑟瑟发抖的婴孩”j。所以,这首《安魂曲》最后不是结束于渐渐低沉的心灵与肉体的催眠和安慰,而是结束于投向自我与他者的诘问——
取缔的未来你们不会相信/但是,可以一问:明天是否照常来临?
“绝对之诗”的探寻!据说瓦雷里认为,一切诗歌都将通向“绝对的诗”。瓦雷里说出这样的格言并不奇怪,但当它从周伦佑的口中传出,似乎多多少少有些奇怪,因为在批评家的笔下,作为八十年代“非非诗派”领袖的周伦佑似乎太过喧哗。其实这只是浮浅和浏览式批评所造成的错觉。周伦佑1970年代初中期的《夜歌》《挽歌》,就既有着启蒙诗学的反叛与浪漫英雄主义的情怀,同时又表现出几分超然的先锋性的探索。接着是八十年代反叛的张扬与诗歌纯粹性的深度挺进。八十年代末的那场巨大的震荡,也将周伦佑送进“仙人洞”,被迫面壁打坐,但这同时也成就了他,成就了他之“刀锋上的句法转换”。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述过周伦佑完成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刀锋二十首》:
因此毫不奇怪,这种诗歌的语言不可能再是红色诗歌的浅白、暴力性的排比、铺陈、直吼,而是集精炼、质朴、深度、坚韧、力度、弹性甚至玄幽于一身的语体,从而真正达到了“语境透明”的境界 。正是在这里,现代汉语、中文,第一次真正达到了成熟而超绝的晶体品格。k
当我邂逅了《绝对之诗》l时,则发现周伦佑又以更为纯粹的形式,追求“绝对之诗”的透明之语:
当一匹奔马向天空自我飞跃
我看见一支旷世的笔在书写
绢帛从很古的高处
悬
挂
下
来
握笔的手得意而忘言。我知道
这是时间在写
它自己的编年史
熟悉周伦佑作品者,从此开篇之节依然可以发现几分他所惯有的借沉浸式自语入诗的特点,但经过足够光阴濯耀、多样人生历练的诗人,已大大压缩了唯我的玄思,而任凭“一匹奔马向天空自我飞跃”,千古绢帛赫然悬挂,日月之诗矗立眼前。
追击马的嘶鸣,道路升得更高
天空微妙,谁在独享落日的炙烤?
残损的身躯,被神圣的意志婉转
奔马在丝绸的演义中一路汗血
朝圣者匍匐的身子在诗行中异步
在高处,那高过人类头顶很多的
地方,最高的穹顶。至纯至美的
原诗,在我们的瞻望中,以水晶的
透明涵养光华,然后向我们透露
被光明击中者,幸哉而成为诗人
……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启蒙诗学的坚守、现实的直面与超越、精纯之诗的绝顶攀援等哪一方面看m,当代诗歌或当下写作,绝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浮华、混乱不堪,那样自娱自乐、闭门造句、远离读者,那样一味西方、放逐传统。不错,优秀之作肯定是当下诗坛的少数,但是任何时代写作的代表,从来都是少数的;人们往往本能地拿漫长历史所成就的杰作与百年新诗、与当下诗歌比较,这并不公平。对于我们的批评家来说,批评当下写作所存在的问题是应尽之责,但或许更重要的工作是拨开纷杂的乱象,去为世人发现、为历史铭记那些真正的优秀写作。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是被表相所障目,随流俗或主流意识形态起舞,遗忘或压抑富于真正良知和自由精神及艺术高峰攀登的写作,那实在是放逐了批评家应有的责任与良知了。
【注釋】
a殷实:《新诗如何继续成长?——对几份文学期刊诗歌作品的抽样观察》,《未央文学》,双月刊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597670102v462.html
b丘树宏:《中国新诗何日走出乱象?———读殷实〈新诗如何继续成长〉有感》,http://www.zsnews.cn/Backup/2015/02/01/2732150.shtml
c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读书》1990年第3期。
d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e参见张颐武:《在边缘处求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1993年版,第3、81、96、123页。
f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见姚新勇:《“第三世界文学”:“寓言”抑或“讽喻”——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中国错译及其影响》,《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g如周伦佑的《刀锋二十首》,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 《啤酒瓶盖》 《坠落的声音》,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 《墨水瓶》,叶舟的《灯:黎明的点灯人所唱》,邱正伦的《面对偶像》,杨远宏的《磨难与家园》,王小妮的《注视伤口到极大》,翟永明的《死亡图案》,杨炼的《冬日花园》 《谎言游戏》 《断水》,唐晓渡的《死亡玫瑰》,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胡途的《死鱼之时》……。不错,其中的某些诗作创作于1989年之前,但是它们分散而在与集结于此期《非非》中,文学的时代意义自然不同。
h黄翔有诗名为《我在黑夜中摇滚喧哗》。哑默先生1956年开始写作至今,七十年代末起以贵州为基地,开始参与诗歌启蒙运动,创办和协办多个民间诗歌刊物,长期坚持搜集贵州及全国地下诗歌运动的史料,现已集成《文脉潜行——寻找湮灭者的足迹》 (1950年代至2000年贵州潜在写作综述),《咆哮的群星》 (1978—2000年贵州地下诗歌民刊原件扫描、拍摄档案),《哑默诗集·世纪的守灵人》九卷,《需要温暖相伴》 《时代微痕》等潜在写作历史材料等。或许对哑默的诗艺,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其所表征的民间性的独立的启蒙诗学的行动,则绝对不应该被遮蔽。
i罗振亚:《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j此节的诗句与引文均引自沈苇:《安魂曲》,据作者所赠电子版本。
k姚新勇:《囚禁式写作境况的烛照与穿越》,《非非》2009年卷,新时代出版社2009年版。
l《绝对之诗》是作者所赐电子稿,其为《狂草奔马的诗》的精简版。此处的引文,揉合了两个版本的诗句。
m 这里还没有论及更多的方面,比如那些切近自然、大地的优秀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