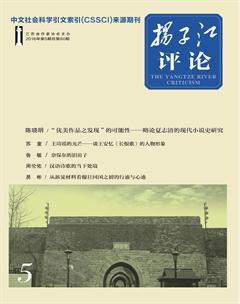王琦瑶的光芒
苏童
一部优秀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应该是一盏灯,不仅照亮自己的面目,也要起到路灯的作用,给别的人物做向导,指引他们的来路,也要起到更大的探照灯的作用,给整部小说提供空间照明。
从亮度和色彩上看,《长恨歌》读起来忽明忽暗的,那是因为小说里的主人公王琦瑶很像是一盏灯,在从1946年到1985年这段漫长的时间段里,这盏灯忽明忽暗的,社会现实的变化很像一种不稳定的电压,导致这盏灯的灯光光源的不稳定,尽管这一束持续四十年的灯光不足以照亮上海的夜空,甚至不能完全照亮小布尔乔亚的狭窄地界,但对于王琦瑶的世界来说,这盏灯是一个完美的光源。
王琦瑶的世界是上海,很大也很小,上海在这篇小说里很像一个精心搭建的舞台,王琦瑶从不离场,很像一盏灯,其他的人物都是灯下的过客,过客走过灯下,在灯下逗留的时间有长有短,对灯的感觉有的依恋,有的好奇,有的既不依恋也不好奇,仅仅是需要一盏灯,当以程先生、蒋丽莉、老克蜡为代表的这些过客走过灯下的时侯,灯光有时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了很久,再慢慢亮起来(比如程先生),有的会随着来人的脚步声亮起来,亮了再暗淡下去(比如李主任、老克蜡、康明逊),有的过客自己也是一盏灯,是来喧宾夺主的,于是王琦瑶这盏灯一方面要收纳别人的灯光,另一方面还要用自己的灯光覆盖别人的灯光(比如蒋丽莉、张永红)。但是不管怎么说,王琦瑶的灯光最终要熄灭,是宿命的灯光,它只能亮四十年,控制灯光的是定时开关,从她跟吴佩珍去片场看见那个扮演死人的女演员之后算起,只能亮四十年,这是一盏灯的使用年限,也是人物的最终命运。
我们来看王琦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小说第一章的末尾,王安忆对人物俯瞰式的预先描绘很值得注意,可以看作是对王琦瑶气质的概括,也可以看作是王琦瑶出场的白皮书宣言,用的是一种很奇特的人和地点对照的手法,始终是将王琦瑶和上海弄堂统一在一起,意图是让她充当上海弄堂的灵魂,王琦瑶出场,上海的弄堂也出场了。
“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姐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也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它是不够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它有点小心眼,小心眼要比大道理有趣的。它还有点耍手腕,也是(耍得)有趣的,它难免有些村俗,却已经过文明的淘洗。”“弄堂墙上的绰绰月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纱窗帘后面的婆娑灯光,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叫卖桂花粥的梆子敲起来了,好像是给王琦瑶的夜晚数更,三层阁里吃包饭的文艺青年,在写献给王琦瑶的新诗,出去私会的娘姨悄悄溜进了后门,王琦瑶的梦却已不知做到了什么地方。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因为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
所以种种暗示都告诉我们,王琦瑶如果是一盏灯,它所发出的光芒首先是弄堂的光芒,反过来说,王琦瑶不一定能承担弄堂的灵魂这样的角色,但弄堂生活中最亮的光芒,也就是王琦瑶的光芒。
我们来看看王琦瑶身上闪烁的是什么光芒。
身世和经历:她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弄堂女孩,家景既不很好,也不很差,十七岁参加上海小姐选美,获得第三名,有一个含蓄的意味深长的封号:沪上淑媛。推敲起来,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褒奖,这封号的主人一定是美丽的,但美得有分寸感,不是那么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不是外滩和南京路的气势,它的美也是弄堂之美,谦虚地低了头的美,符合王琦瑶的身份,也符合弄堂的地位,褒奖王琦瑶,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褒奖弄堂。王琦瑶在选美比赛中的角色和地位,也是上海的弄堂在上海的角色和地位,对王琦瑶的认同与否,对王琦瑶的认同程度,可以看出上海的趣味和胸怀。
但一个人不是一条弄堂,他是有内心生活的,人生的道路总比弄堂的路面要曲折得多要漫长得多,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给她留下记忆,有的记忆一生都是他的包袱,有的包袱可以随时丢弃,有的丢不了,也不愿意丢,所以有的人一生都是带着沉重的包袱前行的,王琦瑶就是这么一个带着包袱前行的人。十七岁她就得到了那个包裹,那包裹是在她三心二意半推半就的努力下获得的,最初是灿烂的,有重量的,但渐渐地包裹的颜色旧了,分量也越来越轻,当她意识到那包裹的意义时,包裹其实已经空空荡荡的了,王琦瑶后来一直拿着一个空包裹,从一个少女渐渐地徐娘半老,上海变成了一个红旗下的城市,一个城市的繁华还在,生机还在,但一个人的繁华已经不在了,一个人的青春已经过期了,王琦瑶就是一个过期的人,当她懂得繁华时,来敲门的是寂寞,她学会在寂寞中怀念繁华时,繁华已经变成一个无法挽留的过去时。总体上说,王琦瑶的命运比弄堂的命运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算计,但始终有一只无形的手,把王琦瑶和弄堂纠葛在一起,如果弄堂有记忆,王琦瑶是弄堂记忆中最亮的一盏灯,而弄堂恰好也是王琦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盏灯,在《长恨歌》里,王琦瑶一生中有两次离开弄堂,一次是在选美前后客居同学蒋丽莉家中,那个家是所谓的有钱人家的豪宅,还有一次是被李主任包养那段时间里,住在爱丽丝公寓里,但一个是别人的家,一个虽然是家,却更像一个冷宫,是为无休止的等待和煎熬准备的。王琦瑶的一帘幽梦破碎以后,她还是回到了弄堂,弄堂的名字叫平安里,有趣的是,我们在这里甚至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前途的担忧,平安里,让王琦瑶在这里生活得平安一些吧。
但平安里是保不了王琦瑶的平安的,在王琦瑶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承诺,从少女时代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开始,“王琦瑶就靠着这个不承诺保持着平衡。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她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王琦瑶的人生哲学是一种弄堂哲学,作为另一种平衡,平安里对她的平安,也作不了承诺。而王琦瑶的一生如果写成一本字典,这字典里最大的两个字是“错失”,她一生投入的唯一一次爱情是在爱丽丝公寓里作金丝鸟时对李主任的爱,独守空阁,天天等待着爱人,但当行踪不定的李主任利用仅有的两个小时空隙回到爱巢的时候,王琦瑶却恰好出门去了,时局混乱的时候,王琦瑶曾经有机会与吴佩珍一起去香港,但她为了等李主任回来,错过了香港,等来的却是李主任飞机失事的噩耗,王琦瑶一生都在与人打交道,但这些交道打下来的记录都是空白,她错失了爱情、友情、亲情,错失了婚姻、家庭,唯一留下的女儿薇薇,最后也随着自己的丈夫去了美国,王琦瑶的时光要比别人长,因为她始终在等,她在四十年后依稀等到了什么,在“红房子西餐馆”请女儿女婿吃西餐的时候,王琦瑶“禁不住有些纳闷:她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她却成了一个旁观者。”在王琦瑶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那种“错过”的感觉更加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王琦瑶给薇薇准备嫁妆,就好像给自己准备嫁妆。这一样样,一件件,是用来搭一个锦绣前程。这前程可遇不可求,照理说每人都有一份,因此也是可望的。那缎面上同色丝线的龙凤牡丹,宽折复褶的荷叶边,镂空的蔓萝花枝,就是为拿前程描绘的蓝图。”可是,“王琦瑶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嫁妆,这前程是被她绕着走过的,她走出去老远四下一看,却已走到不相干的地方。”
王琦瑶是绕着她的前程走的,但是她的前程是什么,其实她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她走到了一个不相干的地方,那么与她相干的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还在吗?其实她也说不清楚,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确认,“错过”这个词语可以贴切地描绘王琦瑶的生活状态,王琦瑶的光芒就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中消耗的,所以说王琦瑶这盏灯亮了暗了,什么时候熄灭,都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灯下的弄堂是旁观者,灯下的那些过客也是旁观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王琦瑶的灯光范围里,进入了她的生活,但他们不能也不敢去掌控这盏灯的开关,不能阻止那种“消耗”,所以没有人能够维护或者修理王琦瑶这盏灯。
王琦瑶的灯光吸引了许多男女走到了她身边,小说的人物关系很清楚,王安忆自己有一句话可能无关小说内在的主题,倒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小说人物圈的设计思想,在《长恨歌,不是怀旧》这篇采访中,王安忆说,“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资料,但它其实是个现时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小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长恨歌》里用四十年代作了背景,这不代表怀旧,关键在于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偌大的上海,偌大的人群,去说谁的故事?用谁的故事去关照这个现时?王安忆是从小布尔乔亚开始着手的,所以她设置的人物圈经过了谨慎的过滤和筛选,是一个小规模的小布尔乔亚的队伍,程先生、蒋丽莉、严家师母、毛毛娘舅等人围绕着王琦瑶这朵小布尔乔亚的花朵,在四十年的时代风云变幻里,在无产阶级的背景音乐里,被挤压,被调整,被冲散,然后是新的组合,渐渐变形,直至最后无产阶级的长脚、张永红加入这支队伍(这其中甚至也可以包括王琦瑶养育的无产阶级的女儿),随着王琦瑶的死,这支队伍便彻底覆灭了。
《长恨歌》里的人物几乎都是王琦瑶灯下的过客,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来的,主要是程先生和蒋丽莉,他们和王琦瑶组成的人物关系是小说里唯一一组纵深的人物关系,是三角恋爱的关系,但三个人的情感纠葛是在二十年后,随着蒋丽莉的死,作了了断,隔了两个时代,读起来便是一种很沧桑的三角恋爱,比平面的三角恋爱高明许多,王琦瑶、程先生和李主任三人之间也有模糊一些的三角恋爱的味道,虽然人物没有纠缠,但在第一部第四章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王琦瑶的世界很小,是个女人的世界,是衣料和脂粉堆砌的,有光荣也是衣锦脂粉的光荣,是大世界上空浮云一样的东西。程先生虽然是个男人,可由于温存的天性,也由于要投合王琦瑶,结果也成了个女人,是王琦瑶这小世界的一个俘虏(提醒男同学们注意)。李主任却是大世界的人。那大世界是王琦瑶不可了解的,但她知道小世界是由大世界主宰的,那大世界是基础一样,是立足之本。”在两个男人之间,王琦瑶选择李主任,是情的选择,也是世界观的选择,这一组人物关系由于李主任飞机失事,死了一个,后面没有作任何铺陈,但这两个男人加上王琦瑶,仍然组成了一个链条,传达着男女关系中最美好的声音,在王琦瑶的小世界里,李主任是情的化身,程先生是义的化身。情寿命不长,李主任寿命也就不长,义是要靠时间证明的,所以程先生活到了足够证明的时间,他死在文革的前夕。
《长恨歌》里的人物队伍不是被王琦瑶的美所吸引,就是被那顶选美的桂冠所吸引,并没有人被她的内心所吸引,当王琦瑶风华正茂的时候,他们向王琦瑶走来,有的是出于少女才有的同性间的纯真的友情,比如吴佩珍,有的目的中既有对友情的向往,也有对他人世界的侵占欲,比如蒋丽莉,有的人不知是出于情欲还是爱,比如李主任(这个人凭什么成为王琦瑶的“情”的化身,小说里没有足够的描写,我认为也是小说中不多的漏洞之一),有的人最能代表小布尔乔亚的情感,爱着王琦瑶,更多的是爱照片里的王琦瑶,与其说爱王琦瑶,不如说爱的是一个梦。程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小布尔乔亚的人物,尽管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不食人间烟火,有点过,但是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
当王琦瑶开始在无产阶级的背景音乐里开始她的新生活时,她身上的小布尔乔亚的气息吸引了另外一批人,除了用情专一的程先生外,另外有一批人来到王琦瑶的灯光下重温旧日的繁华梦,或者是要用这灯光来排遣自己的寂寞,比如严家师母、康明逊、萨沙,这些人不一定都来自无产阶级的阵营,萨沙甚至还是共产国际者的后代,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在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至高无上的上海,尽管王琦瑶自己是在靠替人打针注射谋生,但她的生活圈子仍然延续着旧时代的轨迹,她与气味相投者交往,只是那些人已经不是上海生活的主流,是边缘化的人群,是旧上海的遗老遗少了。
这个时期的王琦瑶像一条破烂的船停在狭窄的港湾里,已经没有梦想,港湾里任何一个小小的波浪都可以掀动这条船,所以,平庸的康明逊的出现,竟然改变了王琦瑶的人生,给她留下了一个私生女儿薇薇,这个时期的王琦瑶似乎开始堕落了,她周旋在程先生、康明逊、萨沙三个男人之间,很明显,三个男人都不能替代李主任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对于王琦瑶来说,李主任代表的那个情的世界是不可再生的,她只是在他们身上寻找依靠,三个男人都是矮子里的将军,人到中年的女人,她的矜持和伪装看上去成熟,感情世界和功利目的难以剥离,虽然有了弹性,但仍然是脆弱的,王琦瑶与康明逊的关系始终是两个过来人之间的试探,战战兢兢的,怕这怕那的,但是又互相需要,在王琦瑶看来,自己的前途已经不能托付给别的男人了,但她的欲望和身体还是在挑选男人,既然她是个不许诺的女人,那挑选康明逊这个不许诺的男人,是最公平的,也是最安全的。有关这对孤男寡女偷偷摸摸的情爱,就像一场凄凉的性别的战争,王安忆是敲足了战鼓,但省略了金戈铁马,刀光剑影,“这是揭开帷幕的晚上,帷幕后头的景象虽不尽如人意,毕竟是新天地。它是进一步,也是退而求其次,是说好再做,也是做了再说,是目标明确,也是走到哪算哪!他们俩都有些自欺欺人,避难就易,因为坚持不下去,彼此便达成妥协。”王琦瑶与康明逊的关系,在王琦瑶这边是对自我的妥协,但是王琦瑶处理与程先生的关系,是不妥协的,即使是在物品短缺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她可以与程先生一起度过饥饿的白天,却把黑夜留给自己,从不留他过夜。她用这么一种奇特的方式来报答程先生的恩情,看起来是身体上的排斥,其实是对一种感情小心翼翼的维护,是世故,也是对程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义”的尊重。相反,王琦瑶与萨沙的关系,则充分体现了王琦瑶的弄堂哲学,你吃了我的,喝了我的,总要吃回来喝回来的,与我交朋友,我付出一分,你是要回报三分的,因此,萨沙这么个“除了有时间,什么都没有”的人,在王琦瑶和康明逊的感情游戏中,成了一个玩偶,一个牺牲品,王琦瑶在怀孕以后,甚至毫无顾忌地把“父亲”那顶帽子戴在了萨沙头上。这个时期王琦瑶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是值得注意,一方面她开始堕落了,一方面似乎又正常了,王琦瑶成为了一个母亲,尽管这母亲当得有点可疑,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母亲的身份可以让她的灯光更亮,但对于王琦瑶来说,这是一个更暗淡的生命周期的开始,她蜷缩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人,也多了一份责任,她从不许诺,但对于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不能不许诺,所以,我们从人性的一个角度来看,王琦瑶的生活多了一丝幸福,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一定,也许她遇见康明逊是遇见了苦难。至此,王琦瑶摇曳的灯光变得稳定了,可是也可能是更暗淡了。
然后是八十年代,王琦瑶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时期,仍然有人从她的灯光下来来往往,这个时期,她其实主要是在跟下一代打交道,张永红、老克腊、长脚这些人,这些人中,她与张永红的相遇是两个时代的美女的相遇,这相遇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多少带着一些对抗色彩,又不仅对抗,还在对抗中磨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这就像一只老一点的五彩孔雀和一只年轻的白孔雀,他们走到一起,谁也吃不了谁,最后一起开屏了,谁也不吃谁。请一定注意王琦瑶和张永红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其实也影射了两个时代、两个阶层的对抗和磨合,同时也多少透露了作者本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那态度是和解的、与人为善的。当然,小说的后半部分王琦瑶与老克腊的忘年恋是重头戏,也是完成王琦瑶灯光最后一亮的强电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长恨歌》中最精彩的人物安排,老克腊要从年老色衰的王琦瑶身上寻找虚幻,王琦瑶却在人生最后一个秋天,要从老克腊身上寻找现实,挽留失去的时光。她以为老克腊能够填补她内心的巨大的空白,但老克腊不是王琦瑶的填充物,也不是她的救命稻草,王琦瑶身上的传奇色彩满足了老克腊的好奇心,王琦瑶很像是老克腊私人收藏的古董,欣赏的意义大于其他意义,古董只能被陈列被展示,它是不可以情绪冲动,把收藏者揽入怀中的,王琦瑶一生在与男人的游戏中始终处于上风,在与老克腊的情感纠葛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了下风,其内在的原因还是不甘心,王琦瑶已经成为了一只古董花瓶,但她不甘心做一个古董花瓶,于是破碎便成了她最终的命运,她的灯光明明暗暗地亮了几十年,最后的一亮没有亮出新的故事,而是新的事故,就像王琦瑶和老克腊之间年龄的距离一样,他们的情感世界其实相隔十万八千里,这种爱的结果,对于王琦瑶来说,仍然是两个字:“错过”,也许还要加一个字:“错”。王琦瑶的选择都是错,所有错误的选择加在一起,其命运必然是“错过”。反过来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所有来到王琦瑶面前的人物,不管是怎么来的,不管是怎么走的,其结果都一样,承担了一个险恶的使命,都是来逼迫王琦瑶作出一个错误的选择。王琦瑶无法逃避那些人,为什么?因为她无法逃避她的命运。
王琦瑶的灯光最后灭于长脚之手,让长脚来熄灭王琦瑶的灯光,是否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一直心存疑窦,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也许符合现实生活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死亡逻辑,也许能暗指王安忆所说的让“小布尔乔亚死于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主题,但是我觉得纵观整部小说,长脚如果一定要过失杀人,应该去杀别人,杀王琦瑶的,也许应该是老克腊,如果是这样,现有的《长恨歌》篇幅可能要更长,那个意味深长的“恨”字,含义也就更加悠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