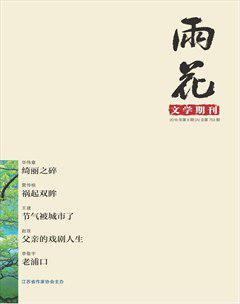寄畅园闻歌:绝情之后的悲调
苏迅
已经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了。康熙九年(1670年)秋季的一天,江南小城无锡西门外的运河中,古老的波纹里,明朝遗民诗人余怀(1616—1696年)驾一叶小舟惝恍而来。诗人已经老去,绿鬓转成苍白,只有襟上酒痕宛然。他依然是遗民,依然是诗人,也依然出游。只是,东南反清势力已经消退。江南,依稀而恍惚,恢复到太平旧观,屠城、掠夺、剃头……都被融化在一片懒洋洋的暖晖中,又被温柔水波像檐尘般冲刷干净了!一切似乎都并未曾发生过。新的生命在诞生,屠城后出生的后生们也已经做了父亲,成天辛劳谋生,为了下一代的生存与繁衍。他们若听见“打仗”二字,一定怕甚至是恨得要骂娘。近十年以来,诗人已经不再敏感地关注所谓时局的变化,一切已无力回天——知识分子曾经的激情与民众的务实对照,虚幻得如同一片羽毛飘荡在空气中——但他的心依然坚硬。他决定把心裹藏起来,彻底忘掉。除了做文人该做的事,他更加精研南曲,于是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南曲鉴赏家和理论家,就连苏州南曲名家徐君见创作的曲谱,甚至也请他写序。
甲申国变之时,余怀刚好二十九岁。在此之前,他的才名已经横溢白门。明末的南京国子监聚集东南数省俊彦,而国子监考试名列榜首者多为寄籍于南京的余怀、湖广杜于皇和江宁白梦鼐,因此人称“余杜白”。余怀的诗得到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老辈的推许。
对于无锡对于惠山,余怀并不陌生。尤其是明亡之后的最初十余年间,他颠沛流离于江南泽国,联络反清志士,他的小舟经常在无锡城里穿梭而过,也经常遥望青葱的惠山。还是在二十年前的顺治七年(1650年)四月,余怀就曾经有过一次出游。那次,他从南京开船,经句容、无锡,到苏州、松江、太仓。后来他还把此次出游的日记编辑为那部绝美的笔记《三吴游览志》。余怀是出发后的第四天抵达无锡的:
微雨东风。自奔牛至无锡。望惠山在烟雾杳霭间,似米南宫用湿笔作滃郁山水,空濛有无,云气与天相接,不复辨草树、峰峦、岭岫也。蹑屐泉水旁,手挹漱齿,荡涤心脾。嗟乎!泉之香清莹洁如此,而曲居第二,正不知金山中冷办何味?古人品藻,岂足据乎!汲数十甓入舟。薄暮,见返照如赤玉盘,云霞捧之入海,真奇观也。
那天,他远远望见如米家山水画般的惠山,还亲自到山下的天下第二泉边汲水数十甓,甚至还为泉水抱怨:这样的好水如果只能屈居第二,那么真不知道所谓的第一要怎么个好法了呢。他为惠山写下了诗篇《海天落照歌》:“空青万里无纤云,明霞掩映红氤氲。朗如赤玉拥球贝,飘若宝马行空群。须臾仙盘堕远海,余光散作天孙文。酒酣发狂望紫气,令人却忆李将军。”那时的诗人满怀着丧国的悲愤,秘密奔波于江南。因为有悲愤在,有复仇的目标在,他的躯体纵然受够了劳顿,他的眼中虽然饱含着血丝,但眸子中闪烁出秋光,如袖里青蛇,神采焕然。因此,他还有牢骚,还有惊讶,还有纵情声色的洒然。枯槁的形容之下,是风神在流动甚至激涌。而九年之后,郑成功的军队在南京城下受挫而返,从此无暇北顾;又过两年,永历帝被擒杀的消息接踵传来,江南反清复明的阵营终于彻底人心冰裂,土崩瓦解……
这一切真像是一场梦。二十年时光就被这样的梦吞噬了。就像这小舟划过水面,沉重的现实只是划出些轻灵的浮影,瞬间也就无影无踪的了。而人,却已老去。
西门外古运河渡头,停泊着同为出游者的诗人刘体仁(1624—1684年)的大船。他准备去访无锡秦松龄。
刘体仁虽然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京赴考清朝的科举并得中进士,但他从小即受父亲的影响,立志效忠明朝。幼年时父亲死于抗击李自成的起义军,弱冠之年他就游幕于抗清保明的阵营。入清后无奈参加科举,违心做了清庭的官,内心一定极度矛盾并饱受煎熬。因此他在职任上,多次做出常人看来“反常”的举动,常常浑然不计个人前程与安危,平反冤狱,强项为官。奇怪的是,他的官运竟然出奇地好,在短短两三年间即从一个小小刑部主事迅速升任为拥有实权的吏部郎中。像这样旁人看来“位居清要”的官职,时当盛年的刘体仁却无心恋栈,没多久就挂冠而去,从此遨游四海,长往而不悔。现在的刘体仁已经是在外游历十余年的闲云野鹤,又在文坛与王士祯、汪琬等“十大才子”并称,且擅长鉴赏书画和娴于鼓琴,文名很盛。而就在这个秋季,他想起了被罢官乡居多年的秦松龄了,他家有著名的园林——寄畅园。
余怀与刘体仁的邂逅,注定是一次奇遇。看着这片满清的新河山,两个诗人携手并立在船头的秋光里,不知道各自心境如何?
余怀对这个颇具才名的留仙太史秦松龄(1637—1714年)应当也有所耳闻。他与刘体仁同为顺治十二年进士,点过翰林。有次顺治帝召试咏鹤诗,秦松龄因为“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两句深受嘉许,皇帝曾对阁臣们讲“此人必有品”,并亲自把他的诗拔置第一。未料两年后散馆时,秦松龄却因逋粮案削籍回乡,从此苦心经营寄畅园。
从明朝户部尚书秦金(1467—1544年)于嘉靖六年(1527年)修建别墅“凤谷行窝”算起,寄畅园在秦氏族人手中累经更迭,屡有兴建已经一百数十年光景。顺治十四年(1657年)太史公秦松龄罢官回乡,他的抱负无处施展,决定重修园林。因为仰慕明朝的造园大师张南垣的艺术,秦家聘请其侄张鉽改造寄畅园。张鉽不负众望,对园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使寄畅园从此成为享誉江南的著名佳构。
秦松龄邀请刘体仁在寄畅园聚会。
而余怀的赴会,明显是沾了刘体仁的光。按照《无锡县志》的说法是:“对岩宫谕(秦松龄)早岁以翰林罢归,招集胜流,名山讌集。澹心以遗民得预佳会,故见之诗歌者如是。”余怀做遗民的时间委实已经太过悠久,他的文名已经伴随着属于他的时代的终结而悄然褪色。但像秦松龄这样的主流文士,是不会太关注这种遗民诗人的,他所瞩目的必定是那些做得一手好应制诗的新贵“才人”。选择做个遗民诗人,同时也注定选择了落寞与憔悴。刘体仁毕竟在新朝出任过要职,且与秦松龄同年,他自然才是有资格参加这样名山宴集的“胜流”与“隐士”——在中国做“隐士”是需要资格的,这个资格就是你有不做隐士的资格。也就是你必须有入仕的途径或者政府的征召,你不去,那才算“隐士”。而像余怀,既不参加清朝的科举,更没有宸音的亲召,那他是连“隐士”一下都是不可能的。
余怀与刘体仁的相识,我猜想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清军南下之际,他们各自在抗清军事力量之间活动,参与幕后策划,那时他们是有可能听闻对方甚至结识的。二是刘体仁在京城任职的三年间,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等遗民多有诗文唱和,也有可能经人介绍而得识荆。刘体仁在性格上残存着明末流行的名士气息,并且具有浓厚的遗民情节,在本质上不属于那个官僚体制,故他与余怀可以惺惺相惜。
而余怀游览寄畅园的动因,倒可能主要是因为那个专擅南曲的秦家班。南曲名家徐君见曾经不止一次告诉他:“得吾之传者,乃在梁溪。今太史留仙秦公之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龙二泉间,不可不见此人、闻此曲。”余怀是慕名已久,故尔自然也是愿意伴随刘体仁前往一游的。
那天,秦松龄姗姗来迟——他乘坐画舫,秦家班的六七个歌者怀抱乐器,一路迤逗凌波而来。同席的还有无锡知县吴兴祚(1632—1698年),以及锡邑名士秦补念、朱子强、刘震修和顾宸、顾天石父子等同好。余怀在他的《寄畅园闻歌记》中作有下述:
于时天际隆冬,木叶微脱,循长廊而观止水,倚峭壁而听响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蹑五丝履,恂恂如书生,绰约如处子,列坐文石,或弹或吹。须臾,歌喉乍啭,累累如贯珠,行云不流,万籁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岂欺我哉!”六七人者各敛袖低眉,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弦、十翻箫鼓,则授之李生。李生,亦吴人。是夕,分韵赋诗,三更乃罢。
秦家班的这六七个歌者仪态万方,黑色的粗麻衣袍与精致的五色丝履相映衬,足见江南特有的典雅与含蓄,更兼人物气质儒雅柔美,难怪要倾倒满座。他们错落列坐于湖石,吹弹演奏。待得歌喉乍启,字吐珠玑,声腔圆润如珠玉落盘,听得停云掩月。余怀不禁故态难遏,狂叫道:“徐君见啊徐君见,你真没有欺骗我啊!”——歌者依然不为外物所动,庄重谨严,法度森然。这样的艺术境界,确实已经超越了技艺的局限。这个夜晚,自然是个尽兴的良宵。久未动情的老诗人爆发出生命底蕴残存的激情,他要呼喊,他要狂歌,释放出已经逐渐冷却的一点光和热。他在当日所作的歌行《寄畅园讌集放歌》中描绘道:
如渑之酒任百罚,淋漓詄荡如奔雷。
华亭唳鹤翔秋水,小队秦宫坐花底。
吹箫擫管拍红牙,细曲清歌遏云起。
悠扬宛转风前度,曲终不用周郎顾。
阳春绝调谁为传?吴郡徐生按宫谱。
却忆香山池上篇,折腰菱与石湖莲。
岛亭合奏霓裳序,赌墅频挥蜀国弦。
淮海风流足千古,河阳移种花千亩。
……
诗人们分韵作诗,直到三更以后方才散却。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无锡城里吴兴祚家中欢宴,秦家班的歌声再次打动老诗人的情怀。
我很好奇,想探究这次聚会在每个人作品中的反映,看看他们不同立场的态度与状态。我特意去图书馆古籍部查证过秦松龄的《苍岘山人文集》,里面虽然收录了几首描写寄畅园的诗词,但这次唱和的记述却不见一字。当日,秦松龄是肯定也有诗作的,但没有收录进集子,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作品一般或者他本人也并不十分看重这一事件。或者又可以反过来看:由于他并不看重这次事件,所以写不出精彩的诗作。刘体仁的《七颂堂诗集》无从查阅,在清末无锡人秦国璋编辑的《寄畅园诗文录》中却发现他的一首题为《寄畅园》的诗,从内容分析,我估计就是这次聚会的唱和作品,却也不见得高明。因为这次际遇,余怀写下了《寄畅园闻歌记》和《寄畅园讌集放歌》一文一诗。这两篇文字,后来成为人们研究昆曲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他的这两篇作品在三百余年后出奇地受到重视,除了文学修辞角度的价值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历史信息以及作者对艺事本身的真知灼见。寄畅园闻歌,对余怀而言,虽然他只是个追随的清客,不过是他乡偶遇的一次随喜,但是,却是他对个体生命价值彻底绝望之后赤诚余绪的一次迸发,他把这一曲悲调付诸文字。这样的文字注定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即便身份的卑微、时光的流转以及价值观的更迭,都无法消解这种文字应有的价值。而他给予三百年后同样作为写者的我的另一个启示是,真正的文章,除却它应有的修辞价值之外,还必须拥有更宽泛的文化上的指向与价值。
欢会后,是离散。
余怀说:“独我凌波向南浦”——他的一叶小舟,向着南昌那边游荡而去。二十三年后,余怀著成他的代表作《板桥杂记》,这是部记述晚明南京青楼逸事的笔记,也是在长达三百余年间,传统文人们一直没有能够将他彻底遗忘的唯一理由——因为这部书表面的香艳。“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后人又有几个能真正懂得余怀写这部书时的用意与心境?
刘体仁还是乘坐他的大船继续泛波五湖,在月明如洗的船头,还会弹奏一曲。十四年后的一天,他出游至湖北钟离,突患急症,不治而亡。日后他被列入《清史稿·文苑传》,很简短,三行字。进入《文苑传》是他本意,三行字也符合他的个性。他的遗作《七颂堂诗集》、《七颂堂文集》和《识小录》流传下来。他短短的三年为官经历,长时期被后人记忆。
秦松龄在寄畅园里又优游了九年之后,终于按耐不住施展抱负的壮心,再次进京参加了“博学鸿儒”科的考试,取得一等,复授官职。像他那样曾经点过翰林的又去考“博学鸿儒”科是很少见的,后来充任顺天乡试正考官,又因监考不谨磨勘落职,终于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所著《苍岘山人文集》和《毛诗日笺》都得以流传,但作为一个以仕途为最终目的的文人,他终究是抱憾终生。
吴兴祚后来则官运亨通,历任福建按察使、福建巡抚、两广总督,仕宦中外四十余年,为官清廉,并以才能干练著称,成为清朝早期的名臣。其著作有《宋元诗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但为官声所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