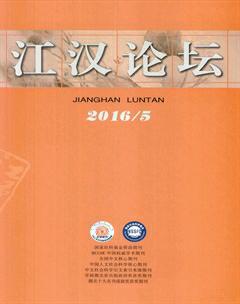《魔山》作者与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之遭际
卢伟
摘要:《魔山》作者托马斯·曼一直保持着对时代思潮和现实图景的敏锐把握,钟情于探讨死亡、哲学和神学等终极性命题。他的思想和作品体现了在人文主义启蒙和科学主义统治的时代对传统宗教神学进行的反思和发展。《魔山》生动描绘了20世纪时代背景下基督宗教神学所面对的理性与信仰、人本与神本、科技与情感之遭际,以及传统神学的演变分化和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其思考和结论对于探索当代基督宗教神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魔山》;托马斯·曼;基督宗教神学;当代神学
中图分类号:B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61-05
写出了名著《魔山》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是一个典型的拿来主义者。他习惯乃至沉溺于对社会百态和精神世界的冷静观照,借用各种思想和知识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组合各种意象拼凑成文。而《魔山》,更是包罗万象,意蕴丰赡。其中。作者与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风云际会尤其不可忽视。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自宗教改革以降,基督宗教神学经历了极大的改变。在纵向上,科学理性的崛起直接给予了传统基督宗教信仰以打击。迫使其放弃原有疆域而转向主观唯心主义的灵性思维;在横向上,欧洲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接触、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日益频繁,基督宗教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族、地域、政治上的派别分野,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层出不穷。由此导致的信仰危机深刻影响了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一大批欧洲学者、作家。见微知著。通过剖析托马斯·曼在诸多形而上命题上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之遭际。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时代背景下基督宗教神学之境遇及其应对策略。并由此清晰对基督宗教神学的整体观照。
一、科技时代之信仰危机
托马斯·曼一直钟情于死亡。“一个人为了善良与爱情,决不能让死亡主宰自己的思想。”这是《魔山》中用重点符号标出的唯一的句子,也是托马斯·曼面对在理性时代颓然崩毁的信仰废墟时做出的痛苦思索。加缪有言:哲学的真正命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擅长哲思的托马斯·曼钟情于死亡,并不奇怪。而对于死亡这一永恒之谜的痛苦思索,也正是神学思想所观照的重要疆域——如果说不是唯一的话。《魔山》主人公的迷惘和追寻,正是现代基督宗教神学求思求变的生动写照。
死亡的主题贯穿于托马斯·曼一生创作的始终。从最初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到其创作的顶峰《魔山》,再到《死于威尼斯》、《浮士德博士》、《绿蒂在魏玛》等作品,对死亡的沉迷如影随形,并伴之以艺术、爱欲、疾病等各种变形。从认识论层面而言,托马斯·曼的这一主题,是科技时代之下传统神学观念和人文思想者所必然遭遇的信仰危机,也是现代基督宗教神学观念的文学化和世俗化表达。现代基督宗教神学态度有别于天主教传统信仰的关键之处,即在于其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的内在论思想倾向,“这种体验性信仰因基于其对宗教的自然理解以及其主体性、历史进化性意义之诠释而使《圣经》和教会传统所强调的超自然启示相对化,并失去其神圣效应。……不同时代之变化而引起的教会理论之多变性、相对性。对基督教真理之绝对性和永恒性打上了问号”。其结果势必是放弃中世纪以来传统天主教关于其信仰、教义和教会具有超自然特征的立场。把信仰等同于纯然内在的、属于人类存在本质的一种对上帝之体验。
《魔山》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大学毕业生汉斯·卡斯托尔普趁暑假到阿尔卑斯山上的达沃斯疗养院探望自己的表哥。原本只打算停留三个星期。结果却与死亡的气息和种种诱惑迎面相撞。女性的肉体、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极端宗教情怀、现代科技对生命的透视等等。使得原本单纯的“正常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变成了一名病人、一名艺术家和思想爱好者,在山上一呆就是七年,在疾病、爱情、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等等“不正常”的事物里面徘徊沉迷,并接受两名“思想导师”的说教熏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把他召唤下山。不难看出,小说文本是托马斯·曼的自我思想解析以及对20世纪初欧洲思想界众生相的细致临摹。这其中的重头戏和最终归宿。则指向基于神学和哲学的对死亡的思考。
《魔山》营造了小说的特殊环境。即与世隔绝的高山,环境清幽,自成一体,如同一个放大了的浮士德书斋。在这里,世俗的生活理念、处世原则统统被置疑。这是一个作家为了展开灵性思维而刻意营造的封闭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作者凸现了肉体的衰弱、放纵和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仰危机。高山疗养院里充满着疾病和死亡的气息,让人时时刻刻感觉到肉体的衰弱和局限,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在死亡面前不值一提。人们看穿了生命的虚无,因此变得放纵起来,于是在疗养院疾病和死亡的腐臭气味儿中间又掺杂了一些尽情狂欢的暖昧气息。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自己身体的x光片后大吃一惊,从那细致入微的血管、神经、骨骼和软绵绵的、云雾一般的肌肉的影象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现实的残酷。“虔敬与恐惧之心不禁油然而生,……透视了自己的坟墓。预先看到了自己身体日后的腐化过程,现在他能活动的皮肉。将来会分解、消失,化成一团虚无缥缈的轻雾”:他所见到的种种疾病莫不经过细致描写而真实得令人恐怖;山上的医生一再细致叙述人体的构造乃至死亡后尸体腐烂的过程……如此种种,是科技进步和理性启蒙给人类带来信仰冲击的真实写照。“信仰是豁出去的,而不是算计出来的。”而当人们学会算计——亦即启蒙——以后。豁出去的勇气消失了。科技使人清楚地透视死亡的全过程。而迷失了以往寄托于死亡背后的生命意义。
这一近代思想启蒙的发展历程在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得到了生动展现。在刚上山时,他敬奉天主教,态度严肃,敬重生命,鄙视夸夸其谈,坚持山下的世俗生活的正确性。然而经历了种种之后.他确实受到了震动,隐隐地感觉到,这个地方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他用警惕的眼光观察着周围。一言以蔽之:他从中世纪传统的天主教信仰之下闯入了启蒙时代的当代神学新语境。也因此必然经历科学进步的大时代背景下基督宗教神学观念所遭遇的尴尬和挑战。一直深受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思想影响的托马斯·曼把小说的主题概括为:钟情死亡,同时又“贬低死亡的诱惑力,贬低极度的混乱对井然有序、并且奉献给秩序的生活的胜利,使之下降到滑稽范畴”。这也正是当代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发展的文学化表达。
现实中,基督宗教神学也确实经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般的迷惘和震惊,在科技时代的大背景下,基督宗教神学所能统辖的人类思想领域迅速缩小。面对科技带来的观念挑战并据此作出教义调整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梵二”会议精神。罗马教廷于1966年6月14日正式宣布取消《禁书目录》;1979年4月4日,约翰·保罗二世进而敦促全世界神职人员钻研科学,要求他们既要有真正的科学训练,又要有世界水平的专门知识;1992年10月31日,约翰·保罗二世在教廷科学院发表演说,公开为伽利略及其“日心说”平反,声称教廷对伽利略的谴责反映出教会过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是“拒绝接受科学进步”的象征。他总结性地指出:“人们可以从伽利略案件中吸取对今天出现的或明天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除了两种偏见的和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外,今天还有一种包括和超越了这两种观点的更开阔的见解。”这些都是当代基督宗教神学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观念和信仰姿态的表现。
二、理性启蒙之神学交锋
在新时代的各种冲击之下,当代基督宗教神学积极求变。按照当代新教神学的立场,此种改变乃是回复正途,“公元1517年及往后的数年中,一连发生了许多事情。把世界历史推进一个新的世纪。这期间,罗马教会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挣脱了专制暴政,基督徒终于恢复自由”。故新教亦称“复原教”。恰如文艺复兴打着“复兴”的旗号而开创了人文艺术的新格局。当代基督宗教神学亦在“复原”的宗旨下。开创了与当代哲学思潮不无契合勾连的诸多神学思想。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梵二”会议之后,更是强调“一种信仰、多种神学”.基督宗教理论思潮呈多元发展之势。在各种神学体系的构筑中.人们有着全新的立意和思路,其考虑问题的视域亦互不相同。例如,“新托马斯主义作为当代天主教神学百舸争流中的一支仍保持住其发展势头。醉心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家则开始建构一种追求形上之探和绝对体验的超然神学。而受存在主义思潮影响的神学家却侧重于人的诗意栖居及其灵性倾诉”。这些纷繁变化发展的思想苗头,早在百年以前已经种下,擅长观察的托马斯-曼也早已将其描绘于笔端。
在《魔山》里,造成汉斯·卡斯托尔普思想转变的,是他的两位“精神导师”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人的思想交锋加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思想变化的描写,构成了《魔山》中哲理思辨部分的主体。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塔姆布里尼是一个外表寒酸、举止优雅的落魄贵族似的意大利人,他直截了当地声称“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自豪地承认人文主义者都有些说教的味儿,从一开始便牢牢地占据了启蒙教师的角色。开始了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谆谆教诲。仿佛慈父对孩子的教诲,又仿佛上帝对子民的训诫。托马斯·曼有意加强人文主义与神学教义的关联,采取了相当明显的象征手法。
有一天大约过了十点钟或十二点钟,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已卧在床上。这时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塞塔姆布里尼就在门槛上出现了;门开时,房里顿时耀眼地亮起来。原来客人开门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天花板的吸顶灯开亮。灯光把天花板照成一片银白色。然后又反射在家具上,转眼间,整个房间就变成雪亮的了。
塞塔姆布里尼以光明的形象出现,给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在以后二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比如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饭桌上对塞塔姆布里尼说:“于是你来了,开亮电灯,把年轻人引到正路上——你不是这样做的吗?”我们知道。托马斯·曼是一位善于并且喜欢运用主导动机的作家,反复提及某一情节,必定有其寓意。在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中,光明与鸽子等物一样,象征着启蒙、救恩和信仰。简言之,就是圣灵。
而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替诺那里,世界的本原是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太一、精神(nDus)和灵魂。太一是至高无上的抽象存在。类似于中国的“道”或基督教的“逻格斯”(L0gos);精神(nous)次之。是太一的影子,也是太一在其自我追求之中的所见;灵魂更次之,居于人的胸中。用柏拉图善用的太阳的比方来说,太一就是太阳。精神则是太阳的光芒,照亮人的灵魂。这光芒既来自于太阳,又证明着太阳的存在。“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光亮就是神,就是启蒙.这种光明的形象和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适合塞塔姆布里尼的身份的。他以启蒙者自居。处心积虑地要照亮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灵魂。然而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L失败了:一方面汉斯·卡斯托尔普经不起肉体的诱惑,爱上了有着东方人面容的肖夏夫人,这在塞塔姆布里尼看来是非常堕落的行为;另一方面,义来了一个对手纳夫塔,此人抱着与塞塔姆布里尼几乎截然相反的观念。同他展开了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灵魂的争夺。
纳夫塔是一名犹太裔耶稣会士。他与塞塔姆布里尼的思想主张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强烈的说教欲和责任感,争先恐后地争夺思想阵地。当其中一位开始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进行谆谆教诲的时候,另一位必定如坐针毡,痛心疾首于青年人思想有堕入歧途的危险,必欲拨乱反正而后快。这种关系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上帝和撒旦对人类灵魂的争夺。实际上。托马斯·曼也确实把这种思想交锋与宗教联系了起来。塞塔姆布里尼出场的一章,其章名赫然曰:《魔鬼》。其后在塞塔姆布里尼劝说汉斯早早下山的一章.章名则是《魔鬼提出不光彩的建议》。而纳夫塔出场的一章,章名则是《又来了一个人》。在这纷繁复杂的交锋之中,托马斯·曼借主人公之口说道:“全然不可能区别真理究竟在哪一边——不知哪里是上帝。哪里是恶魔,哪里是死亡,哪里是生命。”“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虔信宗教的,一种是信奉自由思想的。这两种人各有各的优点,可是我心底里却反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就是塞塔姆布里尼式的人,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理解人类的尊严,这未免言过其实。”这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一种本能的宗教信仰的自我辩护。
当代最为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认为,“现代社会正经历着一种文化病症所带来的痛苦.其不幸可追溯到路德、笛卡尔和卢梭这三位改革家所引起的基督教思想界之分裂和经院哲学之解体路德以唯信称义而使信仰摆脱理性,导致了现代社会反理性意向的主观主义之发展:而笛卡尔以其唯理主义拔高世人,造成了现代人自比天使的唯我孤傲;卢梭则以人性本善、生有美德之论来消除人心的神圣渴求,引起了一种虚幻的乐观主义之蔓延。从此,近代思想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潭中”。实在是妙得很!这三种姿态恰恰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卡斯托尔普及其两位精神导师一一对应。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托马斯·曼对20世纪初欧洲思想界众声喧哗之脉络的精确把握。
理性启蒙与传统神学的交锋。带给人类严重的信仰危机和当代病症。托马斯·曼经过痛苦思考,以小说主人公为传声筒发出的最终结论是:“一个人为了善良与爱情,决不能让死亡主宰自己的思想。”这是基督宗教神学在现代世界的新发展和新结论,同时亦是回归本质的呼声。因为自始至终,基督宗教的共有特点即是要人通过爱而得以成圣。人是“爱的生存”(ens amana)并藉此消除精神与生命的二元对立。精神靠观念来贯穿生命、使生命获得意义,而生命则使精神活跃、得以实现其观念。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理性启蒙时代的挑战是痛苦的,但也是使基督宗教神学回归本质沉思的必要磨砺。
三、多元文化之时代遭际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基督宗教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真髓和灵性本质。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发生接触、碰撞和交流。在与异质文化的交往中,基督宗教已呈现民族化、地域化和政治化等多元发展之势,在许多方面进入了文化转型和体系重建。“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基督宗教的思想和社会发展均出现了扬弃或超越其传统的革新运动。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应运而生,从而促使基督宗教的文化体系本身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和发展于《魔山》及其作者托马斯·曼都表现出明显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借诸上文提及的两位精神导师之口表达出来的。
塞塔姆布里尼所主张的是以人文主义、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他有烧炭党人的家学渊源.一心致力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文主义的弘扬。他为自己的祖国在欧洲大陆率先展现了启蒙、文明和自由的旗帜而自豪,也赞扬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法国的七月革命,甚至慷慨陈词说“巴黎的三天就功绩而言,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足可并驾齐驱,所有的人都将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样的说法在笃信基督教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简直是亵渎神明。然而又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影响。毕竟,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生活的年代,人文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进步等等都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坚信不疑的基本价值观。同时,塞塔姆布里尼的宗教身份也与之匹配。他是一名共济会会士。因此坚定地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启蒙、理性、教育和促进社会进步,并糅合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积极的理性精神。正是由于这样的双重性.即浓厚的宗教色彩源头和鲜明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混合,使得托马斯·曼自然而然地把塞塔姆布里尼描写为上帝和魔鬼的混合体。
塞塔姆布里尼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因循守旧的原则和不断变动的原则,也就是进步的原则。”他显然毫无保留地主张后者。他热爱人类,在政治上对玷污和降低人类尊严的一切观念,都采取反抗态度。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基督宗教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型。
与之观点鲜明对立的纳夫塔是一名犹太裔耶稣会士。耶稣会作为传统的天主教派别之一,由圣依拉爵·罗耀拉(St.Lgnatius Layola)创立于1534年。耶稣会的宗旨是巩固和传播天主教教义,它最大的特点是重视教育和对青年人的培养。因此,纳夫塔十分热衷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谆谆教诲就不足为奇了。耶稣会属于宗教保守派别,抱有“愈显主荣”的宗旨和绝对服从教皇的信念,虽然当初设立并非为反对宗教改革,然而却在日后的发展中成为教廷的有力工具,致力于天主教复兴和反对宗教改革。耶稣会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理性嗤之以鼻,认为那是肤浅。故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和表兄在得知纳夫塔是耶稣会员时,才会大吃一惊,表现得万分惊愕。纳夫塔怀有强烈的宗教情怀,歌颂绝对的精神,歌颂天主教,竭力反对人文主义和新教思想,认为那是泛滥的自由和愚蠢的胡闹,跟人类的利益背道而驰。他有着强烈的末世情怀,甚至是冷酷的世界观。他不像共济会会士那样悲天悯人,积极人世,而是恪守严格的宗教原则。纳夫塔“生来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同时对于优裕的、惟我独尊的和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他梦寐以求”。他攻击国家。鼓吹天下一家。这一点跟塞塔姆布里尼的建立大一统世界的观点倒是比较类似。只不过在纳夫塔这里。他的天下一家是天主教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而在塞塔姆布里尼那里.这个天下大统是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天下。——这种形而上的、近乎审美意识形态的“哲学统一”而非世俗的“政教合一”,也是基督宗教与政治关涉的新形式。
地域及相异文化对这两个人物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如塞塔姆布里尼认为纳夫塔表现了纯粹的宗教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而这种蒙昧和停滞是带有东方文化特点的宗教产物。犹太教起源于东方,正统的天主教也带有相当的东方色彩。而现在的欧洲应该是新教的天下,换言之,是西方的启蒙思想的天下。塞塔姆布里尼指出,基督教起源于东方,因此带有东方可疑的性质。他认为东方人害怕活动,并引用了老子关于清净无为的阐述。在他看来,“主导思想的总是理性、分析、活动,以及进步,而不是什么僧侣的躺椅”,因此,他主张人世和培养生活兴趣,反对感伤地逃避世界。“这是一场理性与非理性、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冲突,而‘非理性也正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中,人们批评东方、尤其是老庄神秘与虚无的着眼点。”塞塔姆布里尼对东方思想的成见,无疑反映出托马斯·曼本人对东方哲学的一知半解。为了挽救年轻人,抵消纳夫塔造成的不良影响,塞塔姆布里尼一再告诫汉斯·卡斯托尔普。指出他是西方文明的子孙:“静寂的极乐和催眠术的冥想,它不是欧洲的要素。而是同这块活动的土地的生活原则无缘的、甚至是敌对的要素……重心可怕地偏向东方。而西方的要素不但直到今天还无法与之抗衡,而且还有烟消云散之虞。”在他看来,东方与西方在世界观上是截然对立的。他还说。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位于欧洲中央,东西方交会之处,因此“贵国应当在灵魂里完成这样一种决定。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它必须作出抉择。它必须最终地、有意识地在各自争夺自己立足点的两个世界之间作出决定。您年纪正轻。您在这样的决定中间也有份,您有责任去施加影响”@。纳夫塔则从四海一家的世界未来图景入手,暗示这些满口理性、自由、进步的肤浅的家伙只关心世俗的进步,不顾精神的信仰。他说:“初期的天主教会的传道士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警告人们,要警惕哲学家和诗人的谎言,特别叫他们提防不要为维吉尔的花言巧语所毒害。今天,当一个世纪已经走向没落,无产阶级的黎明又一次在望时,我们实在应当有同样的感受。”他鄙夷地称呼塞塔姆布里尼是保守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指责资本主义不够先进一样一虽然塞塔姆布里尼一向自封为激进主义者、启蒙主义者。这让塞塔姆布里尼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综上,无论是两位精神导师的激烈争论,还是近代以来基督宗教神学所经历的种种曲折。这场思想的战役包括了无数次小的战争和交锋。涉及领域横跨宗教、哲学、音乐、文学、政治……纷繁深邃,令人咋舌。其结果,必然是促成多种有着共同宗教起源而又大异其趣甚至截然相反的世界观的产生。正如上文曾引用的那句小说主人公的名言:“全然不可能区别真理究竟在哪一边——不知哪里是上帝,哪里是恶魔,哪里是死亡,哪里是生命,”一切都是模糊和不可知的。这也正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基督宗教神学发展的生动写照。
结语
近现代以来的基督宗教之存在与其传统相比已大有不同,在世界范围内的革新运动层出不穷,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应运而生,从而促使基督宗教文化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托马斯·曼继承了德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热衷于哲学思辨。赋予了《魔山》这部巨著丰赡内涵。《魔山》作为20世纪初欧洲文化界的缩影。生动反映了近代以来欧洲思想界与基督宗教神学观念的互动。神学不再是传统的封闭系统,各个基督教派之间、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及思想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成为时代潮流。庞大的神学体系向现实敞开大门,深入到社会处境的各个方面。《魔山》开启了我们认识这一时代发展的途径。见证了其作者作为时代的思想者与基督宗教神学的遭际,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当代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