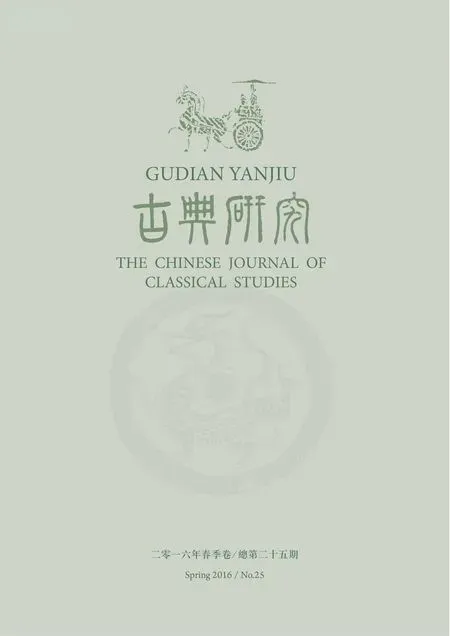《斐德若》中的“忒伍特神話”解析
戴曉光(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斐德若》中的“忒伍特神話”解析
戴曉光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言辭與書寫是《斐德若》集中探討的核心主題。柏拉圖在《斐德若》中表明,對文辭的熱情不僅是關係到斐德若與蘇格拉底個人靈魂的愛欲問題,而且是關切到城邦政體精神品質的政治和文教問題。由於智術師啟蒙的思想背景,斐德若的文辭愛欲是公元前五世紀雅典民主文化的表徵。在“忒伍特-塔穆斯神話”中,蘇格拉底以講述神話的方式,對智術啟蒙式的書寫觀念提出了深刻的質疑。神話中的忒伍特與塔穆斯,分別代表關於書寫與政制問題的兩種理解方式——啟蒙理想與王政傳統。塔穆斯對忒伍特的批評表明,書寫啟蒙的初衷是普遍改進人的天性,但由於試圖以智識化的“記憶”取代靈魂的“回憶”,普遍化的書寫啟蒙將會導致人性的普遍敗壞。蘇格拉底在“忒伍特-塔穆斯神話”的基礎上對智術化寫作提出了深刻的批評。
Author:Dai Xiaoguang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E-mail:polisday@ruc.edu.cn
在所有柏拉圖對話中,《斐德若》是與言辭/書寫的主題關係最爲密切的作品。正是斐德若對成文言辭的愛欲引發了整篇對話的基本情節,不僅如此,對話的主題也集中於言辭寫作與個體靈魂乃至城邦生活的密切關係。蘇格拉底雖然終生未立文字,但柏拉圖恰恰在《斐德若》中表明,無論是爲了完整地理解文字書寫的性質,還是爲了從事以滋養靈魂爲目的的書寫技藝,對“何爲真正的文辭寫作”的探討都將指向蘇格拉底式的智慧。
然而,我們也在柏拉圖的作品中讀到,在民主制的雅典,無論在城邦政制的問題上還是言辭書寫的問題上,蘇格拉底式的智慧都遇到另一種智慧聲稱的挑戰——智術師的啟蒙教誨,後者與蘇格拉底式智慧之間的爭論,構成了蘇格拉底在哲學生命中始終面對的內在張力。在以書寫問題爲主題的《斐德若》中,蘇格拉底與智術師的爭論同樣構成了貫穿對話的內在推動力。《斐德若》不僅呈現了二者的爭論,而且將這種爭論呈現爲蘇格拉底引導、說服斐德若的教育過程。面對沉迷於呂西阿斯智術講辭的斐德若,蘇格拉底不僅通過兩篇講辭揭示了對愛欲的完整理解,從而在講辭主題和技藝上勝過呂西阿斯,而且在對話的後半部分用嚴密的論證向斐德若表明,由於無法認識靈魂的真實,智術師的修辭談不上真正的言辭/書寫技藝。對於淨化斐德若的文辭愛欲這一目的來說,直到完成對修辭技藝的辯證討論後,探討何爲真正的書寫技藝的時機才真正成熟。儘管從斐德若最初向蘇格拉底展示呂西阿斯講辭時開始,書寫的問題就已經籠罩了《斐德若》的對話情節,但直到對話臨近結尾的部分,蘇格拉底才引領斐德若開始了“何爲好的寫作”的探討——在對書寫技藝的探討中,蘇格拉底所講述的“忒伍特-塔穆斯”(《斐德若》274c5-276a)*本文引用的《斐德若》譯文依據劉小楓譯本,參劉小楓編譯,《柏拉圖四書》,北京:三聯書店,2015。文中凡《斐德若》引文皆隨文標注,不另作注釋。神話佔據著最爲醒目的關鍵位置。
一、神話、寫作與政體

蘇格拉底爲甚麼要用一個異邦神話開始關於書寫的討論?
可以注意到,“忒伍特-塔穆斯”神話最鮮明的外在特徵是,這個神話發生在王權統治下的古代埃及。相比之下,如今的雅典城邦則年輕得多,不僅在歷史上年輕,尤其是在政制上年輕*比較《蒂邁歐》(22b-c)中埃及祭司的著名說法——希臘人永遠只是孩子,沒有人能成爲老人。原因是,“希臘人的靈魂是年輕的,其中沒有任何包含長遠傳統的古老觀念,沒有上了年代的知識”。謝文鬱譯,《蒂邁歐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5-16,略有改動。——不斷革新的雅典已經用民主政制取代了曾經的王權政制。不僅如此,忒伍特神話的主題也與王者統治直接相關。那麼,我們通過這個埃及神話首先注意到的是,蘇格拉底是在政體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寫作的討論。進一步說,書寫問題似乎也構成了理解兩種政制差異的切入點。
總之,埃及神話的外觀給我們的直觀印象是,在將討論推進到寫作問題時,蘇格拉底再次將城邦政治生活的主題設定爲對話的總體基調。這種主題上的深化和推進暗示,只有具備能夠理解政治生活品質的智慧,才有能力對寫作問題做出準確的衡量。寫作技藝的討論預設的是王者或治邦者的政治洞察力。事實上,蘇格拉底在剛剛結束“悔罪詩”,隨即倡議斐德若探討何爲好的言辭和寫作的問題時,就曾經通過援引呂庫戈斯、梭倫和大流士的例子,把言辭/寫作問題納入涉及城邦立法的政治視野之中(258c)。蘇格拉底現在通過埃及塔穆斯王的神話探討寫作問題,便與言辭/書寫討論的開頭部分形成了前後呼應。可以說,蘇格拉底用王者、立法者的例子,亦即用政體問題框住了《斐德若》整個後半部分的討論。
書寫討論的埃及背景同時提醒我們,希臘與埃及分別適宜作爲討論言辭與書寫問題的各自語境。也就是說,言辭問題顯得尤其與希臘城邦有關,在埃及則並未構成涉及城邦生活的政治要素。這個差異也揭示了希臘民主政制與古老的埃及王政之間的重要區別。言辭之所以並未在埃及構成政治要素,原因在於,古傳宗教和神聖律法構成了維繫共同體的權威裁斷,*比較伯納德特(Seth Benardete)對埃及王政與神聖律法之間關係的分析,參氏著,《道德與哲學的修辭》(Rhetoric of Morality and Philosophy:Plato’s Gorgias and Phaedru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頁187-188。這種裁斷凝聚了民人關於善惡與正義的權威意見。相反,言辭在民主制的雅典發揮關鍵的政治角色,則是因爲紛爭中的種種道德意見都獲得了平等的地位——民眾在關於善惡的事物上莫衷一是,但也正是這些“莫衷一是”的道德意見取代了權威的位置,並構成了民主政制的常態,說到底,修辭術在雅典城邦的重要角色正是上述政治常態的反映。不過,與言辭之於民主政治的特殊性不同的是,書寫卻具有一種與言辭不同的普遍性——書寫構成了一切文明城邦的政治要素,原因在於,書寫終究涉及的是城邦的立法問題。*對此問題,可參加拿大學者伊尼斯以帝國治理模式爲主題展開的比較文明研究,在比較希臘式“口頭文明傳統”與埃及式“書寫文明傳統”的語境下,伊尼斯客觀上強調了書寫在所有政體中的重要角色。參伊尼斯,《帝國與傳播》,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尤其參見該書第二、四章。另外比較Phiroze Vasunia對書寫與埃及王權政治關係的分析,參氏著《尼羅河的贈禮:從埃斯庫羅斯到亞歷山大時期埃及的希臘化》(The Gift of the Nile:Hellenizing Egypt from Aeschylus to Alexan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頁151-152。無論對於此前提到的斯巴達、波斯、雅典,還是現在提到的埃及,書寫都與立法、亦即共同體的靈魂秩序問題有根本的相關性。與言辭相比,書寫問題更直接地觸及到共同體靈魂秩序的根源。我們因而看到,“言辭”在埃及並未成爲內在的政治要素,但書寫問題在埃及語境下卻尤其具有根本的攸關性。那麼,言辭在埃及所處的邊緣位置以及書寫問題獲得的慎重關注,是否都與埃及傳統中的王者智慧有某種共同的關聯?我們值得帶著這些問題閱讀蘇格拉底所講述的“忒伍特-塔穆斯”神話。
二、忒伍特神話:王政與啟蒙
在埃及的瑙克臘提斯一帶那兒,曾有某個古老的神,屬他的那只聖鳥叫做白鷺,這精靈自己名叫忒伍特。正是他第一個發明了數目、計算、幾何和天文,還發明了跳棋和擲骰子,尤其還有文字。再說,當時整個埃及的王是塔穆斯,他住在這個上埃及地的一座大城——希臘人管它叫埃及的忒拜,把塔穆斯叫阿姆蒙。忒伍特去見塔穆斯,展示他發明的諸般技藝,說得讓這些東西傳給埃及人。(274c5-d6)
蘇格拉底通過對兩位埃及神靈——忒伍特*忒伍特即埃及的赫爾墨城(Hermopolis)的托特神(Thot),希臘人將他等同於赫爾墨斯。參《柏拉圖四書》譯者注,前揭,頁390。與塔穆斯——的介紹開始了這段神話。兩個神所在的地點有所不同,位於尼羅河下游三角洲的瑙克臘提斯(Naucratis)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距離希臘更近,而且本身便是一個希臘殖民城市,是古時埃及僅有的商港。*希羅多德,《原史》卷二179,王以鑄先生譯,希羅多德,《歷史:希臘波斯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頁190。亦參G.J.de Vries,《〈斐德若〉疏解》(A Commentary on the Phaedrus of Plato),Amsterdam:Adolf M.Hakkert Publisher,1969,頁247。Harvey Yunis,Plato’s Phaedrus(Cambridg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頁227。相比之下,塔穆斯所在的忒拜則隸屬上埃及,位於尼羅河上游。伯格(Ronna Burger)關於兩個城邦的評論對我們頗有啟發:“如果瑙克臘提斯代表現代,即貿易和各種技藝的興起,並被視爲希臘的疆土,那麼忒拜則代表著古代,是神諭及其祭司們的家園,並在最初被視作整個埃及”。*伯格(Ronna Burger),《柏拉圖的〈斐德若〉:爲哲學的書寫技藝一辯》(Plato’s Phaedrus: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f Writing),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0,頁93。從蘇格拉底簡短的描述中的確可以看到,忒伍特神不僅在地理上距離希臘更近,而且本身也頗具希臘特性——忒伍特是一位愛好發明技藝的神。忒伍特的發明中既包括數學、天文等嚴肅的學識技藝,也包括供人消遣的技藝,但這些技藝卻大多帶有智識屬性,要求智性天份。因此,忒伍特發明的技藝適合智性很高、天性特殊的人。不僅如此,由於數學、天文的技藝意味著對自然的探究,亦即蘊含著以自然理性挑戰神法秩序的革命性,*這種挑戰其實不僅限於數字、幾何、天文等理論技藝,例如,骰子的發明雖是遊戲,卻預設了偶然-必然的概念,這組概念以不同於神意的自然規律爲前提,因而同樣對宗教和神意秩序提出了潛在的質疑。這類技藝與埃及的宗教傳統存在著潛在的緊張。不過,蘇格拉底讓我們看到,忒伍特前去見塔穆斯,目的是把這些智識技藝教給所有的埃及人。這意味著富於革新精神的忒伍特明顯不同於埃及政體的古老、保守的精神,忒伍特不僅有智慧,而且是一個有啟蒙熱情的神。不過問題是,忒伍特的啟蒙熱情會對埃及人產生普遍的好處嗎?蘇格拉底的敘述已經暗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於習慣於在希臘諸神與埃及諸神之間追根溯源的希臘人來說,蘇格拉底講述的忒伍特形象不難令人聯想到善於發明技藝的普羅米修斯*根據埃斯庫羅斯的說法,普羅米修斯除了盜火給人類外,還發明了建築、天文、數學、航海和文字。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行442-460,采羅念生先生譯文,《羅念生全集》第二卷(《埃斯庫羅斯悲劇三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109。——在《論科學與文藝》中,對古希臘傳統了若指掌的盧梭就強調了普羅米修斯神話的埃及起源,“有一個古老的傳說,從埃及流傳到希臘,說的是一個與人的安謐爲敵的神發明了科學”。*盧梭,《論科學與文藝》,劉小楓譯文,2012未刊稿。英譯見Victor Gourevitch編,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影印本),2003,頁16。盧梭的說法告訴我們的是,忒伍特與普羅米修斯的傳說的確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不僅如此,盧梭對忒伍特/普羅米修斯的評論也印證了我們對蘇格拉底意圖的猜測——忒伍特毋寧是一個“與人的安謐爲敵的神”。*比較西方學者斯文森如何論到普羅米修斯通過技藝實施啟蒙爲政體結構帶來的影響: 理性提供了選擇,人類才能選擇一種反對神聖正義的方式來支配自己。對算術的認識不僅產生了對比例的認識,而且產生了對平等的認識。因此,人們不是根據他們的不同來安排自己,而是根據他們的相似——他們能夠民主地分配權力。宙斯憤怒也不奇怪,他把理智委託給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卻把它給了一個沒體會過自治的新生種族,這個種族不會明白等級安排的本質。 參斯文森,《普羅米修斯、宙斯和伊娥眼中的正義》,引自劉小楓編,《古典詩文繹讀 古代編 上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82。忒伍特的啟蒙意圖恰恰對埃及的古老政治傳統構成挑戰。忒伍特去見塔穆斯王,引發的將是代表兩種政體精神的新神與舊神之間的對話。我們隨即看到,塔穆斯將對忒伍特發明的種種技藝進行評判,而評判的背景正是王政傳統與啟蒙精神的相遇。我們應該注意到,蘇格拉底此後尤其強調了塔穆斯對文字技藝的看法,這種強調仍然以兩種政體要素的相遇爲前提:
塔穆斯就忒伍特的每項發明說了許多,有褒有貶,細說恐怕就會話太長。且說當說到文字時,忒伍特說:“大王,這個是學識哦,會促進埃及人更智慧,回憶力更好。因此,這項發明是增強回憶和智慧的藥。”塔穆斯則說:“極有技藝的忒伍特啊,有能力孕生種種技藝是一回事,有能力判定給就要利用技藝的人帶來害處和益處的命份,是另一回事。眼下啊,你作爲文字之父出於好意把文字能夠做的事情說反啦。”(274e-275a)

然而,塔穆斯王卻對忒伍特的智慧提出了懷疑。塔穆斯首先以最高級(或絕對級)稱呼忒伍特——“極有技藝的忒伍特”,既突出強調了忒伍特在發明技藝方面的卓越才能,又暗示這恰恰是忒伍特的局限所在。畢竟,極其有能力發明技藝是否是智慧的全部,甚至是智慧本身?塔穆斯隨後做的區分恰恰是在有意澄清智慧的類型問題——塔穆斯區別了“孕育技藝的能力”與“判定技藝對人的利害的命份”,認爲二者遠非一回事。換言之,在塔穆斯看來,忒伍特雖然有能力發明技藝,卻對甚麼類型的人適合運用何種技藝缺乏認識。進一步說,忒伍特雖然發明了技藝,卻缺乏對自己所發明的技藝本身的反思,因此,忒伍特的智慧並不完整,這種智慧中缺乏對靈魂本性的真正知識。
相比之下,塔穆斯呈現的是另一種智慧——王者的治邦智慧。倘若對技藝是否有益的判斷終究意味著對“如何照管靈魂”這一問題的知識,塔穆斯與忒伍特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作爲異質靈魂共同體的政治城邦,乃是塔穆斯的王者智慧的根本出發點。相比之下,忒伍特以同質性的技藝爲基礎的智慧,事實上忽略乃至取消了城邦視野所看到的靈魂特殊性。因此,塔穆斯對靈魂的理解很可能比忒伍特的智慧更審慎,也更準確。問題在於,忒伍特發明的文字技藝的確能夠增強回憶、從而普遍性地彌補靈魂的局限嗎?塔穆斯對忒伍特爲文字寄予的美好願望提出了質疑。
畢竟,由於忽略了回憶,文字會給學過文字的人的靈魂帶來遺忘。何況,由於信賴書寫,他們從外仿製不屬己的東西,而非自己從內回憶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你發明的這藥不是爲了回憶,而是爲了記憶。你讓學習者得到的是關於智慧的意見,而非智慧的真實。畢竟,由於你[發明文字],學習的人脫離教誨,聽了許多東西,以爲自己認識許多東西,其實對許多東西毫無認識,結果很難相處,因爲他們成了顯得有智慧的人,而非真正智慧的人。(275a2-b3)

塔穆斯所做的如下區分將會有助於我們的思考:由於信賴書寫,“他們從外仿製不屬己的東西,而非自己從內回憶屬於自己的東西”(275a4-5)。甚麼是內在的“屬於自己的東西”?塔穆斯必定是指人的靈魂,對自身靈魂的認識才應該是回憶的真正內容。塔穆斯的這種區分提醒我們回憶蘇格拉底在“悔罪詩”中描述的靈魂旅程。由於屬人的靈魂此前無不曾經跟隨各自的主神遊歷於宇宙之中,並且上升到天外之境,在“真實事物的原野”看到永恆存在的真實之物(247a-248c),因此,靈魂即便墜落到地上、附著於身體之後,仍未徹底喪失“永恆運動”的真實本性(249b-c,250d-251a)。於是,少數最優異的靈魂出於對真實存在物的神聖愛欲,在不畏勞苦、熱忱回憶的卓絕努力中,能夠最終生出翅羽,追隨諸神再次開始宇宙中的上升運動。
與“悔罪詩”的靈魂教導一致,塔穆斯理解回憶時的前提是,人們通過回憶追求靈魂的自我知識。*葛利斯沃德(Charles Griswold Jr.),《柏拉圖〈斐德若〉中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 in Plato’s Phaedru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頁204-205;伯格,《柏拉圖的〈斐德若〉:爲哲學的書寫技藝一辯》,前揭,頁94。由於認識到關於雜多事物的意見與永恆真實之間的根本區分,回憶過程乃是以靈魂的真實知識——亦即甚麼是真正的正義、美與高尚的知識——爲目標的不斷上升的自我教化過程,推動這種上升的乃是靈魂中品質最高的愛欲。靈魂教養的關鍵在於從整全視野認識自身的內在渴求,這種渴求無法由同質性的智識能力取代。塔穆斯著重區分回憶與記憶的差別,首先強調的是,由於智識化的書寫技藝並非基於對靈魂真實本性的內在洞察,忒伍特用來醫治記憶的文字之“藥”與真正的教育其實並無本質關聯。
不僅如此,忒伍特將智識化的書寫技藝當作回憶本身這一理解,並未充分考慮靈魂間存在異質性的事實。問題在於,所有人都能通過智識性的書寫技藝實現靈魂的教化嗎?塔穆斯區分回憶與記憶,正是批評忒伍特對靈魂的同質化理解。而他的區分正是以靈魂異質性的前提爲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塔穆斯的教導與“悔罪詩”中的靈魂類型學仍然保持內在的一致——根據“悔罪詩”的描述,並非所有人的靈魂都有愛欲、意願和能力從在世生命的雜多感覺中回溯並上升到真實。這種區別首先源於靈魂墜落於人世之前在何種程度上看到了真實——總之,人的靈魂要由地上的東西回憶起天上的美好事物並非易事:
當初匆匆看看那邊的靈魂做不到,翅羽折了跌落在這邊的不幸靈魂也做不到(這些靈魂受某些同伴影響,轉而行不義,忘記了曾經看見的神聖之物),只有極少數的靈魂還葆有足夠的回憶。(250a)
因爲所見到的神聖事物的差別和回憶能力的差別,世人的靈魂也在“悔罪詩”中被劃分爲九種品級。靈魂自然天性的差異既涉及對真實的理解問題,也因爲理解真實的程度及能力的差別而呈現爲德性品質上的差別,說到底,這種既有知識含義、又有德性含義的真實乃是關於靈魂的自我知識。在這個意義上,塔穆斯王與蘇格拉底教誨的共同點在於,關於靈魂的智慧構成了確立靈魂秩序和城邦統治的真正依據。
隨著塔穆斯確認了“悔罪詩”所強調的靈魂秩序,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塔穆斯隨後的批評:以文字技藝爲基礎的智識啟蒙所帶來的後果是,學習者得到的是關於智慧的意見,而非智慧的真實。學習的人脫離教誨,聽了雜多的東西,實際上卻對雜多的東西毫無認識(275a7-b2)。忒伍特的啟蒙設計的根本局限在於,由於以智性化的技藝爲靈魂教育的基礎,因而它以限制靈魂的道德視野爲代價。忒伍特雖然用文字技藝爲每個人許諾了補足理性能力的可能性,但由於這種技藝並不以靈魂的自我知識爲基礎,因而最終只會確認每個人在雜多事物中看到的種種似是而非的意見。“學習的人對雜多的東西毫無認識”的說法表明,哪怕在學習文字之後,眾人在“正義”和“好”這類道德事物上依然莫衷一是,靈魂共同體的異質性並未、也不可能通過普遍化的技藝獲得改變。
同時,塔穆斯既指出了文字啟蒙的教育後果,其實也指出了這種啟蒙在政治上的引申後果。忒伍特式的智術啟蒙提出了靈魂獲得普遍提升這一高遠目標,倘若人的理性可以通過文字教育得到普遍完善,那麼由此引申的政治含義在於,所有的靈魂都可以獲得自我約束的自由德性,智術啟蒙因而試圖爲民主政體提出基於德性的法理論證。*比較葛利斯沃德對忒伍特與塔穆斯各自代表的民主原則與君主制原則的分析,《柏拉圖〈斐德若〉中的自我知識》,前揭,頁203。但是,塔穆斯的批評讓我們看到忒伍特的啟蒙論證並不成立。文字啟蒙的初衷是普遍改進人的天性,結果卻是進一步敗壞常人的天性,啟蒙教育肯定的是人們原本莫衷一是的混雜意見,結果只會讓這些“顯得有智慧的人”變得“很難相處”。總之,智術啟蒙雖然聲稱能用文字之“藥”醫治民主政治,實際上只是通過肯定眾人的混雜意見來替代基於靈魂知識的治邦智慧。
總結蘇格拉底講述的“忒伍特-塔穆斯神話”,我們可以看到,塔穆斯與忒伍特雖然都有智慧,但忒伍特的技藝智慧卻與塔穆斯的王者智慧有根本的不同。具體來說,塔穆斯對文字技藝的批評,既是從王政傳統出發對民主政治的靈魂秩序提出的否定,也是對普遍的智術啟蒙的否定。*葛利斯沃德,《柏拉圖〈斐德若〉中的自我知識》,前揭,頁203-204。以塔穆斯對文字的批評爲前提,我們還看到,由於民主的理論論證建立在智識啟蒙的教育基礎之上,民主政治不可能具有經得住考驗的德性根基。
三、蘇格拉底對成文書寫的批評
蘇格拉底的神話剛剛講完,斐德若便立即感到驚奇——不是驚奇於神話的內容,而是驚奇於蘇格拉底竟能如此輕松地編故事。正像對話開篇時斐德若曾經對波瑞阿斯神話是否真實提出懷疑一樣,如今的斐德若考慮的仍然是蘇格拉底講的神話是否真實,而不是這個神話實際上講了些甚麼——即便這個神話講的正是斐德若最爲關心的書寫問題本身,這個問題仍然沒能成爲斐德若注意力的核心。斐德若的懷疑態度確認的是自己已知的東西,亦即從智術師的自然哲學中學到的成見,卻沒有敏感地在神話中發現與自身靈魂相關的未知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斐德若雖然已經在蘇格拉底的引導下領悟了關於言辭與書寫的許多真實,但仍然在不經意間透露了智術啟蒙影響下的閱讀習慣和書寫模式。*Ferrari,《聽蟬》(Listening to the Cicad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頁217-218。
斐德若曾在對話開篇部分對神話提出質疑,蘇格拉底援引了“認識自己”的德爾斐神諭(229e6),由此暗示斐德若,最重要的不是懷疑神話,而是在神話中看到自己的靈魂本相。由於已經習慣於智術師的教導,即便在先後聽到蘇格拉底講述“靈魂馬車”神話、“蟬與繆斯”的神話和如今的埃及神話後,斐德若仍然很難真正聽懂蘇格拉底的提醒。如今,面對仍然對神話感到半信半疑的斐德若,蘇格拉底只好再次以調侃的語氣提醒他。蘇格拉底提到了多多那宙斯神廟祭司們的說法——據說最初的預言出自橡樹說的話,但當時的人不像今人這般“聰明”,他們聽橡樹或岩石說話就感到滿足,只要所說的是真實(275b-c)。相比之下,“聰明的”斐德若遠不如這些單純的古人更善於理解言辭,因爲這些古人首先盯住的是關於“真實”的教誨。
並非偶然的是,在斐德若與古代人之間的對比背後,存在著兩種類型的書寫和教育的差別。著眼於外在來源考察神話的斐德若代表智術師的啟蒙教育所教出的聽眾/讀者,相反,那些單純卻直面真實的古代人則受神聖律法、宗教和詩歌的教育。通過對比斐德若與單純的古代人,我們可以看到,作爲讀者,更智術化的斐德若反倒距離靈魂的真實更遠。但是,沒有能力看到真實的不僅有斐德若,還有智術化的書寫方式本身。通過指出古今兩種聽者/讀者的差別,蘇格拉底也暗示了古今兩種教育/書寫方式之間的區分。
以調侃的方式批評斐德若後,蘇格拉底開始回顧自己講述忒伍特神話的用意——“阿姆蒙的預言”(亦即塔穆斯對文字的批評)告訴人們的是,技藝化的文字寫作所涉及的只是“已經知道的東西”(275c7)。蘇格拉底因此總結說,無論是以技藝化的方式寫作的人,還是相應的讀者,倘若相信“成文的東西”中有清楚穩靠的東西,頭腦都太過簡單了(275c5-8)。蘇格拉底將批評矛頭同時指向作者和讀者,相當於批評了技藝化的啟蒙教育本身——從事寫作的啟蒙教師沒有能力傳授真實,而受到啟蒙的讀者也沒有能力辨別怎樣的文字才能傳達真實。
我們由此能夠理解蘇格拉底隨後對成文書寫所做的著名批評。首先,“書寫的模樣有些可怕”,猶如繪畫的子女一樣,“立在那兒仿佛活人,但倘若你問甚麼,他們卻威嚴地緘口不言,而書寫的言辭做的是同樣的事情”(275d4-6)。第二,倘若讀者想要就書寫的內容提問,書寫的文字就總是只說同樣的話,只能指示同一樣東西(275d7-8)。第三,言辭一旦寫下來,就以相同方式到處傳播,既傳到懂得的人那裹,也傳到根本不適合以這種方式懂的人那裹。寫下的言辭不懂得該對誰說,該對誰沉默(275e1-3)。第四,面對責難或不義的辱駡,寫下的言辭沒法兒保護自己(275e4-6)。
從上述批評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從幾個不同方面質疑成文言辭。蘇格拉底看起來在批評所有類型的寫作,*學界已有的研究大多把蘇格拉底對啟蒙式寫作的批評理解爲對一切寫作本身的批評,因而通過口說與書寫的對立來解釋蘇格拉底的含義。這種理解方式忽略了蘇格拉底針對智術啟蒙的特殊意圖。畢竟,蘇格拉底在《斐德若》中多次強調書寫的重要性,因而他的批評並非針對所有書寫形式本身。費拉里、德里達、伯格等學者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這個問題。但仔細辨別後可以發現,這些批評都合乎塔穆斯對忒伍特技藝的懷疑——換言之,蘇格拉底的批評都具體指向智性啟蒙意義上的言辭技藝。
具體來看,蘇格拉底的第一條批評揭示出智術啟蒙式的寫作本身並未認識真實,也無法在讀者的靈魂中引起對真實事物的回憶,因而只能對靈魂的真實“緘口不言”。值得注意的是,繪畫子女的比喻暗中與《斐德若》此前所提到的“青銅少女”銘文形成呼應(264d)——正如冰冷的青銅雕像束縛著少女的生命那樣,書寫的言辭也禁錮了靈魂通過回憶上升的道路。*伯格,《柏拉圖的〈斐德若〉:爲哲學的書寫技藝一辯》,前揭,頁97-98。在這個意義上,呂西阿斯的講辭正是智術啟蒙式書寫的典型例子。蘇格拉底的第二條批評比前一條有所推進:成文的文字不僅未能傳達靈魂的真實,而且沒有就不同靈魂類型實施有針對性的分別教導。這正是成文言辭永遠只說同樣的話、指示同樣的東西的原因所在。只有對讀者有所區分的文字,才有可能在不同讀者眼中體現爲不同的教導。
與前兩條批評不同,蘇格拉底的第三點批評不再僅僅著眼於作者,而且有意強調讀者之間存在的差異——並非所有的讀者都適合閱讀智術啟蒙式的成文作品。對於“不適合以這樣的方式懂的人”,成文的言辭不僅對其沒有益處,反而會對其天性造成傷害——產生這種傷害的根本原因在於,認爲“靈魂普遍可教”的看法恰恰會敗壞靈魂。因爲,倘若沒有認識真實的能力,接受者只會因爲智術式寫作而加強已有的意見,把智識化後的意見當作“真實”,並通過這種看似如此的“真實”去質疑城邦傳統中原有的教育方式。蘇格拉底特意強調有些讀者不適合“以這樣的方式”理解,無異於說,智術式寫作並不懂得對不同讀者應該採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如果以整齊劃一的自然理性教育所有人,結果只能像塔穆斯所說的那樣,使人們“顯得有智慧,而非真正有智慧”,最終使受到教育的人變得“很難相處”。
蘇格拉底的最後一條評論不再單純關注寫作內容的真實問題,而是轉向寫作者的外在處境問題。因此,這條評論既是批評,又像是在對啟蒙者提出勸告:由於從事寫作之人難免會涉及關乎道德善惡的問題,而這類讓人們感到莫衷一是的重大問題又尤其容易導致紛爭,因此,寫作尤其需要顧及審慎和正義。
事實上,蘇格拉底對成文書寫的批評既針對啟蒙式的教育方式本身,也有針對斐德若發言的具體用意。正如蘇格拉底已經通過檢驗何爲好的言辭逐漸淨化了斐德若對修辭術的愛欲,如今他也試圖淨化斐德若對成文文章的愛欲。回顧全篇對話可以看到,正是記錄著呂西阿斯講辭的書卷把斐德若引向了城邦之外。不僅如此,斐德若也對修辭家們寫下的各種技藝指南頗爲熟悉(266d-267d,尤其見266d5)。說到底,熱愛言辭的斐德若早已是啟蒙式書寫教出來的典型讀者。不過,通過此前對修辭術與辯證術的比較,斐德若應該開始明白,無論言辭還是書寫,都必須以教導靈魂的真實爲基礎。蘇格拉底向斐德若指出智術式寫作的缺陷,已經爲探討關於書寫的最後問題——甚麼是好的寫作鋪設了道路,這也正是全篇對話的核心問題。
參考文獻[References]
Benardete,Seth.RhetoricofMoralityandPhilosophy:Plato’sGorgiasandPhaedru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Burger,Ronna.Plato’sPhaedrus:aDefenseofaPhilosophicArtofWriting.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0.
de Vries,G.J.ACommentaryonthePhaedrusofPlato.Amsterdam:Adolf M.Hakkert Publisher,1969.
Ferrari,G.R.F.ListeningtotheCicadas:AStudyofPlato’sPhaedr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Griswold Jr.,Charles.Self-KnowledgeinPlato’sPhaedru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希羅多德,《歷史:希臘波斯戰爭史》,王以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Herodotus.History.Trans.Wang Yizhu.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59.]
伊尼斯,《帝國與傳播》,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Innis,Harold.EmpireandCommunication.Trans.He Daokua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3.]
劉小楓編,《古典詩文繹讀·古代編》(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Liu,Xiaofeng,ed.Commentariiversuumetprosarumantiquarum.Vol.1.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8.]
劉小楓,《斐德若》課程講義,未刊稿,2015。[Liu,Xiaofeng.LecturesonPlato’sPhaedrus.Unpublished transcripts.]
羅念生,《羅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Luo,Niansheng.CollectedWorksofLuoNiansheng.Vol.2.Shangha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2007.]
柏拉圖,《斐德若》,載劉小楓編譯《柏拉圖四書》,北京:三聯書店,2015。[Plato.Phaedrus.Trans.and ed.Liu Xiaofeng.FourTextsofPlato.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
——,《蒂邁歐篇》,謝文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Timaeus.Trans.Xie Wenyu.Shanghai: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2005.]
Rousseau,Jean-Jacque.TheDiscoursesandOtherEarlyPoliticalWritings.Ed. and trans.Victor Gourevitch.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3.
盧梭,《論科學與文藝》,劉小楓譯文,2012未刊稿。[Rousseau,Jean-Jacques.DiscourseontheScienceandArts.Trans.Liu Xiaofeng.Unpublished manuscript.]
Vasunia,Phiroze.TheGiftoftheNile:HellenizingEgyptfromAeschylustoAlexan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Yunis,Harvey.Plato’sPhaedrus.Cambridg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uth mythos” in Plato’sPhaedrus
The themes of Logos and Writing stood in Plato’sPhaedrusas the focus of discussion.As Plato demonstrated in thePhaedrus,the enthusiasm to written-speeches not only indicated the orientations of personal eros for individual souls of Phaedrus and Socrates,it further took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bearings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for the regime of the city.Rooted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Sophist Enlightenment,Phaedrus’ eros for written-speeches w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culture in the 5thcentury B.C. In the tale of“Theuth and Thamus,”Socrates posed deep challenges by his narrative of myth to the idea of writing guided by the Sophistic Enlightenment.Theuth and Thamus represented two ways of understanding of writing and political regime-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tradition of kingship.By his critique of Theuth,Thamus demonstrated that although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through writing was initiated by the aspiration for the universal improvement of human nature,it would end up with the pervasive deterioration of humanity,due to its attempt to replace the memory of the soul by an art of reminding.On the basis of the“Theuth-Thamus”mythos,Socrates proposed a profound critique to the idea of writing guided by sophistry.Socrates’ critique to written-speeches was aimed at sophists’ ideas of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According to Socrates’ examination,sophists’ enlightenment writing was no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ruth,thus had to remain tacit about the truth of the soul.The sophists’ written works were not able to adjust to the diversity of readers,nor could they convey different messages to varied audiences.Moreover,since not all readers were suitable to have access to enlightenment writings,the written works of sophistic enlightenment might render detriment to certain readers.After all,the notion of“all souls are universally teachable”stemmed from an impaired and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ouls.The attempt to replace the pre-existent traditions of education with the idea of universal enlightenment would have the repercussion of corrupting the souls on a vast scale.On the basis of the“Theuth-Thamus”mythos,Socrates’ critique of the written-speeches prepar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scussion of a genuine art of writing,namely,the writing in the soul.
Theuth;Thamus;art of writing;Enlightenment;politeia
關鍵詞:忒伍特 塔穆斯 書寫技藝 啟蒙 政制
——《理想国》卷八刍议
——论色诺芬的《雅典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