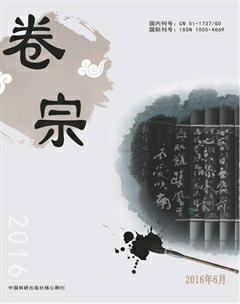论侦查中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
魏延明 陈宇涛
摘 要:侦查中的疲劳讯问的认定应当建立在对其性质进行分析,其归属于刑讯逼供行为,同时也是非法取证方法,与侦查策略相区别。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其次还应参考域外国家的认定标准,对讯问时长标准与任意自白性标准进行借鉴。在此基础上,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应当基于我国国情,采用较为刚性的讯问时长标准,对连续讯问时间以及讯问间隔进行界定,同时也要合理看待任意自白性标准,分析其在司法实践适用上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疲劳讯问;刑讯逼供;讯问时长标准;任意自白性标准
Abstract:The determination of fatigue in the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investigation.It belongs to the inquisition by torture behavior, and is also the illegal evidence collection method, comparing with investigation tactics.Standard fatigue trial should also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other countries ,for interrogation time standard and arbitrary confessional standards.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standard to judge the fatigue tria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using explicit time interrogation standard, carries on the limits to the continuous interrogation time and the interval of the interrogation.It also need to rationally treat confession standards,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existe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fatigue interrogation,inquisition by torture,interrogation time standard,arbitrary confessional standard.
2010年5月,两高三部聯合发布《两个证据规定》,首次系统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通过,首次以法律形式固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遏制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变相刑讯逼供日益突出,在实践中调查发现,审前被羁押人约有60%反映受到剥夺睡眠与饮食等形式的疲劳讯问;从近年来的冤假错案来看,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以及赵作海案等,都存在有疲劳讯问的重要因素。那么,疲劳讯问作为具有危害性的非法讯问手段,利用该手段所获取的相关证据应予以排除,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文件在认定标准上的缺失,疲劳讯问长期以来都难以受到有力约束。
1 疲劳讯问的性质
疲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疲劳讯问开始受到广泛重视,国内学界对疲劳讯问的诸多讨论方兴未艾。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是实践中的主要难题,这不仅涉及到法律的适用,而且也受其自身性质的影响。疲劳讯问的性质长期以来是较为模糊的,需要对其进行较为明确的界定。在学理探讨中,疲劳讯问与刑讯逼供具有本质上的相同,应当归属于刑讯逼供,其同样也是非法取证行为。
(一)疲劳讯问属于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非法方法,同时其概念由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之规定,“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所获取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这是国家法律层面对刑讯逼供的明确规定,但是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含义的理解上留下了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将三类行为归属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即“肉刑”、“变相肉刑”、“其他非法方法”。那么,在这三类行为中,刑讯逼供具体包含的行为又应当如何界定。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刑讯逼供”是指肉刑与变相肉刑,而“等非法方法”是指其他与刑讯逼供程度相当的方法。综上来看,“刑讯逼供”与“等非法方法”是并列关系,但在具体含义上存在不同,前者指的是直接肉刑与变相肉刑的非法方法,而后者则强调其他与“刑讯逼供”在违法程度与强迫程度上相当的非法方法。
然而,疲劳讯问的正式提出,在弥补了法律空白的同时也带来了其概念归属以及法律认定方面的问题。《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第8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讯问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意见》首次规定了“疲劳讯问”非法方法,并且将其与“刑讯逼供”并列,这在一方面体现了疲劳讯问在违法程度与强迫程度上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却在疲劳讯问与刑讯逼供的关系方面留下疑问。
有学者对此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疲劳讯问属于“等非法方法”的范畴,即疲劳讯问与刑讯逼供为并列关系。有学者对《意见》第8条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从学理以及实践来看,疲劳讯问应当属于“刑讯逼供”,而该条文如此表述是将疲劳讯问进行突出强调。笔者较为赞同后者,首先从学理角度来看,刑讯逼供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广义上的刑讯逼供包括直接肉刑与间接肉刑,既包括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直接性、暴力性的手段来造成痛苦,如殴打、电击、悬吊等方式,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间接性、非暴力性的手段,如限制休息、饮食以及长时间的冻、饿、晒、烤等方式;而狭义上的刑讯逼供则是只是专指对犯罪嫌疑人直接的肉体性的手段来造成痛苦。疲劳讯问具有限制与剥夺休息时间的特点,对犯罪嫌疑人造成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间接性与非暴力性的变相肉刑,应当属于刑讯逼供。其次,《意见》第8条的表述,将疲劳讯问与“刑讯逼供”并列,应当是对其程度的限定。只有当疲劳讯问在违法程度与强迫程度上与刑讯逼供达到一致时,才应当认定为非法方法。
(二)疲劳讯问属于非法取证方法
疲劳讯问是区别于侦查策略的非法方法。具体而言,疲劳讯问主要表现形式为限制与剥夺休息时间,在侦查实践中,部分侦查人员误将其当作侦查策略来使用,混淆了非法方法与侦查策略。首先,疲劳讯问的本质在于对法律规定的违反。我国刑诉法针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采取了专门规定,明文规范与约束职权机关的公权行为。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疲勞讯问是属于刑讯逼供行为,其违反了“严禁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法律规定,因而是一种非法方法。其次,在新刑诉法视角下,疲劳讯问还表现在对公民人权的侵犯上。“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一个重要的指标,新刑诉法在理性惩罚犯罪的前提下,同样将保障人权作为重要追求目标之一。而疲劳讯问在实践中多表现为连续性不间断讯问、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休息与饮食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的肉体与精神造成了极大痛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疲劳讯问所获取的口供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采纳的重要规则,已然成为了法治化国家证据制度的标志。非法证据广义上分为三大类,分别为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毒树之果”(非法言词、实物证据的衍生证据)。我国法律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待非法言词证据采取绝对排除态度,对于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实体性违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疲劳讯问是一种非法取证方法,其与刑讯逼供存在共性,都是对犯罪嫌疑人造成痛苦以获取口供,这不仅是违反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而且会破坏证据的实体性效力。因此,依据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利用疲劳讯问所获取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2 疲劳讯问的域外认定标准
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在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尚未有统一定论,在此种情形下,国内相关研究应当借鉴域外疲劳讯问的相关标准。域外立法受不同司法制度以及法律文化的影响,对于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各不相同,但在差异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却体现了几种较为普遍的认定标准,分别为讯问时长标准与任意自白标准。域外国家关于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我国应当予以借鉴。
(一)英国的疲劳讯问标准
英国的警察制度影响后世深远,其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是建立对警察权力重新配置与规范的基础上的一部成文法。该文首先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予以定义,第76条规定:该供述不是出于被迫或其他容易产生不可信供述的环境。其次对警察讯问权力加上了许多程序性限制。该法实施细则C规定了除恐怖主义犯罪外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状态状态下的讯问时长限制。具体如下:每24小时讯问时间内应享有连续八小时的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尽量安排在夜间,在此期间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与干扰,但是法定情形除外。与此同时,英国《警察拘留、对待及询问当事人执行守则》来对讯问环境以及讯问间休息与饮食加以具体规定:讯问应在暖和的、有充足的光线和通风的讯问室进行,不应让被讯问的人处于站立状态,犯罪嫌疑人可以坐着接受讯问。
(二)德国的疲劳讯问标准
德国以严格的成文法形式而享誉世界,其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德国法律对于疲劳讯问的理解与我国学界的主要关注点有所不同,疲劳讯问被认为一种存在于人身的客观独立的状态,不依附于长时间、不间断的讯问,同时在认定时也不以侦查人员是否得知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为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律同样没有对疲劳讯问的具体时间界限加以规定,只是在判例将疲劳讯问的认定加以体现。在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决中第1集第390页记录的案例中,法官所判决的依据是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是否早已经处于疲劳状态,以及分析该疲劳状态对其意志判断力的影响是否会使他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
(三)美国的疲劳讯问标准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对于疲劳讯问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是,究其历史,曾经一度猖獗的以肉体疼痛与心理折磨而出名的三级审讯则是与疲劳讯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之处。1930年,在托尼·科莱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状态下的26个小时内被不间断讯问、殴打、剥夺进食与饮水、禁止睡眠,最后作出有罪供述,并且法院最终采纳这一证据。1944年发生的阿什克拉夫诉田纳西案则开始对以疲劳为特征的讯问方式予以否定,美国联邦认为警察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36个小时,并限制必要的饮食与休息时间后,犯罪嫌疑人所所作出的供述应属于违背了任意自白原则的供述,不予以采纳。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以疲劳为特征的讯问方式并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主要是依据对犯罪嫌疑人任意自白的违反,如在1961年的罗杰斯诉里奇蒙德案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英国的疲劳讯问认定标准所采用的是讯问时长标准,即在24小时内要保证连续8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德国的疲劳讯问认定标准更倾向于任意自白标准,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了严禁“疲劳战术”,但是对于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却并不以具体的时间界限为标准,而是以疲劳这种客观人身状态有无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本身的自由意志为标准,是一种较为灵活性的认定标准;最后,美国的疲劳讯问认定标准则是采用了任意自白标准。对于疲劳讯问的认定主要从判例中体现,而判例中也未能规定严格的时间界限,主要是以任意自白原则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基础,对实践中疲劳讯问的认定主要从年龄、健康状态、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来考虑,从“整体环境”角度来判断是否侵害了任意自白原则。
3 我国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
我国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应当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以现有法律体系为框架,充分借鉴域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对侦查中的疲劳讯问行为进行有力规制。而我国对于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羁押状态与未羁押状态,因此在考虑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时应当考虑这两种情形。同时,鉴于国内司法实践,我国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还是应当确立讯问时长标准。
(一)讯问时长标准
国内学者对于疲劳讯问的时间界限存在有一定争议。一种观点赞同区分羁押与未羁押状态,提出羁押期间一次讯问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应超过24小时,期间至少休息6小时,而且两次讯问之间的时间间隔也不得少于24小时。而非羁押状态参照我国刑诉法关于“传唤与拘传”的规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未对羁押状态进行区分,提出如果连续讯问超过12小时或者24小时之内连续休息时间不足6小时的,则属于疲劳讯问,所获口供应当排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疲劳讯问只发生于羁押状态,因此只需要对羁押状态下的讯问时长标准予以明确。
笔者赞同区分羁押状态与非羁押状态的讯问时长标准,这种区分是由我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实践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通常会采用传唤、拘传等强制措施来进行侦查讯问,获取可靠的侦查证据与线索后即变更为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也从未羁押状态到羁押状态进行转变。羁押状态与未羁押状态就具有各自的存续时空,并且在对人身自由的强制程度上也存在强弱之分。从法律角度来看,未羁押状态的讯问时长标准有法律明文规定,而羁押状态下则无明确规定。
首先在未羁押状态下,犯罪嫌疑人被传唤、拘传来接受讯问,根据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传唤、拘传的时间一般情况为12小时,特殊情况为24小时。在对讯问持续时间进行规定的同时,刑诉法同样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必要的饮食与休息时间”,但是该项时间并未有详细的规定,实践中的做法是依据逻辑规则与经验法则,认为正常人的休息时间为6-8小时,并且应当保证有三餐的正常进食。但是,在侦查办案活动中,不同侦查机关在具体实施上存在差异,有学者调查发现,某地侦查机关在办案时只给犯罪嫌疑人吃一顿饭,这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与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休息时间。以上是单次传唤、拘传中容易产生的问题,而实际上多次传唤、拘传同样存在不合法的做法。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通常灵活变通两次传唤、拘传之间的间隔,利用时间差来实现连续讯问,而这种做法是违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八十条中“两次拘传间隔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二小时”的规定,如果存在这种连续讯问的行为,也应当认定为疲劳讯问。
其次在羁押状态下,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逮捕后人身自由被剥夺,完全处于侦控方的控制之下,其合法权益的侵犯更容易发生。具体而言,羁押状态存在两个阶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宣布拘留、逮捕决定后的24小时,该时间段中其仍旧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下;二是犯罪嫌疑人被送看守所后的数月时间,该时间段在看守所的控制下。那么,实践中疲劳讯问较为容易发生的时间段主要是什么呢?疲劳讯问多发生在传唤、拘传变更为拘留、逮捕之间,以及拘留、逮捕宣布后到送监后的第一次讯问之间,侦查机关通常将前者与后者的持续时间连接起来,从而实现连续讯问与限制剥夺饮食和休息时间。因此,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要考虑到强制措施变更时,以及拘留、逮捕后送监时的非法讯问行为,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拘传的时间间隔,对于这种变相的连续讯问行为应当明确十二小时的间隔时间。
在对羁押状态下间隔时间进行探讨的同时,笔者也对讯问持续时间提出一定看法。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连续讯问超过十二小时以及24小时内休息时间少于6小时的,应当认定为疲劳讯问。首先,以12小时和24小时作为疲劳讯问的时间节点是合理合法的,我国刑诉法长期将12小时和24小时作为讯问时长的重要时点,同时这也符合正常人的健康的生理标准。其次,必要的休息时间界定为6小时有待商榷,有学者提出6小时是现行刑诉法草案中限制传唤、拘传的时限方案之一,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并不合理,修订方案不能直接作为参考依据,而是应当参照《公安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的规定,即在押人员要保证有不少于八小时的睡眠时间,不能以提讯为由影响正常休息以及就餐。
(二)任意自白性标准探讨
学界主流观点较为赞同上文的讯问时长标准,同样也有少数观点提出了任意性自白标准来作为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有学者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应当是施行全面的自白任意规则”。笔者认为这种少数观点值得商榷,无论是疲劳讯问,抑或是刑讯逼供,都采用非法手段使犯罪嫌疑人感到痛苦,从而作出有违其意愿的供述。那么,对疲劳讯问的任意性自白标准的适用就要建立在痛苦與非自愿性供述的关系上,如果痛苦足以造成其违背个人意愿,那么才可以认定为疲劳讯问。但是,犯罪嫌疑人的痛苦通常是难以量化的,在司法实务中通常只有讯问时长可以作为参考因素,而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以及讯问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因此,在任意性自白标准的适用上,我国的法治环境尚不能完全引入该标准,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推敲与完善的地方。
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可以引入医学鉴定,对痛苦进行判断,从而辅助疲劳讯问的认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有待商榷,众所周知,疲劳讯问所造成的痛苦感受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疲劳状态是具有即时性的,也就是发生于侦查讯问中的某个阶段,而犯罪嫌疑人提出疲劳讯问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通常是在法庭审判阶段,此时其人身状态与受到疲劳讯问的状态必然存在差异,若以此为鉴定依据则是不合理的。而至于疲劳讯问发生时,犯罪嫌疑人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由其本人提出相应的医学鉴定申请则是较为困难的。这项标准的建立是依赖于其他保障性权利的实现的,如建立律师在场权、完善全程录音录像等,因此疲劳讯问的医学鉴定的引入并非是合理有效的。
任意自白性标准是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个体特征、讯问环境、讯问时长等因素,对犯罪嫌疑是否出于痛苦而作非自愿供述进行合理判断。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任意自白性标准本身的适用缺乏可行性,目前只能以讯问时长作为参考因素,而由于其他犯罪嫌疑人权利与保障制度的局限,不能做到对综合因素的考虑,故而不能作出合理合法的认定。所以,当前我国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还是应采用讯问时长标准,而非任意自白性标准。
注释
[1]国内有学者对审前被羁押人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发现被羁押人在讯问中受到“挨饿、不让睡觉、长时间站立、轮番审讯、故意冷冻”等变相刑讯行为的比例为60.1%。参见林莉红、邓刚宏.审前羁押期间被羁押人权利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8).
[2]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3]在1961年的罗杰斯诉里奇蒙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判定,若讯问期间讯问人有威胁被讯问人的行为,则即便是6个小时连续讯问后做出的供述也不具有可采性。参见郑曦.疲劳讯问的法律规制[EB/OL].[2013-11-20].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3-11/20/content_73041.htm?div=-1.
[4]参见陈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若干问题研究——以实证调查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4,35(9).
[5]参见万毅."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J].证据科学,2011,19(6).
[6]参见陈苏豪.论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17(2).
[7]陈苏豪提出6小时是现行刑诉法的修改草案中提出的。参见陈苏豪.论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17(2).
[8]参见杨宇冠,郭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J].证据法学,2014(1).
[9]参见方淳.疲劳讯问的法律界定及其应对措施[J].法制与社会,2015(10).
参考文献
[1]林莉红、邓刚宏.审前羁押期间被羁押人权利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8).
[2]郑曦.疲劳讯问的法律规制[EB/OL].[2013-11-20].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3-11/20/content_73041.htm?div=-1.
[3]陳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若干问题研究——以实证调查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4,35(9).
[4]万毅."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J].证据科学,2011,19(6).
[5]陈苏豪.论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17(2).
[6]刘志伟,魏昌东,吴江.刑事诉讼法一本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魏延明(1995-),男,山东潍坊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本科生。
陈宇涛(1995-),男,浙江金华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