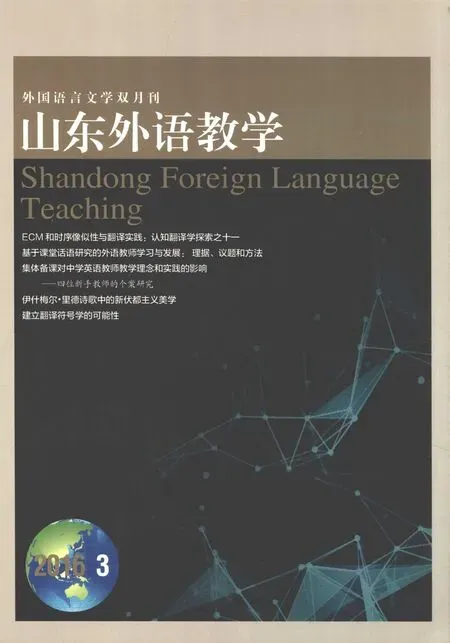“追累”句式的歧义新解
周长银,周统权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2.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追累”句式的歧义新解
周长银1,周统权2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2.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9)
[摘要]“追累”句式有宾语指向、主语指向和施受颠倒三种解读,是现代汉语多歧义句式的代表,也是近年来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思路和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事件结构分析的新方法,对“追累”句式的三种语义分别解读为状态维度上的有界致使运动事件、时间维度上的有界自发运动事件和时间维度上的有界无意致使运动事件。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反映了汉语V-V复合词生成的语序特点及相关事件的深层语义关系,还能得到汉语体标记嵌入和相关句式转换关系的支持。
[关键词]“追累”句式; 事件结构; 歧义分析;动词复指
1.0 引言
“追累”句式是近年来汉语研究中广泛讨论的一种结果句式①。它是汉语多歧义结果句式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汉语结果句式语义指向灵活和施受可以颠倒②等独特的句法特性。以“陶陶追累了友友了”这句话为例。按照“谁追谁”和“谁累”的逻辑,这句话有(1a-d)四种解读,但实际成立的却只有(1a-c),(1d)被排除掉了:
(1)陶陶追累了友友了。
a. 陶陶追友友,友友累了。(宾语指向解读,成立)
b. 陶陶追友友,陶陶自己累了。(主语指向解读,成立)
c. 友友追陶陶,友友累了。(施受颠倒解读,成立)
d. *友友追陶陶,陶陶累了。(被排除)
由于具有多种解读,“追累”句式近年来成了汉语生成句法研究③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拟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然后本着运动事件与变化事件平行的理念,从维度、界性和影响性等概念出发对该句式的几种解读进行新的阐释。
2.0 “追累”句式的研究概观
2.1 词汇生成论
词汇生成论的代表是Li (1990,1993,1995)。他把“追累”看成是一个在词汇层面生成的V-V复合词,“追累”的核心是其主动词“追”,“追”的题元层级在显著性上应该与整个复合词“追累”保持一致(核心特征渗透假设),“追”和“累”的题元角色可以发生重合并重新指派给整个复合词“追累”的一个论元。解读(1a)和(1b)都符合核心特征渗透假设,因此都能成立。而(1c)和(1d)则都违反了这一假设。但是,Li (1995)认为,由于“陶陶”在(1c)中是致使原因而在(1d)中却不是,因此,被现有假设所排除的解读(1c)能被Grimshaw (1990)的致使层级所拯救,因为当题元层级与致使层级发生冲突时,应该保证后者。这样,(1c)的施受颠倒现象就得到了解释。Li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但Gu (1992)也指出,Li的方法有过于概化之嫌,因为汉语中并非所有与“追累”类似的复合词都有它这样的歧义解读。
2.2 句法生成论
句法生成论的观点与词汇生成论相反,这种观点认为,类似“追累”这样的V-V复合词并非是在词汇层面生成的,而是由移位和并入等句法操作生成的,其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主要有:
2.2.1 并入法
并入法包括Cheng (1997)和王立弟(2003)的词汇并入分析法和Zhang(2001)、赵杨(2006)的句法并入分析法。他们或将“累”表征为“追”的补足语,再让“累”向上移位并附接在“追”的右边,或将“累”直接并入到动词“追”的右边,以生成复合词“追累”。这种句法分析采用的通常是右附接的操作。
对于“追累”句式的不同解读,王立弟(2003)认为,(1a)是由下层非宾格复合词“追累”向上层致使性空核心V移位来生成的,“友友”被标记为受格,是直接内论元,(1b)代表一个肇始事件,“友友”被标记为旁格,是间接内论元,而(1c)则是“友友追累了”在致使化过程中添加外论元“陶陶”后生成的。上述推导的缺陷是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谁追谁”的语义关系。另外,王立弟(2003)将(1b)中的“友友”看作一个起附加语作用的旁格论元,这会面临现代汉语附加语在左的类型学特征的挑战。而Cheng (1997)则认为,(1)只有(1a)和(1c)两种解读,解读(1b)是不可能的。她认为,在“追累”的词汇关系结构[VP[V追] [VPNP [V’V [AP[A累]]]]]中,处于下层[Spec VP]位置的NP有“追赶者”和“被追赶者”两种潜在的事件角色。这种不确定性是造成(1a)和(1c)两种歧义解读的根本原因。Zhang (2001)和赵杨(2006)只讨论了“追累”句式的(1a)和(1b)两种解读。对于这两种歧义解读,赵杨(2006)运用了控制手段而Zhang (2001)则运用了Chomsky (1995)最短距离原则中的等距性来解释。他们在解释(1b)时都把“友友”当成了“追累”的宾语。
2.2.2 功能核查与扩展法
Zou (1994)、王玲玲、何元建(2002)以及熊仲儒、刘丽萍(2006)对“追累”句式都是采用最简方案中功能语类对实词语类进行特征核查或功能扩展的思路来进行分析的。通过采用控制手段,Zou (1994)④和王玲玲、何元建(2002)⑤的分析都清晰地反映了“追累”句式中“谁追谁”和“谁累”的深层语义关系。但在Zou (1994)的分析中,为了保证“追累”生成后的语序,实词“追”和“累”在向功能语类I嫁接时出现了不同解读中顺序不一致的现象。王玲玲、何元建(2002)的分析只允许“追”向上层致使性的轻动词v嫁接,克服了Zou (1994)的问题,但其在“追累”句式的三种解读中都要让主动词“追”去承担致使功能的做法值得商榷。另外,同Zhang (2001)和赵杨(2006)一样,王玲玲、何元建(2002)对(1b)的分析中也是将“友友”处理成了“追累”的宾语,这种处理不仅没有表达出该论元所应具有的事件性⑥,也无法解释沈家煊(2004: 11)所指出的(1b)不能转换为“把”字句的特性。为了保证“追累”生成后的语序,熊仲儒、刘丽萍(2006)在底层结构中将“追累”表征成了核心在后的结构并对其不同解读进行了分析:
(2)a. [DoP [陶陶][[Do 追累了] [CausP [陶陶 ][Caus’ [[Caus追累了] [BecP [友友 ] [Bec’ [Bec 追累] [VP [ 累][V 追-累]]]]]]]]
b. [DoP [陶陶][[Do 追累了] [CausP [友友 ][Caus’ [Caus追累了] [BecP [陶陶 ] [Bec’ [Bec 追累] [VP [ 累][V 追-累]]]]]]]]
c. [CausP [陶陶][Caus’ [Caus追累了][BecP [友友] [Bec’ [Bec 追累] [VP [ 累][V 追-累]]]]]]]
根据熊仲儒(2004a),句法扩展中词汇核心总是在后而功能核心总是在前。这样,辅助谓词“累”先向主动词“追”作右向嫁接,生成的“追-累”结构再被BecP等功能语类扩展,最后就能生成按照自然语序排列的“追累”句式。单从语序的角度讲,(2)中的设计对于汉语结果句式的生成来说是很理想的。但他们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词汇核心和功能核心对补足语的扩展方向是不一样的。另外,(2)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追累”句式中“谁追谁”这种语义关系,让CausP作为DoP的补足语去推导非致使性解读(1b)也值得商榷,因为,正像熊仲儒(2004a:191)自己意识到的那样,这里面不存在致使的问题。
2.2.3 句法复合法
王奇(2006)把汉语中V-V复合词的生成看作是一种能产性的、根词复合的连动现象,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左向嫁接的问题。他运用Mateu (2002)的论元结构理论,对“追累”句式的岐义现象进行了分析。但他并没有对(1a)和(1c)做出区分,认为这两种解读具有同样的结构(3a)而(1b)则具有自己单独的结构(3b):
(3) a. [VoiceP [DP陶陶] [Voice′ [Voice ∅] [vPCAUSE [vCAUSE [root追] [vCAUSE ∅]] [vPGO [vGO ∅] [x1 [DP友友] [x1 [x1 ∅] [x2 [x2 ∅][y 累]]]]]]]]
b. [vPCAUSE [vCAUSE [root 追] [vCAUSE ∅] [vPGO [vGO ∅] [x1 [DP 陶陶] [x1 [x1 ∅] [x2 [x2 ∅] [root [root 累] [x3 [x3 ∅] [DP友友]]]]]]]
(3a)比(3b)多出一个VoiceP投射,其Spec是一个表致使的外论元。致使轻动词vCAUSE合并了根词“追”,而根词“累”则经过一系列并入操作后形成动词“累”。经过重新分析后,二者就能构成复合词“追累”。(3)解决了“追累”生成的语序问题,但(3a)把(1a)和(1c)纳入了相同的底层结构,没有清晰地表达出相关事件中“谁追谁”的语义关系。另外,由于(1c)表达的是一种无意致使事件,此时“追”已不再是“累”的致使原因且“追”的实施者也不再是“陶陶”,这样根词“追”再合并进vCAUSE就值得商榷了。在(3b)中,(1b)被处理成了一个致使运动事件。但我们认为,(1b)在本质上是一个非宾格性的自发运动事件而不是致使运动事件。另外,王奇(2006)把“友友”处理为辅助谓词“累”的补足语,这种处理只注意到了谓词“累”和“友友”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追”和“友友”语义上的动宾关系。
3.0 “追累”歧义句式的事件结构分析新解
3.1 运动事件与变化事件的平行性
事件结构研究中有一种重要的观点(Hoekstra & Mulder,1990;Goldberg,1995;Snyder,1995;Washio,1997;Rappaport Havov & Levin,2001;Mateu,2002等),认为运动事件和状态变化事件之间有一种平行关系。Snyder (1995)、Mateu (2002)对罗曼语以及Washio (1997)对日语的研究表明,如果一种语言不允许表方式的动词与表目标的PP共现,那么这种语言也不会允许表方式的动词与一个结果性短语共现。Mateu(2002)把表到达的PP句式也称为介词性的结果句式,而Goldberg (1995)则将AP结果句式分析为一个包含抽象路径的构式。在Hale & Keyser (2002)、Mateu (2002)、Lin (2004)以及国内的沈家煊(2004)、王奇(2006)、宋文辉(2007)等学者的研究中,发生状态变化的事物与其最终所处的状态之间都被表征为运动事件中凸体和衬体的关系。本文认为,空间、时间和状态都是事物存在的维度(dimension)。变化事件可以看成是运动事件在时间或状态维度上的投射。运动和变化事件平行的理念完全可以应用于汉语“追累”句式的歧义分析。
3.2 “追累”句式的宾语指向解读:状态维度的有界致使运动事件
我们认为,“追累”的宾语指向解读(1a)是一种状态维度的有界致使运动事件。也就是说,在追赶事件中,追赶者“陶陶”的追赶使得被追者“友友”的状态产生了一种抽象的运动,其终结点就是“友友”变累了。根据这一思路,解读(1a)的底层结构可以作以下表征⑦:
(4) [...[...[Asp1’[Asp1[+D]了][AFF+P [Spec陶陶i] [AFF+’ [AFF+[+A]] [Asp2P [Asp2 [+T]了] [vCauseP [Spec ti] [vCause’ [vCause [vDO [root √追] vDO][ vCauseФ]] [AFF-’ [AFF-[-A]][Asp3P [Spec友友j] [Asp3’ [Asp3 [+T]了][vGOP[Spec tj][vGO’ [vGO Ф][pP [p Ф][PP [PФ][NP√累]]]]]]]]]]]]]]]
在(4)中,最内层的vGOP表达的是“(变)累”这样一个内核事件。表示被追赶者最终所处状态的根词√累通过一系列的并入操作,为轻动词vGO’提供语音内容,实现为不及物动词“累”⑧。NP“友友”最初位于vGOP的Spec位置,随后又移到表达完整内核事件的Asp3P的Spec位置并在原位置留下一个语迹tj。为核查内核事件的界性,最内层的vGO’左向嫁接到Asp3。由于它表达有界事件,因此通过了体标记词“了”的界性核查。表达完整内核事件影响性的是一个没有Spec的AFF-’,做vCAUSE’的补足语,vCAUSE’的核心vCAUSE为空(Ф)。由于内核事件是一个表达逆向影响的有界事件,因此Asp3P之上的AFF取负值。为核查其影响性,带上体标记词的动词“累(了)”向AFF-’的核心AFF-嫁接,在被核查完影响性特征之后,就会位于表达完整内核事件的Asp3P的Spec NP“友友”之前。根词√追相继被轻动词vDO和vCAUSE合并,实现为表达致使的动词核心“追”,再和表达逆向影响的动词核心“累”经过重新分析,就构成了V-V复合词“追累”。整个复杂致使事件的界性由Asp2P的核心“了”来核查。内核事件所附带的“了”与整个复杂致使事件所附带的“了”重合,由音系规则删除一个“了”。(4)中最上层的AFF取正值,表示施事陶陶对受事友友施加的顺向影响。整个复杂致使事件的动性特征由Asp1P的核心(句尾)“了”来核查。句子的其它推导过程从略。
(4)中的AFF-表示的是动词的非宾格性,其功能与表示致使的vCAUSE有些类似,只是它表达的是一种相关主体受到发生事件的逆向影响而已。Davis & Demirdache(2000)以及胡旭辉(2014)的研究表明,非宾格动词在其底层语义表达中具有致使性。而汉语结果句式的演变过程(梁银峰,2006)也表明,现代汉语中V2为不及物动词的致使性结果句式Vt1Vi2最早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动并列格式“Vt1+Vi-t2+O”,这其中的第二个动词就用作使动。只是到了六朝时期,及物不及物两用的V2的致使义素开始脱落,变成了不及物动词。现代汉语中典型的致使性V-V复合词“V-死”在唐宋之前更多地被表达为“V-杀”就是很好的证明。(4)中所体现的AFF-与vCAUSE在功能上的平行性设计正好与上述观点相契合。此外,现代汉语V-V复合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个动词之间不能插入体标记词。体词标记“了”不能加在“追”上,只能加在“累”上。(4)中的设计和推导既反映了汉语V-V复合词的语序特点,又为汉语中的词尾和句尾两个体标记“了1”和“了2”安排了恰当的位置。
3.3 “追累”句式的主语指向解读:时间维度的有界自发运动事件
“追累”句式的主语指向解读(1b)是一种非致使解读,事件的观察视点是追人者“陶陶”。在追“友友”的过程中,他的身体或者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这种追赶过程可以看作时间维度上的一种有界的自发运动,运动的终点就是追人者变累了。这样,(1b)就可以表征如下:
(5)[...T[Asp1P [Spec陶陶i ][ Asp1’ [Asp1 [+D]了][ AFF-P [Spec ti”][ AFF-’ [AFF-[-A]][Asp2P [Spec ti’] [Asp2’ [Asp2 [+T]了][vDOP [Spec ti] [vDO’ [vDO [vGO’ [vGO [vDO [Root √追k] vDO] vGO] [pP [p Ф] [PP [P Ф] [n’ n [vGO’ vGO [pP [p Ф] [PP [P Ф][NP √累]]]]]]]] vDO]][n’ n [vDO’ [vDO ekvDO ] [NP 友友]]]]]]]]]]]]
我们首先看(5)中的复合词“追累”是怎样生成的:表示动作内容的根词√追先后被轻动词vDO和vGO合并为动作和运动。vGO所表示的“追赶”这个运动事件的终点是“(追赶者自己)变累了”这样一个次事件。该次事件由一个vGO’表示。轻名词n的作用是将vGO’所代表的次事件“累了”进行动名词化,表示“追赶者自己变累”这个运动事件的终结点。轻介词p和介词P则分别表示终点的到达和方位。可以看出,复合词“追累”就代表了“(陶陶)追到自己累了”这样一个有界的自发运动事件,“追累”在本质上类似于一个不及物动词。但这个复合词后面却带了宾语“友友”。为此,我们将解读(1b)处理成了一个有界的主事件“(陶陶)追到自己累了”和无界的副事件“(陶陶)追友友”复合而成的复杂事件。副事件“(陶陶)追友友”由一个事件性的轻名词短语n’来表示。n’中表达动作内容的根词是一个空动词。它与复合词“追累”中的根词√追之间类似于代词与其所指代的名词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深层复指”(deep anaphora) (Hankamer & Sag,1976;邓思颖,2010),我们称之为动词复指(verb anaphora)关系。正像邓思颖(2010:54)所指出的,深层复指并不是通过(移位等)句法操作产生的,而是通过语用因素得到复原(或被激活)的⑨。这样,复合词“追累”生成后,由轻动词vDO合并,之后再与后面n’所代表的事件性的类宾语共同组成一个vDO’,同时在语义上激活n’中的空动词ek。之后,该vDO’左向嫁接到Asp2上⑩接受其核心“了”的界性核查。在得到“了”的允准后,就获得了完整体的解释。然后再向上层的AFF-嫁接,以核查整个复合事件的影响性。由于该复合事件是一个非宾格性的有界自发运动事件,本质上表示一种逆向影响(van Hout,2004等),故Asp2P之上的AFF取负值。句子的其它推导过程从略。
对于(1b)中“友友”的处理,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并不是复合词“追累”的真正论元。施春宏(2008)认为,从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原则来看,解读(1b)是不允许的。石毓智(2003:15)也认为,汉语中补语语义指向施事的动结式不能够带宾语。他们都将解读(1b)这种现象看作是句法规则的例外或是特例。我们认为,“友友”在解读(1b)中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动名词化了的事件性的伪宾语(pseudo-object)。同“吃饱了饭”中的“饭”和“喝醉了酒”中的“酒”一样,是一个Gu(1992)所讲的准论元(quasi-argument),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论元,因此就大大降低了(1b)的可接受度。
3.4 “追累”句式的施受颠倒解读:时间维度的有界无意致使运动事件
“追累”的第三种解读(1c)显然是一种无意(non-volitional)致使现象。现有研究中对这种无意致使很多(Gu,1992;赵杨,2006;王奇,2006等)是采用与有意致使相同的处理办法。但是,我们知道,在“追累”句式中,在“谁追谁”这个深层的语义关系上,无意致使与有意致使正好相反。(1c)中的语义关系是“友友追陶陶”,这种语义关系应该在句法表征和推导中得到反映。根据这一精神,我们把“追累”句式的施受颠倒解读(1c)的底层结构表征为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有界的无意致使运动事件:
(6)[...[AFF+P [Spec Ф][ AFF+’ [AFF+[+A]] [Asp1P [Spec Ф][Asp1’ [Asp1[+T]了][vCauseP [Spec Ф][ vCause’ vCause [AFF-’ [AFF-[-A]][Asp2P [Spec友友][ Asp2’ [Asp2 [+T]了] [vGOP [nP [Spec Ф] [n’ [n [vDO √追vDO ][NP 陶陶]]]] [vCause’ [vCauseФ] [vGO’ [vGO [vDO [Root √追 (manner)] vDO] vGO][pP [PP [P Ф] [n’ n [vGO’ vGO [pP [pФ][PP [P Ф] [NP √累]]]]]]]]]]]]]]]


4.0 结语
对“追累”句式歧义解读进行句法分析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在体现深层语义关系和保证能生成复合词“追累”自然语序的前提下,推导出“追累”句式各种不同的解读。现有研究中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各种解读中复合词“追累”是以何种句法操作生成的;主语指向解读是否具有致使性,该解读中的“友友”是何种性质的论元;施受颠倒解读是否应该同宾语指向解读进行区分,如果要区分,该怎样对这两种解读进行区分?
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维度、界性和影响性等事件结构特征出发,本着运动事件与变化事件平行的理念,对“追累”句式的歧义解读进行了新的分析和阐释。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将其宾语指向解读分析为一种状态维度上的有界致使运动事件,通过AFF-等表达事件特性的功能语类较好地处理了内核事件的有界性及逆向影响性(即辅助谓词“累”的非宾格性)同“追累”的生成语序之间的关系,同时为汉语两个体标记“了”安排了恰当的位置。
第二,将其主语指向解读分析为时间维度上非致使性的有界自发运动事件,认为此时类宾语“友友”是一个事件性的伪论元。它同主事件的语义关系是通过动词复指来实现的。主语指向解读的可接受度偏低且不能转换为“把”字句等语言事实可以支持这种分析。
第三,将其施受颠倒解读分析为一种不同于宾语指向解读的有界无意致使运动事件,认为施受颠倒解读(1c)是由动词拷贝结构“陶陶追友友追累了”派生而来的。个体性致事“陶陶”是由事件性致事“Ф追陶陶”经动词删略和动词复指激活通过转喻机制转换而来的。施受颠倒解读是无意致使与被动经历的统一。这种分析既能反映相关事件的深层语义关系又能得到汉语无意致使句的体貌特征及汉语相关句式转换等方面的支持。
注释:
① 本文所讨论的汉语结果句式均是指汉语中的短语型结果句式(亦称动结式),即不含“得”字的结果句式。
② 例如,“一锅饭吃饱了十几个人”就是典型的施受颠倒型结果句式。
③ 在生成语法框架外,学者们还从词汇-函项语法的词汇映射理论(何万顺,1997;Her,2007)和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结构理论(沈家煊,2004;宋文辉,2007)等角度对“追累”句式的岐义现象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④ Zou (1994)的分析如下:
a. [IP 陶陶i[I 追j-累k-了] [VP1 [NP1 ti] [V1’ [V1 tj] [ VP2 [NP2 友友] [V2’ [V2 tk]]]]]
b. [IP陶陶i[I追j-累k-了] [VP1 [NP1 ti] [V1’ [V1 tk] [ VP2 [NP2 pro] [V2’ [V2 tj] [NP3 友友]]]]]]
c. [CP陶陶n[C (追j-累k-了)l ] [IP 友友i[I tl][VP1 [NP1 ti] [V1’ [V1 tk] [ VP2 [NP2 pro] [V2’ [V2 tj] [NP3 tn]]]]]]]
⑤ 王玲玲、何元建的分析如下:
a. [vP [DPj(施事) 陶陶] [v’ [v 追jv] [VP [XP PROi累了] [V’ tj[DPi(客事)友友]]]]]
b. [vP [DPj(施事) 陶陶] [v’ [v 追jv] [VP [XP PROj累了] [V’ tj[DPi(客事)友友]]]]]
c. [vP [DPi(致事)陶陶] [v’ [v追jv] [VP [XP PROi累了 友友] [V’ tjti(客事)]]]]
⑥ 王玲玲、何元建(2002:22)自己也意识到了(1b)中“友友”具有明显的事件性,应该类似于英语中的动名词,但他们的句法表征中并未体现出这一点。
⑦ 本文的句法模型体现的正是变化事件是运动事件投射的思想。由内到外的三层AspP表示的是事件结构中的词汇体、语法体和时间体(完整体、一般体和将来体)等三种体结构。词汇体和语法体在现代汉语中分别表现为动词词尾的“了1”和句子句尾的“了2”。[+T]表示的是事件的界性特征,[AFF+/-]表示的是事件的发起者或肇始者对受事所施加的顺向影响(用AFF+表达,简写为+A)和遭受到的负面的逆向影响(用AFF-表达,简写为-A ),[+D]表示事件的动性(dynamicity) 特征。事件结构中的这些特征都是句法中需要核查的特征。此处省略了Asp1P以上的TP和CP的表征,此后的几处表征均有不同程度的省略。
⑧ 这一过程可以表征为[vGO’ [vGO √累i-Ф-Ф-Ф] [pP [p ti”-Ф-Ф] [PP [P ti’-Ф][NP ti]]]]。
⑨ 邓思颖(2010:54)认为,汉语“形义错配”结构“[他的Ф老师]当得好”中就包含这样一个本质上是深层复指的空动词Ф。
⑩ 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这一过程。


a. *青草吃肥了羊儿了/青草吃肥了羊儿。
b. *茅台酒喝醉了他了/茅台酒喝醉了他。
实际上,汉语“追累”句式的无意致使解读(1c)也不允许两个“了”并存,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中的(1)忽略了这样的细节。
参考文献
[1] Cheng, L. Resultative compounds and lex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s[J].ChineseLanguagesandLinguistics, 1997,(3):167-197.
[2] Chomsky, N.TheMinimalistProgram[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3] Davis, H. & H. Demirdache. On lexical verb meanings: Evidence from Salish[A]. In C. Tenny & J. Pustejovsky (eds.).EventsasGrammaticalObjects[C]. CSLI Publications, 2000.97-142.
[5] Goldberg, A.Constructions: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6] Grimshaw, J.ArgumentStructur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7] Gu, Y.TheSyntaxofResultativeandCausativeCompoundsinChines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8] Hale, K. & S. J. Keyser.ProlegomenontoaTheoryofArgumentStructure[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9] Hankamer, J. & I. Sag. Deep and surface anaphora[J].LinguisticInquiry, 1976,(7):391-426.
[10] Her, One-Soon. Argument-function mismatches in Mandarin resultatives: A lexical mapping account[J].Lingua, 2007,117(1): 221-246.
[11] Hoekstra, T. & R. Mulder. Unergatives as copular verbs: Locational and existential predication[J].TheLinguisticReview, 1990,(7):1-79.
[12] Huang, C.-T. James. Complex predicate in control [A]. In J. Higgibotham & R. Larson (eds.).ControlandGrammar[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119-147.
[13] Li, Y. F.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J].NaturalLanguageandLinguisticTheory, 1990,(9):177-207.
[14] Li, Y. F. Structural head and aspectuality[J].Language, 1993,(69):480-504.
[15] Li, Y. F. The thematic hierarchy and causativity[J].NaturalLanguageandLinguisticTheory, 1995,(13):255-282.
[16] Lin, J.EventStructureandtheEncodingofArguments[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4.
[17] Mateu, J.ArgumentStructure:RelationalConstrualattheSyntax-semanticsInterfac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at Autnoma de Barcelona, 2002.
[18] Rappaport Havov, M. & B. Levin. An event structure account of English resultatives[J].Language, 2001,(77):766-797.
[19] Snyder, W. A Neo-Davidsonian Approach to Resultatives, Particles and Datives[A]. In J. N. Beckman (eds.).ProceedingsoftheNorthEastLinguisticSociety25[C]. Amherst: GLSA, 1995.457-471.
[20] van Hout, A. Unaccusativity as telicity checking [A]. In A. Alexiadou, E. Anagnostopoulou & M. Everaert (eds.).TheUnaccusativityPuzzle:ExplorationsoftheSyntax-LexiconInterfac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60-83.
[21] Washio, R. Resultatives, compositionality and language variation[J].JournalofEastAsianLinguistics, 1997,(6):1-49.
[22] Zhang, N. The structures of depictive and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J].ZASPapersinLinguistics, 2001,(22):191-221.
[23] Zou, K. Resultative V-V Compounds in Chinese[J].MITWorkingPapersinLinguistics, 1994,(22):271-29.
[24] 邓思颖. “形义错配”与汉英的差异[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3):51-56.
[25] 何万顺. 汉语动宾结构中的互动与变化 [M]. 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7.
[27] 胡旭辉. 英语致使结构:最简方案视角下的研究及相关理论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4):508-520.
[29] 梁银峰.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和演变[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0] 沈家煊. 转指与转喻[J]. 当代语言学,1999,(1):3-15.
[31] 沈家煊.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J]. 语言科学,2004,(6):3-15.
[32] 施春宏. 动结式致事的类型、语义性质及其句法表现[J]. 世界汉语教学,2007,(2):21-39.
[33] 施春宏. 动结式“V累”的句法语义分析及其理论蕴涵[J]. 语言科学,2008,(5):242-258.
[34] 石毓智. 语法的规律与例外[J]. 语言科学,2003,(3):13-22.
[36] 宋文辉. 现代汉语动结式的认知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7] 王立弟. 论元结构新论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38] 王玲玲,何元建. 汉语动结结构[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39] 王奇. 并合与复合:第一语阶句法的跨语言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6.
[40] 熊仲儒. 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a.
[41] 熊仲儒. 动结式的致事选择[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b,(4):471-476.
[42] 熊仲儒,刘丽萍. 动结式的论元实现[J]. 现代外语,2006,(2):120-130.
[43] 赵杨. 汉语使动及其中介语表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6-03-002
收稿日期:2015-07-3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事件结构理论与跨语言类型比较参照下的汉语结果句式研究”(项目编号:12BYY089);“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长城学者)计划项目”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周长银(1972-),男,汉族,山东齐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认知神经语言学。 周统权(1966-),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2-2643(2016)03-0012-09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biguity of the MandarinZhui-leiConstruction
ZHOU Chang-yin1, ZHOU Tong-quan2
(1.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Zhui-lei construction has as many as three interpretations, namely the object-oriented, the subject-oriented and the agent-inverted-with-patient ones. It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gh ambiguous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and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the recent studies on Mandarin.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major disputes and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Then, based on the idea of parallelism between motion event and change-of-state event under the notion of dimensionality, it proposes new analys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mbiguity of the zhui-lei construction. The thre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 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through the three corresponding analyses of the events it denotes as a telic caused motion event in the dimension of state, a telic self-initiated motion event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a telic non-volitional motion event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The analyses and derivations concerned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word-order property in the derivation of Mandarin V-V compounds, underlying semantic relations in the events concerned, the proper insertions of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legal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ones.
Key words:zhui-lei construction; event structure; analyses of ambiguity; verb anaph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