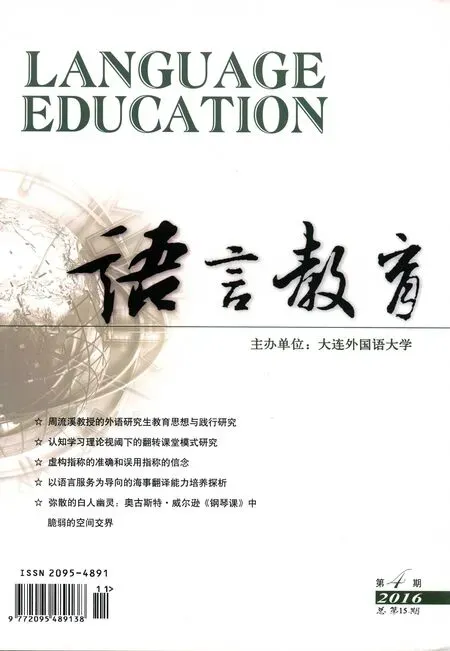大学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测量与培养
——以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为例
王婀娜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大学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测量与培养
——以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为例
王婀娜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文章首先从外语教育的视角对跨文化能力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其次,通过发放问卷对大学德语专业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进行了测量,以期对学生跨文化能力的现状进行测量,并检验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外语教学改革的实验效果。最后,结合实证性研究结果,针对大学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薄弱环节,并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提出一种呈现为过程性的、符合建构主义理念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
跨文化能力内涵;跨文化能力测量;教学对策
引言
由于全球化的浪潮的兴起和居住地点的变换,适应异文化的社会环境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成了日常生活的新挑战。特别是对于外语专业的大学生而言,由于其工作环境的国际化,跨文化能力已是“21世纪人才的必备能力”(庄恩平,2006:79-80),并且有专家呼吁“外语教学大纲应提出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人才的要求”(庄恩平,2006:79-80)。然而,就目前有关中国外语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而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为数不多,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以基于实证性研究而得出的跨文化能力内涵为参考值,对大学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实际值进行测量,从而找出问题所在,并据此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1. 跨文化能力内涵
“跨文化能力”这一概念在不同学科都被频繁使用。一般来讲,对于跨文化能力内涵的研究可分为两种:传统的结构思维模式和整体过程的理解(丛明才 王婀娜,2013:95)。传统的结构思维模式认为,认知、意识和行为是组成跨文化能力的三大要素;整体过程的理解是指,跨文化能力不是一个聚合的结构性概念,而是一个聚合的过程性概念。
本文主要从外语教学的视角出发,对跨文化能力的内涵进行综述和界定。有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包含跨文化态度、知识、解释和关联的技能、互动的技能以及批判性的文化意识(Kotthoff/Spencer-Oatey,2009:469-470)。Leenen (2008)等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与跨文化相关的个人性格特点、与跨文化相关的社会能力;特定的文化能力和普通文化能力(Leenen/GroB/ Grosch,2008:109-111)。Knapp将跨文化能力概括为能够参与某种特定文化的能力,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与不同文化的成员达成理解的能力。具体来说,跨文化能力包括以下几点:与异文化成员交际、并有接触的愿望;对特定文化知识的掌握;对文化和交际的一般了解;策略能力:掌握与互动相关的策略、学习策略和研究策略是动态跨文化能力的基本要素。跨文化能力具有伦理层面的问题(Knapp,2008:81)。史笑艳从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对跨文化能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在认知层面,重视学生们对母语文化和异质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其对母语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共性与差异的了解。在情感层面,关注学生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及其心理调试过程。在行为层面,注重学生们在跨文化环境中将情感态度和文化知识综合运用,从而与异质文化伙伴适当且有效地进行交际的能力”(史笑艳,2015:79)。此外,张红玲认为,“跨文化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实践和跨文化研究方法等核心内容,其中跨文化意识指的是对文化差异敏感性和态度的培养。跨文化交际实践主要是指有教材和教师提供或创造跨文化交际的机会或情境,让学习者去体会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教学,其意义在于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因此掌握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是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张红玲,2008:192-199)。由此可见,就外语教学领域内的跨文化能力内涵来看,学者们普遍倾向于采用聚合的结构性概念,强调的是一个聚合的过程性概念。
本文旨在对大学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中的一个维度——跨文化意识(敏感性和态度)进行实证性量化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本文采用陈国明等的跨文化敏觉力量表,因为这个量表的效度和信度是经过实证性检验的。陈国明等把跨文化敏觉力定义为“一个人对了解与感激文化的差异,与促进适当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正面情感的能力”(Chen & Starosta,1997)。还有众多学者把跨文化敏觉力界定为发展正面情感的内在能力(陈国明,2011:230)。这种正面的情感的形成建立在内心推动我们去适当地处理文化差异以达到互动效果的愿望。本文采用陈国明等的跨文化敏觉力元素理论,认为跨文化敏觉力包括:自爱、自我检视、开放的心灵、移情、互动投入以及暂缓判断这六大要素。陈国明等(2000)以前面所引述的跨文化敏觉力的六个主要元素为基础,经过连续四次的测试,将七十二条项目最后提炼出二十四个效度和信度都可以接受的项目,作为跨文化敏觉力的量表(Chen & Starosta,2000)。并且该量表中有正反向命题,可以对数据的可信度进行内部验证。在美国、英国、德国、中国与西班牙等国家,都有学者正在测试这个量表使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可靠性,其中在德国已确认了这个量表可以使用在该国的样本与环境(Fritz,Mollenberg & Chen,2002:165-176)。该量表测量的五个因素为:互动投人、尊重文化差异、互动信心、互动享受与互动专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及研究问题
本课题以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第三学期四个班,共95名学生为研究对象。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前三个学期的授课中,对于课程“基础德语1—3”授课班级教师做过有意识的安排:在每周10课时的授课中,有两名跨文化专业背景的教师在实验班加大跨文化方面知识的传授,另外两名非跨文化专业背景的教师则不刻意进行跨文化方面知识的传授。所选用的教材一样,均为《当代大学德语》;学生均为德语初学者。通过该问卷研究如下两个问题:(1)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第三学期的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现状如何?(2)专业教学中跨文化知识的渗透是否有作用?
2.2 研究工具
调查工具为陈国明和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度问卷》(陈国明,2011:234)。经过对3个学生的预测试发现,学生在理解反向设置题目方面有困难,故笔者将该问卷中的反向设置题目转换为正向设置。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经过实验检验。“跨文化敏感度问卷”围绕“对互动的热情、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对互动的信心、互动过程的享受和互动的细心程度”五个因素展开,共24道题。每个问题赋值5分,要求被调查者从“1”到“5”选择一个数字为自己的实际情况打分。
2.3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具
问卷调查由各班级老师随堂进行。发放问卷95份,收回95份。其中实验组人数为46人,对照组人数为49人。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各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将实验组(1、4班)与对照组(2、3班)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互动热情较高、互动细心程度及互动过程的享受程度较高,但互动的信心及对文化差异的尊重程度不足,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低。
表1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在“对互动的热情”(总分为35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分分别超过了总分值的80%和73%)、“互动过程的享受”(总分15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分分别达到总分的76%和71%)和“互动的细心程度”(总分为15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分分别达到总分的76%和71%)上平均得分均较高,表明学生对于跨文化互动是积极且乐于关注互动中的细节的;但是,在“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总分为30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分分别达到总分的51%和41%)、“对互动的信心”(总分为25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分分别达到总分的61%和50%)平均得分较低,表明学生在实施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信心不足,且并没有较好地做到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由此可以看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对互动的信心”是所有受测人员在跨文化敏感力的自我测评中最为薄弱的两个环节。若以85%为优秀水平衡量标准的话,上述五项均未达到优秀水平,跨文化能力整体水平偏低。由此可见,对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第二,教学改革对于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水平是有显著提高的。
由表2可知,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实验组与未进行改革的对照组对互动的热情(t=3.15, df=93, p<0.05, MD=2.33)、对文化差异的尊重(t=3.82, df=93, p<0.05, MD=2. 88)、互动过程的享受(t=1.83, df=93, p<0.10, MD=0.76)、对互动的信心(t=3.82, df=93, p<0.05, MD=2.88)以及互动的细心程度(t=1.83, df=93, p<0.10, MD=0.76)方面均有显著不同,且实验组在各项的表现均优于对照组。

表1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跨文化能力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2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跨文化能力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3. 2 引入外部评价
为了对抽样调查对象的跨文化能力水平做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评价,研究引入了外部评价。负责这4个班授课的2名德国外教对该四个班的平均分数评价显示,实验班1、4班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得分均高于2、3班。
3.3 小结
由上述两个数据表格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学生具有如下特点:一、对文化差异有着积极的态度。该班学生能更敏感地识别不同文化背景和交流情境下的差别,然后进一步地表现出他们的尊重,更懂得在互动中维持自我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生思路更开阔,能从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文化差异,乐于接受不同的观点。二、实验组在“互动过程的享受”和“互动的细心程度”方面略微高于对照组,这与其专业语言考试成绩不佳有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期末考试成绩不佳导致其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异文化的更多了解反而会对自己的跨文化互动行为不够满意。由此可见,第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好外语很重要,是培养跨文化能力的重要工具和途径”(潘亚玲,2008:72)。第二,经过这样一个为期1.5年的教学实验可以看出,有关跨文化知识的渗透是有作用的,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固然与学习成绩有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的。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并且可以通过教师的有意引导而得到加强。同时也表现出,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的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方面都表现出较低水平,特别是“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对互动的信心”是亟待高校外语专业教师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应当将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视为一个开放型的、自我构建知识和能力的渐进式过程。
4.提高德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教学策略
跨文化能力是完全可以经过有效地培养而获得的。一方面,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是开放型的终身学习过程,即“从民族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从对本文化和异文化单一表面的认识到全面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从不自觉、欠当的跨文化行为到自觉、有效地跨文化行为”(潘亚玲,2008:71)。另一方面,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而且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Duffy & Jonason,1991,转引自刘学惠,2003:34)。若将上述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便是一种呈现为过程性的、符合建构主义理念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模式。为此,应当从教师与教材、跨文化专业课程的开设和跨文化环境的营造进行教学改革。
4.1 教材与教师
作为担当着外语传授职能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我与他我”进行清晰的认识,只是单纯地向具有异文化背景的人传授专业特殊性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让学习者熟悉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和互动能力的其他要素,在新的社会文化范围内传授给学习者社会行为。学习者既要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理解为其所有行为的前提条件,又要努力将自己的世界用德语予以解释。
首先,应注重培养学生解决文化误解及冲突的能力。在对《当代大学德语》教材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到里面涉及的中德文化对比的主题,如:学校生活、家庭关系、饮食以及居住、婚姻形式、理想职业。在这些课文中,教师可以尝试引导学生将德国的情况与中国的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并引导学生描述出自己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理解、感知及可能的行为。在对涉及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章节进行分析后发现,教材没有强调成功解决文化误解及冲突能力的重要性。
其次,应重视培养教师的跨文化能力。通过上述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均值对比结果可知:教师的跨文化能力背景知识对于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有直接影响作用。外语教师应当将语言教学与文化相结合,提高自身在语言水平、文化知识和个人态度三个方面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主导”的授课方式应转变为“学生为主导”的分组讨论、角色扮演、项目教学、专家谈话等以“行动为导向的”现代课堂教学形式。比如,讲授在公司工作为主题时,可组织学生进行跨文化情境下企业谈判的角色扮演。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最核心的要素是师资队伍建设,可以通过出国进修、学术研讨、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提高外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
教师不仅应当引导学生理解文本的显性信息,而且还要引导学生思考文本的隐含信息、课文内容对自己有何相关意义、文化背景对于理解课文的困难是什么等,而学生自己也要主动建构自己的学习过程。隐性文化学习的优点在于能够“提升学生内在的文化素质”(刘学惠,2003:36),并且“这种文化学习模式与现代教育的建构主义学习观相吻合”(Williams & Burden,1997,转引自刘学惠,2003:35)。
4.2 开设跨文化专业课程
2002年柏林工学大学提供的跨文化课程分为两个学习阶段:一是基础课程阶段。在这一阶段,课程围绕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展开,如文化、交际、能力等。二是具体应用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可以将在第一阶段习得的知识、能力具体运用到和外国学生合作的项目中(陈正 钱春春,2011:377)。
针对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的跨文化能力,德国的学术机构通过实证性研究,探索学生的跨文化交流中的问题所在,并通过跨文化专业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比如,2005年,第一期“MUMIS项目”(大学中的多语言性和多文化性项目)启动,该项目旨在对大学学习生活中的冲突和误解进行实证性研究,得出学术文化内的行为和行动差异。2012年,该项目开展了旨在将人际交流中的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关联反映出来的第二期活动。该项目在对524个关键性事件进行语料库的分析之后,得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雷根斯堡大学自2009年冬季学期起开设了“国际关系和管理”本科专业(Blod, Elze und Woerz-Hackenberg,2011:269)。该专业传授跨文化能力的科学性基础知识和实践知识,主要采用的理论是Aleander Thomas的文化标准理论。该理论重点放在关键能力的传授上,比如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团队工作和分析性思维能力。为提高外语水平,该课程自第二、三学期开始用英语授课。从第4学期开始结合经济或政治领域授课。在介绍世界各地的课程中,有关地区课程结合相应的语言授课:西欧用罗马语,东欧用东欧语,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用英语,拉丁美洲用西班牙或葡萄牙语,中国用中文,阿拉伯国家用阿拉伯语。该专业包括必修的国外学习1学期以及到国际性企业实习1学期。设置该专业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适应国际化组织或企业,或者在国际领域内从事有创造性的组织、协调、交流的工作。
关于德国高校的教育精神也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从“洪堡精神”到“能力”的转变。虽然洪堡精神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人的教育理论是研究与教学的统一,只有当科学研究没有目的性,研究的自我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理想主义的教育和科学的自由在德国历史上从未完全实现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Habermas,1981)。总的来说,现在有一种从客观知识的传授向能力的传授发展的趋势,即获取知识的能力,显得越发重要了(Bleck,2001:98)。
4.3 营造跨文化环境
加强校企合作和国际办学合作都是增强学生跨文化实践能力的有效措施。正如跨文化能力的具体内涵所述,对异国文化的积极情绪是发展跨文化能力的重要前提。多中心的思维方式和理解并接受异国文化的决心是非常必要的。“跨文化能力”并不是脱离应用领域而存在的“空中楼阁”,不能脱离应用领域空谈。
到国外学习可以为学生打开广泛、多样的行动领域,学生可以在其中感受到文化的差异(Nothnagel,2010:433)。在高校教育之内的外国学期为进行跨文化学习提供了重要可能(Deardorff,2006:232)。在国外学习的目标主要是提高外语知识水平、增强跨文化能力、深化专业知识和扩展视野(Budke,2003:22)。国外学习的益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可以更好地与当地居民沟通增进理解;第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Ehrenreich,2008:33)。
获得文化知识的渠道很多,包括网络、外国电视剧或电影。在网上可以使用聊天软件聊天,也可以读书、小说或杂志。有研究指出,“网上学德语已经成为学生在自学时间内的主要选择。”(葛艳 朱建华,2011:153) 举办“德语角”,展播跨文化主题的电影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可以开展“读书会”,教师可以与学生就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进行交流、讨论。
5. 结语
总之,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开放型不断学习的过程。跨文化能力内涵的界定是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额定值。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发放问卷对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所做的测量是跨文化能力的实际值。为了弥补额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距,我们需要从教学人员、教材、课程的开设以及为学生营造跨文化环境等方面共同努力,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1] Bleck, W. 2001. Geschichte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M]. Mnchen: C. H Beck.
[2] Blod, G. S. Elze & C. Woerz-Hackenberg. 2011. Bachelo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anagement”-ein interdisziplin rer und interkultureller Studiengang an der Hochschule Regensberg[A].In Dreyer, W./H βler, U. (eds.). Perspektiven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C]. G 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3] Budke, A. 2003. Wahrnehmungs-und Handlungsmuster im Kulturkontakt. Studien ber Austauschstudenten in wechselnden Kontexten. Studien ber Austauschstudenten in wachsenden Kontexten[M]. G ttingen: V-und R-Unipress.
[4] Chen, M. & J. Starosta. 1997.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 Human Communication, (1): 1-16. [5] Chen, M. & J. Starosta. 2000.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A]. In M. Chen & J. Starosta, (eds.).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C]. New York: Peter Lang. [6] Deardorff, K. 2006.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study abroad students[A].In M. Byram & A. Feng (eds.). Living and and studying abroad. Research and practice. [C]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7] Ehrenreich, S. 2008. Auslandsaufenthalte quer gedacht- aktuelle Trends und Forschungsaufgaben. Anmerkungen aus deutscher Warte[A]. In S. Ehrenreich & G. Woodman & Perrefort, M. (eds.) Auslandsaufenthalte in Schule und Studium[C]. Mnster/New York/Mnchen/ Berlin: Waxmann.
[8] Fritz, W. & A. Mollenberg. & M. Chen. 2002.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context[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1 ):165 - 176.
[9] Habermas, J. 1981. Konzept de herrschaftsfreien Diskurse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I [M]. Frankfurt: Suhrkamp.
[10] Kotthoff, H. & H. Spencer-Oatey. 2009.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1] Knapp, A. 2008.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Ein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Persperktive. [A] In Auernheimer, G. (ed.).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und p dagogische Professionalit t. [C] Wiesbaden: VS Verlag f r Sozialwissenschaften.
[12] Leenen, R. & G. Andreas & H. Grosch. 2008. InterkulturelleKompetenz in der Sozialen Arbeit [A]. In Auernheimer, G. (ed.).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und p dagogische Professionalit t. [C]Wiesbaden: VS Verlag f r Sozialwissenschaften.
[13] Nothnagel, S. 2010. Auslandssemester[A]. In A. Weidemann, J. Straub & S. Nothnagel (eds.). Wie lehrt man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C].Bielefeld:Bertelsmnn.
[14] Thomas, A. 2003.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Grundlagen, Probleme und Konzepte[J]. Erwaegen, Wissen, Ethik, (14) : 137-156.
[15] 丛明才 王婀娜.2013.国内外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内涵研究综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11):95-98.
[16] 陈国明.2011.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7] 陈正 钱春春.2011.德国“跨文化教育”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启示[A].王小梅 丁晓昌编.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C].苏州:苏州大学.
[18] 葛艳 朱建华.2011.大学德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的培养[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48-153.
[19] 刘学惠.2003.《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J].外语与外语教学,(1):34-36.
[20] 史笑艳.2015.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过程实例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1] 潘亚玲.2008.我国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实证研究[J].中国外语,(4):70-72.
[22] 吴显英.2008.国外跨文化能力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 (3):190-192.
[23] 杨洋.2009.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与评价[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24] 张红玲.2008.跨文化外语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5] 庄恩平.2006.跨文化能力——我国21世纪人才必备的能力[J].外语界,(5):79-80.
On the Measur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aking German Majors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about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econdl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measure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German majors of bot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Meanwhile, the effects of the cultivation reform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were further explored. Finally, wi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conjunction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a procedural and constructive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training model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weakness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measurement, teaching strategies.
H319
A
2095-4891(2016)04-0016-06
本文系2014年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4SD0038A)、2014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4BYY009)和2013年大连外国语大学校级教改立项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3Y02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婀娜,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跨文化经济交流、德国教学法、德国经济外交。
通讯地址:116044 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6号 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