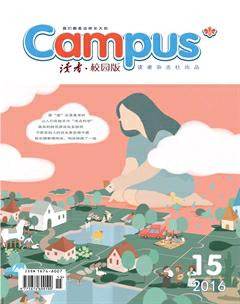我的爸爸要结婚了
咪蒙
你的爸爸,要结婚了。
听到这样的通知,该做出什么表情、给出什么回应,我没有事先排练过。我花了一点儿时间,去理解这个句式的意义。
我的爸爸,要结婚了。
这是他第三次结婚。和谁呢?这个问题我并不想问。只要不问,它对我的影响就会减弱;只要不问,其他人很快就会忘掉。这是我逃避现实的方法,似乎也不太管用了。
爸爸第一次结婚,是和妈妈。妈妈年轻时皮肤白皙、气质温婉,同时追求她的有四五个人,之所以选择了爸爸,是因为他聪明、口才好、长得不错。
在外公看来,妈妈是下嫁——外公家虽然穷,但起码是书香门第。妈妈是幼儿园教师,一直做着作家梦,爱看《收获》《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学杂志。爸爸是在爷爷58岁高龄时出生的,小学还没读完,因为缴不起学费就辍学了。爸爸进床单厂当了工人,下班也接些木工活儿。我家的床有极其复杂的雕花,是爸爸做的。
小时候,我很喜欢待在爸爸做家具的现场,看着墨线从轮子里放出来,贴着木头,轻轻一弹,印下漂亮的黑色直线。我等着刨花一层层掉下来,集齐一堆,就撕成我想要的形状。在我眼里,木工真是了不起的职业,如果他愿意,可以再造一个王国。
爸爸还很会钓鱼。周末的早晨,他带我去嘉陵江边,他拉着钓竿等鱼上钩,不一会儿就能钓到好几条,够我们好好吃上一顿了。我在旁边画画,尝试用水彩表现出江水波光粼粼的样子。
爸爸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赌博,一年365天,他大概有300天都在外面打牌,除夕也不例外。
但我每一次生病,他都不会缺席。4岁时我得了猩红热,住院一个多月,他每天下班来医院陪我,跟我比赛吃橙子,他一口气吃7个,我吃6个。6岁时我的脚后跟卷进自行车轮,一块肉掉下来,血滴了一路,他背着我飞奔去医院。7岁时我得了肠梗阻,胃管从鼻子插进去,呛得我眼泪直流,爸爸不忍心看,站在病房门口,眼眶有点儿红。读小学那几年,爸爸每天早上骑着边三轮车(四川方言里叫“耙耳朵车”),先送妈妈上班,再送我上学,之后才折回去,骑很远的路上班。他是迟到大王。他们厂门口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公布迟到者的姓名,别人的名字是用粉笔写的,爸爸的名字是用油漆写的。
我上了初中,爸爸开始做生意,成了老板。他的身边多出一个红颜知己,也是他的合伙人。那个女人有老实巴交的丈夫,以及把活青蛙抓起来往嘴里塞的彪悍的儿子。
爸爸常常组织我们两家人聚会。有一次去嘉陵江边游泳,那个女人的泳衣肩带掉了,爸爸很友善地提醒了她。是我早熟吗?我从他自然的语气中读出了不自然的信息。
爸爸请他们一家三口来我们家吃饭。大概是沉浸在热恋中的缘故,他非常殷勤,亲自下厨做了大鱼大肉,让我打点儿杂,剥几个松花蛋。我动作慢了点儿,他着急之余,扬手给了我一耳光。爸爸不常打我,大概一年一次。这一次是因为我耽误了他的意中人早几分钟吃上松花蛋,这也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那时我很胖,那个女人调侃我,说我这样胖下去,以后会嫁不出去。爸爸也跟着附和:“是啊,你晚上睡觉还嫌床太硬,一身肥肉怕什么床硬啊。”一个男人为了向心爱的女人表忠心,一定要舍得拿自己亲近的人开刀。他和她是一国的,我和妈妈成了他们的外人,以及敌人。
家里成了肥皂剧的现场,每天定时上演哭闹、吵架、无情翻脸、互相羞辱的戏码。
妈妈说,为了我,她不能离婚,必须维持家庭的完整。有时候放学回家,想到妈妈为了我委曲求全,我开始厌弃自己。我算不算伤害妈妈的帮凶呢?如果这世上没有我,会不会变得和谐一点儿?我骑着自行车,两行眼泪背叛了地心引力,被风吹着往后飘散,那画面有点儿喜感。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失眠,造成失眠的主题是,我该如何保护妈妈,该如何报复他们。我阅读侦探小说,设计各种杀人方案,甚至想过绑架那个女人的儿子——那个吞活青蛙的儿子。
因为长期失眠和头痛,我去精神病医院看过病。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或许抑郁症是种高级的病,我还不配得。
对妈妈,他越来越冷漠。妈妈发烧在家,他不闻不问。一次吵架,他把妈妈推到地上,妈妈撞到床角,腰部受了重伤。爸爸说自己很善良,因为他很爱小动物,冬天怕家里的小狗着凉,半夜起床给它盖被子。这么看来,爸爸确实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是,他的发妻、他的家人,也是动物啊。
很多时候,我的固定食谱就是眼泪拌饭,咸咸的,味道不错。
爸妈终于离婚了。妈妈心情不好,有时候我顶一句嘴,她就会抽我一耳光。如果打我耳光她会开心点儿,倒也无妨。我每个月要见爸爸,需要拿生活费。爸爸说,他一直很爱我。我分不清他是在演戏,还是所谓的人格分裂。你爱我,却以伤害我和我最爱的妈妈的方式来表达。
一年之后,爸爸多次回来找妈妈忏悔,声情并茂,他们复婚了。爸爸说,他对外面那些女人彻底死心了。
爸爸“死心”之后,却又跟自己手下的会计好上了。他的一大特异功能是“小三”永远都是窝边草,一定要给妈妈就近的羞辱。
他和妈妈之间又调成了吵架模式。我考上大学,去了外地,他们继续吵,继续冷战,继续敌对。
我寒暑假回家,爸爸和朋友们在家里吃饭喝酒,高谈阔论。他们是同类项,找“小三”,出入夜总会,以拥有多位情人为荣。爸爸说:“守着一个女人过一辈子,是一个男人无能的表现。”
我在自己的房间,冷冷地想:“该给你们发奖杯,表彰你们乱搞吗?”当他欢快地跟朋友们分享自己跟一个洗脚房姑娘砍价的故事时,我很想做点儿什么,比如割开自己的动脉,把不太干净的血,打包还给他。
时隔多年,如果可以,我想回到那个晚上,告诉爸爸我自己的狭隘理解:所谓成功,无非就是你身边的人,因为有你而感到快乐。而一个男人,能给你的孩子最好的呵护,就是永远爱他的妈妈。如果你做不到,至少不要太嚣张、太自私,这会影响孩子对人性的判断。人性固然是复杂的,但没必要撕毁得如此彻底。
有一次我去大学同学家,饭桌上,她爸爸给她妈妈夹菜,耐心地听她妈妈唠叨,说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排名第四,仅次于老婆、女儿和一条狗。我突兀地起身,假装去上厕所,让眼泪可以自由释放。原来正常的家庭是这样的,正常的爸爸是使用这些语言的。
这些事,这些感受,我从不对身边的朋友讲。说出来又怎样呢,考验对方安慰和敷衍的技巧吗?不过是徒增尴尬罢了。我擅长装开朗,开朗到浮夸的程度。总有人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心理多少有些不正常。我努力扮演正常,还不行吗?
是的。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是演技派。
父母再次离婚。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儿解脱。单亲家庭总比虚假家庭好。妈妈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在发现丈夫出轨且翻脸无情时及时放手。对于老派的中国人而言,离婚是一个惨烈的词,妈妈总想绕过它,她多花了十几年,浪费在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身上。而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他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可持续的、螺旋上升的,他不吝每天展示全新的冷漠无情。
离婚之后的妈妈反而变得轻松愉悦,她把和爸爸斗气的时间省下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重新学习与世界相处。她学跳舞、读小说、玩微博、听音乐会,这世上,少了一个苦情女人,多了一个文艺师奶。
而我,目睹爸爸和他同辈的大部分男人,对自己的发妻从细心呵护到横眉冷对,爱情完全就是易碎品,随时毁坏,随时另起一行。那时候,我怀疑所谓永恒的爱情,只是文艺作品里的意淫,山盟海誓是自欺欺人,厮守一生是痴人说梦。
“幸福的人是沉默的,他们只顾着幸福,舍不得拨出时间来展览自己的完满。不能因为你没看见,就否定真爱的存在。”暗恋我十多年的男人对我表白之后,我说爱情都是瞎扯淡,他这样回答。他是我的幼儿园同学,小学、初中也是同班,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先后到了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单位、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从恋爱到结婚后,这11年,我们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他说,他爱我,早就超过了爱自己。他用他的坚定、他的顽固、他的偏执,治好了我的悲观。
有人说:“你的爸爸,又何尝不是十多年之后,才感情变异的呢?”是的,曾经完好的家,也几乎是在一夜间瓦解的。对于单亲家庭出身的人而言,安全感是稀缺资源。身处幸福之中,反而有隐隐的负罪感。我配吗?接下来会进入灾难时段吗?我想掐幸福一把,增加一点儿真实感。如果我特别珍惜它,尽力挽留它,幸福这家伙是不是可以跑得慢一点儿?
爸爸因为生意失败,这几年过得相当落魄。当年一掷千金的他,现在吃一碗十几块的红油抄手都心疼不已。
我也许该恨他,但是在送我上大学时,他的不舍、他的眼泪,是真的;每次打电话,他对我的叮嘱和念叨,是真的;每次见面,他不再笑我胖,让我多吃点儿,说长胖点儿更健康,是真的;我过年回家,生病打吊针,他在旁边担心不已,是真的;他哪怕经济上再窘迫,也不好意思主动跟我说,怕增加我的负担,是真的;我过生日,他打电话,很感慨地说,还记得我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也是真的。
最近他要结婚了。他给我妈妈打电话,深情表白,说在他心里,我是第一位,我妈妈和我外婆是第二位。我不知道现在和他结婚的女人,是和我并列第一,还是和我妈妈、我外婆一起并列第二。爸爸也许不是影帝,只是他的感情总是呈网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