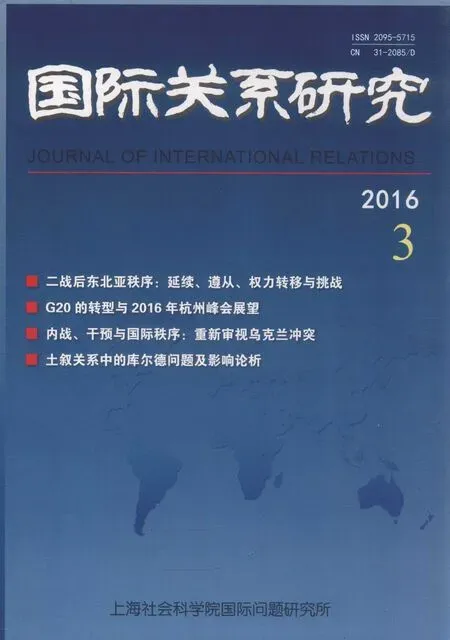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国家的融合模式探究
虞卫东
国际关系
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国家的融合模式探究
虞卫东
[内容摘要]随着进入西欧国家穆斯林人数的增加,穆斯林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社会议题。西欧国家为了促进穆斯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分别推出“同化”、“多元文化”和“客籍工人”等三种融合模式。不过,由于伊斯兰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不小差异,加上穆斯林移民人口迅速增加,导致穆斯林移民无法适应西欧国家的教育和就业体制,陷入社会底层。“9.11”事件之后,尤其在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等国相继发生穆斯林青年制造的袭击刺杀事件,西方社会产生了“伊斯兰恐惧症”。西欧各国政府和社会认为穆斯林移民的融合是失败的。
[关键词]融合穆斯林移民伊斯兰恐惧症
随着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穆斯林移民能否融入当地社会或者能否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欧国家尤其严重,法国的穆斯林人口613万,约占总人口的 9.6%;德国的穆斯林人口403万,约占总人口的 5%;英国的穆斯林人口295万,约占总人口的4.6%;荷兰的穆斯林人口 92万,约占总人口的 5.5%;比利时的穆斯林人口 67万,约占总人口的 6%,比利时的穆斯林人口上升较快,2013年时穆斯林人口才38万。2004年,亨廷顿和福山等美国学者曾质疑欧洲在21世纪是否能在伊斯兰教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他们认为,按现在的形势,“25年内欧洲便可能陷入严重分裂”。*《设法将伊斯兰问题摆入欧洲议程》,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176085.欧洲人必须正视与身边穆斯林移民的异同,开始积极定义自己的特性,积极寻求融合。
一、融合的尝试
西欧各国政府意识到, 如果不能使欧洲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将对欧洲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以及未来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Robert J. Pauly, Islam in Europe: Integration or Marginaliz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p. 87.为了帮助穆斯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西欧各国推出了自己的融合模式。法国对移民施行同化政策,即不承认移民的少数族裔地位,要求其放弃文化和宗教特性,整合进入主流民族,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法国政府要求所有法国居民必须无条件使用法语和法国的习惯规范, 恪守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该政策脱胎于大革命时期法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过程中所确立的 “共和同化”原则:当时的革命政府因担心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和分裂主义倾向而禁止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世俗化和强制推广“国语”——法语等文化建构手段来推行一元文化,以达到弱化地方和族群的认同、培养共和国归属与认同的目的。法国禁止在学校内戴面纱(为穆斯林女子所佩戴),同时禁止佩戴大号十字架和亚莫克便帽(为犹太男子所佩戴)。
英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受到二战后左翼思潮的兴起和对从前殖民统治良心上的歉疚影响。*洪霞:《当代英国的穆斯林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5页。英国在不同文化的殖民地进行控制时,它更关注的是公共秩序的稳定,而非让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受宗主国的文化。*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以法国为例》,http://www.doc88.com/p-3337920084300.html。左翼政党甚至对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存在与传播持宽容乃至欢迎态度。他们认为,外来文化丰富了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不仅不应限制,反而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实现在欧洲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理想。*《欧洲穆斯林现状与“反穆斯林”浪潮》,http://news.ifeng.com/a/20150107/42881272_0.shtml.1997年,英国工党正式推行系统的多元文化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简化了难民管理程序,缩短了审批周期。移民来到英国之后,可以不用讲英语,也可以完全按原有的方式生活。学校的宗教教育设立了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等多种宗教;穆斯林女生可配戴不与校服颜色相冲突的头巾;英国部队的穆斯林现役军人可保留短胡须等等。2000年英国通过《种族关系修正法案》,2003年通过了《就业平等法案》,2006年通过了《平等法案》,*Randall Hansen,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in Post-war Britain: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a Multicultural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5.很多在西方国家也是首例。
德国采取的客籍工人政策(1955~1973年)是迫于当时“经济奇迹”导致工人短缺的情况。因此,德国把穆斯林移民当成一种暂时现象,认为他们迟早都会离开,不愿意给予其公民资格。德国的客籍工人体系建立在“轮换”原则基础上,定期遣返一批工人回国。当土耳其人开始在德国定居时,德国官方并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准备,只是把这看成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没有任何同土耳其人打交道的想法。从五六十年代的客籍劳工移民开始,德国一直否认移民社会的现实。当时,联邦德国没有一部移民法,直到很晚才就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话题展开讨论并采取应对措施。*Rita C-K Chin,The Guest Worker Question in Postwar German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16.

三种融合模式之比较*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以法国为例》,http://www.doc88.com/p-3337920084300.html。
二、融合的瓶颈
西欧国家本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或者迫于经济压力,尝试引导穆斯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和所在国。但是,穆斯林移民要真正融入西欧社会面临很大挑战,存在一些瓶颈问题:
1.文明冲突问题
从伊斯兰教与欧洲主流基督教的固有差异来看,两者很难调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说:“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他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他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他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版,第231页。穆斯林移民带来了伊斯兰教,在欧洲国家和社会空间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世俗社会发生了碰撞,相互抱有歧视,加以排斥。西方社会害怕穆斯林把宗教带入日常生活,偏好于与自己相通的文化群体。然而,“穆斯林身份”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宗教信仰,*黄昕瑞:《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欧洲探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第44页。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在认知上与伊斯兰教存在对“他者”的抵触和防备。西欧国家都是世俗化国家,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禁止宗教介入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而穆斯林坚守宗教的神圣地位,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大约有75%的穆斯林声称自己按照宗教规定在清真寺里做礼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穆斯林对欧洲所在国的认同十分有限,大多认同自己先人的穆斯林故国,这种状况招致欧洲国家的不满,*尹斌:《欧洲的穆斯林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第64页。而针对欧洲穆斯林公民的调查显示,一定比例的穆斯林人口有敌视西方文明的倾向。比如在英国,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认为西方人是“自私、傲慢、贪婪和不道德的”,一半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认为西方人是“暴力的”。这两种现象互相强化,加剧了欧洲内部“西方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包刚升:《极端主义的兴起与西方世界的挑战》,http://news.ifeng.com/a/20160601/48891645_0.shtml。
不过,“9·11”事件之前欧洲穆斯林与当地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稳的。如对于宗教问题,多数居住在意大利的穆斯林都认为自己享有信仰自由,他们对意大利政府对于伊斯兰教的包容感到满意。尽管如此,罗马约翰·卡伯特大学教授帕沃切洛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伊斯兰教以及穆斯林的包容,但他们做到的仅仅是对于不同宗教或文化采取一定限度的‘容忍’,距离真正的‘尊重’还差得很远。”*尹斌:《“9.11” 事件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穆斯林问题》,《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第26页。结构性的同化无法改变“穆斯林身份”的刚性认同,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社会的难度很大。
2.人口结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移民,欧洲穆斯林人数增长了3倍。合法的穆斯林移民仍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进入欧洲,非法穆斯林移民每年大概也有50万人左右,预计到2020年时穆斯林将占欧洲总人口的10%。穆斯林移民留给欧洲人的印象是:移民总人数之大、涌入速度之快和当地居民对经济的不安全感。在布鲁塞尔出现频率最高的七个男婴名字分别是:穆罕默德、阿达姆、拉扬、阿尤布、迈赫迪、阿米内和哈姆扎。马赛和鹿特丹的穆斯林人口比例都已超过25%。正如荷兰一社会学家所言,从来还没有这样多的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在这些世俗国家里永久定居,这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不仅使欧洲的主流社会感受到压力,而且让欧洲穆斯林重新权衡自身的地位,以谋求新的影响力。*尹斌:《欧洲穆斯林生存现状》,《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1期,第58页。
到本世纪中叶,整个西欧的穆斯林人口可能将超过非穆斯林人口。在20世纪,奥地利总人口中有90%为天主教徒,但到2050年,奥地利15岁以下人口中伊斯兰教徒将占多数。对增长速度的预测是有争议的,因为出生率很难预估。但是,伊斯兰代表的是有意愿和年轻,欧洲则是老龄化和福利。欧洲由于人口减少无法维持福利社会,只能引进移民,而进来的移民大多是穆斯林,冲突不可避免。*《美国悲伤的孤独:欧洲的穆斯林化和西方的衰落》,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1116130519_all.html。有迹象表明,第二代及第三代穆斯林移民比他们的父母更难融入社会。英国一家智库发表的报告表明,55岁以上的穆斯林移民人口中有超过70%的人认为自己和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是在16岁至24岁的穆斯林移民人口中只有62%的人这样认为。人口变化引起了不安。欧洲人经常在民意测验中声称,他们国家的移民已经够多了,但政治家却大都回避讨论这个问题。随着穆斯林移民数量的上升,加上他们的生育率高于欧洲本土人,欧洲面临穆斯林化的可能。
3. 教育体制以及就业问题
法国公立学校禁止进行任何与宗教有关的教育,大多数年轻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在家中或祈祷室、清真寺等地方完成。在法国,相当一批伊玛目来自开罗或突尼斯的神学院,据统计,他们之中只有三分之一会法语,另外三分之一法语能力很差,还有三分之一根本不会法语。*Jytte Klausen,“Counterterris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slam in Europe,” Watch on the West, Volume 7, No. 7,July 2006,http://www.fgri.org/ww/0701.200607.klausen.integrationislameurope.html.今天法国的教育系统并不能保证机会平等。客观地说,这个问题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法国的等级分层教学模式增加了不平等性。学生很少能参与讨论,也就使得准备不足的学生(通常是少数民族学生)无法及时消化所学的东西。在穆斯林移民的后代中,没有学位的人数比例远大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Claire L Adida,David D Latin,Marie-Anne Valfort,Why Muslim Integration Fails in Christian-Heritage Societ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67.另外,欧洲穆斯林移民子女迫于家庭和穆斯林社区的要求,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清真寺学习《古兰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课程;他们在学校经常受到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压力,难以像其他民族的孩子一样正常地进行学习,并最终导致学习成绩低下, 甚至无法完成学业。*Ake Sander, Goran Larsson and Dora Kos-Dienes, “State Policies towards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GrantAgreementVS/2000/0671of31/12/2000ArchivesNo:000907 (AddendumrefNo:VS/2001/0137.如在英国,穆斯林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低于其他民族孩子的平均水平。在德国,穆斯林70%仅有中学或中学以下的学历,受高等教育的穆斯林平均比例为19%,取得高等学历的仅有5%。无数生于德国的土耳其或阿拉伯裔中小学生,尤其是女学生,以伊斯兰教规为由不上体育课,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出参观旅行活动,不上性教育课。然而,拥有学位是成功求职的关键。那些没有学位的人,失业率比那些具有硕士学位的高约3倍,比拥有商业或工程学位的毕业生高10倍。在英国,巴基斯坦裔青年(16~24岁)的失业率高达36%,而孟加拉裔的失业率高达25%。
无论是歧视下的封闭还是封闭下的歧视都会造成恶性循环,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收入低的穆斯林一直生活在贫困中。收入高、需要掌握技能的熟练工人往往是本地人,穆斯林移民只能从事最艰苦、工资最低的工作。移民聚居区是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方,类似“隔都”。从居住的状况看,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做支撑,欧洲穆斯林的居住条件普遍比较恶劣,其居所嘈杂、拥挤不堪,而这些居所通常还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穆斯林移民聚居地塞纳-圣丹尼省每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8355欧元,而与其相邻的中产阶级聚居地的上塞纳省为31500欧元。经济落后、失业率高导致年轻人无所事事,引起社会不稳定,容易滋生暴力事件。
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正是由于欧洲穆斯林在经济上的贫困,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影响力受到极大的影响。如在英国下院659名代表中只有2名穆斯林移民代表,上院也仅有4名穆斯林血统的代表,英国180万穆斯林只有1名欧洲议会代表。由于所在国家选举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德国的穆斯林移民代表更少。*Jorgen S. Nielsen,Musli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p. 41.在法国国民议会577个议席中, 没有一名穆斯林的代表,导致穆斯林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中缺少发言权。
在西欧国家,穆斯林移民已经形成一个不小的群体,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一个固化的穆斯林社会对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三、融合的失败
“9·11”事件后,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波兰等国的调查表明,55%的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要对“9·11”事件负部分责任,与伊斯兰教无关。他们还认为,穆斯林对欧洲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移民的纳税数额要多于他们所享受的公共开支。*李维健:《欧洲穆斯林:历史与现状》,《世界知识》2003年第5期,第13页。但是,随着欧洲国家相继发生穆斯林移民暴力袭击事件,加上穆斯林移民人数的不断上升,欧洲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2004年8月,以批评伊斯兰教对妇女态度著称的的荷兰导演特奥·梵高遇刺事件引发荷兰乃至全欧排外情绪上升,鹿特丹、乌特勒支、布雷达等地发生了清真寺纵火的行为。在英国2005年伦敦爆炸案后,穆斯林协会的哈里德·索菲声称“整个穆斯林社区都已成为警察的目标”,“95%~98% 被搜身的人是穆斯林”。近10年英国穆斯林移民囚犯数量增加一倍,英国监狱里的囚犯14%是穆斯林,每7个在英国的穆斯林中就有一人因暴力和吸毒被拘捕。2013年,法国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1189名受访者中73%的人对伊斯兰持否定态度,他们突出的印象是“原教旨主义”、“偏执”、“狂热”和“恐怖主义”以及“攻击”等,几乎没有正面印象。
由于一些媒体在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上进行夸大报道,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当地穆斯林群体的猜疑,加之一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渗透和煽风点火,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特别是当地的排外事件时有发生,这使原有的隔阂进一步加剧, “伊斯兰恐惧症”开始在欧洲蔓延。德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怀疑和恐惧情绪明显增加。一名在柏林洪堡大学做研究的巴基斯坦籍学者也表示,自己接受了德国大学的教育,已获得德国国籍,但还是很难真正融入德国,他甚至考虑离开德国。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德国非穆斯林公民中有57%视伊斯兰教为一种威胁,这种恐惧情绪要大于从前。此外,约40%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就像是“本国中的陌生人”,约有25%的受访人甚至认为,应该禁止穆斯林移民到德国。*“对穆斯林的偏见和隐性歧视使欧洲穆斯林难融主流”,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01_16_306507.shtml。
事实上,“伊斯兰恐惧症”主要是由一些穆斯林移民暴力袭击事件引发媒体渲染和当地社会的即时关注而形成的。“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群际威胁,是指在社会群体生活中,某一群体拥有的资源、观念和价值观等特征对另一群体的生存安全、发展与福祉等带来的威胁。群际威胁的存在使个体容易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态度,即群体偏见。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心理机制。群际威胁可分为三大类:现实威胁、文化威胁和认同威胁。*李彬、杨爽、吴奇:《群际威胁及其群体偏见的影响》,《心理学进展》 2015年第5期。在年轻的穆斯林身上,由于初来乍到而引起的怨恨,他们感觉没有得到尊重,便会受到“要是他们不尊重我们,那至少让他们害怕我们”言论的蛊惑。
随着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德国科隆相继发生一系列穆斯林恐怖袭击事件和爆炸案,西欧舆论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伊斯兰移民没有融入西欧社会,而是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平行社会”,缺乏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响应。边缘化越来越突出,第二代、第三代欧洲穆斯林仍旧被贴上外国人、移民、局外人的标签,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胡雨:《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边缘化还是整合》,《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32页。
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不断收紧文化包容政策。2010年3月27日,来自欧洲多国的右翼政党代表在德国开会,目的是为了“保卫欧洲文化”,并公开宣布要加强合作,在全欧洲掀起一场反对穆斯林建造清真寺宣礼塔的运动。2010年12月底,《明镜周刊》对29000人进行调查,有76%的受访者支持德国禁止修建宣礼塔,82%的人声称“觉得感受到宣礼塔的压迫感”。2010年10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演说时称,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彻底失败”。自2010年初以来,德国民众的排外情绪持续高涨。2010年10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希望定居德国的外国人回国。2011年2月,法国、英国、荷兰相继宣布本国多元文化主义失败。2010年1月,意大利立法禁止该国穆斯林女性戴面纱和包裹头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类似的法案都获得了70%左右民众的支持。
如何界定融合模式的成功与否?是不是只要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融合模式就失败了?一些穆斯林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成为掣肘欧洲政府的利器。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后,英国开始对多元文化政策进行调整,提高了移民的门槛。或许就像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自由社会拥有自身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个人的同等权利和尊严。那些不接受这些前提的文化在自由民主社会就不配得到平等的保护。*《英国多元文化政策下的移民融合问题》,http://www.visa800.com/a/ouzhouguojiayimin/haiwaishenghuo/20130606645.html。
在融合问题上,主流社会和移民社会都有各自的立场。伯纳德·刘易斯认为:“欧洲具有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说一句‘你们必须接受它’并非不合情理。欧洲人必须放弃他们的政治正确性,正视事态发展。” 然而,穆斯林想在欧洲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表面上无害的要求——国家应该尊重并适应他们的认同——是更广泛的、同一种伊斯兰的文明,来取代“不信教的”和“堕落的”欧洲的目标的一部分。*Bhikhu Parekh,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54.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长,不但体现在移民的数量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穆斯林的家庭规模方面。“欧拉巴”观念日趋突显。*[美]彼得·伯格、[英]格瑞斯·戴维、[英]埃菲·霍卡斯著,曹义昆译:《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第152页。在欧洲,许多穆斯林觉得宗教习俗应该纳入西方文化范畴。戴面纱更多的是个人选择和自由,不是传统文化的延续。*Cesare Merlini & Olivier Roy,Arab Society in Revolt: The West’s Mediterranean Challenge,Brookl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220.关于同化,德国《世界报》2015年8月23日刊登记者托马斯·基林格尔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前主任、当代史学家瓦尔特拉克尔的访谈录,题为“欧洲将推行绥靖政策”*《美学者说欧洲在对待穆斯林移民问题上将推行“绥靖”政策》,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247904。。瓦尔特拉克尔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移民潮都被以某种方式同化了。请回想100年前的犹太人移民——他们融入东道国文化的愿望是极其强烈的。当然犹太人渴望被同化,但是很多穆斯林并不希望被同化。在德国,根据1985 年所作的调查,只有13%的土耳其人宁愿与德国人分开居住,有33%的土耳其人表达了希望自己的邻居是德国人的想法。而同时对德国人的调查却显示,只有9%的德国人选择住在周围主要是土耳其人的社区里,许多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特点都比较反感。
四、结语
要判断一个社会的外来人口是否融合于主流社会之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考察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强度与频度。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当地移民的居住环境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就目前情况来看,穆斯林移民与当地居民的隔阂在逐渐加深,相互之间的猜疑和排斥也在加大。
“宽容”是一种社会建构,可以运用在某些场合,但在其他场合却遭到禁止。*[美]彼得·伯格、[英]格瑞斯·戴维、[英]埃菲·霍卡斯著,曹义昆译:《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第146页。西方把伊斯兰等同于文化,与穆斯林视之为信仰存在较大分歧。固有的认识框架和认知模式决定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即使尝试双方对话交流,也是土耳其人所称的“聋子的对话”。*Jonathan Lyons,Islam Through Western Eyes: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War on Terror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p.17.同时,西欧社会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局面:穆斯林人口的上升与穆斯林地位的边缘化。如何避免穆斯林移民的社会环境“固化”,或许应该抛开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国家公民的角度去对待穆斯林移民,用处理日常事务的方法去应对穆斯林移民的事情,*S. Lathion,“Fight Islamophobia in Europe? Less Islam and Muslim and More Citizenship!”, Islam and Christian-Relations,2015,p.135.既不强硬地实行同化,也不做多元化的“迁就”,尽可能做到正常化。在一些恐怖袭击事件面前,如何客观对待穆斯林移民,不被这些事件左右和情绪化,最好的办法是习以为常,不把“恐怖分子”与穆斯林移民划等号。或许,最好的融合就是相安无事,不是按部就班地去争取达到各自的标准。
[作者简介]虞卫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