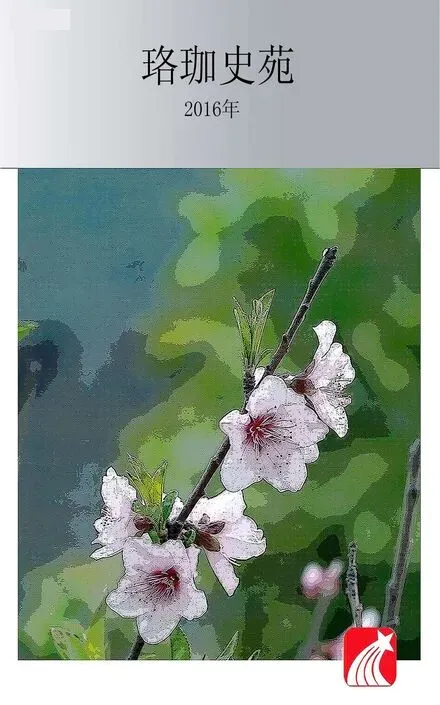獬豸冠小考
韩织阳
獬豸冠小考
韩织阳
本文综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对“獬豸冠”的渊源进行考证,以补法史学界实证之不足。“獬豸冠”随着“法”观念的流变而产生,其原型为楚国圭角状“觟冠”(秦人所谓“南冠”的一种)。西汉时,在汉儒的神话附会下,廌成为协助皋陶断案的独角神兽,法官成为廌在人间的化身。“觟冠”因其形似独角,而被认为是“法冠”渊源,相关神话由此产生。于是“觟冠”变为“解廌冠”“觟廌冠”。为了发挥法律的震慑效果,廌的形象渐渐由仁兽变为猛兽,被“豸”所替代。“觟”“解”“獬豸”的称呼由是而生。
獬豸冠;觟冠;南冠;楚冠;灋
一、引 言
“獬豸冠”在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从东汉时起,它就是御史、廷尉等监察、执法者所戴之冠,①见《后汉书》卷119,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1页。唐宋时法冠皆名“獬豸冠”,御史服之。明清时以獬豸冠为风宪官补服。②见《明史》卷67,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3页;张荣铮等:《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在众多古代文学作品里它更是被借代为执法者。
那么东汉之前的情况如何?獬豸冠是怎样产生发展的呢?有学者认为,至少在战国时期,经过官方的反复宣传和倡导,以獬豸作为正义的化身(执法官员的榜样),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①张亦工:《神兽“獬豸”和“角端”》,《寻根》1998年第2期,第26页。还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楚王好服獬豸冠,秦汉时以獬豸冠为御史官帽,当这些御史们头顶獬豸冠,身着绣着獬豸图案的官服断案时,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獬豸的化身,借獬豸的威力来辨别是非,秉公执法断案。②陈荣:《獬豸冠与羌人图腾崇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116页。这些说法在法史学界影响甚大,然而遗憾的是,它们多是建立在对传世文献不加甄别采信的基础之上,这就难免与事实真相有所偏离。
一顶帽子的来龙去脉本是无足轻重,然而因其与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化身的“獬豸”相联系,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有关它的历史与中国法律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其考证的严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獬豸冠、灋,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被神格化的意象到底是如何发生发展,在此过程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法文化变迁呢?本文运用考古和历史文献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从实证角度来寻求神话背后真实的“獬豸冠”。
二、关于獬豸冠的早期材料
据唐代刘知幾与今人吴树平考证,“舆服志”这种题材最早为东汉蔡邕组织编订《东观汉记》时首创。然而《东观汉记·车服志》亡佚非常严重,好在蔡邕后续之作《独断》中也有关于“舆服”的内容,应是沿袭了《东观汉记》的相关记载。我们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对“法冠”的总结性描述就出自这里:
常被后人引用的《后汉书·舆服志》中相关内容也是延续此处,只是略有出入:
这两则材料均认为法冠又名獬豸冠,等同于南冠、楚冠。区别在于前一则材料指出东汉时御史廷尉监平所戴獬豸冠为两角,而后一则材料去掉了此句,而加入了“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的传说。要想搞清楚獬豸冠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把这些信息一一梳理,再结合起来冀以还原獬豸冠真相。
三、獬豸冠与觟冠
今本《淮南子·主术训》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注:“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后世均沿袭高诱之说,认为“獬豸冠”又名“獬冠”。
然而,《太平御览》卷684引《淮南子》云:“楚庄王好觟冠,楚效之也。”
此处这两个版本差异有二:一是“觟冠”与“獬冠”之异;二是庄王与文王之异。对差异的讨论往往会引导我们接近真相,因而赘述于下:
(一)出处与关系
1.“觟冠”与“獬冠”
“觟”与“獬”古音相同,可通假。目前所见最早的“觟”字出现在战国,凡两处:一处出自《尊古斋古鉥集林》中所录一印,字形为“”,用作人名;另一处见于望山二号楚墓出土遣册,作“二觟()冠,二组缨(简62)。①张政烺:《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7页。
而“獬”在已公布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中不见,《说文》中亦无收录。两汉文献中“獬豸”皆作“解豸”,故可知“獬”乃后起之字,较“觟冠”而言,“獬冠”的写法较晚出现,今本《淮南子》中“獬冠”的写法应是流传过程中直接改用新字的结果。
2.庄王与文王
《墨子·公孟》的一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昔者齐桓公……昔者晋文公……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
此段“鲜冠”中的“鲜”与“觟”字古音相通,可通假,“鲜冠”即“觟冠”。这段记述中与“觟冠”联系在一起的是楚庄王,他和文中提到的齐桓公、晋文公皆位列春秋五霸。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非常大,与儒家并称“显学”,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编写《淮南子》时虽以道家思想为主,但同时也掺杂了各家学说,《墨子》必然是其重要的参考来源。因此,其对于楚王和“觟冠”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此。可知《淮南子》中“好服觟冠”的主人公当为楚庄王。
两处差异均指向《太平御览》所引《淮南子》年代更早。即“觟冠”乃“獬冠”最初写法,而后者的出现当不早于东汉。
(二)“觟冠”之考古学线索
“觟冠”是一种怎样的冠式呢?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两件器物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第一件是用于记录随葬器物的遣册,上书有“一桂(冠)、组缨”(简259)。整理者指出:“桂疑读作獬”,②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桂”上古音为见母支部,“獬”为匣母支部,二者音同。“桂”当是“觟”的假借字,“桂冠”即“觟冠”。也就是说,这座墓的随葬品中就有“觟冠”,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随葬的冠已泯灭不见。
不过,彭浩、黄凤春、刘玉堂等学者从同墓出土的另一件漆奁上找到线索,他们认为,这件漆奁上所绘人物戴的就有獬冠(见图1中①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黄凤春、黄婧:《楚器名物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③、⑥、⑦、⑧、⑨)。①

图1 ②彭浩先生认为图中④、⑤、⑥、⑦、⑧、⑨为獬豸冠,然此线描图所绘并不准确,仔细辨认原画,该图中②、③、⑥、⑦、⑧、⑨实为同种冠式,而④、⑤并不相同,且其实际并非獬豸冠。
黄凤春先生根据包山二号楚墓的墓主为主管楚国的司法的左尹邵,进一步认为遣册中的“桂(冠)”应是墓主的生前服着之物,说明楚国的獬冠与法律有关并为楚国独有。①黄凤春、黄婧:《楚器名物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然而黄说有一处难以解释的地方:另一处女性墓葬——望山二号楚墓出土遣册亦载有“二觟冠,二组缨”(62简)。②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据前荆州博物馆馆长彭浩先生告知,男性衣冠用于女性陪葬,尚未见过,也就是说此种冠式女性亦可佩戴。史籍未见楚国女性为官的记载,女性彼时并无担任司法官的可能性。故认为此“觟(獬)冠”与法律有关似乎有些牵强。

图2
况且漆画(见图2)中着服所谓“獬豸冠”的人数量众多,为御者、随从,虽然这些人身份最起码也是低级贵族,但是漆画所描绘的是王孙迎亲的场面,而非“法官聚会”,也证明了漆画上的冠与司法无关。即漆画中的冠并不一定是觟冠,觟冠与司法的关系在这里也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三)文字学角度看“觟冠”
学者们对漆画上冠式的猜测固然有启发性,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无法成为定论,我们不妨换一个方向,从文字上进行分析。《说文》:“觟,牝牂羊生角者也。”马叙伦先生认为许说有误,“如此训则觟为羊名矣,羊名安得从角?”①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第4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12页。
《说文》中从“角”的字,其字形另一部分不仅表音,也有许多兼具表意功能,如“解”,右面为以刀解牛;“廌”的另外两个异体字“”“”,指长角的“豸”与“虎”。“觟”也不例外,其右部“圭”兼具表意功能。《说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楚爵有执圭。”周南全先生指出,考古发掘器中,圭的共同特点是体扁平,断面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上端尖锐或弧圆。②战国时代“觟”字字义因文例匮乏,无法据文意来判断。但据构字规律推测,“觟”字本义应指尖角形的圭,或圭的尖角。许说代表的只是东汉人对文字的认识。
《说文》:“楚爵有执圭。”高诱注《淮南》曰:“楚爵功臣赐以圭。谓之执圭。比附庸之君。”《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中记载:“闻楚之法令,得伍胃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据顾久幸先生考证,执圭是楚国较高等级的爵位,在它之上,仅有列侯一个级别,其下有执帛、五大夫等爵位。③参见顾久幸:《“执圭”杂考——兼论楚国爵制》,《江汉论坛》1992年第5期。《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了秦楚间的一场战役:“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一次战役中,楚国死去的列侯执圭就有七十余人,可见获此爵位人数之多。这从段玉裁对“圭”所作注中也可见端倪:“若《国策》之景翠,庄辛。《淮南》之荆佽非,子发。《说苑》之鄂君子晳。《吕览》之能得五员者。皆楚执圭者也。”
“觟冠”是否可能最初是执圭者所服,然后渐渐风靡楚国呢?这还有待更多证据来佐证。不过楚人对于圭的尊崇和喜爱有可能反映到对冠式的设计上,尖圭形的“觟冠”可能正源出于此。
四、楚冠、南冠与獬冠
与杂糅各家学说的哲学著作《淮南子》相比,《左传》所载的内容更为忠于史实。其中一处关于楚人冠饰的记载引起后人注意:《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
此处所提到楚泠人所戴的南冠,到东汉时一般人已不知所指何物,因而东汉经学大师胡广对其作出了解释,这些解释被收录在一些史籍中:《晋书》载:“南冠即楚冠。秦灭楚,以其冠服赐执法臣也。”后人多据此把南冠、楚冠等同于獬豸冠。然而《后汉书·舆服下》同处引用胡广言的表述却略有不同:“《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此处《晋书》与《后汉书》的差异有二:其一,《晋书》中“南冠即楚冠”的表述是把这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而《后汉书》中“楚冠”仅仅是用来解释《左传》中的“南冠”,意为“南冠是一种楚冠”;其二,《晋书》中“以其冠服赐执法臣也”意为把泠人的冠服赐予执法近臣;而《后汉书》中多一“君”字,“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意为把泠人国君的冠服赐予执法近臣御史。
从常识上讲,高贵的国君和身份低微的泠人装束必然不同。秦把楚国君王的服饰赐予臣子,可达到羞辱丧国之君,彰显自己功业的效果,而把楚国地位卑贱的泠人的冠式赐予臣子则并不合情理。
从《后汉书》与《晋书》成书时间和史料来源来看,前者不但时间更近古,而且史料来源也更为可靠。范晔所著《后汉书》有纪、传二体而无志,南朝梁刘昭为该书作注时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把晋人司马彪所著《续汉书》中的志文补入范晔之书一并作注。即《后汉书·舆服志》出自司马彪之手。其史料来源包括曹魏董巴的《大汉舆服志》、东汉蔡邕的《独断》、东汉董珍等人所著《东观汉记》等前代史志。①杨艳芳:《〈后汉书·舆服志〉探析》,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页。《独断》中对法冠的记载和《后汉书·舆服志》类似,亦是“以其君冠赐御史”。蔡邕与胡广是同时代人,同朝为官,其所录当可靠。而《晋书》成书于唐代,年代晚矣。
有人据《淮南子·主术训》:“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而断章取义地认为獬冠是楚国的风尚,楚人不分贵贱都可佩戴。且不说这则经史不见的材料可信度有多大,即便是史实,通看全句“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可知,若是匹夫布衣来冠獬冠,则是会被人耻笑的怪异举动。故假若《淮南子》中记述真实,效仿楚王的也当是地位较尊贵之人。从包山漆画上也可以看到,楚国的冠式多样,因佩戴者地位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中原国家看来,这些冠饰都应归为“南冠”。无论南冠、楚冠都是总称,而非具体某一种冠式,不可把它们和獬冠完全等同起来。
五、从“觟冠”到“獬豸冠”
从上述出土与传世文献中可知,“觟冠”为战国时楚冠,这种称谓后来演变为“獬冠”,并最终被“獬豸冠”所取代。那么,这种变化发生的时代和动因又是什么呢?
战国时代,列国竞相变法,古老的“灋”字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战国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概念之一。那个时代人们观念中的“法”可以从《尔雅》中体现出来:“法,常也”,“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法被认为是一种规范、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法并未被赋予神话色彩。
随着秦国的统一,法的重要性被提到了治国纲领的高度。汉承秦制,在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就照搬了秦律,并沿袭了秦对法的重视,法的观念深入人心。西汉《二年律令》和睡虎地秦律有着明显的顺承关系,西汉奏谳书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上所记载的秦代案例在程序法上也非常相似。这时的法仍是工具主义的,并未附加任何玄虚内涵。
转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当是时,董仲舒在“大一统”政治需求的驱动下,对儒学进行神学化的改造。他杂糅阴阳五行学说,吸收原始宗教迷信和方术,发展出天人感应学说。他提出“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统治者所谓的“教”实际是通过糅合了宗教迷信和方术的儒学,使人民萌生敬畏之心,从而自发地维护统治和秩序。
在这种氛围下,灋字中兽形的“廌”被汉儒进行了神话附会,成为协助皋陶治狱的神羊,意在警示世人:灋乃天道,世间作恶之人逃脱不了天道的处罚。这种对法的认识已经和战国时代有所不同——法不再仅仅是规范,而更是一种上天的惩戒。
灋字中兽形的“廌”被汉儒神话附会为协助皋陶治狱的神羊,成为正义裁判的象征。这只是整个理论系统的一小部分,完成了“灋”的神格化,还有另一个问题势必要解决,即找到“廌”在现实生活中的对应,来实现对统治的助力。这就是“执法官员”——“廌”在人间的化身。他们所戴的帽子因此被命名为“解廌冠”。①而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在此之前并无法官戴此帽的传统。先秦两汉同音字混用现象很普遍,解廌、獬豸、觟廌、觟、解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从字形上看,廌()明显不是一种猛兽,为了起到威慑效果,同音的“豸”()慢慢取代了“廌”。出于相同原因,“解”“觟”逐渐被带犬字旁,表示兽的“獬”取代并固定下来。这样,“解廌冠”变为“獬豸冠”。
如此,一个关于“灋”的完整的天人感应体系形成了:
天(正义)—神异(皋陶之神羊)—人(法官),“灋”字的字源也被完美地融入这个体系,体现出当时人们心中“灋”的理念。许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写下了对灋字的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汉儒把“法冠”冠以獬豸之名,就要向上追溯(或者说编造)其渊源,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不同意见的出现:蔡邕《独断》云:“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后惠文冠,高五寸,以裹铁柱卷。”然而应劭认为齐王的高山冠是东汉法冠的前身:“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①《晋书》卷25,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62页。《晋书》:“高山冠,一名侧柱,高九寸,铁为卷梁,制似通天。顶直竖,不斜却,无山述展筒。”蔡邕和应劭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描述的“法冠”雏形都差不多,上端有凸起,形似高山或兽角,应皆是出于对“廌”的附会,最后为何“楚冠说”占据了上风呢?上文讲到,楚的独角冠叫“觟冠”,“觟”本义为圭角形,可作形容词,与“廌”连用,可突出“廌”为独角兽的特点。比起“高山冠”来,更与“灋”字中独角的神兽“廌”相合,于是这种说法渐渐占据上风,“觟冠”便被拿来作法冠的渊源。
六、结 语
顾颉刚先生曾提出震撼中国古史学界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要内容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一命题对研究“獬豸冠”乃至先秦法制史仍有重要启发意义。
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獬豸冠的概念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见图3)。
《春秋左氏传》中,载有楚国泠人戴南冠,然而此处并未描述南冠具体为何种冠式。战国时期《墨子》记载楚庄王曾戴过一种叫“觟冠”的冠式。这两处记载主人公均为楚人,并提到了他们的帽子。然而国君和泠人,南冠与觟冠差别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图3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在汉儒的神话附会下,廌成了协助皋陶断案的独角神兽,并以法官作为其在人间的化身。法官的冠饰作为一种象征也需要和“廌”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到历史中找寻合理性解释的动因。“觟冠”因其形似独角,而被认为是“法冠”渊源。与之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编纂《淮南子》时,也难以避免受到其思想的影响,于是出现了“楚王好服觟冠,楚效之”的记载。这条经史不见的记载很可能是糅合前述《左传》和《墨子》相关内容的结果,这种看法很可能就是当时儒者所为。
到了东汉,獬豸冠的来历变为楚王尝获能别曲直的獬豸神羊,而以之为冠。神话色彩更为浓烈。《后汉书》《晋书》中对“法冠”的记载均源于此。“觟冠”变为“解廌冠”“觟廌冠”。为了起到法律的震慑效果,廌的形象渐渐由仁兽变为猛兽,“觟”“解”“獬豸”的称呼由是而生。
从最初与“廌”并无关系的觟冠,变为依“獬豸神羊”为原型而成的冠,“獬豸”的形象从无到有,从最初仁兽演变为后来的猛兽,从最初与楚庄王相联系,到后来溯源至皋陶时代,这一变化生动地阐释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獬豸冠”的诞生与变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